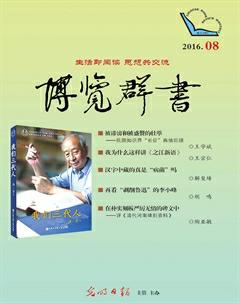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
刘强
最近这十年,我和《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之,学之,讲之,注之,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曲径通幽,乐此不疲。
这份缘,似乎来得有点迟。但,毕竟还是来了。我深知,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拥有这份缘。特别是经受过近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强势侵袭,领略过欧风美雨无孔不入的浸润洗礼,扮演过或主动,或被动的各种新锐角色之后,完全乱了方寸、失了方向、画不成方圆的现代人,已经在思维方式、话语形式、学术范式、处世模式诸方面,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基因突变”,自以为“是”且自以为“新”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向故纸堆里的经典示好,向被扫地出门的传统示弱,向充满道德教训的《论语》示爱,向被泼了一百多年污水的孔夫子示敬呢?
这个弯儿,对于言必称革命、行必道先锋、理必称平等、学必标自由的左右两派“新青年”们,尤其难拐!
不过,于我而言,这似乎不是“拐弯儿”,而是一次命中注定且又自然而然的“回正”。回到源头活水,回到祖宗家法,回到母语和故园,回到仁本和中道!
因为说到底,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不过程度、深浅、自觉与不自觉、认可与不认可,情况各不相同而已。那些经常批判儒家的人,事实上也是潜在的儒家,因为自古以来,儒家士大夫就是最敢对强权和无道说“不”的人!
为此,我不得不感恩造化,感恩生命,感恩经典,感恩圣贤。冥冥之中,或许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为我这样一个资质驽钝却又不甘平庸的问津者,指引一条路,打开一扇门,点亮一盏灯!
我想,不该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个缘。孔夫子,早就坐在那20篇泛黄的竹简里、500章鲜活的章句里、16000多个蹦跳的汉字里,虚席以待,翘首以盼!——斯文在兹,吾道不孤,百世以俟,来者不拒!
他等来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等来了子思、孟子和荀子,等来了毛亨、孔安国和董仲舒,等来了司马迁、扬雄和班固,等来了马融、包咸和郑玄,等来了王肃、何晏和王弼,等来了刘勰、皇侃和王通,等来了杜甫、韩愈和柳宗元,等来了周濂溪、张横渠和邵雍,等来了欧阳修、范仲淹和胡瑗,等来了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等来了吴澄、王阳明和刘宗周,等来了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等来了颜习斋、戴震和阮元,等来了刘逢禄、曾国藩和张之洞,等来了廖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来了熊十力、马一浮和梁漱溟,等来了王国维、陈寅恪和钱宾四,等来了徐复观、唐君毅和牟宗三……
我知道,孔夫子还在等,并且还会等下去。等你。等他。等我。等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等前赴后继的炎黄子孙!
夫子的耐心足够好!不管你怎么看他,他都那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威而不猛,气定神闲!他把自己坐成了一道云卷云舒的风景,坐成了一座仰之弥高的山,坐成了一汪浩瀚无垠的海,坐成了一场可以说走就走且没有终点的生命漫游和精神旅行!
夫子其人,大概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记载最丰富、细节最生动、面目最清晰、气象最宜人的伟大圣哲,也是华夏文明之学统和道统的重要奠基者,他不惟是“千古一圣”的不二之选,更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恩人!
《论语》其书,几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私家著述,其取法之高、化人之深、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绝非一般经典之可比,即便称其为“中国人的圣经”,亦毫不为过。窃以为,凡有血气、通文墨、思进取、求良知、明善道的中国人,皆应在有生之年阅读此一“圣经”,而且,起始年龄越早越好,阅读次数多多益善!
其实,只要是读书人,都应该寻找这个缘,把握这个缘,扩充这个缘。我素所敬仰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诚哉是言也!
我因读《论语》而受益,久而久之,不免技痒心动,必欲加入“劝人读《论语》”的行列而后快。本书之撰写,盖缘于此。
作为“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的一部,本书计划甚早,而动笔甚晚。最早的想法,是延续《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和《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的路子写下去,甚至书名都想好了——《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今读》。然而,当我终于完成现在这部《论语新识》之时,却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当时没有率尔操觚,信马由缰,否则岂不唐突圣贤、误人子弟?盖《论语》非一般文学经典,稍有“玩赏”甚至“赏析”之心,便有可能乱其肌理、泄其元阳、散其真气!故此书写作暂且搁置起来,而且一放就是七年!
这七年,我在等待,在沉潜,同时也经历了学术及思想上的一次“蜕变”。简言之,即由西而中,由文而玄,由玄而佛,由佛而儒!十年弹指一挥:弥望中,“山重水复疑无路”;猛回头,“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所以转换如此迅速而自然,盖因西学、文学、玄学、佛学四端,哪一样我都未曾精研深究,哪一样都谈不上根深立定,惟其如此,反而易于辗转跳脱,另辟蹊径。当我囫囵吞枣地读过可以读到的大量儒书之后,终于发现,原来“风景这边独好”,大有柳暗花明、相见恨晚之感!
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说:“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又说:“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徐先生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写于1966年的这段话之所以毫无那个狂躁年代的语言印记和思想症候,除了因为彼时其人侨居印度,未受世俗之侵蚀,还因为其学殖深厚,精通多种语言,会通中、西、印三种文化,视野开阔,信道诚笃,故能超越一时一地之“我执”,登高望远,吐纳古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其对儒学和孔子的精微体贴和无上尊崇,犹如一面质地优良而一度封尘的铜镜,甫一出匣,便光芒四射!
近读吴学昭所写《吴宓与陈寅恪》一书,陈寅恪先生下面一段自白,又让我眼前一亮:
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
至此,我终于了悟:为何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先生,竟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这是那种“为此一文化所化”之“文化托命者”才会产生的一种民族身份识别、文明本位认同和文化价值信仰。在西学东渐、新旧磨荡、咸与维新和革命之年代,唯此一种“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之文化信仰,方能使人格挺立,风骨刚健,慧命延展,理想不磨,斯文不灭!
儒学,并非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学问。陆放翁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亦云:“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
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素为我所深喜,真可谓践行为己之学、反求诸己的方便法门。所以,这本小书只能算是我这些年“求放心”的一张答卷,尽管私心颇不满意,但还是愿意以此表明心迹,确定坐标。——下一站,我已知道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