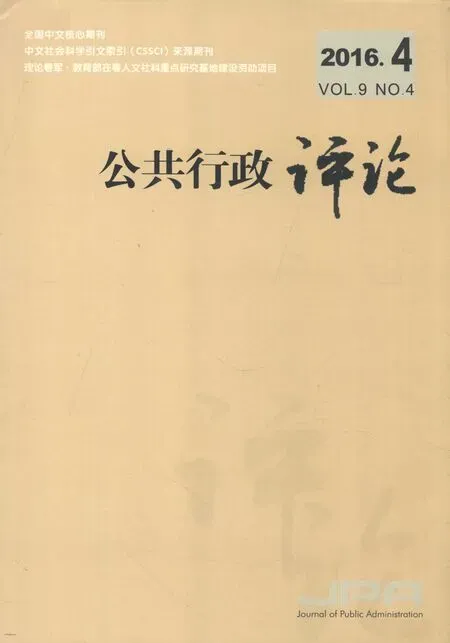政策的肌肤: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
臧其胜
理论述评
政策的肌肤: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
臧其胜*
态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策设计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政府的责任,是福利态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内地学界的相关讨论较少。论文基于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回顾并重新界定了概念,勾勒出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发现:福利态度的分析维度具有多重性与动态性,福利态度差异可以采用福利体制与福利文化的双重解释路径,据此提出了研究的本土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与专业的参照坐标,也为学术对话提供了知识基础。
福利态度福利体制福利文化社会政策社会福利
一、引言
态度是政策的肌肤、社会的晴雨表。政策的冷暖、社会的晴雨可以通过公众的态度知晓。在任何情况下,公众对福利政策的认同范围构成政治与社会科学关于福利国家争论的重要主题。一项社会政策若要成功,社会认同达到合理的程度是其基本要求。缺乏认同则意味着合法性的危机,而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正是福利态度研究的首要动机(Gelissen,2002;Sihvo & Uusitalo,1995a)。
福利态度是合法性的核心(Svallfors,2012a),福利国家政策的设计与范围形塑与决定它们自身的合法性(Edlund,1999)。因此,在社会政策的设计上,积极回应公众对自身的生活品质问题的关切与期望,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的合法性才能得以持续维持与增进(江治强,2013)。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所言,在制定政策时,要把人们的预期、信念和看法都包含在内(田晓玲,2011)。否则,类似于“延迟退休”方案所受到的质疑仍会不绝于耳。
公众的福利态度是影响一个国家福利制度或体制的重要因素。然而,不仅态度影响政策,政策也影响态度(Hedegaard,2014)。问题是:态度应当何时追随政策,政策应当何时追随态度?如何实现“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向“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再向政策议程的转变?这都需要我们在福利治理进程中正确处理好福利态度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而欧美与港台等地学者关于福利态度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启发与借鉴。
福利态度的研究兴起于欧美,以彼特·泰勒-古比(Peter Taylor-Gooby)、斯蒂芬·斯沃福斯(Stefan Svallfors)与维姆·凡·于肖特(Wim van Oorschot)等为代表,始于1930年代的美国(Erskine,1975),1980年代开始从国别研究转向跨国比较研究,以1980年理查德·M.考夫林(Richard M.Coughlin)出版的《意识形态、公共舆论、福利政策:工业化国家中关于税收与支出的态度》一书为起点(Jger,2009),1990年代以来显著增长。研究围绕的核心是政府的责任(The Role of Government)或政府的边界*政府的边界(The Scope of Government)是指政府活动的范围与政府参与那些影响公众日常生活活动的程度。范围/广度(Range)是指政府活动的全部范围(Gamut),例如在服务与纳税人上的支出,对他们行为的管制,提供保障,改善环境,有时候什么事情也不做;程度/深度(Degree)是指政府追求一个特定活动的强度,例如健康照顾,不仅关心治疗疾病的健康照顾的形式,还采取健康促进项目,包括控制水质与食品添加剂等(Borre & Goldsmith,1995)。从研究内容来看,其实是在讨论政府福利责任的边界,包括介入的广度与深度,而测量则是借助公众的福利态度。(The Scope of Government),关注社会福利领域内的“政府所及”(Reach of State)与“政府所能”(State Capacity),通过考察公众对福利国家或社会政策的支持度,试图重新确立福利国家合法性的边界。而政府责任也正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和转型发展的核心议题(彭华民,2012)。
关于福利态度的研究,港台学者已有较多探讨,以王卓祺(Chack Kie Wong)、王家英(Timothy Ka-Ying Wong)、古允文(Yeun-wen Ku)等为代表,在1990年代末成为研究的主题。内地也已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毕天云、张军等在福利文化的研究中涉及到福利态度概念的辨析(毕天云,2004a;张军,2009),万国威等通过经验研究考察了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万国威,2014,2015;万国威、金玲,2015;张军、陈亚东,2014),黄叶青等(2014)依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ISSP)数据分析政府福利责任的边界,而臧其胜(2015a,2015b)则依据国内数据探讨了政府福利责任的边界。此外,少量探讨公众对福利的认知、满意度和福利意识的研究也可归为该类(陈劲松,2011;赖伟良,2004;张朝雄,2007;彭国胜,2012)。
总体而言,内地学界对与福利态度主题相关的讨论较少。鉴于研究的现状,本文主要基于英文文献回顾福利态度研究的文本脉络,关注其国际前沿,尽可能呈现文本叙事的内在逻辑,力图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完整与专业的参照坐标,为学术对话提供知识基础。限于篇幅,研究主要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福利态度的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包括哪几个分析维度?第二,福利态度生成的解释路径有哪些?第三,福利态度国际研究的总体态势是什么?对中国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本土意义?
二、福利态度:概念与分析维度
(一)概念界定
在英语文献中,福利态度有如下表述:福利态度(Welfare Attitudes/Attitudes to Welfare)、福利国家态度(Welfare State Attitudes/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福利国家意见(Welfare State Opinion)、对福利国家政策或项目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 Policies,Attitudes to Social Policy, or 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Program)、对福利国家的认同(Public Consent to the Welfare State)、社会福利态度(Social Welfare Attitudes)等*福利态度研究中除以人为对象,还有以动物为对象的,本研究只关心前者。。尽管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等不能划等号,但在日常研究中,两者涉及的对象相当一致,都是指国家或社会所采取的降低风险、减少不平等和提供生活保障项目的社会项目(Amenta,2003[转引自刘军强,2010])。因而,上述表达在中文语境下可以统一使用福利态度这一术语。
福利态度的研究必须基于清晰的术语定义(Cnaan,1989)。王家英等人认为福利态度是指人们如何看待政府在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供给上的政策(Wong et al.,2008),其定义指出了政府为实现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而介入的方式,但仅将对象限定在方式而未能扩展到目标、过程及结果等,是一种静态描述。乔金·库林(Joakim Kulin)在回顾相关定义的基础上将态度定义为一个人评价一个特定的对象(如一种行为、一个人、一种制度或事件)是好还是不好的倾向(Kulin,2011),这一定义忽视了态度的行为倾向,无法将福利态度与福利制度、福利文化和福利运动的演进联结起来。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特鲁德·桑德伯格(Trude Sundberg)引入了斯图尔特·奥斯卡姆(Stuart Oskamp)的定义,认为态度是就特定的态度对象而言以给予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作出回应的一种倾向(Oskamp & Schultz, 2005;Sundberg,2014),能够较好地避免前述定义的缺陷,不足之处是未关注作为态度对象的“福利”的维度。从性质来看,社会福利是指一种幸福和正常的状态,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制度(尚晓援,2001)。制度则是多维的、动态的,其行动主体是多元的,是福利态度研究的重点。结合已有研究,福利态度可以界定为行动者对幸福状态与社会福利制度以给予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作出回应的一种倾向。
(二)分析维度
福利态度的维度的构建是研究的重点,它是概念得以操作化的保证,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围绕态度的对象及其本身的维度,专家学者们提供了有益的探讨。
1.欧美学者的研究
以1980年理查德·M.考夫林(Richard M.Coughlin)出版的《意识形态、公共舆论、福利政策:工业化国家中关于税收与支出的态度》一书为起点,福利态度的研究从国别研究进入跨国研究,但是直到1980年代末,拉姆·A.克纳安(Ram A.Cnaan)还惊讶于关于公众对福利国家成分与维度的态度的研究如此之少,而就概念、分析单位和对潜在进程的理解而言,关于福利态度研究的知识缺乏一个清晰的术语定义(Cnaan,1989)。时至今日,关于福利态度的定义、维度等研究在欧美学者中仍未达成共识。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孤立地研究讨论与福利主题相关的意见,基本忽视了福利态度的多维问题;二是将相关福利主题的意见整合成一个单一的、附加的维度,却从不解释为何如此设计,更没有信度测试(van Oorschot & Meuleman,2012)。
早期的研究大多数只关注福利态度的单一因素的测量,主要的缺陷是依赖一个或很少的几个总体性问题去测量态度,容易给出一个概要式的图景,但也可能带来更大程度的歪曲(Svallfors,1991)。针对早期研究的不足,克纳安使用公共支出水平、受益者数量与服务品质三个指标测量(Cnaan,1989),开启了福利国家态度研究的多维度取向。在此之前,约翰·麦克亚当斯(John Mcadams)只是关心在经济领域中公众对政府责任(The Role of Government)与福利国家广度(Extent)的态度(Mcadams,1986),但两者却是福利态度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进入1990年代,福利态度的研究开始更多走向多维度。斯沃福斯参照福利国家的结果与组织的不同方面,将福利政策区分为分配、行政、成本与滥用四个维度(Svallfors,1991),由于使用旋转因子时强制定义了本存在关系的不同维度之间不存在关系,其结果也就仅仅是呈现了预先定义好的福利态度的维度,其结论值得商榷(van Oorschot & Meuleman,2012)。
已有研究显示了福利国家态度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但很难将彼此的结论联结起来,因而福利国家态度究竟有几个维度始终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可以从公众对福利国家的认知分析起。沿此方向,特里尔·希沃(Tuire Sihvo)与汉纳·乌西塔洛(Hannu Uusitalo)将福利态度区分为福利的责任、福利国家的使用、输出、福利国家的效果(Sihvo & Uusitalo,1995b)。由于该研究仅仅是对每个维度单独做了因子分析,而不是所有维度同时处理,导致其无法寻找出福利态度的真实维度(van Oorschot & Meuleman,2012)。
斯沃福斯等人较早地开展了福利态度的多维度分析,但学术界更多引用的却是来自埃德尔乔德·诺勒(Edeltraud Roller)的分类。参照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与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在公民文化研究中的分类,诺勒将福利国家态度区分为两个维度:态度的对象(Objects)与态度的模式(Modes)。前者包括目标、输入(方式或工具)与输出(政策)三个维度。因而,对福利国家的支持度能够参照政府为实现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而介入的目标、方式和结果(Outputs)的测量。目标包括两个维度:(1)政府是否的确有责任实现社会经济保障与社会公平(广度/范围),反映的是一个偏好;(2)如果政府的确有责任,那么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强度/程度),通过在社会保障上,或在专项社会政策上的开支多少的偏好来测量。方式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1)制度,反映人们对长期社会政策的评估;(2)项目,关心的是对短期社会政策项目的态度。公众评估的结果也可分为两类:(1)有意识的结果;(2)无意识的结果。这些概念描述了公众对政府介入的态度的所有方面。针对福利态度模式,诺勒的分类是基于利益取向与价值取向,为众多学者采用(Roller,1995;Gelissen,2000)。这一分类与斯沃福斯有共同之处,如对结果的关注,但诺勒明确区分了态度的对象与态度的模式,后期从事福利态度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此分类的影响。
参照诺勒、希沃与乌西塔洛等人的观点,汉斯-于尔根·安德斯(Hans-Jürgen Andreß)与托尔斯登·海恩(Thorsten Heien)将福利国家态度区分为福利国家的功能*在其1999年为参加德国Bielefeld会议而提交的报告中采用的是“福利国家的目的”(The Aims of the Welfare State)(Heien & Hofäcker,1999)。、福利国家的方法、福利国家有意与无意的效果、福利国家的财政能力四个维度(Andreß & Heien,2001),这一分类增加了对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财政能力的考察。这对分配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该研究仅考察了对福利国家功能的影响。斯沃福斯根据1996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政府责任模块数据将福利态度区分为三个指标:支出指标、财政指标与服务指标(Svallfors,2004),同样包含了对财政能力的考察。
有所欠缺的是,多数研究采用单一标准,主要是政府行动的范围(The Scope of Governmental Action),或曰政府责任的边界,以此检验结构的效度。在此背景下,克拉拉·莎巴芙(Clara Sabbagh)与彼特·凡胡斯(Pieter Vanhuysse)采用了基于市场的框架与福利国家主义的框架,以分属自由的、激进的、保守的与社会民主主义四种福利类型的八个国家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体制下的福利态度的差异。结果显示,福利态度六个层面的体制类型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体制类型的效应依赖于当下考虑的福利态度的特定层面,意味着福利框架结构化了公众的态度,也反映了福利态度是复杂的、天生多维的(Sabbagh & Vanhuysse,2006)。研究的不足在于,样本仅仅是来自八个国家的大学生(van Oorschot & Meuleman,2012),因而所谓的公众态度就只是学生的态度。
既有的研究通常将福利国家视为不同要素的静态组合,而凡·于肖特与巴特· 迈乐曼(Bart Meuleman)则将福利国家定义为一种动态的制度,因而福利态度就不再是聚焦于福利国家静态的指标,而是整个政策执行的过程,完成了从静态视角到动态视角的转变。在此基础上,福利态度结构被区分为六个维度:对福利国家原则的支持;政府责任的偏好宽度(广度);政府开支的偏好深度(强度);福利政策的执行评估;福利国家结果的评估;福利国家可感知的后果(van Oorschot & Meuleman,2012)。其研究从对福利态度某环节的碎片化取景发展到对福利态度生成过程的全景式扫描,福利态度的维度也就随之从静态转向了动态。
上述研究共同的缺陷是,福利态度指向的对象——福利国家或福利政策的维度,与福利态度的维度混在一起。芬克·罗斯玛(Femke Roosma)、约翰·吉利森(John Gelissen)与凡·于肖特明确区分开了福利国家的维度与福利态度的维度。他们将福利国家的维度区分为福利混合、福利国家目标、广度、深度、再分配设计、执行过程与产出。这个框架追随政策进程发展的逻辑:从政策目标的形成,经过政策的执行,最后实现政策的产出,同样秉持了动态视角。福利态度的维度则区分为一维与多维,一维的视角提供的是关于支持或反对福利国家的总体态度;多维的视角则认为人们对福利国家不同维度的态度是不同的,而且可能是矛盾的(Roosma et al.,2013)。
罗斯玛、吉利森与凡·于肖特的研究发现是基于欧洲社会调查2008年轮换模块——“变化欧洲中的福利态度”的框架与数据。根据克利斯汀·施塔克尔(Chritian Staerkl)、斯沃福斯与凡·于肖特的介绍,该概念框架基于以下部分构成:以风险与资源作为起点,被视为主要因素;制度框架被视为强烈形塑福利意见的变量,并影响风险与资源的分配;社会价值倾向承担形塑福利态度的主要责任,涉及平等主义、传统主义与权威主义,作为一种倾向受风险与资源以及制度框架的影响;福利态度指向的对象包括:福利国家的边界与责任;税收与财政;可选择的福利国家模式和目标群体/接受者;而福利评价是福利态度的又一系列,涉及福利国家政策的经济、社会与道德的结果(Staerkl et al.,2008)。因而前者的维度设计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在最新的研究中,斯沃福斯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概念框架(见图1)(Svallfors,2012b)。

图1 福利态度分析的概念框架
资料来源:European Social Survey Round4,2008. 转引自(Svallfors,2012b)。
与已有研究相比,这一区分走出了过去概念混淆的局面,明确了福利态度对象的维度与福利态度的维度之间的差异*此处尚未区分福利国家的维度与福利的维度之差异(Allardt,1976)。。然而,不足的是,对福利态度的研究仍然忽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除库林、桑德伯格和王家英等给出福利态度的明确定义外,多数学者并未讨论。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福利态度的调查主要是依据支持率,因而其态度可界定为就特定的态度对象而言给予一种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作出回应的倾向;根据态度问题的变量取值,可以区分为支持或不支持两个答案,或按程度区分为不同取值,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本质上只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因而事实上仅为一个维度。福利态度也就可以限定为以福利为特定的态度对象的态度,而当下所讨论的福利态度的多维也就仅仅是态度指向的对象——社会福利的多维。至此,福利态度的研究完成了从一维到多维、从静态到动态、从态度与其对象维度不分到两者分开的转变,但福利态度究竟应该包括哪几个维度,研究究竟基于政府、市场还是其他的分析框架并未达成共识。
2.港台学者的研究
港台学者*由于台湾学者的资料难以获得,因而主要是转引了毕天云的研究(参见:毕天云,2004a: 58-61;何承晏,2014)。的研究由于文化上的同根性,对我们的研究或许具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吕宝静把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概括为八个方面:对于贫穷和社会救助的态度;对于社会福利和工作伦理关系的看法;对于社会福利对象的选择的态度;对于个人(家庭)自赖原则的看法;对于政府福利角色的看法;对于社会福利经费支出的看法;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的看法;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吕宝静,1995[转引自毕天云,2004a])。可以发现,这八个方面涉及到了价值观、行动主体(政府、家庭)的权利与责任、制度与方案、财政等问题,类似于诺勒的分类。古允文则从政府政策的目的(经济发展优先或福利提供优先)和政府政策的手段(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两个维度划分出四种类型的福利态度(Ku,1997[转引自毕天云,2004a])。该模型充分考虑了政策的目的与手段,类似于莎巴芙与凡胡斯的基于市场与基于国家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政策的执行、政策的产出及过程与结果的评估等未纳入分析的框架中。综合西方学者和林万亿关于福利态度的观点,王方将福利态度分为三种类型:经济个人主义、社会公平与传统慈善的福利态度(王方,2001[转引自毕天云,2004a])。这种类型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价值取向,其隐含的假设是秉持不同价值取向的行动者其态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价值取向可能是制度与文化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基于詹姆斯·梅志里(James Midgley)关于社会福利的定义(Midgley,1995,1997[转引自Wong & Wong,1999]),王家英、王卓祺将福利态度区分为三个维度:社会问题控制,包括贫困、犯罪与公共安全、失业三类子指标;需要满足,包括社会福利的政府供给、个人生活满意两类子指标;社会流动机会的最大化(Wong & Wong,1999)。这一分类与前述研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它是在界定好福利态度的对象——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再操作化后生成测量指标的,避免了福利国家维度与福利维度不分的局限。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没有摆脱静态视角的局限;二是社会福利的定义值得商榷。
王卓祺依据制度与意识形态,将福利态度区分为四大维度:社会—经济平等、社会福利的制度基础、社会福利观念、社会福利的规则与条件,每一个维度又对应不同的指标(Wong & Chau,2003)。这一分类体现了本土化的努力,但依据的标准过于单一,难以反映福利态度对象的复杂性。王家英、尹宝姗(Shirley Po-San Wan)与罗荣建(Kenneth Wing-Kin Law)则借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与斯沃福斯的指标,从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供给两个维度定义了福利态度,主要是围绕国家干预与福利开支两大方面对香港公众进行了调查(Wong et al.,2008)。从问卷来看,其指标体系的设计仍处于“采借”阶段,优点是可以与已有的国际研究直接进行横向比较,缺点是难以跳出西方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制约下的理论窠臼,无法体现本土特色。
综上所述,在福利态度维度的设计上,经历了从一维到多维、从静态到动态、从概念不清到概念清晰的转变,政府责任的边界也因依据原则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欧美学者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港台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本土化的努力,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知识基础与行动保障。
三、制度与文化:福利态度生成的解释路径
在明晰维度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福利态度的差异。福利态度的研究通常是从个体特征和/或国家或体制类型背景的视角来研究(Sevä,2009;Sundberg & Taylor-Gooby,2013)。限于篇幅,本文并不回顾个体社会人口学特征对福利态度生成的影响,而将福利态度的生成从理论上区分为制度与文化两个解释路径。
(一)制度路径
社会福利研究中有两个经常导致分裂的传统:一是福利体制类型的比较研究;一是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的价值观、态度与认同的比较研究(Svallfors,1997)。前者始于埃斯平-安德森1990年首次提出的“福利体制”的概念,但它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就不同体制下生活的人群中发现的态度结构与价值认同而言的制度特征;后者的研究则经常忽视了历史或制度的解释以及态度或信仰体系的说明(Svallfors,1997)。目前,斯沃福斯与其他学者已经开始探询不同福利国家体制的制度结构是如何影响公众的价值与态度结构,或是如何被影响的(Sabbagh & Vanhuysse,2006)。
福利态度研究假设每种体制与福利国家态度的特定模型有关,不同的福利国家体制意味着不同的结构,最终导致福利国家态度的不同模式。例如,自由体制国家的公民至多支持政府在疾病与养老方面的立法介入,而社会民主体制国家的公民将支持如全面就业政策或保证收入平等的介入那些影响深远的政府行动(Andreß & Heien,2001)。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差异能够为福利体制解释(Heien & Hofäcker,1999;Andreß & Heien,2001)。在桑德博格与泰勒-古比的文献回顾中,24项研究中有7项明确基于体制路径,这7项都发现一些可支持的结论(Sundberg & Taylor-Gooby,2013)。因此要了解福利态度的不同模式就有必要先了解福利体制的类型。
福利体制可以被定义为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相互依赖组合来生产和分配福利资源的模式,而非营利的志愿组织或第三部门也可添加其列(Esping-Andersen,1999)。依据去商品化和阶层化两个指标,福利国家被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三种体制(埃斯平-安德森,2003)。1990年代以来,该分类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这些批评集中在理论(国家与体制的范围、性别缺失的世界、福利国家体制的幻觉)、方法论与经验主义上,因而福利体制的定义、概念与方法都需要澄清并达成一致(Bambra,2007;Powell & Barrientos,2011)。基于不同的批判视角,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福利国家体制类型(Deacon,1993;Holliday,2000;Arts & Gelissen,2002;Holliday & Wilding,2003;Bambra,2007)。事实上,真实的福利国家通常是混合型的,而很少是纯粹理想的类型;同时,由于正式理论学说的缺乏与比较研究中仍然无法确定的结果,福利国家的理想类型仍然无法获得满意的回答(Arts & Gelissen,2002)。因而,福利体制对福利态度影响的研究就更为错综复杂。
态度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是态度与福利体制的关系的直接表现,个人或公众的态度受社会政策/福利体制设计的影响。据此,赫泽戈尔德(Troels Fage Hedegaard)提出公众与个体对政策的支持受到政策设计的影响的政策反馈理论,认为个人或公众“接近”受益于选择型社会政策的津贴接受者的态度受到的影响很大;“接近”受益于普惠型社会政策的津贴接受者的态度几乎不受影响,而“接近”受益基于贡献的社会政策的津贴接受者的态度受到的影响介于两者之间(Hedegaard,2014)。这类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福利体制/制度对福利态度存在影响的假设。
然而,制度路径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克利斯汀·阿尔伯特·拉什(Christian Albrekt Larsen)就指出,“先前联结制度与福利态度的企图已经不可信”(Larsen,2006: 1)。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上涉及态度与项目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制度安排与福利国家态度的关联或许反映的是成功的政客在提出政策建议或决策时考虑到了或是受到了公共舆论的影响。如此一来,公共舆论应该是影响了制度安排。(2)对制度结构假设仅有混合(Mixed)的支持,即使在从政策到态度的单向因果关系的假设中。(3)关于制度结构与福利态度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当每种制度类型仅由少量的国家代表时,国家层面的因素的经验检验是不可信的。国家层面的差异或许归因于已测量的结构特征,也可能归因于其他尚未测量的特征(Hasenfeld & Rafferty,1989;Blekesaune & Quadagno,2003)。不幸的是,仅有少数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总体层面的态度变量由个体层面的变量导致的可能性(Andreß & Heien, 2001; Blekesaune & Quadagno, 2003; Jger,2006;Jakobsen,2011)。
(二)文化路径
文化是“一个模糊的,令人难以界定的结构”(Triandis et al.,1986: 258),可以定义为共同的价值、规则与态度的系列(Baldock,1999)。它有强弱之分,前者是严格限定的,如鲍多克(John Baldock)关于文化的定义;后者是较少限定的,为社会政策的文化分析留下了空间。绝大多数研究者追随的是前者(van Oorschot,2007)。
福利态度的研究初期集中在态度与体制的关系上,后期才开始转向文化因素的考量。追踪福利制度史的研究可知,现有关于福利国家的社会—历史分析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是结构—功能主义路径,关注“结构”并认为工业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工业主义逻辑、涂尔干式路径、新马克思主义等(Pierson,1996;Uusitalo,1984);二是行动者路径,关注“能动”并认为不同行动者在福利制度生成中的重要的作用,如权力资源理论、国家中心视角、雇主中心视角、性别关系视角等(刘军强,2010)。但这些研究都忽视了文化作为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在福利制度生成中的作用。
在福利国家政策的比较研究中,跨国差异通常由福利国家制度的特定轮廓与一系列社会行动者所解释,而文化差异的解释却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视为边缘主题。事实上,文化与福利国家政策的关系是复杂的和多面向的,它同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制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Pfau-Effinger,2005;熊跃根,2007)。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政策有关(Baldock,1999),文化的偏好如何在社会福利政策的文本中留下了它们的踪迹(Schram,2000),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有学者否认文化因素在理解社会政策中的作用,认为文化并不是理解社会政策的缺失的变量,如鲍多克;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如凡·于肖特(Baldock,1999;van Oorschot,2007;van Oorschot et al.,2008)。
在桑福德·F.施拉姆(Sanford F. Schram)看来,无论它是“契约”“依赖”,还是“保险”,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类型都限制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可能性(Schram,2000: 3)。相似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认为,文化不只是经济的后果,同时也能形塑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本质。因而,把握其差异并了解它是如何跨文化并随时间而变化的,而不是假装看不见,可以使得社会政策的效力得到很好的保证(Inglehart,1988)。然而,文化研究既不能限于“精英文化”(High Culture),也不能过度“深描”,前者范围太窄,后者将不会导致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因为一切皆为文化,则文化无法解释任何一切(van Oorschot,2007)。
当下的文献很少直接关注文化与福利态度的关系,更多关注的是文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争论可归为“福利文化”研究。这一概念由英国社会政策专家罗伯特·平克(Robert Pinker)最早提出和使用,包括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毕天云,2004b),现有讨论集中于东亚福利模型的研究中。凯瑟琳·琼斯(Catherine Jones)是东亚福利模型的第一代分析家,他将文化视为决定性变量,认为儒家主义是贯穿开始、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型意识形态与福利意识形态(Jones,1990,1993;Aspalter,2006);朴炳铉在解释“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福利制度”的问题时,同样强调了儒家文化对东亚福利体制建设的作用(朴炳铉,2012: 14)。与之相反,戈登·怀特(Gordon White)与罗杰·古德曼(Roger Goodman)认为,尽管文化的解释在文献中是“一个或多或少显著的主题”,但它在说明东亚福利体制进化中是一个“无用的”变量(White & Goodman,1998: 12,15)。目前富有挑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的作用,形成了国家中心说而否认文化的作用(Holliday,2000)。然而,文化无论有用与否,都只能通过外在的显示而揭示,不可能被直接观察或测量(Baldock,1999)。文化影响我们的价值,价值影响态度,接着影响行为,而行为又会影响文化(Adler & Gundersen,2008)。因此,福利文化的观察与测量最终不得不依赖于询问公众的福利态度进而观察与测量,它对政策的影响只有通过对价值、态度与行为的作用才能生效,这使得福利态度的研究与文化、社会政策的研究始终缠绕在一起。
广义而言,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相对于文化,它可能是暂时的,但它对公众福利态度转变的影响可能是激烈的,而福利文化对公众福利态度形成的影响通常是潜移默化的。制度具有重要的规则创造功能,而价值很少能够解释公众的偏好(Kulin,2012)。制度并非要等到某种类型的福利文化成熟后才会出现,它有可能通过制度化的传播路径形塑人们的福利态度,进而形成新的福利文化。中国现有的福利文化可能更多地是支持传统的高度稳定的福利制度。然而,文化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长期存在的,文化遗产可能被制度安排所侵蚀(Wong et al.,2009);反之,经久不变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为文化变迁所摧毁。因而,研究福利态度有必要事先考察这个国家的福利体制或福利文化。
四、研究的总体态势与本土意义
从福利态度研究的历史、分析维度的变化及其解释路径的变迁,可以发现研究的总体态势是:从国别研究到跨国研究;从一维到多维;从静态到动态;从制度独尊到文化共存;从数据依附到数据专用;从简单描述到模型建构;从碎片取景到全景扫描;等等;绘制出了一道学术研究的繁荣景观。然而,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表现在以下方面:缺少理论建构,多为经验研究或政策研究;未能在福利态度的定义上达成共识;多数学者未能将态度指向的对象维度与态度本身维度区分开;未能在福利态度的维度上达成共识;维度的确定几乎都是数据驱动型(Data-driven)的;研究倾向于制度主义的决定论,忽视了态度对体制的能动性建构作用;偏重制度分析而淡化了文化的作用;主要是在西方福利制度与文化或其影响的背景下探讨;较少研究关注了行动者的主体的多元性及其能动性;未能在福利态度与社会福利运动的研究之间建立有效的学术联结;等等。
限于篇幅,本文尚有许多主题未能详述,如:福利态度在人口—社会学特征上分布的差异;合法性与国家能力、再分配、应得(Deservingness)与需要、公民身份、社会团结等核心概念与福利态度研究的关联;制度、文化与态度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与政策设计效应;以及从态度到社会福利运动再到政策议程的演进机制;等等;只是尽可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以索引的文本脉络与参考坐标。
福利态度是在回应西方福利国家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迅速发展的,围绕的核心是政府的责任,“理应成为现代社会的秩序、治理与合法性的核心成份”(Svallfors,2012a: 1)。在西方工业国家,公众的支持是福利国家合法性的基本组成部分(Jger,2006)。同理,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应是中国社会福利政策或项目合法性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按照理论推断与政策预想应该获得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福利中国仍未成为现实,社会福利制度时常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在顶层设计的狂欢背景下,尊重底层实践智慧的福利态度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福利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寻找出连接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人态度的机制。人类的需要是理解福利制度的关键,是社会资源分配和福利制度运作的价值基础(刘继同,2004)。在欧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一般呈现一条由民众社会需求推动到政府决策行为的被动型的成长轨迹(郑秉文、史寒冰,2002)。在中国,我们过多地关注了顶层设计,而忽视了来自公众的底层需要、实践智慧与参与权利。未来的福利态度的研究应以公众的基本需要为逻辑起点,考察宏观的结构化背景(如制度、文化)与微观的初始化资源(如社会权利)对福利态度的影响,并寻找出从个人困扰上升为公共论题,进而推动制度与文化变迁的机制,从而在宏观与微观、社会与个体、客观与主观、结构与行动、历时性与共时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图2)。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既能呈现自下而上公众反思引领下的需方参与,也能呈现自上而下官僚技术设计下的供方推动的福利制度演进的脉络。

图2 态度—行动—结构的互动关系
注:虚线表示连接的两端构成成对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次,有助于回答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判断未来福利制度改革的重点与方向。从目标上看,现行的福利制度设计大致有两大取向:一是福利国家,一是福利社会;从方向上看: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那么未来中国的福利制度是两者取其一,还是存在第三条道路?福利态度的研究可以为未来中国的福利制度的选择或设计提供合法性保证,而对政策进程中行动主体福利责任边界的厘清则可以让我们清晰地了解未来福利制度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第三,有助于恢复公众在社会政策制定中的主体性地位,保证“小人物发出大声音”。政策是一种控制,也是一种角逐现存秩序和声音参与权利的工具(科尔巴奇,2005),公众要实现自己的福利目标就需要具有设定政策议程的能力,但在中国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受惠者的需要很少被倾听,在福利的输送中他们也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个体的福祉成为机构统计中的概率福利。福利态度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福利制度的设计从“政府需要为本”向“人类需要为本”、从“需要”向“公民身份”、从“社会稳定”向“社会团结”的转变,推动公民参与,从而实现“小人物发出大声音”。
最后,有助于推动跨国、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与本土研究。比较研究是福利态度研究的内在要求与最基本的方法。通过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可以了解公众福利态度在空间与时间上是如何变化的以及为什么变化,可以了解公众福利态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可以回答为什么福利体制与(或)文化相同而公众的福利态度会不同,可以回答态度何时追随政策与政策何时追随态度的问题,从而为国家或地区的福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或实践的证据。
总体而言,由于缺少高质量、大样本、可做纵贯研究与跨国比较研究的以福利态度为核心模块的数据库,国内学者的研究目前只能说处于萌芽阶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经验与本土特色提炼出适合内地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解释模型与测量指标体系(如儒家文化、户籍制度),并据此建立起高质量的、可供纵贯研究的大型数据库。近期则可以通过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中申请增加福利态度的轮换模块增强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未来既要重视理论梳理,也要重视经验研究;既要重视结构的形塑作用,也要重视行动者的能动性;既要重视循证数据库的建设,又要重视证据的开放与转化。在此基础上,推动跨学科、跨国、跨区域的平台建设与比较研究,为社会政策的设计提供先进的理论与科学的证据,从而推进国家福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背景下,无论福利制度的颜色与成份如何,我们都期望公众的福利态度是形成政策选择的基础。
毕天云(2004a).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毕天云(2004b).社会福利的文化透视:观点与简评.社会学研究,4: 50-63.
陈劲松(2011).建构北京市大福利制度的思考.北京社会科学,5: 47-52.
H.K.科尔巴奇(2005).政策.张毅、韩志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何承晏(2014).台湾民众福利态度的阶级差异.台湾中正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黄叶青、余慧、韩树蓉(2014).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公共行政评论,6: 88-106.
江治强(2013).中国社会福利转型的驱动因素与路径选择.学习与实践,4: 106-111.
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200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赖伟良(2004).澳门市民的福利意识形态:中间路线取向.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继同(2004).人类需要理论与社会福利制度运行机制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8: 29-33.
刘军强(2010).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发展述评.社会学研究,4: 199-221.
彭国胜(2012).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西北人口,3: 38-44.
彭华民(2012).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范式演变与制度转型创新.天津社会科学,6: 77-83.
朴炳铉(2012).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 高春兰、金炳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尚晓援(2001).“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3: 113-121.
田晓玲(2011).国际经济学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制定政策要考虑人们的预期.文汇报,7月25日第009版.
万国威(2014).我国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定量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36-149.
万国威(2015).中国大陆弱势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公共管理学报,1: 58-69.
万国威、金玲(2015).中国弱势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双层解构.人口学刊,5: 18-31.
熊跃根(2007).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江苏社会科学,4: 48-56.
臧其胜(2015a).政府福利责任的边界:基于华人社区公众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 110-117.
臧其胜(2015b).政府福利责任的边界:基于农民工福利态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载岳经纶、朱亚鹏主编《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9卷).上海:格致出版社.
张朝雄(2007).混合福利模式:当代大学生社会福利意识测评.青年研究,9: 23-27.
张军(2009).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解析——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张军、陈亚东(2014).中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民意基础——基于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态度的实证调查.西北人口,6: 88-93.
郑秉文、史寒冰(2002).试论东亚地区福利国家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 19-28.
Adler, N. J. & Gundersen, A.(2008).InternationalDimensionsofOrganizationalBehavior(5th). Ohio: Cengage Learnign.
Allardt, E.(1976). Dimensions of Welfare in a Comparative Scandinavian Study.ActaSociologica,19(3): 227-239.
Andreß, H-J. & Heien, T.(2001).Four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Norway, and the United States.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 17(4): 337-355.
Arts, W. & Gelissen, J.(2002).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r More? A State-of-the-Art Report.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 12(2): 137-158.
Aspalter, C.(2006).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15(4): 290-301.
Baldock, J.(1999).Culture: The Missing Variable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Policy?.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 33(4): 458-473.
Bambra, C.(2007).Going beyond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Regime Theory and Public Health Research.JournalofEpidemiologyandCommunityHealth, 61(12): 1098-1102.
Blekesaune, M. & Quadagno, J.(2003).Public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State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4 Nations.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 19(5): 415-427.
Borre, O. & Goldsmith, M.(1995).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In Borre, O. & Scarbrough, E.TheScopeof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naan, R. A.(1989).Public Opinion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SocialIndicatorsResearch,21(3): 297-314.
Deacon, B.(1993).Developments in East European Social Policy. In Jones, C.Ed.NewPerspectivesontheWelfareStateinEurop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Edlund, J.(1999).Trust in Government and Welfare Regimes: Attitudes to Redistribution and Financial Cheating in the USA and Norway.EuropeanJournalofPoliticalResearch, 35(3): 341-370.
Erskine, H.(1975).The Polls: Government Role in Welfare.ThePublicOpinionQuarterly,39(2): 257-274.
Esping-Andersen, G.(1999).SocialFoundationsofPostindustrial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lissen, J.(2000).Popular Support for Institutionalised Solidarity: A Comparison betwee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9(4): 285-300.
Gelissen, J.(2002).WorldofWelfare,WorldsofConsent?. Leiben: Brill.
Hasenfeld, Y. & Rafferty, J. A.(1989).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SocialForces, 67(4): 1027-1048.
Hedegaard, T. F.(2014).The Policy Design Effect: Proximity as a Micro-level Explanation of the Effect of Policy Designs on Social Benefit Attitudes.ScandinavianPoliticalStudies, 37(4): 366-384.
Heien, T. & Hofäcker, D.(1999).HowDoWelfareRegimesInfluenceAttitudes?AComparisonofFiveEuropeanCountriesandtheUnitedStates1985—1996. Working Paper No.9. Bielefeld: ECSR-Workshop. Available at(July 29, 2016): http://eswf.uni-koeln.de/forschung/wme/wme_ap9.pdf.
Holliday, I.(2000).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Politicalstudies,48(4): 706-723.
Holliday, I. & Wilding, P.(2003).WelfareCapitalisminEastAsia:SocialPolicyintheTigerEconom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Inglehart, R.(1988).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82(4): 1203-1230.
Jakobsen, T. G.(2011).Welfare Attitudes and Social Expenditure: Do Regimes Shape Public Opinion?.SocialIndicatorsResearch, 101(3): 323-340.
Jones, C.(1990).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Oikonomic Welfare States.GovernmentandOpposition, 25(4): 446-462.
Jones, C.(1993).The Pacific Challenge. In Jones, C. Ed.NewPerspectivesontheWelfareStateinEurop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Kulin, J.(2011).ValuesandWelfareStateAttitudes:TheInterplaybetweenHumanValues,AttitudesandRedistributiveInstitutionsacrossNationalContexts. Umeå University PhD Thesis.
Kulin, J.(2012).PublicSupportforRedistributiveStrategies:TheImpactofPersonalValuesandInstitutionalNorms. Working Paper, Umeå University. Available at(July 29, 2016):http://www.soc.umu.se/digitalAssets/88/88750_nr-3_2012-kulin_public-support-for-redistrbutive-strategies.pdf.
Larsen, C. A.(2006).TheInstitutionalLogicofWelfareAttitudes:HowWelfareRegimesInfluencePublicSuppor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McAdams, J.(1986).Status Polar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Attitudes.PoliticalBehavior, 8(4): 313-334.
Oskamp, S. & Schultz, P. W.(2005).AttitudesandOpinions(3rd).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fau-Effinger, B.(2005).Culture and Welfare State Policies: Reflections on a Complex Interrelation.JournalofSocialPolicy, 34(1): 3-20.
Pierson, P.(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WorldPolitics, 48(2): 143-179.
Powell, M. & Barrientos, A.(2011).An Audit of the Welfare Modelling Business.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 45(1): 69-84.
Roller, E.(1995).The Welfare State: The Equality Dimension. In Borre, O. & Scarbrough, E. Eds.TheScopeofGovernment.No. 3.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osma, F., Gelissen, J. & van Oorschot, W.(2013).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A European Cross-National Study.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13(1): 235-255.
Sabbagh, C. & Vanhuysse, P.(2006).Explor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 Students’ Views in Eight Democracies.JournalofSocialPolicy, 35(4): 607-628.
Schram, S. F.(2000).AfterWelfare:TheCultureofPostindustrialSocialPolicy. New York &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evä, I. J.(2009).WelfareStateAttitudesinContextLocalContextsandAttitudeFormationinSweden. Umeå University PhD Thesis.
Sihvo, T. & Uusitalo, H.(1995a).Economic Crises and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in Finland 1975—1993.ActaSociologica, 38(3): 251-262.
Sihvo, T. & Uusitalo, H.(1995b).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 have Several Dimensions: Evidence from Finland.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4(4): 215-223.
Staerkl, C., Svallfors, S. & van Oorschot, W.(2008).TheFutureESS4ModuleonWelfareAttitudes:Stakes,ChallengesandProspects. Available at(July 29, 2016):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conferences/documents/34th_ceies_seminar_documents/34th%20CEIES%20Seminar/1.4%20%20C.%20STAERKE%20EN.PDF.
Sundberg, T.(2014).Attitudes to the Welfare State: A Systematic Review Approach to the Example of Ethnically Diverse Welfare States.SociologicalResearchOnline. Accessed at(June 10, 2014):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9/1/28.html.
Sundberg, T. & Taylor-Gooby, P.(2013).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ttitudes to Social Policy.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 47(4): 416-433.
Svallfors, S.(1991).The Politics of Welfare Policy in Sweden: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and Attitudinal Cleavages.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 42(4): 609-634.
Svallfors, S.(1997).Worlds of Welfare and Attitudes to Redistribution: A Comparison of Eight Western Nations.EuropeanSociologicalReview, 13(3): 283-304.
Svallfors, S.(2004).Class, Attitudes and the Welfare State: Swede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 38(2): 119-138.
Svallfors, S.(2012a).ContestedWelfareStates:WelfareAttitudesinEuropeandBeyo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vallfors, S.(2012b).WelfareAttitudesinEurope:ToplineResultsfromRound4oftheEuropeanSocialSurvey. ESS Topline Results Series-Issue 2. Available at(July 29, 2016): http://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docsfindings/ESS4_toplines_issue_2_welfare_attitudes_in_europe.pdf.
Triandis, H. C., Bontempo, R., Betancourt,H., Bond, M., Leung, K., Brenes, A., Georgas, Hui, C. H., Martin, G., BSetiadi, B., Sinha, J. B-P., Verma, J., Spangenberg, J., Touzard, H. & de Montmollin, G.(1986).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tic Aspec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cross Cultures.AustralianJournalofPsychology, 38(3): 257-267.
Uusitalo, H.(1984).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State of the Art.EuropeanJournalofPoliticalResearch, 12(4): 403-422.
van Oorschot,W.(2007).Culture and Social Policy: A Developing Field of Study.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16(2): 129-139.
van Oorschot, W, & Meuleman, B.(2012).Welfarism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Welfare State Legitimacy: Evidence from the Netherlands, 2006.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 21(1): 79-93.
van Oorschot, W., Opielka, M. & Pfau-Effinger, B. Eds.(2008).CultureandWelfareState:ValuesandSocialPolic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 Cheltenham &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White, G. & Goodman, R.(1998).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an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In Goodman, R., White, G. & Kwon, H-J. Eds.TheEastAsianWelfareModel:WelfareOrientalismandtheStat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Wong, C-K., Wang, K. Y-T. & Kaun, P-Y.(2009). Social Citizenship Rights and the Welfare Circle Dilemma: Attitudinal Findings of Two Chinese Societies.AsianSocialWorkandPolicyReview, 3(1): 51-62.
Wong, C-K. & Chau, K. K-L.(2003).Attitudes towards Social Welfare-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Options for Policy Changes. In Lau, S. K. et al. Eds.IndicatorsofSocialDevelopment:HongKong2001. Hong Kong Institute Asia-Pacific Studies, CUHK.
Wong, T. K-Y. & Wong, C-K.(1999).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Social Welfare in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Development.SocialDevelopmentIssues, 21(1): 1-11.
Wong, T. K-Y., Wan, S. P-S. & Law, K. W-K.(2008).High Expectations and a Low Level of Commitment: A Class Perspective of Welfare Attitudes in Hong Kong.Issues&Studies, 44(2): 219-247.
责任编辑:朱亚鹏
D669
A
1674-2486(2016)04-0171-20
*臧其胜,南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本文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彭华民教授在本选题研究上的引领与指导。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10JZD0033)、南通大学2015年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