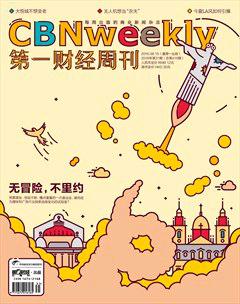美丽新世界?
路意
人们通常以为,人工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大概是因为之前许多年里,科幻小说和电影无一不在塑造人形机器人,比如《终结者》《我,机器人》《机械姬》等,它们中的人工智能都是有形的。很显然,人形机器人还要许多年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其实早已被人工智能包围很多年了,它们无形地存在于我们周围,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机器人”是传感器和执行器结合在一起的特例,而在更多数的情况下,传感器是散落在环境中的,比如路灯上或者智能手机里,而执行端则在远处的一个集群服务器中,随着传感器越来越小,它们会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卡普兰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有一天当你走在一片原始荒原时,你可能并不会注意到你眼前有一个巨大的网络,大量组织和协作的设备正在维护这个环境,同时也在照看你,就像在参观迪士尼乐园时那样。”
最初,计算机一直被视为“只能按照编好的程序工作”,然而,以AlphaGo为代表的深度学习算法所展示出来的人工智能,已经足以改变人们的看法,即智能软件在特定问题上的智能已经远超人类最为杰出的选手,而智能软件其实早已在量化投资、电子商务、互联网广告等领域处理着每秒数以亿兆计的数据洪流,并从其中赚取巨额收益。
卡普兰指出,由于智能软件有着极快的信息处理速度、更高的准确度,以及更低的成本,比如量化投资软件可以做到每秒十万次交易,它们可以不知疲倦地24×7小时工作。实际上,智能软件所能获取的数据也远多于人类,比如互联网广告可以从数以千计的信息中交叉判断用户特征;电子商务中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知道所有卖家和买家的信息……这些都意味着人类是没法和智能软件抗衡的。
虽处于劣势,但卡普兰认为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并不会像《终结者》中那样发生战争,机器并不会拿起武器来挑战人类的统治。它们会很缓慢而隐秘地接管控制权。因为人类会对它们逐渐地加深信任,“让它们运送我们,为我们介绍合适的对象,定制每日新闻,保护我们的财产,监控我们的环境,种植和烹饪食物,甚至教育孩子……”,在此情形下,人类会逐渐失去大局观,无法再介入控制了。
卡普兰对未来的预测并不美好,人类很可能会被机器所圈养,“地球可能会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动物园,我们的机械看管者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转偶尔会推动我们一下,而我们会为了自身的幸福高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帮助。”当然,他并未止步于此,他看得更为深远。他希望能够引起大众对人工智能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失业与经济发展、贫富差距等问题的重视,并思考这些问题。
今年5月,特斯拉的一名车主由于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特斯拉官方声称“自动驾驶”功能被误解了,实际上他们提供的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即只有用户双手握在方向盘上,才可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另外,特斯拉已经有了数十万小时的无事故率,因此不是特斯拉的责任。
在传统的汽车驾驶中,发生驾驶责任的事故肯定是驾驶员的责任,但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而言,事故的责任方应该是谁?车主,汽车生产商,还是自动驾驶技术提供方,亦或是可以自动驾驶的汽车自身?卡普兰提出,如果智能机器已经具有可以意识到自己权利的时候,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对机器采取处罚呢?按照“消除其达成目的的能力”的原则,针对智能机器,则可以消除它们的“记忆”。像AlphaGo这样的智能软件,它们需要花许多时间深度学习,如果消除它们的记忆,那么它们就需要从头来过。
如果说法律问题还不太棘手,那么智能机器所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就复杂得多了:
—能否让自己的机器人代自己排队?
—如果你心脏病发作,而你的自动驾驶汽车拒绝加速更别说超速把你送到医院,你该怎么办?
—如果自动驾驶汽车与一辆载有很多孩子的汽车在一座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的桥上相遇,智能汽车是救你还是救孩子们?
从古希腊到现在,道德一直是西方哲学家思考的重要问题。数千年的争辩仍然未有定论。这大概就是因为在处理不同的利害关系时,会有不同的视角。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博爱、奉献成为绝大多数人们所认可的优秀品质,然而,你个人是否会购买一个会牺牲你而拯救更多人的智能汽车?
讨论到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无法回避失业问题。据调查发现,美国注册在案的 720个职业将会有47%被人工智能取代。这其中不仅是蓝领,还包括律师、医生这类金领。未来,有接近半数的人会失业。很多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因为人类可以创造出新的和更多的职业。的确,相比工业革命之前,现在许多职业都是新事物,比如软件工程师、形象顾问等,因此,很多人认为失业不是大问题。
然而,与许多人不同,卡普兰认为这次和工业革命时期不同。这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即劳动细分市场的变化速度会比人们学习新技能的速度快得多。在工业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样的时间中,人类实际上是通过代际更替来解决职业变更的。比如,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可能还是以农业或者工业为生,而我们可能已经以服务业为生。从70%的人口从事农业到只需要2%的人从事农业就能满足美国所有人口的需求,这个时间是100多年。而人工智能时代,职业的更替要快许多,可能就是5到10年,甚至更短。一个失业的驾驶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学会软件编程的工作技能的;而用户体验设计和增长黑客这样的岗位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
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卡普兰提出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不再由学校指定授课的内容,而是由对工作有需求的企业,它们发布所需求的岗位和技能,由学校来培养,如果你学会了这门技能并被企业录用,那么就可以从工资中扣除你的教育贷款。卡普兰认为需要推出一个类似房贷一样的新的金融工具:职业培训抵押贷款,以未来可偿付的工资收入来解决再就业的问题。
不过,说实话,这对失业的人来说是很大挑战,人们可能会疲于应对职业危机,生活陷入无助。这又不得不提到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问题。卡普兰认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高效率,会导致财富过度向金字塔顶端聚拢。根据数据分析,1970年代,美国收入前5%的家庭获得的平均收益比后20%的家庭高10倍,而4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扩大到了20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已成为事实。
如何消除这样的分配不公?卡普兰提出了一个“公共利益指数”的概念。即类似基尼系数一样,需要一个可以反映资产所有权在目标人口数量中的广度的可度量指数。当资产只为一个人拥有时,指数为0,而资产为目标人口中所有人平均拥有时,指数为1。国家可以通过“公共利益指数“来制定税收政策,为指数分值较高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甚至减免,让具有“公有”性质的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
卡普兰所预想的未来,是人机共生的形态。如果能解决好法律和道德、失业与经济发展及贫富差距的问题,人类将享受到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福祉,有干净而安全的环境,用之不竭的资源……然而,这样的社会是否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发展限制?不得而知。不过,就人类的天性而言,大多数人应该会希望生活在那样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