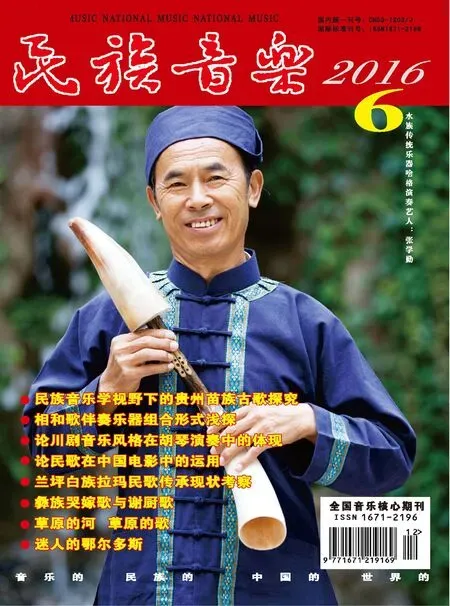论川剧音乐风格在胡琴演奏中的体现
——以胡琴套曲《西蜀琴韵》为例
■夏 毅(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
论川剧音乐风格在胡琴演奏中的体现
——以胡琴套曲《西蜀琴韵》为例
■夏 毅(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
川剧以四川、重庆方言为唱念的基本腔调,同时融入了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唱腔,经过近300年的演变,呈现出了自己特有的艺术特征。川剧音乐是川剧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川、渝以及云、贵、鄂的部分地区广为流传。另一方面,胡琴与戏曲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地方剧种伴奏乐器中必然会有胡琴的身影。随着时间的变迁,胡琴艺术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表现手法与手段上更是有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在当代许多作曲家目光的聚焦下,戏曲音乐也在不断发展。通过对戏曲音乐与各种音乐表演形式的嫁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声乐、器乐作品。川派胡琴套曲《西蜀琴韵》,是近年来胡琴艺术与川剧音乐艺术交融诞生的代表性作品,研究该部作品对了解与掌握川剧音乐风格在胡琴艺术上的演绎是有重要价值的。
胡琴艺术在戏曲音乐中的地位
戏曲音乐的主要表现因素包含了声乐和器乐两个方面。声乐部分主要包含了演员的唱腔与念白,而器乐部分主要指各种过场音乐与文武场面的伴奏,二者在互为依托的过程中相互转换。
胡琴是我国民族乐器中主要拉弦类乐器的统称。它的种类繁多,常见的有高胡、二胡、中胡、板胡、革胡、京胡、京二胡、四胡等。还有许多地方特色的胡琴,如四川的盖板子、潮汕的椰胡、湖南的大筒等。总的来说,胡琴的音色个性很强,且不说在乐队中与其他乐器之间的音色差异,就同组乐器中,各种胡琴的辨识度也非常之高。
从演奏的声效上讲,胡琴属于线性乐器,即常态化以演奏长线条音乐旋律为主要表现手段的乐器。在板腔体戏曲音乐中,它常常与唱腔用跟腔、衬腔、垫腔、托腔等多种形式伴奏于唱腔,与唱腔形成不离不弃、相互辉映的格局,因此胡琴与戏曲是形影不离的。而在音色上,胡琴类乐器甚至可以直接用来模仿人的说话与唱腔。记得在1988年春晚上,王开春老师通过拧动擂琴琴轴来改变音高,这一特殊演奏方式,完美模拟了京剧名段《铡美案》包拯的唱腔,更能体现出胡琴类乐器出众的模拟唱腔的能力。
《西蜀琴韵》的创作思路与艺术特点
(一)创作思路
《西蜀琴韵》的作者贺超波,是我国一位少有的优秀胡琴演奏家——在全国范围内,既能在胡琴演奏艺术上有着很高造诣,又能对川剧艺术非常精通的艺术家寥寥无几,而他两者兼备。这和他自幼在川剧团的积淀密不可分。《西蜀琴韵》的创作初衷,正是作者为了表达对胡琴与川剧两种艺术门类交融的情怀酝酿而成。但凡对川剧艺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川剧的声腔主要分为五大类,即昆曲、高腔、胡琴、弹戏以及灯调。这五大声腔风格各异,在它们的表现下,川剧的艺术魅力得以展示与丰富。而作者根据这5种声腔的特点,在段落安排上经过精心的调配,无缝地将许多声腔在旋律发展中进行搓揉重组,最终形成了高腔韵、胡琴唱以及弹戏闹3个乐章,以此对川剧艺术在二胡中的体现进行了诠释。
(二)艺术特点
提及胡琴套曲《西蜀琴韵》的艺术特点,笔者认为首先要谈到的是音乐语言的使用。该曲通篇都采用川剧音乐语汇作为创作语言,根据不同声腔的情绪、风格特点以及声腔之间的横向联系,使音乐具有很强的带入感,仿佛把人们带入到美丽的天府之国。在段落交接处,以川剧高腔曲牌《端正好》 《二郎神》元素凝练写成的音乐主题作为各大段的结束音乐,有机地把各音乐段落串联起来。
其次是该曲在旋律的发展手法上与当代许多创作类作品不同。如果说西方传统动机式的作曲技法在旋律构成的着眼点是音乐素材本身,那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东方音乐文化创作的焦点,更多是集中在音乐的神韵之上。中国音乐文化的神韵之奥妙,就如同中国文学的散文体一般——形散而神不散,又如书画艺术中浓淡松紧、张弛有度,寥寥几笔便能做到传神传韵,而这正是典型的中国艺术的创作思维。《西蜀琴韵》全曲以“起承转合”与“上下句”(或称对联式结构)为主要旋律发展手法,继承了中国戏曲板腔体“散、慢、中、快、散”的段落结构,每个段落都相对独立,而又统一与作品的宏观布局之中,非常符合老百姓对川剧戏曲音乐的认知与审美。
再次,这部作品既然成为胡琴套曲,在演奏乐器上自然不会拘泥于一种胡琴。作者在整部套曲中,通过自己对于不同胡琴特性的理解,根据不同段落的意境,对演奏的乐器进行了大胆的编排、演奏,这样的举动在当今的胡琴作品中也是鲜有使用的。另外作者在对胡琴左右手演奏技法上也有一些特殊要求,下面将着重进行介绍。
《西蜀琴韵》演奏手法特点综述
(一)偏音的音高把控
五声音阶是我国自古沿袭下来的汉族音律,也是在中国传统音乐创作中运用最为广泛的音列。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入清角与变宫所构成的七声音阶,在表象上与西洋大小调体系的音阶记谱完全一样,但由于使用的频率相对宫、商、角、徵、羽五音较少,且位置往往以经过音、辅助音以及特征音方式呈现,故而称之为偏音。由于清角音的韵味往往在情感气质上有伤感、晦暗、悲愁以及哀怨之感,所以梆子剧种中,如秦腔等一些地方剧种把包含了清角的音,称之为“苦音”。而川剧音乐中所强调的“苦皮”,则是强调清角音而忽略角音。另外在实时演奏川剧音乐中,清角音较十二平均律略高,变宫音略低。
(二)用胡琴把控川剧声腔的行腔与润腔
胡琴演奏中左右手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右手运弓擦弦是胡琴的主要发声手段,这就好比戏曲演员发声演唱,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戏曲术语将右手运弓称为“行腔”。另一方面,胡琴演奏者的左手触弦,除了可以改变音高之外,更多的技法则是提升对声音的美化,这又与戏曲演员演唱过程中的各种润腔手段相仿,因此我们又可将胡琴的左手演奏手法称为“润腔”。
就戏曲音乐行腔手段来看,它的演奏风格与非戏曲音乐在手法上是不同的。胡琴在实时演奏戏曲音乐过程中,为了模仿在行腔过程中跌宕起伏的唱腔,会存在许多的变体演奏手法。右手的运弓往往会配合左手的润腔,在弓速和强弱上做出非常夸张的变化。
滑音与揉弦是构成左手润腔的两大代表性技法。滑音的种类颇多,风格迥异,哪怕是同种类风格的滑音,其间也有着许多细微的区别。从四川地理位置上看,属西南地区,音乐风格理应归于南派。但由于清末“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原因,使四川成为一个多种文化交融发展的地区。川剧的五大声腔分别有着不同的起源:高腔是由弋阳腔演变而来;昆曲源于江苏;胡琴源于皮黄腔;弹戏的鼻祖是梆子戏;灯调源于四川的小调音调,在川北地区的灯调还具有一定的陕北风味。这些不同地域的唱腔,在行腔和润腔手法上都各有特点。因此准确说来,不同的声腔都有不同的行腔、润腔手法。
《西蜀琴韵》中昆曲、高腔、胡琴的演奏手法与各声腔的发源地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因此这里不再赘述。但川剧音乐中有关弹戏以及灯调这两种声腔,有必要稍作解释。
川剧声腔的弹戏应属于“梆子腔系”[1],因此又称之为“川梆子”。提及梆子戏,众所周知,它的主奏乐器是板胡,而在川剧弹戏中,使用的主奏乐器是“盖板子”。盖板子是四川独有的拉弦乐器,它的面板材质的使用与板胡大同小异,但传统的盖板子使用的琴弦以及演奏方式却与板胡大相径庭。盖板子的琴弦在早些年使用的是牛筋线,后逐渐改成了钢丝弦。但由于使用的琴弦非常粗,且非常割手,因此在左手按弦时必须戴上金属指套。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左手按弦问题:其一,戴上指套后,指稍关节不可完全弯曲,触弦部位不再是指尖,而是在指腹与指稍关节的中间地带;其二,金属指套通常只佩戴于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上,并进行演奏;其三,揉弦方式也受到极大限制,几乎只有滑揉这一种揉弦手法。右手持弓运弓上,因其使用的弓杆通常是由很粗很厚的楠竹制成,持弓时手掌力量要足,运弓更是需要非常规的大力度的演奏。胡琴演奏的常规运弓法是与地面几乎平行、水平运动的。而在演奏盖板子时,为了追求力度,持琴要更为向前倾斜,运弓时需首先向下压住琴弦,再配以大幅度的运弓动作,使之发出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因此在川剧界对演奏盖板子会用到“杀”(拟声词)这样的行业术语。在定调上,盖板子的演奏一般只使用弦来进行演奏。
灯调往往是比较诙谐的音乐情绪,它的主奏乐器是“川二胡”。川二胡的琴筒用竹子制成,蒙蛇皮,琴筒短而略大,因此得名“胖筒筒”。以前戏班子演戏都是没有扩音设备的,为了演出的需要,它的音响大、高亢,有“粗喉咙”的别称。川二胡的传统持琴方式类似于京二胡,即放在左腿胯关节与膝关节盖中间,少有下把演奏,常用于与京胡、盖板子等其他拉弦乐器进行“老配少”。运弓手法与盖板子、京胡相当。揉弦手法也与京胡相当,滑中带揉。跟腔是川二胡在演奏灯调时的主要任务,它的滑音使用非常频繁,往往会根据演员的唱腔,做出非常夸张的大滑音。
川剧音乐风格在《西蜀琴韵》各乐章中的具体把控
《西蜀琴韵》的音乐风格、结构、演奏手法的在前文有了初步的概述,现就各个乐章的具体特点进行剖析,并结合前文所提到的行、润腔手法诠释如何演绎川剧风格的作品。
(一)《高腔韵》
《西蜀琴韵》的第一乐章取名为《高腔韵》,可见本乐章的主要创作素材取自于川剧五大声腔中的高腔。据相关资料考证,川剧高腔曲牌数目多达300多支[2],高腔剧目约占川剧剧目比例的70%①,由此可见高腔在川剧音乐中的重要地位。而川剧也是中国所有戏曲中将高腔这一声腔发展到极致的剧种,因此但凡有研究过川剧的当代作曲家都会对川剧高腔情有独钟。
此乐章的段落划分为:引子、散板、极慢板、慢板、散板、快板6个部分。情绪以细腻内在的情感表达为主。引子部分的音乐为一个起承转合的四乐句段落,由乐队协奏完成。前两句为模进关系,第三句无论在音乐材料或是节奏形态上都形成了鲜明的“破”句,合句第一次出现了前文提到的用《端正好》与《二郎神》揉捏写成的核心主题音调。
独奏二胡在引子段落渐弱的趋势中引出,进入一个较自由的散板段落。此段落的音乐素材取自川剧高腔的曲牌《红衲袄》。此段落共由6个乐句组成,前4句采用了起承转合的手法构成第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旋律结构上,此乐段的乐句内部结构为2+3+3+2,属非方整性乐段,并呈现出橄榄状,这样的乐段构成比较少见。第五句为戏曲音乐中常见的慢起渐快再渐慢的句式,旋律是用五声音阶由低到高写作而成,属非呈示性连接段落写法,并在结构上做了相应的扩充,从而使音乐在此段落中形成高点。最后一句落音羽音,乐队第二次协奏出核心主题音调。整个散板段落的音乐形象高亢,但又饱含深情,可谓“外刚内柔”。
一乐章上板的主题是一个吸收了高腔《端正好》曲牌行腔风格的原创主题。此段落速度为每分钟四十四拍的极慢板。整个音乐形象婉转而内敛,属人物内心刻画音乐段落。从曲式结构上看,此段落为一个无再现的单三部曲式。段落的设计也非常独特,其段落图示为:a+a1+b+b1+c+c1+d+d1。从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上采用了中国传统民间音乐连续的上下句的创作手法,使音乐呈现类似“对联”的结构。
第一乐章第四段音乐的速度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加快,所表现的是诙谐中略带一丝得意的音乐形象。作者在创作素材上采用的是高腔中徵调式的《青纳袄》和《红纳袄》的结合体。
随后的散板音乐与一段慢起渐快再渐慢的音乐。这个段落体现出非呈示化的特征,属于连接性质的段落。但从音乐形象看,旋律外柔内刚,逐步向紧张的音乐气氛过渡,与之前的音乐形成明显的转折,音乐呈现出一种奋发且不安于现状的意境。
之后进入到高腔韵的最后一个段落,也是本乐章唯一的快板。旋律承接了前面连接段情绪,由极具紧张气氛的连续十六分音符过渡句引入。音乐节奏素材取自川剧的套打音乐曲牌《单锤》 《[两锤》 《水波浪》。川剧锣鼓与乐队音乐同步,在戏曲中多用于武打场面,或者气氛热闹的场面。音乐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周期性结构的四句体,第二部分作者用节拍进行了对比,并在尾部做了扩展,第三次呈示了核心主题音调,并作为此乐章的收尾。
宏观上看,整个《高腔韵》的乐章情绪多变,反差强烈,因此在行腔与润腔上的手法需体现出多样性。首先,右手的运弓在呈示化主题段落应注意连贯性,且富有歌唱性,运弓应当平稳。起伏的铺垫与过渡应统一在音质饱满圆润的恒常力演奏方式之中。而在引子与个别连接句(段)中,由于戏曲音乐的风格需要,在演奏的弓法运用上则需要“突变”的手法。
其次左手的润腔中,滑音部分的多变性主要体现在:根据不同的段落需求,滑音的速度、幅度、手法都不相同。川剧声腔中,高腔是高亢的,它的帮腔非常丰富,拖腔非常舒展、优美,这就和北方戏曲有着天壤之别,故在滑音的使用上,川剧风格作品的滑音需做到粘连、柔和,且需要多用垫指滑音这项滑音技术,形成“刚中有柔,柔中带刚,刚柔相济,不瘟不火”的态势。揉弦需要注意的是:四种揉弦——滚、压、滑、吟均有使用,其嫁接的揉弦方式如:“滚压”“滚吟”的揉弦手法最为常见。戏曲拖腔的润腔手段非常多变,故“迟到”的各种揉弦手法使用非常频繁。(二)《胡琴唱》
《西蜀琴韵》的第二乐章之所以取名为胡琴唱,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本乐章的音乐唱腔依次用到了昆曲、灯调、皮簧戏的唱腔素材。其二,在演奏乐器上,作者有意安排使用了高胡与京胡这两种胡琴来进行演奏。用高胡来模仿昆曲中的柔美和粘长,用京胡来诠释川剧中的胡琴唱腔。胡琴戏本来就是特指的皮黄腔,用京胡来进行演奏是再合适不过了。
本乐章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昆曲唱腔的段落,音乐结构是有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结构,音乐由笛子声部吹出昆《[南清宫》曲牌中架桥音乐的素材,在主奏高胡徐缓的主题呈示下,音乐营造出比较优美,犹如花前月下般甜美的音乐形象。
作者在第一部分的音乐结束后,插入了一个具有起承转合的连接段落,素材来源于灯调。而后音乐进入到了用京胡演奏的胡琴戏段落。此段落属皮簧腔中的西皮音乐,音乐舒缓,曲式结构为没有再现的单三部曲式。
在这个乐章的演奏中,因为演奏乐器、音乐类别均不相同,故而演奏手法上有着比较大的出入。昆曲是典型的南派戏曲音乐,它的特点是细腻温婉,而皮簧腔虽吸收了昆曲的许多元素,但又因嫁接了其他的音乐元素,音乐风格已经北方化。所以,在行腔的右手运弓上,前半部分音乐要演奏得连贯绵长,后半部分音乐在运弓手法上弓速相对较快,换弓、换弦干净利落,不可拖泥带水。在左手的润腔手法上,昆曲音乐因旋律优美、婉转,并在演唱习惯上是以吟唱为主,讲求声音的细腻、圆润,所以,换把的抹音要圆滑自然,过程稍长,揉弦以吟揉为主,滚揉为辅,以符合吟唱的方式。反之,在演奏皮簧音乐时,演奏手段应与之前大相径庭。由于传统京胡的演奏中少有用到换把技术,一般直接采用“老少配”的八度移位手法,或定把使用开放指法来完成个别的高音演奏。因定把伸指的范围有限,且北方音乐性格的特性需求,所以滑音的滑动速度较昆曲音乐干脆、直接,滑行距离短而重。揉弦方面,京胡多用滑揉,乃至滑揉过渡到滚、吟揉的技术来完成左手的润腔。
(二)《弹戏闹》
川剧的弹戏主要是由山西与陕西的梆子戏演变而成。《西蜀琴韵》的最后一个乐章以川剧音乐中的梆子戏素材为创作动机,表达了高兴、热闹的音乐情绪,《弹戏闹》因此而得名。前文提到弹戏的主奏乐器是盖板子,但在四川,会演奏盖板子的人不多,为了乐曲的流传,作者没有设计使用盖板子来演奏此乐章,而是采用善于演奏梆子戏的板胡作为了独奏乐器,创作素材运用了川剧弹戏中“甜皮”与“苦皮”的融合。整个乐章的音乐呈多段体,上下句结构与起承转合结构交替出现,加之“句句双”的传统作曲技法,使独奏板胡与乐队间的呼应此起彼伏。作者在创作延伸、加花变奏之余,经常会无缝穿插弹戏音乐的素材片段,使音乐在发展中能牢牢把控其风格的统一性与音乐材料的集中性。最后的套打音乐取材于第一乐章尾部的素材,进行了变化重复,整部作品最终再次落足于“核心主题音调”,使音乐前后呼应,加深了听众对该曲的印象。
在演奏手法上,梆子戏是北派戏曲的代表曲种之一,所以行腔要刚劲有力,运弓以干净利落为主,其中的慢板因为运用了苦皮的音调。在北派的梆子戏中,有苦音的段落,为了表达人物内心的苦闷,行腔都比较婉转,因此,在演奏苦皮时,运弓流动通畅,音乐的起伏与之前的高腔有所区别,更多的注重大线条的美感。润腔的技术中,滑音来去比较直接,虽然在慢板也有个别委婉的滑动手法,但仍应保持北方戏曲音乐一贯的滑音风格。只是可能因为文化的融合,在演奏川剧弹戏音乐时,更需强调头音滑法的轻重缓急。在揉弦的频率上,此段音乐总体来说稍快,幅度与指尖的力度也应偏大。
另外,在乐曲尾部的高潮部分,作者在写作中运用独奏板胡与乐队一问一答的方式,旋律线条经常采用六度、七度、八度跳进后迅速级进回落的手法。
谱例:

笔者在对弹戏进行研习时,对盖板子的演奏做了一定的了解。原则上为了追求音乐的连贯性,“大肚子运弓”的现象应该避免,但在演奏弹戏时确有例外。如谱例中第一、三、五、七小节带附点的3音用传统民间手法进行演奏时,就应采用轻出弓、鼓肚子的手法,随后的音轻收尾,形成枣核形态。但是,这个枣核形态并非循序渐进而成,反而有点类似于抽风的音响效果。虽然作者最终是用板胡进行演奏,但是为了还原川剧弹戏的音乐风格,模仿盖板子的演奏技法无疑是最为科学,也是最为准确地表达方式,同时也是最能贴合本乐章标题中“闹”子的音乐性格与形象。
结 语
《西蜀琴韵》在贺超波先生的创作与演绎下,无疑是成功的蜀派胡琴套曲的代表作之一。笔者在撰写本文的同时,也有幸请教贺超波先生本人,跟随他潜心研习川剧音乐风格在胡琴上的演奏手法,并加以凝练与总结。有以下几点感想: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胡琴的表现力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不仅能胜任曲牌唱段中,对戏曲演员的行腔与润腔的跟腔与模仿。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充分发挥其器乐的特性,满足当代作曲家的“异想天开”,以及对风格作品的继承与延伸。由此可见,川剧艺术与胡琴艺术,两者互相嫁接是完全可行的。
其次,四川的胡琴作品在目前全国少为人知,其实数量并不少,而川剧风格的胡琴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抛开《西蜀琴韵》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谈,就其社会价值是不容小觑的:它既是对川剧音乐风格的传承,又能为提炼蜀派二胡艺术的演奏技法添砖加瓦,更是为胡琴艺术与川剧音乐艺术融合提供了可行依据。
再次,作为音乐艺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胡琴艺术与川剧音乐艺术之间的交叉深入,更能促进两种学科的共同发展。学科需要发展,学科之间需要碰撞,文化更需要升华。《西蜀琴韵》的诞生为创作者、演奏者以及受众者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延展,这为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蜀派音乐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笔者作为一名四川本土的音乐工作者、胡琴艺术传道者,在研习该曲过程中,深刻体会到“隔行如隔山”的无奈:但凡想要体会川剧音乐风格作品的精髓,如不能在川剧团里摸爬滚打多年,怕是很难体味之。保留、延伸川剧这一特色音乐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在为传承四川二胡特色音乐的同时,又能为四川二胡事业尽绵薄之力。
[1]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
[2]彭潮溢.川剧高腔曲牌的分类[J].川剧艺术研究,1988.
四川音乐学院院级青年项目《论川剧音乐风格在胡琴演奏中的体现——以胡琴套曲<西蜀琴韵>为例》研究成果(CY2014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