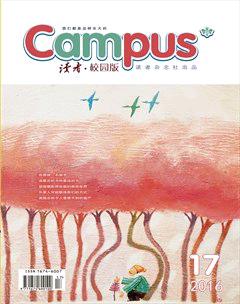毕业是那些想见的人,再也没有那么容易见到了
卢思浩
1
上小学时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是很不好。因为我小时候是大舌头,做完矫正手术已经上二年级了。别人因为普通话讲得好,开始收到老师奖励的小红花,而我还在拼音字母表上挣扎。
班长是个好看的姑娘,小时候就已经是个标准的美人了,扎着两个马尾辫,个子又比同龄的小男孩高。有一天语文老师苦口婆心地教我拼音时,班长正好在旁边。我总读不好拼音,老师开始叹气,班长说:“让我来教他吧。”
于是,我每天中午都有和班长单独相处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每天翘首以盼午休,下课了就跟着班长到一个空教室,一个字一个字地练发音。很快我就学会了拼音,很快我也收到了一朵小红花。
我一路小跑,跑到班长面前,把小红花给她。
她抬头笑着对我说:“谢谢!”
我整个小学的记忆,细细想来居然只记得这一幕。只有这一幕,我可以肯定是真实发生过的,因为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她的表情。
想想那时真年少,心里的情绪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可大概也多多少少莫名地对班长多了些关注,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后来小学毕业,我还不明白什么叫难过,她却哭得很伤心。我们彼此留下的联系方式,还是家里的固定电话。
再后来,我们的联系变少了,写过两次信,就再也没了后续。
今年年初,我当了主播,需要再次正视我的普通话。有一天看着视频矫正口型,突然想起那时她也是这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我的。
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重新练习普通话,我大概再也不会想起我小时候的那个班长了。
2
大一时我刚到堪培拉,人生地不熟,好在程序都很简单,顺顺利利入学,顺顺利利上课。
很多人不知道我学的是金融,那时我总是早早到教室,抢第一排的位置。
后来人越来越多,我抢占的位置渐渐变到第二排、第三排,最后我只能抢到第四排的位置了。
可就在我只能坐第四排的那天,身边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你旁边的这个座位有人坐吗?”
后来她就成了我在大学时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因为大家都是留学生,总觉得很聊得来。
后来我们发展成4人小团体,顺理成章地一起做小组作业,期末时一起去图书馆跟课题死磕到底。总是半夜或者凌晨走出图书馆,我们都累得不行,她却最有精神,总拉着我们吃完夜宵再回宿舍。
偶尔我们需要集体熬通宵,写完作业我们抬头互相看时,都大笑起来,毕竟每个人都憔悴得不成人形。这样重要的时刻,她就会拉着我们一起拍照。当我们其中某个人过生日时,她就会把那个人的丑照印出来,做成红包的样子送给他。
毕业那天,我妈漂洋过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却没有什么真实感。毕业典礼之后,我带着我妈逛校园,给她一一介绍:“这是我上课的地方,这条小路我每天都会走,这是图书馆……”那时我已经确定要回国,才突然意识到,这些我每天走的路,可能再也不会走了。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去了墨尔本,其实离堪培拉不算很远,我却真的再也没有回去过。
至于她,毕业之后选择了去英国,我们偶尔会联系。
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她正在唱歌呢,突然想起了以前我们一起唱歌的日子。她说:“我们第一次唱歌是在几年前?”我在电话另一头说:“6年了吧,有6年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啊,都6年了。”
而我们居然也有4年多没见了。
3
你喜欢的学长,或许你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上一句话,他就毕业了;一直照顾你的舍友,你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你们就告别了。我毕业时压根儿就没有明白毕业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不过就是去一座陌生的城市生活,再面临所谓成人世界里的那些糟糕的规则,每天过得很辛苦。
我现在才明白,毕业到底是什么。
毕业就是那些想见的人,再也没有那么容易见到了。
我上初中时一起回家的小伙伴,我如今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上高中时喜欢的姑娘,我也失去了她的消息。还有在大学时意气风发、说要实现梦想的人们啊,现在都在哪儿呢?
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记住一辈子的事情,不过几年时间,我竟然忘记了故事里的那些人到底长什么样。
记忆真是不可靠啊!
我们迟早会面临离别,有些我们无法避免,有些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发自内心地想要留住一些人,却还是任由他们四散天涯;可我始终坚信每次相遇都有意义,觉得每次陪伴都很珍贵。
就算我们天各一方,就算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不同,我们还是需要见一下这些人。哪怕一年两次也好,一年一次也好,因为他们都是陪我们走过青春的人。
还好,在不断地失去中,我终于学会了珍惜。
我弄丢过很多人,但我都用心珍惜过。就算如今只是偶尔联系,我也知道他们过得很好。这样就好,我就很开心了。我还有很多留在身边的人,就算我们很少见面,但总还是拼命聚在一起,谢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
我最怕有人突然离开自己的生活了,那时我才发现,当时想说的话一句也没说。
就算毕业,就算分道扬镳,就算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就算我们再见面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也不轻易说“再见”,因为我们都陪伴了彼此这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