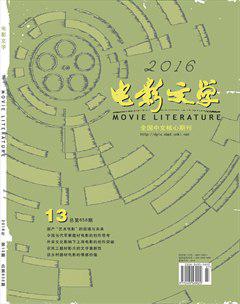《菊豆》:封建礼教与火海中的悲剧礼赞
[摘 要]张艺谋导演的《菊豆》以中国清末中国农村某小镇染坊为背景,以“叔婶”“父子”、婚姻等关系的错综复杂和混淆为故事梗概,诠释了封建礼教的根深蒂固和残忍,再现了在封建礼教苦海中挣扎又葬身火海的菊豆夫妇的爱恨情仇,是一曲旧时代农民的悲剧礼赞。从中西文化背景来解读影片的深刻内涵,才能理解有颠覆性、触及文化根基的真谛。电影的视觉语言和独特音乐都深化了主题,为中西电影思想艺术的开发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张艺谋;《菊豆》;悲剧; 形象; 音乐
《菊豆》是张艺谋导演继《红高粱》之后推出的一部新电影,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中的一匹黑马。影片上映后曾饱受非议,不同观众群体的情感态度也截然不同。香港华人大多抱有沉重的思想感情,而许多内地观众是持批判意见的。不过,一些西方电影评论家是在大多数观众持赞赏态度的形势下批判《菊豆》富于性挑逗的。无疑,种种评论加大了这部影片的争议性,对于电影本身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分析电影的内容和视觉语言,《菊豆》并无明显的道德导向与谴责,主人公菊豆与杨天青,最终还是以悲剧的命运结局,天青最终被天白杀死,使所谓对“淫”以及“不孝”的反对者感觉“秩序”得到了延续,倾斜的心理天平似乎平衡了。
该影片在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时候,张艺谋导演曾经毫不隐讳地表示,那些认为影片有问题者,主要是针对影片当中对性场面处理的“阴暗色调”现象,而并不是因为影片当中出现的性场面。不容置辩,《菊豆》所展示的色情内容并非一种简单的自恋:故事情节开始时,菊豆有意把胴体让“侄子”偷窥。而事实上,影片中对菊豆肮脏、满是伤痕的身体表现,结合与画面相伴刻意呈现的音乐效果,无论是天青还是观众都无法得到视觉上的愉悦。相反,过程的体验并不美好。这些挑逗行为,表现了菊豆对虐待她的杨金山以及家长制的无声抗议。
《菊豆》公开地展示了一种由情感相通到性相爱的关系。因此,若要引领观众的视听,把握中国人的性观念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的礼节规范是围绕“忠、贞、孝”观念形成的一种伦理体系,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奠基石。
《菊豆》之所以在西方观众群体中能得到赞赏与肯定,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西方文艺批评中对“淫”与“不孝”的矛盾并没有中国这么沉重,而“淫”与“不孝”却刚好是《菊豆》情节与立意的深化。如果想弄清电影众说纷纭的辩论中的所以然,就必须理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理解中国的宗法制度的真谛。《菊豆》饱受争议的原因,并非是它本身存在某种政治隐喻,也并非情节与内涵违背了传统,而是因为《菊豆》中显现出来的中国特征: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的锁链,死死地缠绕着一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那些特殊手段的运用,是中国人对传统信仰、理念和墨守成规习俗的大胆挑战与归宿。
一、神话历史演绎与变迁
人性是个广阔无际又内涵深刻的话题,包蕴了无数美好与丑恶,也引来了无数赞扬与抨击。“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传统观念赋予人们的烂熟于心的口头语。但是《菊豆》却对这种人人必须遵从的人性进行了批判与反抗。可能很多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挑战,因此,一些所谓的正义之士自然而然地对其嗤之以鼻。
《菊豆》改编自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我们剖析一下小说的背景与内涵,或许就能领悟许多深层次的文化与思想。
远古时期对道德乱伦是没有明确意识的。伏羲与女娲本是兄妹关系,传说是他们的结合孕育了宇宙,获得了子嗣:人类的诞生。电影《菊豆》中,菊豆与天青虽然也生育了天白,但天青不是菊豆的血缘兄弟,天青也并非金山的亲儿子。小说把菊豆和天青的“婚姻”与神祇的结合相比,本身就暗示着这爱情是合乎道德与天经地义的。伏羲与女娲式的婚姻,不受道德礼法的约束。而在《菊豆》中,菊豆与天青生活于遵循封建伦理的社会环境中,才被规范为罪恶行为。
清规戒律是时代的产物,附有不同的时空标签,也与权力、地位、目的、手段相挂钩。追溯历史,不难发现:秦始皇的曾祖母宣太后芈月,在维护政权平息战乱中,就有很多公开的、从不隐瞒的风流韵事,除了正牌丈夫秦惠文王外,还和深爱她的义渠君交往30年左右并生两子,秦国强大后又诱惑其杀之。试想:在宣太后执政时代,她何以有罪?唐朝时期的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媚娘,和唐高宗李治结为夫妻后,生子、执政,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地位显赫、政绩卓绝的女皇。有人敢谴责吗?父权、夫权、神权,岂不退避三舍?可知,权力与道德之间,前者重于后者。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就是以自然与人为的矛盾以及制度与人类实际之间的矛盾进行辩证的讨论。制度的建立是以控制人的行为为目的,但在权力面前,又反被人所控制。
《菊豆》中,影片对制度与人的认知矛盾是通过对染布活动的详细拍摄来表现的。在菊豆所处的时代,染布在我国大多数农村都很常见,人们将染布机器组装完整,通过将染料加到布上的工作行为,染布活动才能得以开展。《菊豆》以特定的镜头对染布机器的各个部分进行了细致的展现,以全景镜头对染布机器每个部件的严丝合缝与按部就班、周而复始的工作过程进行了细致表现。与此同时,结合高度风格化的逆光镜头,将影片打造出一种沉重与压抑的感受。
机器虽然是没有感情的物体,但是却与菊豆所处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形象有着辩证的关系。在杨金山的染坊中,人与牲畜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生产的工具。电影中将巨型染布机器置于前景,而将从事染布工作的人们以微弱渺小的形象进行展现,表现出人们的活动都是围绕着机器的运转而进行的。画面一转,染坊中挂着整整齐齐染好的布匹,则象征了结构和秩序。那些挂着的白色条幅,犹如葬礼上的幡,是死亡的象征。
尽管机器的体系庞大,依然不能永远遏制生命的迸发。《菊豆》中有关菊豆的镜头以逆光仰拍的方式拍摄,对菊豆年龄阶段应有的青春朝气进行了生动表现。菊豆动人的自然美和她所处环境的非自然性形成强烈的反差,印证了她的不幸婚姻就是这一环境的缩影。菊豆年轻、漂亮,杨天青和她相互吸引。菊豆对压迫与虐待她的杨金山厌恶、憎恨是必然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纲常之下,菊豆的感情为社会所不容,她与杨天青的结合被定位于“淫”,万恶中排第一,是不合礼制的。其实,《菊豆》中并没有对道德进行过多的评判,对人与自然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同样以象征的方式进行了表现。菊豆生下天青的孩子后,村里长者为孩子取名“天白”,以天字命名,使天青与天白陷入了既是父子又是兄弟的矛盾之中。这两个名字合成后就是“天青白”,其含义是清洁无瑕。而“天”字的应用,则让人有意识地联想到了原著《伏羲伏羲》中的神祇,或许是导演的匠心独具,也是影片的画龙点睛之笔。
二、孝道:悲剧的必然
《菊豆》辛辣地批判了命名传统,因为命名颠覆了“父与子”的关系,把“父亲”规范到了“哥哥”的行列,“儿子”变成了“弟弟”,也规定了二者的权利和规范。杨金山中风后,知道了真相,他失去了父亲的地位;天白的孝道,又归还了杨金山“父亲”的地位。电影通过命名与天白杀掉天青的逆行,推动着叙事发展。而影片最后烈焰冲天,菊豆悲愤交加、义无反顾自焚的镜头,与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着异曲同工的归宿。
《菊豆》一开始分别用简单的镜头对菊豆与天青的性格进行了交代。菊豆与天青都是年轻、温顺的被压迫者,有各自痛苦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结合是简单的,也是人类自然的、本能的表现。杨金山对菊豆的性虐待使其性关系也呈现公开的状态。天青知道了叔叔滥施淫威时,对菊豆有深深的同情。他们有了染布坊那场热恋后,杨金山中风了。他们本以为水到渠成,已经拥有了追求幸福的可能。因此,对杨金山的监督公开进行反抗,将杨金山置于被管制地位。由于杨金山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所以只能生活在恼怒、仇恨的情绪之中,忍受那对恋人肆无忌惮的调情、愉悦、放荡的行为。这时,丈夫、妻子、儿子的关系又被颠倒过来了。菊豆和天青以夫妻身份相处,而金山却必须让他们像照顾儿子一样给他喂饭、洗澡、穿衣。
但是,杨金山不甘被摆布、受侮辱、戴“绿帽”,他试图杀死天白以宣泄心中的怨恨。而杨天青则为孝道伦理所束缚,认为他与菊豆的关系是大逆不道的,不敢反抗。与此同时,在那个畸形家庭中成长和受教育的天白也就成了他们身边的定时炸弹。杨金山利用天白的天真无邪,报复他的父母。他在天白面前宣布自己是父亲,菊豆是母亲,天青是哥哥。重新确定了原来的丈夫、妻子、儿子的关系,恢复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权和无权的关系。在这种象征关系之下,菊豆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折磨,任凭悲剧发生。在杨天青的意识里,对杨金山尽孝道义不容辞。菊豆谴责他懦弱时,他居然打了她耳光。正是天青的暴力让菊豆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循环式的压迫中,她永远都是牺牲品。故事最残忍的是杨金山为了报复这对恋人,要杀死他们的孩子天白,结果自己溺水身亡;最可悲的是天白居然成为杨金山的帮凶,让亲生父亲成了自己的刀下鬼。
电影的悲剧还通过那个象征性的葬礼镜头进行了展示:天白高高地坐在棺材上,成为杨金山的“代理人”,构成了一种再生仪式。菊豆与杨天青作为杨金山的遗孀和长子,需要连滚带爬49次阻挠送葬队伍以示孝道。无疑,天白的存在就是世俗社会对人们的报复。从整部电影复杂人物关系以及前后对应的剧情结构来看,“逆弑父情结”与我国一直延续的以孝道为主流的传统相符。电影用反复的仰角特写镜头,把杨金山的棺材塑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而菊豆与天青则必须屈于权力之下。菊豆无疑是悲惨的,三个男人(丈夫、情人、儿子)轮流折磨她的身心。这三个男人分别在宗法制度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剥夺了她的自由与生命。由此可知,女人如果无法摆脱权力循环的轨道,将注定永远是悲惨的结局。
三、视觉形象和音乐效果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向来以表现英雄主义为倾向,比如《红高粱》《英雄》《十面埋伏》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菊豆》却表现了不同时空中人的性格被摧残、被奴役,深层昭示出软弱对人们精神与肉体的杀戮,是中国的希腊悲剧再现,进而让人们从反面思索悲剧的根源,思考怎样活着的原理。
(一)视觉形象
影片中的人物身份有多种:杨金山是菊豆的丈夫和名义丈夫;菊豆是杨天青的名义婶子和妻子;杨天青是杨天白的父亲和名义兄弟。《菊豆》就是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构建了俄狄浦斯情结(恋母和弑父)剧情。
杨天青是个悲剧人物,他名义上是杨金山的侄子,实则是杨金山的长工,他只有干活的权利,只有偷看婶子洗澡满足欲望的极限;他听到婶子被杨金山性虐待发出惨叫声音的时候,拿着斧子在楼梯上砍了一下,被杨金山质问时吓得连气都不敢大喘;为杨金山送葬,他和菊豆哭天喊地拦棺材,他儿子却坐在棺材上充当父亲的“父亲”;菊豆激怒他,让他杀了杨金山,他为孝道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还谴责打骂菊豆;他不敢带菊豆逃离染布坊,最终被儿子所杀。他的忍耐、软弱,让他儿子把他推入坟墓,他又把自己心爱的人拽进坟墓。与其怜悯,不如说痛恨。所以,悲剧成为必然。
菊豆具有反抗精神,未被命运压垮,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却仍死在了封建礼教的屠刀下、宗法制度的残忍中。她的善良(不忍离开丈夫和儿子)不足以让她挣脱杨金山为她绑定的锁链,她的悲剧是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存在酿成的;是那三个男人剥夺了她爱和被爱的权利酿成的。无形的剑,有形的刀,多么凶残!
(二)音乐效果
《菊豆》的背景音乐都是以传统乐器埙的声音进行呈现。整部影片伴随着埙的声音,后加上童声的演唱,缓缓表现故事情节,带给观众情绪的感染。影片中,菊豆和杨天青在杨金山瘫痪后拜堂时候的音乐比较欢快悠扬,悦耳动听,表达了两人两情相悦的心情;而在菊豆病重阶段的音乐则舒缓、低沉,对菊豆与天青两人生活的无奈进行了生动表现,同时,缓慢的音乐节奏也表达了主人公无声的控诉。影片最后是儿童的演唱,激昂,犹如行军曲,是个比较完美的收场。埙的应用,时而缥缈,时而低徊,是线性的白描手法,讲述了封建统治下一个小乡镇的悲剧爱情和伦理道德碰撞的火花。
[参考文献]
[1]宫瑱.张艺谋电影创作的两次转型[J].剧影月报,2015(05).
[2]秦廷斌.电影《菊豆》的民俗视点[J].大众文艺,2010(03).
[3]徐仲佳.刘心武论——爱情、性描写的变迁[J].文艺争鸣,2008(10).
[作者简介]殷翰(1984— ),女,河南新乡人,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专业2012级在读博士研究生,河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音乐教育与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