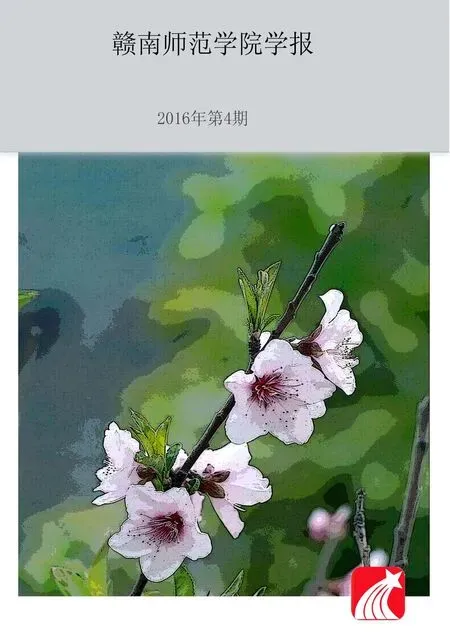“她们”的长征
——论长征中的女红军*
谈思嘉,高晓林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她们”的长征
——论长征中的女红军*
谈思嘉,高晓林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女性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主体。女红军分布在四大主力部队中。女红军长征体现她们追求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两大奋斗目标,肩负着前线作战和后勤保障的两项任务,克服了斗争环境和女性生理的两大挑战。虽然女红军数量不多,但女红军长征彰显了女性革命和革命女性的两大历史意义。
女性;长征;历史意义
常言道:战争让女性走开。因为女性往往被认为难以承受战争所造成的苦难和动荡。然回顾历史,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战争从未让女性走开,她们有的饱受战争蹂躏和摧残,还有的则在战火和硝烟中抒写巾帼本色。在中国工农红军六万五千里长征*一般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同起来,其实“两万五千里”只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里程数,而红军长征是“3 + 1”的长征,还包括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将四支红军的长征路累计相加,约为6.5万多里,故采用“六万五千里长征”的说法。中就涌现出了一批女红军战士,她们参与革命战争的进程,影响着革命战争的走向,在革命战争中扮演着耐人寻味的角色,为革命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该群体处于重要战役、会议和主要领导人等主流叙述之外,故对长征中女红军的研究相对匮乏,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和女红军的回忆录,发掘“她们”与中国革命的交集,勾画出一段属于“她们”的长征史。
一、女红军数量与分布概况
为了全面地、完整地叙述女红军的历史,有必要对女红军的基本情况做一交代,以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女红军”这一概念是指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与土地革命战争,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并且为红军组织所承认的女性,包括长征时期正式参军的女战士和担任重要职务的女同志,同时也包括随大部队出征的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其中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或中央领导人夫人的女同志,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加入红军队伍,参加革命时间较早,长征期间随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出征。而更多的女红军则是在革命根据地扩展时期,接受革命思想而加入红军的。
在红军长征的四大主力部队中,女红军的人数和分布情况并非完全一致。中央红军有贺子珍、邓颖超、蔡畅、李坚真等30名女红军参加长征。[1]除了康克清、蔡畅、危拱之、刘英、周越华、李建华编在各中央机关外,其余被编入干部休养连妇女班。[2]最终,甘棠、李桂英、谢小梅、王泉媛、吴仲莲、吴富莲6人因另有革命任务和安排离开长征队伍,其余24人自始至终跟随部队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中女红军约有25名,分散在机关、宣传、医疗卫生、后勤等单位,没有统一的编制,随军征战,也大都随队完成长征。红四方面军中女战士“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担负的任务也最繁重,牺牲也最大”[3],分布在妇女独立师及下辖两个团,共2000余人( 1936年后缩编为妇女独立团) ;妇女工兵营及下辖3个连,近500人;医院和洗衣队也各有女红军数百人。因途中红四方面军女红军常有扩编和缩编,具体数字已无法确切统计,大约有3 000余人。[4]至长征结束后(包括西路军西征),红四方面军只剩下女红军300余人。此外,红二十五军中原本7名护士要被解散,在她们强烈要求下,才得以随军长征。最终7人中只有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延安永坪镇,曾继兰、曹宗凯二人则牺牲在长征路上。据此,红军长征出发时,四大主力部队共有约3 062名女红军参与长征,完成长征的女红军约354人,其余则大都在途中牺牲或离队。
表1长征前后女红军人数与红军总人数表①参考李安葆、刘录开编著的《女红军长征记》和郑广瑾《长征事典》中相关数据制成。
长征部队长征出发时女红军人数/红军总人数长征后女红军人数/红军总人数中央红军30/约8680024/约7000红二方面军约25/约14300约25/约13300红四方面军约3000/约80000300/约33000红二十五军7/约29805/约3400总计约3062/约184080约354/约56700
由此可见,无论是长征出发前,还是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女红军数量在工农红军长征的总人数中仅仅占了极其微小的比例。然而在这幅红色历史长卷中,女红军们为了人民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两大奋斗目标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在面临残酷的斗争环境和女性生理的双面束缚下,肩负起了前线作战和后勤保障两项革命重轭,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史谱写了壮丽篇章。因而,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有必要重新审视长征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女红军群体,缅怀她们英勇奋战的光辉事迹,追溯她们在与所有红军们共同创造六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雄伟的壮举”中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二、追求两大奋斗目标: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
杨·海伦在《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一书中提及,她在采访女红军的时候,问及“你为什么要入党和参军”时,她们都给出了精彩纷呈的答案,包括了她们在童年时代的生活细节、家庭地位,她们当时是如何预见自己的未来,她们是什么时候、如何被政治化的,她们是如何理解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的。[5]120从女红军五花八门的回答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激发她们成为革命者,从而走向战场的原因也是千差万别。但是归根到底是出于对人民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解放两大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
首先,救国救民,改变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实现人民的解放是绝大多数女红军参加革命的首要因素。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救亡图存的重任和使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着救国与发展的道路。腐朽的大清王朝对此不仅束手无策,还接二连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甚至一步步沦为中华民族解放的首要障碍。然随之建立的民国,虽令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轰然倒塌,但是国门洞开、列强肆意践踏的境遇未曾改变。其后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连番登上政治舞台,然而在守护民族利益和捍卫国家安全面前,依旧显得软弱无能。如何改变现状?正如《国际歌》歌词中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于是救国救民成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诉求和共同理想,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入汹涌的革命浪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却已逐渐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无疑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一条为社会公平和民族独立而奋斗的振奋人心的道路”。[5]121
一些出身书香门第或革命家庭的女性,或接受过一定的近代新式思想教育,或受到家族成员的革命教诲和熏陶,或直接间接地接触地下革命组织,促使她们也开始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并对共产主义事业较为崇尚,由此为了人民的解放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女战士贺子珍在自述中回忆,她在福音堂办的女学读书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中国,也传到了永新;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使永新一批激进青年热血沸腾”,她也在此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之时,在共产党先进思想的引领下逐渐萌发了“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太多,不把社会翻个个儿,人民没法活”的革命思想,进而投身革命洪流,“找到了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解放穷苦人民的革命道路”。[6]湖南慈利的蹇先任、蹇先佛姐妹则是受到了弟弟和家人的影响形成了革命信仰,继而参与革命的。她们的弟弟在湖南一所进步中学求学,后参加湖南省工人运动讲习所,成了革命者,并被认为是有前途的共产党的“年轻的好苗子”。他经常将革命书籍和杂志寄往家中给姐姐阅读。蹇氏姐妹通过这些书籍和刊物,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分校期间又深受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影响,成为一名政治积极分子,并把理想付诸实施,参加到革命之中。正如康克清和谢飞所言,“那时我们的理想只有一个,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怀着革命必胜的决心,抱着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信念”,[7]邓颖超、彭儒、刘英、张琴秋等女同志先后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其次,伸张女权,积极展现女性生命主体意义,实现女性自身的解放也几乎是所有女红军参与革命的直接因素。自古以来,中国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下,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摧残。女子从出生起就受到忽视和歧视,“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尤其在一些贫困的家庭,女孩是家中养不起的奢侈品,大都一出生就被溺死或卖为童养媳。红四方面军女战士刘坚回忆,由于家中过于贫困,无力养活接连生下的三个女儿,第一个送给别人家,其后两个“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她们放到尿桶里面,再盖上盖子闷死”。[5]124侥幸苟活下的,不久也大都被送到别人家中当童养媳或“等郎妹”。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还自编歌谣描绘了当时的景象: 18岁姐嫁三岁郎,朝朝夜夜抱上床,等到郎大姐已老,等到花开叶已黄。[8]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的李贞在自述中提及,早年因家境贫寒,6岁就被送走成了别人家的童养媳,在家中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而且身心受尽虐待和凌辱。于是,改变不堪忍受的生活境遇成为她参加革命的直接因素。
民国建立以后,各种新思潮不断孕育,女权运动亦随之兴起,中国女性不再安于传统命运安排,面对扼杀人性、忽视人格的种种现象奋起反抗。孙中山早年深受欧美思潮教育影响,力图以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改变传统社会的遗毒,在倡导男女平等、保障女权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中共创立后,更为关注女权问题,并把男女平等写进党的文件。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为保护妇女权利、解放妇女提供了多种途径。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案中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劳动妇女的群众”,即要积极动员妇女参加革命,把妇女自身的利益和革命的活动联系起来。在中共妇女政策的吸引下,苏维埃根据地周边大量处于生活最底层的备受压迫的女性,如王泉媛、邓六金等绝大部分女红军同志,出于改变自身悲惨境遇的考量,纷纷选择投身革命,走上一条崭新的生活道路。后来很多女红军在回忆中都讲到一句话,“党就是我的家”[5]121,因为革命帮助她们逃离了卑微的地位、凄惨的生活,并且为之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
三、肩负两项革命重轭:前线作战和后勤保障
1930年冬,蒋介石挫败阎、冯、李等军阀力量,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使蒋介石有“围剿”红军的力量和时机。是年12月至1932年12月期间,蒋介石先后四次下令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企图达到围歼中央苏区的狂妄目的,但结果均被红军成功反“围剿”。次年7月,蒋介石调集8个师约100万兵力第五次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然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下,中央红军伤亡惨重,最终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而当时在根据地的女红军大都不了解中央的具体计划,后来很多女红军都回忆道她们“接到通知要出发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是被告知“到敌人的后方去”“以后的情况会非常非常困难”。[5]178-179当然,并非所有的女红军战士都有资格随军转移,除了担任干部职务以及领导人夫人的女性免去体检即可随行外,大部分女红军必须经历严格的挑选和体检。只有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身体素质佳的女红军才能最终被挑选出来,随同部队一起转移。其余体检未能达标的则只能留在苏区继续战斗。当然也有一些被组织决定留在苏区的女红军自发组织了“跑反队”,坚持跟在红军大部队后面。可惜大部分在途中或牺牲或在队伍中被打散,只有个别坚持走到了延安。
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后,女红军不仅要与红军大部队一同转移,而且在长征途中承担了大量繁重的工作。但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以往有关长征的研究著作中,大多关注男红军的事迹,而鲜有谈及女红军的贡献。然而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长征大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忽视。根据女红军晚年的口述回忆,当时在长征途中,她们同男红军一样肩负了革命重轭,可分为前线作战和后勤保障两项。
在红军长征的同时,蒋介石再次调集军队进攻,致使红军不得不一边栉风沐雨地行军,一边还要抵抗国军的围追堵截。男红军无疑是前线作战的主力,但是女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也作出了重要的战斗贡献,从中涌现出大量英勇善战的女红军以及她们创造的光辉战绩。朱德曾就此高度评价说:“她们在夺取敌人的辎重和武器上,很能胜任”。如她们在剑阁战役、痛歼保安团、永昌战斗、临泽战役、祁连山战役等沙场囹圄中都尽显顽强英勇之气概。值得一提的还有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师。该师发源于1933年建立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后因战斗需要于1935年多次扩编而成,下辖两个团,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建制最高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师一经成立,即刻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并于是年3月开始长征。期间,妇女独立师冲锋陷阵、英勇抗敌,在剑门关战役中佯装撤退后发起猛攻,一举拿下猝不及防的敌军。而后妇女独立师又参与了伏泉山、千佛山一线的数次战斗,接连获得重大战果并成功占领该线,成功掩护红四方面军西进,为与中央红军早日会师、结束长征立下汗马功劳。[9]207-209军队中还闪现出一批极具出色军事指挥才能的女红军将领。女红军创造的赫赫战绩离不开她们杰出的战术指挥。
除了在前线抗敌作战、浴血奋战外,女红军战士在后勤保障上作出的贡献更是不可泯灭的。主要包括医疗救护、筹运物资、扩红宣传三方面的工作。在医疗救护上,女红军对在前线负伤的伤病员进行急救和看护,有时在粮草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伤病员补剂营养,有时承担起替民夫抬担架的“重任”,有时还为了掩护病号而伤亡。她们救死扶伤、任劳任怨的工作,“宁愿自己多受累,也要千方百计减少阶级兄弟的痛苦”[10],也得到了张国焘的赞叹:“她们在救护伤病兵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11],陆定一也由衷称赞,“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时时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病员,总是不知疲倦”[12],以及负责卫生部门工作的姬鹏飞也夸奖她们是“真正的长征英雄”。[13]筹运物资也是女红军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到一地女红军都通过打土豪没收土豪物资和没收土豪的钱款向农民购买物资两种方式进行。红四方面军还专门成立了妇女工兵营和妇女运输连负责物资运输的工作,女红军们几乎每天平均要背负二三十斤重的物资急行军,运输队的女红军则要担负近四五十斤物资跋山涉水,[14]在她们看来“资财比人重要”。[15]当然,女红军在后勤保障工作的开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在筹款借粮过程中,常常遇到农民们轻信反动派的造谣而躲避红军。为此,女红军不得不每到一地就以布告、标语、演讲、文艺表演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中共的政策和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以及军队的纪律,以此打破群众的戒备心理,让群众了解当前革命形势和任务,调动群众参与红军工作的积极性。董必武后来回忆,中央红军中“做工作的女同志,绝大多数是自背行李,包裹一卸,马上又要去做群众工作,这些都和男子一样”。[16]21女红军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动员了大批底层劳动人民、青年甚至是妇女加入到革命事业之中,达到了“扩红”的目标,有力支援了红军。
四、面临两重艰苦挑战:斗争环境的挑战和女性生理的挑战
马克思曾断言:“每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17]长征顺利结束依靠的不仅是男红军的英勇奋战,女红军同样用实际行动昭示了毛泽东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深刻内涵。而且,女红军当时不仅经历着强敌环伺的战争环境考验,还要面临万分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女性特殊的身体机理所带来的束缚和不便。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漫漫长征路可谓是险象环生,深不可测的泥潭沼泽、高山缺氧的高海拔地区、雪山地带的极寒气候、长期的日晒雨淋和缺衣少食时刻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邓六金说:“在长征中有些战士牺牲在战斗中,但是大多数人是由于缺少药品、食物以及各种险恶的自然环境而牺牲的。”[5]205钟月林后来回忆过大渡河时的情景说,“河水有齐腰深。过河的时候,我们大家手拉手,害怕被湍急的河水给冲走”[5]200,但结果却是“三、五个人同时被冲走……冲出去很远很远还隐约听得到她们的惨叫声”。[18]129-130爬雪山的时候,恶劣的天气使得爬山更为艰难,还时常遭受狂风和冰雹的袭击。再到后来过草地,对于疲惫不堪的红军来说,又是一道自然难关。谢飞在口述中提到,“这该死的地方真奇怪!只有草,没有树。也没有山,就是一片平地。每天下雨,又每天出太阳。地上永远是湿的。刚开始时,先头部队陷进了沼泽。如果你想把他们拉出来,你也会陷进去。他们自己爬不上来,别人也无法救他们。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5]204邓颖超曾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陷入沼泽地,当她被后来赶上的部队救起的时候,她骑的马匹已被泥潭吞没。为此,女红军们过草地时都特别小心,走得很慢,刘英说“每天走路,走了整整七天才穿过”。[5]207
除了行路艰难,食宿问题也给女红军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早在湖南的时候,因为要给前线的战士节省粮食,女红军的“粮食就不够吃了!饭菜里没有一滴油,更糟糕的是连盐也没有”。[5]184后来红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后粮食供给又时断时续,当时的红军战士包括女红军在内只能吃草根、啃树皮。甚至有的女战士实在饿得不行,拿起牲口拉的粪便中的玉米烤着充饥。另外由于当时行军紧张,经常在野外露宿,女红军的正常起居和个人卫生都无法保证。致使很多女红军身上长起了虱子。钟月林打趣地回忆道,“如果你没长虱子,你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因为没有地方洗澡,也没有办法换衣服。”[5]184每当女红军将衣服放在脸盆中用水煮后,总会有一层虱子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女红军长发中长了虱子,无奈只能剃成光头。此外,女红军如厕解手也极其不便,大都是几个人将床单围起后在中间方便。尽管如此,大部分女红军还是凭借着钢铁意志和非凡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爬过崇山峻岭,攀过皑皑雪山,走过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渡过深涧激流。
当然女红军面对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男红军同样要面对。然而,女红军还要承受女性身体机理所带来的束缚。由于长途跋涉和日晒雨淋造成很多女红军身心俱疲,从而导致了经期紊乱和身体多部位的机能损伤。加上卫生条件落后,据陶才桢回忆当时来了月经后只好“独自跑到水塘边,悄悄用发黑的污水洗干净”,[18]184因而很多女红军原本健康的身体都患上了妇科疾病,甚至造成了终身不孕不育。[19]除了经期,还有孕期和哺乳期也给部分女红军带了巨大困扰,“产后一晚半日就要行动,应有的休息和调理都得不到的”。[16]20不仅在途中生产条件极其艰难,而且生育下来的孩子也不方便一同行军,有的孩子甚至在途中夭折。故而为了革命利益,为了使红军长征不受到拖累,如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中记录的,“那些有婴儿的妇女,要么将孩子留给农民,要么干脆扔掉,就像处理过多的装备那样,别无其他选择”。[20]这一系列由特殊女性身体机能带来的问题,并没有摧垮女红军,反而更能见证女红军的坚韧不拔。
五、余论:“女性的革命”与“革命的女性”
毛泽东曾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革命是不会胜利的。”[21]女红军在长征中的伟大实践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一方面,女红军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打破禁锢妇女的枷锁,试图通过参与革命来改变自身悲惨的命运。同时,她们通过宣扬革命精神启迪更多妇女得以觉醒,加入到女性解放的队伍中。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女红军可谓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宣传队、宣言书和播种机。她们为近代以来“女性的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必将永载史册。
另一方面,女红军们怀抱着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牢筑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支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并击退一切反革命势力,充分体现了革命者应有的革命性。她们与所有红军在革命战争的历练中共同缔造伟大奇迹,共同铸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无奈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她们的光芒被男性遮蔽,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她们也是长征历史的参与者和长征精神的塑造者,我们不能把这些“革命的女性”遗忘在历史的洪流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与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曾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广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面向的目标更加远大,更需要广大妇女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此,我们要继续推进妇女解放并实现男女平等,同时要继承和发扬女红军在长征中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贡献力量。
[1]师永刚,刘琼雄.红军1934~1936[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 117.
[2]邵雍.长征中的女红军[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7) : 117-118.
[3]李安葆.女红军长征记[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6.
[4]郑广瑾.长征事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21-22.
[5]杨·海伦.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6]江西省妇女联合会.女英自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3.
[7]叶心瑜.放眼看长征[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6: 652.
[8]小野和子.革命世纪中的中国妇女[M].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 114.
[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三) :红四方面军征战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207-209.
[10]汤文德.“七仙女”长征记[J].妇女生活,1984,( 8).
[11]张国焘.我的回忆[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 348.
[12]李海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66.
[1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新记[M].北京:新华通讯社参考材料编辑部,1986: 185.
[14]星火燎原编辑部.星火燎原——女兵回忆录专辑[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231.
[15]何方,宋以敏,采访整理.刘英,口述.刘英谈红军时代[J].炎黄春秋,2016,( 1) : 5-13.
[16]《董必武选集》编写组.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86.
[18]曾志.长征女战士第二卷[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5.
[19]四川省阿坝藏羌族自治州妇女联合会著.女红军在雪山草地[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184.
[20]侯燕如.女红军述论[D].兰州:兰州大学,2008.
[21]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68-05-15.
责任编辑:侯伟浩
Their Long March
——On the Female Red Army in the Long March
GAO Xiaolin; TAN Sijia
( School of Marxis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Women ar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Red Army in the long march.Female Red Army distributed in four main forces.The long march of women's Red Army reflects their pursui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nd women's liberation two goals,and the two tasks of combat and logistics,which overcome the two challenge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omen's physiology.Although the number of women is not much,but the long march of women's Red Army shows the two majo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women's revolution and revolutionary women.
female; the long marc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2016-06-10
10.13698/j.cnki.cn36-1037/c.2016.04.0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 14JD710059)
谈思嘉( 1992-),男,上海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高晓林( 1968-),女,辽宁大连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K264.4
A
1004-8332( 2016)04-0013-05
网络出版地址: http: / /www.cnki.net/kcms/detail/36.1037.C.20160708.0948.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