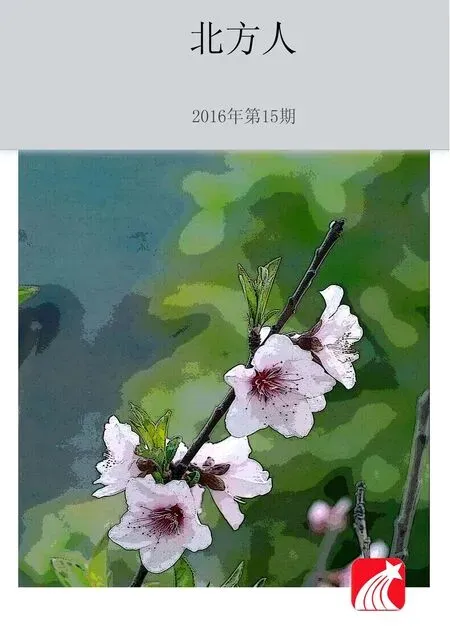我是天生的诗人
文/施立松
我是天生的诗人
文/施立松

1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在剑桥求学期间,邵洵美和徐志摩成了“双胞胎般的挚友”,两人都喜着一袭长衫,风流倜傥,儒雅潇洒,但邵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徐志摩更漂亮些。金粉世家的公子哥自然少不了颓废享乐气,邵洵美迷恋上萨福、史文朋等唯美先驱。他自己也说:“人总是半人半兽,一方面被美来迷醉,一方面又会被丑来牵缠。”游学欧洲期间,他奉萨福为女神,甚至仿萨福诗格,把中国诗写成希腊文,他还凭想象写出诗剧《莎茀》。
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陈梦家的一句点评最精彩:“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只是那绻绵是十分可爱的。”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写成一首诗,只要老婆说好,已是十分快乐;假使朋友再称赞几句,便是意外的收获;千古留名,万人争诵,那种故事,我是当作神话看的。”
2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
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身材高大、面色白润、鼻梁高挺的邵洵美,总是保持着一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有如激流边上的浮萍。他好客、亲切、随和、健谈,让人一见如故。
这大概可算是中国文坛最好最美的时光吧。也许,自有文学以来,中国文坛从没有过这样的时光,即便著名的兰亭雅集和李白笔下的“春夜宴桃李园”,也难以媲美。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1000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3
略带忧郁的男人,似乎更能激发女人的爱,何况邵洵美宽容善良、幽默风趣、俊俏优雅、见识广博,又有中性阴柔的诗人气质。但邵洵美不是喜欢猎艳的花花公子,他钟爱的生活是,有艺术修养,精神生活丰富,物质生活健康。他在《时代》画报上发表了《对1931年男子的话》:
我希望1931年的人,每一个男性同类都和我一样做:假使我物质上不发生困难,我要在每天早晨上工,每天黄昏散工以外练习踢毽子,我要学会去玩丝竹管弦里面无论某一种乐器!我要每天洗一个澡,每星期看一二次影戏,跳一二次舞!我要订一份《小说月报》、一份《新月》月刊、一份《东方》杂志,《时代》画报是每期会送给我的,所以不必订了。
在邵洵美心中,他喜爱的理想异性是有艺术修养的新时代女性:
你们不应当再以柔弱为绻绵,应当存为强壮荣耀的观念。假使你已经是一个新女子,那么你应当更彻底去做一个现代女性的模范,要是光会换上旗袍,认识些男朋友,看看影戏跳跳舞,那你仍不过是个玩具,仍不过是个穿上了时髦衣衫的泥娃娃。
1935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社通讯记者埃米莉·哈恩来到上海,她为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书,不远万里到上海搜集素材。接风宴会上,她一见邵洵美,立刻被他的容貌和气质打动,再见便倾心于这位面白鼻高的希腊式美男子。几度相会下来,他那一口纯正的英语,一首首精美的英文诗作,令她倾倒。女性的爱慕之情,总是伴随了些许崇拜之心、敬佩之意的。
邵洵美对埃米莉的爱,来得热烈又猝不及防。他陪伴她探访金陵,登临黄山,泛舟西湖……还给她取了个好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
这段爱情持续了五年。他们的爱情不只是风花雪月,他们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合办了抗日杂志——中英文版的《自由谭》。由于《自由谭》宣传抗日,项美丽受到日本人的警告,发行七期后,被迫停刊。
虽然,这段生活在项美丽近百岁的人生中,只是小插曲,却美丽妖娆、动人心魂。耄耋之年,她还说,她只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成了她厮守终生的丈夫,一个就是中国人邵洵美。
4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回国后,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金屋》效仿英 国唯美派杂志《Yellow Book》,用金黄色的封面,里面用黄色的毛边厚纸,新颖独特。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不带色彩,不主张旗帜,不趋就低级趣味、赶热闹、卖笑,要用人的力的极点来表现艺术,抒发至上的美。”后来,他成立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创建“第一出版社”。他前后办了11种刊物,他的“宝贝们”装帧精美、内容丰富。他是要培养大众的精神品质、趣味情操,造就会幸福的民族。
有位朋友斥责邵洵美出版毫无目的,说办杂志应当有政治野心。他微微一笑回答说:“出版便是我的目的。”
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成立时代印刷厂后,印刷成本和印刷质量一再提高,印刷品价格却一降再降,最后他连妻子的嫁妆都变卖了,可谓倾尽精力财力。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5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是啊,被低估又有什么关系。风过霜过,花过月过,倾过心倾过情,倾过力倾过囊,已是彼岸的幸福。
黄永玉先生曾给邵洵美做了一首诗《像文化那样忧伤——献给邵洵美先生》:“下雨的石板路上,谁踩碎一只蝴蝶?再也捡拾不起的斑斓……生命的残渣紧咬我的心。告诉我,那狠心的脚走在哪里了……不敢想,另一只在家等它的蝴蝶……”
或许,这样的话语,才能安慰到那颗诗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