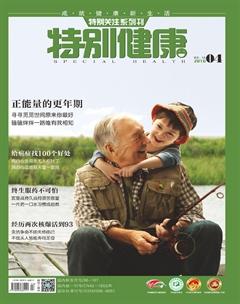给老乡造农机
张树森
我插队在翼城县东续大队。刚到农村时,村里的木工组得知我会干木工,就把我要了过去。做木工是我在北京自学的。“文化大革命”别人都造反去了,我自制、购买了一点简单的工具,找了一些废旧木料,借了一本《木工工艺》,边学边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一点木工,没想到在农村还真发挥了作用。
当上小组长
到木工组后,我发现不少农机十分落后,有的不实用,就想把它们改造得更好一点。可是“知识青年”没知识,连最简单的机械零件图我都看不懂,更谈不上改造农机了。
怎么办?学!于是把在北京学习《木工工艺》的笔记翻了出来,又托人买了一本《木工识图》,将叔叔的两本中专教材《制图》和《制图习题集》也要了来。每天夜晚,我在小油灯下,伏在木箱上,用一只三角多钱的学生圆规,两只小三角板,一支铅笔,一张白纸就画开了。仅有的一点书打开了我心灵的又一扇窗口,驱走了我心中的苦闷和惆怅。半年后我已能看懂木工图、机械图及建筑图,可以绘制机械零件图、木工家具图及机械组装图了。
那时,村里种棉花都是用种小麦的播种耧直接播种。这种耧种出的棉花如同种的小麦一样,都是密密麻麻一行一行的,既费种子,以后间苗又费工。能否将这种一行一行的播种耧改为一窝一窝的耧呢?如能这样,起码可节约四分之三的种子,而且棉苗长出后又节省了不少间苗的时间。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生产队长,他很支持。于是以我为主,外加两个木工、一个铁匠组成了改耧小组。开始村里人反应不一,支持的有,泼冷水的有,冷嘲热讽的也有。对这一切我都不管,白天干完活,晚上就在小油灯下搞我的设计。
难题一个个解决
要將小麦播种耧改造成一窝一窝播种的耧,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如何解决按一定距离一次播一定数量种子的问题。如果采用小麦播种耧的设计,在储种箱和耧腿间加一个机构,在耧前进过程中使种子按一定时间一次落三到六粒,再经由耧腿出口播入地下,似乎就能解决问题。但经实验,这种想法行不通。
我们反复研究,又想出了一个新方案。白天,我和铁匠、木工一起加工研究、改造;夜晚,我伏在小油灯下计算、画图。草图不知画了多少张,光耧中间的出种木轮就改了四五次模样,终于,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努力,第一架样机做成了。
结果试机后发现,种子虽然可以一团一团落下,但落得不集中,有时甚至散成一片跑到沟外。分析原因,原来种子从储种箱到地面的距离过大,在下落的过程中就会散开。如何保证种子不散开?我设想在出种木轮的前面加一个半圆形的保护装置,使种子离开储种箱进入出种木轮的方洞后,在方洞中保持一定时间,直至离地面最近时再撒出。我们用两块半圆形木板,前面钉一块较软的传动带,这样保护装置就做成了,将它套在出种木轮的前侧,果然种子再也不散开了。
老乡舍不得我走
公开试机那天,公社干部来了,大队干部及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在两匹大骡子的牵引下,经过改造的双轮双耧播种机缓缓走动了。播种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设想,播种距离一致,种子多少适中,开沟、盖土合理。
成功了!面对人们的赞许和祝贺,我陶醉了。双轮播种耧是我们几个人心血的结晶,它虽然还很粗糙,但它的成功坚定了我搞农机改革的信心。
春天,我们打造的四台双轮播种耧开始在田间播种了。不久,地里长出一丛丛整齐嫩绿的棉苗。望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的棉苗,那种喜悦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
邻村、邻公社的木工、铁匠来取经了,公社、县里开大会也时常表扬我。
此后,我们又为村里设计制造了两台弹棉花机。过去村里的老乡背着棉花到外村去弹,既跑路又花钱,如今外村的老乡也到我们这里来弹棉花了。我们还为村里制作了两台打浆机,红薯的粉碎打浆比以前方便了不知多少倍。村里的粉坊开张了,别村的村民都跑到我们村来买粉条。有了粉坊,村里的养猪场更兴旺了,村里的经济收入大增。
几年后,省广播局招工,我被挑走了。临走时,村里的老支书拉着我的手说:“要是村里管知青分配工作,让谁走也不会让你走的,村里需要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