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也任性:苏珊·桑塔格与疾病
霍源江
如果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著名女作家、文艺评论家)大概就是那种“力比多”(指本能欲望。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则定义为心灵能量)泛滥的人。读她的东西,脑子里最强烈的信号是,这个女人思考力极强,身体里万马奔腾,元气淋漓。作为20世纪绕不过去的风云人物、西方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女知识分子之一,不用说她在越战期间的“河内之行”、早期的左派立场,也不用说她袭击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骁勇,以及在知晓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后的怒不可遏,向政府开炮;单单她的几次患病经历,便促其追剿谜团重重的疾病史,还疾病一个清爽面目,藉以抚慰患者,伐毛洗髓,使之无畏。
对桑塔格而言,疾病是一种生产力。
说起她一生的患病经历,除了小时候的哮喘病,使人谈之色变的癌症,她就遭遇三次。这些经历见于她的儿子戴维·里夫所撰《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的最后岁月》一书。特别是2004年,她第三次遭遇癌症——致命性的血癌,没有侥幸和励志故事发生,死神把她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我连自己都不懂自己了。”她不是钢铁,作为敏感的思想者,与痛楚、感伤和失眠的接触反而更近。她一个劲儿地感叹,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要写的文字排成队挤在脑子里,闹腾腾的。
众所周知的是1975年第一次检查出癌症,乳腺癌晚期的噩耗降临她的头上。多年以后,香港作家黄碧云写道:“或许你从来不感到破灭。你是那么顽强的人。医生诊断你只有25%的生存机会。你活了下来,多活了28年,并且活得美丽丰盛。”事实上,也许并非“美丽丰盛”,戴维·里夫“认为他母亲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桑塔格褪去了偶像的外壳,如同凡人一样对抗疼痛和离别。她一直就是个凡人,她拆解贵族派遗留下来的文化习气,与僵化一元的教条观念周旋,目的就是抵达一个凡人应该拥有的生活审美。于是有了《反对阐释》(1966)。她的作品和思想,像是反对一元论、还原价值与真相的注解——剥离价值判断与事实真相之间缠绕的千头万绪,展露峥嵘。她是那种被大众托举起来的凡人,潇洒、自由、勇敢的凡人。
1975年10月,桑塔格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化疗,大团大团地脱发。与癌症斗争期间,除了追问自己作了什么孽,谴责错误的生活习惯外,她想的是用写作填补生命的空隙。她把希望寄于未来,却没有想到后面还有病魔等着她,一秒秒逼近性命。海德格尔在关于“存在”的讨论中,就“向死而生”的命题说道:“死亡看似无期,幽深隐蔽,于是人们浮在生之长河,浪荡无涯,不察光阴霸道,转眼而至,以恢复个体自我、独立尊严来抵御平面复制时代的无为。”他说这话的大背景是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倒错,工业化、现代化对生命本相的掩盖。而桑塔格在病中之忧患,是此概念极佳的注脚。

癌症于她像分水岭,自那以后,她渴望和儿子、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每当在公众场合出现,身边呼朋引伴,抓紧一次次相见的机会。生命有时,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
如果说病患是对健康的罪与罚,那么思考则是上天对患者的赏赐。1980年,美国作家查尔斯·鲁阿斯采访患病的桑塔格时,她说道:“它(病患)像任何一次把人最好和最糟的东西激发出来的重大紧急事件一样,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75年,桑塔格去法国治病。她查阅了关于癌症方面的医学资料,并咨询医生治疗方案的可行性,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她每周去几次医院。她捕捉到一些异象:病人遭受另类目光,自感羞愧;医生不负责任,轻视病人;还有外界对癌症的解读……这些刺激了她。为什么癌症被视为洪水猛兽?承受疾病之痛也就罢了,无法忍受的是加诸其上的象征意义。于是,一本剖析疾病不能承受之重的书——《疾病的隐喻》,孕育而出。在此后所著的《艾滋病及其隐喻》中,她骄傲地说“驳倒了医生们的悲观主义观点”。
那么,疾病是如何作为隐喻的?她又是如何拆解的?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贵族和资产阶级争锋夺食,抢占审美话语权,饮食、服饰和绘画等等门类被设置了一条条莫须有的界限、赋予各色标识,以供贵族们抢座占位。就连疾病也未能幸免地被绑架并贴上标签——结核病作为一枚高标,打上贵族的标签,以此维系他们日益下坠的优越感。19世纪末期,结核病几乎成为文艺界的时尚,肖邦、拜伦、雪莱、席勒、勃朗特姐妹、卡夫卡、劳伦斯以及中国的郁达夫等都患有肺结核,《汤姆叔叔的小屋》《董贝父子》《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格维塞夫人》等作品也都涉及结核病。忧郁、激情、文雅、精致、富于创造性、浪漫主义的、悲伤的……结核病被混乱地任性地赋予重重意义,饰以层层光环,仿佛成了身份与荣耀的象征。
桑塔格从文学和历史中搜寻了大量证据,逐一剥离结核病与道德、政治的关系,说明它们之间乃“强买强卖”而已。而产生这样的原因也很有意思:首先是医疗卫生条件差,人们不知道结核病的患病原因而妄加猜测;加之贵族中心主义横行,“占位”宣传铺天盖地,导致真相缺席,假象上场。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把事实和价值判断锁到一起,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面孔,俘获了时代的青睐。疾病被横征暴敛,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代代如此,于兹为盛。桑塔格罹患癌症,揭示了癌症只是疾病而已,无关道德高低,不干政治倾向,而外界有色眼光的渲染,使它的内涵,多到挤出水来,流成一条河。疾病的隐喻从审美领域,进入道德范畴,进入政治种族范畴,演绎成排斥异己的修辞武器。隐喻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真相,而是掩盖真相。
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写道:“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结核病为雅致、敏感、忧伤、柔弱提供了隐喻性的对等物;而那些似乎冷酷、无情、损人利己之事,则被类比为癌症。”至于癌症发生的原因,多被归结到情绪、心理层面,“把癌症与情绪消沉、缺乏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中常用一系列战争话语类比之,比如说起癌细胞,经常用到“入侵”“杀死”“消灭”等隐喻。渐渐地,人们谈癌色变,对之讳莫如深,看待癌症病人的眼光也是悲戚而复杂的。隐喻如谣言一般,遮蔽疾病的真相,令患者备受猜忌与怀疑的重负。桑塔格扫描癌症遭受不公待遇、被扭曲的隐喻历史,考察它在政治、文学中扮演的角色。现象世界,从来不是意义世界。试想,我们身边,言语隐喻之下,篡改了多少可爱的事实。仅基于此,桑塔格的犀利与骁勇就令人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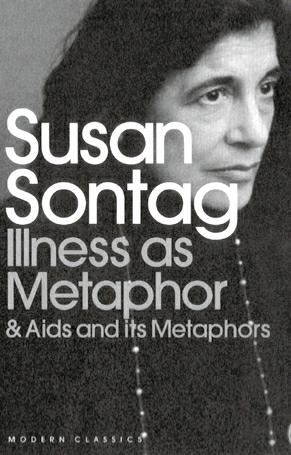
生病也任性。万象错杂,字与字编织的秘境,也要用字与字来救赎,病中的桑塔格与疾病的隐喻持久对抗着,以打捞沉淀的事实,如她在书尾所言:“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如果说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描述的话,那么描述者的身份、立场和动机本身在时过境迁之后便应加以二次审视,曾经之是也许便是今日之非,此时,应当剥离语言隐喻、事实真相、价值判断三者的枝蔓,还它清爽面目,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疾病常有,而桑塔格已不在。
——芭芭拉·秦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