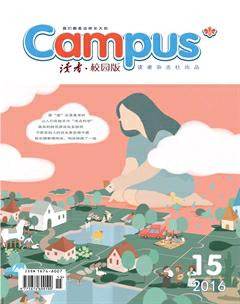笔会
姚懿童
这是一个两条平行线相交发生交集的故事,很多年以后,当我从车窗的一角瞥见自己的青春的时候,依然记得Sunny和Sanny以及那些风格迥异的花。
我是生活在父母和老师特别关心下的孩子,生活的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读多少字,画多少画,背几篇文章,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睡觉,都有人替我安排好。大人们总是这样,无论在其他问题上有多大的争议,却在我学习的问题上齐刷刷地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你不去读书还能干吗?”“你不用功读书,长大了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去搬砖。”好吧,九年来,我的上学路线都从未改过,因为路上有怪叔叔,专门骗小姑娘。再说说我画画这件事吧,我画国画,从六岁开始,只画花花绿绿的花草,那些花一朵一朵地在宣纸上绽开,可是在我眼里,却始终只是没有生命的墨迹而已。我看着它们在我的手下一点点地风干,一天又一天,直到十四岁时遇到了一束阳光。
大炮是我的同学,就坐在我的正后方。当时老师的意思是让我多多帮助差生,于是不久他就成了我的同桌。“我的艺名是Sunny,同学,我看你骨骼清奇,给你指条明路,放学后出门右转直走,看我的涂鸦。嘘,一定要保密哦!”神秘兮兮地说完,他就倒头大睡。放学时,我在校门口犹豫很久,因为“那条路上有坏人”,最终却还是鬼使神差右拐踏上了那条路。学校的右边是快要拆迁的民房,墙上鲜红的“拆”字在阳光下很是刺眼。“嗨,你看好,很酷吧,记得我是Sunny!”大炮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果然,在那些碍眼的“拆”字旁边有一束阳光。我目瞪口呆,我从来没有想过涂鸦也可以这么有艺术感,单纯是字体的扭曲变形就可以这么有动感,每一个字都是跳动的音符,每一个字母都可以从墙上跳入你的眼里。字母与字母之间嚣张对峙,却又完美地融为一体。第一次踏上那条险恶的小路,我就爱上了涂鸦,它不同于国画的细腻、温婉,却有着生命的张力。
大炮其实有一颗孤独的心灵。听说他爸妈离了婚,妈妈丢下他不管了,这真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他上课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高兴时拿我的笔记本抄抄,兴致来时和我聊聊涂鸦,聊那些他喜欢的涂鸦大师,外国人的名字很长,我总也记不住。每次聊到最后,就以“我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结束。
有一次他说:“看得出来,你很喜欢涂鸦,要不,我们搞个组合,怎么样?”“不行,我是学国画的,不能被这种街头艺术带偏了。”大炮当时一脸不信。我把床底下那十几箱宣纸拉出来,背到学校摔到他面前。“完美啊,中西方艺术的完美结合,是吧,Sanny。”我终究义无反顾地被带偏了,而且跑到“爪哇国”了。
放寒假了,照例考得还不错,老妈奖励我可以放松几天。于是,三天时间,我迅速地了解了字体的变形和涂鸦的历史、发展等相关知识。多亏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都还不错,听着他长期不用而退化的语言,基本靠脑补。大炮说:“第一次涂鸦,就算是丑得要死,也要画在人潮汹涌的地方。”于是踩了无数次点,终于选定了小菜场面馆旁边的围墙上。我们没钱,手头只有几罐工业漆和几瓶丙烯颜料,但这些颜色足以挥洒出青春的激情。当晚,一轮新月当空,路灯放出清冷的光。两幅手稿,两张兴奋的小脸,四只闪亮的眼睛。那些熟悉的花,形形色色的花,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开放。这次,我清晰地感觉到,是我赋予了它们生命。因为有了Sunny,所以花开得更艳。
大炮后来没来上学,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在这个小镇上,我和当年的Sunny一样,留下了许多痕迹。涂鸦人把自己叫作写手,而不是画家,因为每个人都在用挥舞的彩漆书写自己的人生。
两条平行线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行,但终有一天还会有交集,因为有梦就会有荼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