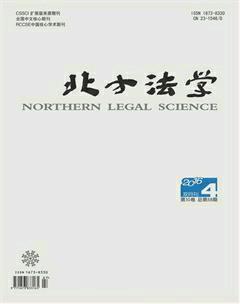古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赎刑制度探析
刘蕊

摘 要:赎刑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制度,中原地区的赎刑制度在秦及汉初具有替代刑和独立刑种的双重属性,唐代以后赎刑发展成为刑罚适用的一般原则。罚金刑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多处于与赎刑合而为一的并存状态。以藏区“赔命价”制度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赎刑制度,在古代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在现代则表现出明显的和解性质。赎刑制度中的价值理念和合理规则,对于我国刑罚替代措施和死刑的司法控制等方面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赎刑 赔命价 刑罚制度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151-10
在人类社会早期,以赔付财产作为避免“血的复仇”的手段在成文法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在西方早期习惯法以及欧陆古代成文法中,赔偿被作为侵害行为的惩罚措施加以运用,而后逐渐发展为侵权损害赔偿,而在我国古代法律中则表现为赎刑的样态。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在与中原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吸收并借鉴了中原地区法律制度,与其特有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相结合,同样形成了以赔偿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的成文法或是习惯法,并且这种做法在维持少数民族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处理刑事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为典型的就是盛行于藏区的“赔命价”制度。本文期待通过对赎刑制度的发展变迁过程予以梳理,探源赎刑制度的性质与机能流变,把握赎刑制度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以对我国刑罚制度以及刑罚体系的完善有所借鉴。
一、赎刑在中原地区法律制度中的地位演变
上至虞舜下至明清,赎刑作为一种刑罚的替代与变易手段在中国古代刑罚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赎刑的性质、地位如何,其与同样以缴纳财产为内容的罚金刑关系如何,则历来都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赎刑并不是刑罚的替代措施,而属于正刑的一种,①或说赎刑是一种特定的刑名;②一种观点认为,赎刑是实刑的替代刑,而罚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是对有罪过的人直接处以罚金,从轻发落。③实质上,在赎刑制度中,作为替代刑的部分、财产刑的部分与作为易科罚金的部分有着难以分离的阶段,正如沈家本先生所指出的,“古者辞多通用,罚亦可称刑,凡经传之言刑者,罚亦该于其内,赎亦可称罚。”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6页。 随着刑罚体系的不断完备,赎刑制度的内涵、性质、地位也随之演变,逐渐形成一项明确的法律制度。
(一)同为“正刑”与“替代刑”的赎刑制度
制度意义上的赎刑可上溯至夏。西周本着“训夏赎刑”的精神,作《吕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尚书·吕刑》。 《吕刑》对于经检查不能核实,不应适用五刑的,正于五罚。根据郑玄《周礼·职金》所注:“罚,赎也。”在这里,罚与赎虽是通用的,但本质上是依照夏朝“金作赎刑”的精神制定的对于死刑和肉刑的易科罚金制度,属于刑罚的替代方式,无所谓罚金。
秦汉时期,赎刑制度既作为刑罚替代措施加以规定,也包含作为独立的刑罚种类的规定,同时规定了赀刑,同为剥夺犯罪人财产的刑罚。赎刑作为刑罚替代方式的立法例,在《法律答问》中有所体现:“真臣邦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谓‘赎鬼薪鋈足?可谓‘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罪,赎宫。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此。”上述规定中,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首领犯了耐罪以上的包括劳役刑、肉刑、死刑等罪都可以赎免,这是赎刑制度对特殊身份者的例外适用。但在普遍意义上,赎刑是作为刑罚种类予以独立规定的。《法律答问》规定:“甲某遣乙盗,未到,得,皆赎黥。”“‘抉钥,赎黥。何谓‘抉钥?抉钥者已抉启之仍为抉,且未启亦为抉?抉之弗能启即去,一日而得,论皆何也?抉之且欲有盗,弗能启即去,若未启而得,当赎黥。抉之非欲盗也,已启乃为抉,未启当赀二甲。”“盗徙封,赎耐。可如为封?封即田千佰。顷畔封也,且非是?而盗徙之,赎耐,可重也?是,不重。”《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在上述规定中,“赎黥”、“赎耐”是法律条文直接规定的赎刑,并非刑罚替代方式。如富谷至教授所指出的,赎黥或许可以认为其正刑是黥刑,但是如果认为赎耐的正刑也是耐的话,那么具体是耐城旦、耐鬼薪、耐司寇、耐隸臣中的哪一个呢?也就是说,赎耐的规定并不能确定其正刑是哪一种,因而,赎耐本身就是正刑的一种。并且秦律中盗窃的量刑是依据盗窃数额而定,对于盗窃未遂的乙而言,并没有盗窃数额,所以对乙规定的“赎黥”应当是正刑,而不是替代刑。 参见前引①,第40—41页。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在这类条文规定中,所谓的赎刑应当是针对特定罪名的定罪量刑,它直接反映的是具体的罪刑关系,因此是独立适用的法定刑,而不是某一种刑罚的替代刑。
赀刑的罚金刑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根据《说文》:“赀,小罚以财自赎也。”赀刑适用于官吏轻微的失职行为,也适用于百姓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因而赀刑与赎刑的区别在于,赀刑在财物数额以及犯罪行为性质上要轻于赎刑。如《法律答问》中规定:“盗百,即端(故意)盗加十钱,问告者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前引⑥。 根据《说文》,尽管赀刑与赎刑有所区别,但是赀刑仍属于“自赎”。《司空律》中的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点,“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 根据上述规定,赀刑仍属于赎的一种,且可适用于没有爵位的人。赀刑的规定体现了赎刑独立刑种的性质,是对犯罪行为直接判处的财产刑而并非其他刑罚种类的替代刑。
汉承秦制,汉初赎刑制度同样具有这两种属性,但赎刑的刑罚性质表现得更为突出。《二年律令·具律》规定:“其有赎罪以下,及老小不当刑、刑尽者,皆笞百。鬼薪白粲有耐罪到完城旦舂罪,黥以为城旦舂;其有赎罪以下,笞百。”从该条规定来看,汉律已将“赎罪以下”作为刑罚种类纳入到刑罚体系中,属于一种轻刑制度。而秦律中的赀刑在汉代则发展为罚金罪。《二年律令·囚律》规定:“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穹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其当击城旦舂,作官府偿日者,罚岁金八两;不盈岁者,罚金四两。购、没入、负偿,各以其直(值)数负之。其受财者,驾(加)其罪二等。所予臧(贼)罪重,以重者论之,亦驾(加)二等。其非故也,而失不审以其赎论之。爵戌四岁及击城旦舂六岁以上罪,罚金四两。赎死、赎城旦舂、鬼薪白粲、赎斩宫、赎斩劓黥、戌不盈四岁,击不盈六岁,及罚金一斤以上罪,罚金二两面三刀。击不盈三岁,赎耐、赎千(迁)、及不盈一斤以下罪,购、没入、负偿、偿日作县官罪,罚金一两。”汉初的刑罚体系根据刑罚轻重由重至轻进行排列,分别为赎死、赎城旦舂、鬼薪白粲、赎斩宫、赎斩劓黥、赎耐、赎千、罚金,由此可以看出赎与罚金分别为两种刑罚方法,且赎罪是重于罚金罪的,但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以交付财产为内容的刑罚方式。随着汉文帝刑制改革,残割肉体的肉刑逐步废止,秦以及汉初律令中的赎宫、赎黥等独立的刑罚制度也不复存在,但是两汉时期仍然存在大量的赎刑规定,如赎斩右趾、赎凳钳城旦春、赎完城旦春直至赎死刑等,前引②。 大多可以用金钱赎罪,汉武帝时期以特权身份作为赎刑适用条件的刑罚方法的赎刑制度逐渐消失,赎刑的性质被确定为以金钱赎免刑罚的替代措施逐渐盛行,并在东汉时期形成定制。参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7—48页。
(二)作为刑罚适用制度的赎刑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关系的变迁,唐朝的刑罚体系逐渐成熟,“赎刑”不再是一种“正刑”,而成为刑罚适用制度,是一种纯粹的刑罚替代措施。唐律中的赎刑依附于笞、杖、徙、流、死这五刑而存在,必须在这五种正刑的基础上方能适用,因而不是独立的刑罚方法。唐律明确规定了赎铜原则,并对每一种刑罚所对应的赎铜数额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参见(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并且规定了若没有财产赎铜的加杖处罚,如《名例律》规定:“应征正赃及赎无财者,准铜二斤各加杖十,决讫,付官、主。”《疏议》:“犯罪应征正赃及赎,无财可备者,皆据其本犯及正赃,准铜每二斤各加杖十,决讫付官、主。铜数虽多,不得过二百。”前引B13,第84页。 即无财产赎铜的,可易科为杖刑,并以二百为上限。《唐律·名例二·应议、请、减》一章对赎铜的适用范围和事由规定了四类情形,即特殊身份者、老小废疾者、过失犯特定罪者以及疑罪。前引B13,第17、48—49页。 值得注意的是,过失杀人的,赎金交付于死者家属,这一点在其他条文中有所印证,如以毒药药人罪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疏议》:“……因即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征铜入死家。”该规定是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雏形,但是这类赔偿并非私法上的赔偿责任,很大程度上只是公法、刑事责任的反射效果依附于刑罚体系而存在,赔偿数额也并不考察实际损失,而是以主刑为标准确定赎铜额度。
宋、元在赎刑的规定上基本沿袭了唐律。而明律中的赎刑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分为两类,即“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明史·刑法志》。 律赎在唐律规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在限制对官吏适用赎刑制度方面,明律规定:“应议者不许擅自勾问,先奏议请,议定奏问,取自上裁,并未减等及准赎之法。”薛允升:《唐明律和编》卷二,《唐律卷第二·名例二》,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与唐律相比,特权阶层适用赎刑在犯罪行为、正刑条件以及程序上具有严格的条件,反映出赎刑维护特殊身份者利益的职能趋于弱化。例赎是指规定于条例中的赎刑制度,由于规定较为分散、多样,所以其对律赎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即“例以辅律”,讲求实用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因而例赎较之于律赎,适用范围更加普遍,几乎扩大到所有的群体。在赎罪方式上,例赎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之名尚存也。”龙文彬:《明会要》卷六十七,刑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303页。 特别是罚役的规定,反映出明朝在赎刑制度上的目的价值由以往恤刑思想为主的立法原则转向实用主义、经济主义,可以说缺什么赎什么,以通过劳役赎刑的方式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虽然这种做法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目的,并且是由宝钞严重贬值、劳动力异常紧缺等政治、经济原因直接决定的,但是赎刑方式的扩大,对于无力支付赎金的犯罪人来说无疑是减轻其经济压力、避免牢狱之灾的出路,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赎刑制度违背平等原则、贫富异刑的缺陷,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劳役负担。此外,明代赎刑继承了唐律中过失杀人的规定,“若过失杀、伤人者,其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家。”《大明律》卷十九,《刑律二·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在诬告收赎条款中也明确要求赔偿受害人损失。参见王新举:《明代赎刑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 此时,赔偿已由传统的报复性、惩罚性属性开始向被害人赔偿的性质转变。
清代赎刑制度在适用范围、赎刑方式上都有所发展。其赎刑分为三类:一曰纳赎,无力照律决配,有力照例纳赎。二曰收赎,老幼废疾、天文生及妇人折杖,照律收赎。三曰赎罪,官员正妻及例难的决,并妇人有力者,照例赎罪。群众出版社编:《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576页。 补偿性的赔偿在清律中也有所体现,如《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规定“若过失杀伤人者,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以为茔葬及医药之资”,这是古代法律中首次明确规定了赎金的赔偿功能。
纵观中国古代中原地区赎刑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赎刑是一项具有多重属性的法律制度。其一,赎刑为法律条文所明确规定的具体刑名,一方面表现在秦代以及汉初属于刑罚序列的赎刑的特殊规定,此类赎刑的适用根据犯罪的性质等主客观因素而定,与身份无关;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赀刑、罚金刑的规定,典型的罚金刑仅存在于汉、晋等朝代,孙力:《罚金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则处于罚赎合一的状态,赎刑的扩张直接挤占了罚金刑的适用空间,赎罚并非对称的关系。其二,赎刑表现为刑罚的替代措施,秦及汉初赎刑的替代刑性质体现在对具有特殊身份者的赎罪、赎刑适用上,与犯罪的性质无关。汉以后赎刑逐渐成为纯粹刑罚适用制度,不具有刑罚方法的性质,在更为宽泛的适用条件下作为替代刑而存在。其三,赎刑具有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面。自唐代起规定了如“铜入被告及伤损之家”的条文,此时的赎刑制度一方面具有惩罚犯罪人的属性,同时在赎金的流向上不同于前两类赎刑制度的赎铜入官,客观上具有民事赔偿的性质,但是这种对于被害人的赔偿的规定形式分散、内容较少,多数仅规定在过失杀伤人的犯罪之中,并且不以权利救济为首要目的,仍属于“赎刑”制度的内容,作为刑事责任的补充而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所以赎刑制度自产生伊始就饱含刑罚惩罚与报复的因素,同时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目的,对于私人的救济,国家并不关心,几乎不被统治者所提倡。
二、赎刑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表达
(一)赔命价制度——少数民族与中原法律文化的融合
在出现死伤后果的纠纷场合,以赔偿金解决冲突是在人类社会早期部落组织的社会常态,人命赔偿金是作为报复措施以维系部落延续的必要手段而存在的机制。在中原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命赔偿金已然从成文法中脱身而出,逐渐与刑罚制度相结合,发展成为替刑措施以及罚金刑。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私和钱”则相当常见,发生人命后,以赔命价的方式双方讲和,命价付给苦主或被杀之家,《元典章》中随处可见的私和钱、打合钱就是吸收了蒙古族的人命赔偿金习惯法并加以改造的产物,参见[日]岩村忍、潘昌龙:《元代法制中的人命赔偿——试论烧埋银与私和钱》,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1期。 形成了“诸杀人者,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的烧埋银制度。赔命价制度是少数民族法制文明与中原王朝法律文化冲突与妥协的适例之一,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于烧埋银,藏区的赔命价制度也是如此。赔命价不仅具有浓厚的民族、宗教气息,同时与儒家思想、传统的中国法律文化相融合,而且在当代也并未绝迹,成为与国家制定法强烈冲突和逐渐趋同的法律现象。
在藏区命案发生之后,经原部落头人或宗教人士的调解,行为人及其家庭给付被害方一定数量的财物或金钱,案件即可了结,这就是赔命价制度。吕志祥:《藏族习惯法及其转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赔命价制度是在中原法律文化输入藏区后,与藏区独特的人文、地理条件相结合而逐渐形成的一项法律制度。唐代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后,吐蕃与唐朝之间的人员往来、文化传播不断加深,包括《左传》《尚书》《汉律》以及《唐律》在内的律法相继传入,中原的法律思想、刑法规定以及刑罚制度逐渐输入藏区,《唐律》的刑罚制度、特别是“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宽宥思想,对于赔命价制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也是赔偿价制度形成的契机之一。文成公主将佛像、佛教教法等带入藏区,大力修建寺院,推动了中原地区的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根据佛教教义,人死后进入轮回,转生于“六道”之中,因而人在被害后灵魂不灭,对于其家人来说杀人者不偿命并不是难以接受的,而即使处死杀人者,他在死后也会进入轮回,因而支付命价对于被害人家庭来说反而更有意义。
据考证,赔命价源起于松赞干布时期的《法律二十条》,与中原地区法律一样规定了肉刑和罚赎,其前四条规定:“争斗者罚款,杀人者以大小论抵;偷盗者,除还原金外,更处以八倍的罚款;奸通者,断其肢体,流放异方;说谎者,断其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西藏社会概况》,中央民族学院1955年版,第64页,转引自陈光国、徐晓光:《从中华法系的罚赎到藏区法制的赔命价的历史发展轨迹》,载《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基础三十六制》中明确规定了赔命价,并在其后世颁布的《吐蕃三律》中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其中规定了故意杀人仍适用“杀人偿命”的原则,赔命价主要针对过失伤害案件,且被害人、加害人的身份地位对赔命价适用规则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加害人身份高于受害人或者身份相近的,可以适用赔命价;如果加害人身份明显低于受害人,那么无论受害人是否死亡,加害人一律处死,并且株连子孙,抄没家产,命价额度也因双方身份地位而差异巨大。参见仁青:《吐蕃法律初探》,载《藏族研究文集》(第2集),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1984年版,第146—150页,转引自淡乐蓉:《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到了元朝末帕主政权时期,《法律十五条》明确了“杀人者要赔偿命价”,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的《十三法》《十六法》也均规定了杀人应赔命。衣家奇:《“赔命价”——一种规则的民族表达方式》,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此后赔命价制度在藏族诸多部落中建立起来,主要内容有:禁止打人、杀人,违者依法论处;杀人者赔命价;命价按死者身份确定,即依照高低贵贱分上中下三等;命价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调头费”,意指劝退复仇之兵,使被害人家属从复仇情感上调头回来;第二部分为经调解确定的命价“正额”;第三部分为“煞尾费”,即通过宗教性和补偿性的安慰善后,双方家庭的仇恨彻底了结,永不反悔。张济民主编:《诸说求真——藏族部落习惯法专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6页。 赔命价制度是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赎刑制度,规定了杀人、伤人案件双方的实体权利,即对什么身份的被害人赔偿多少。由于身份性规定,赔命价不仅是一种解决社会冲突的刑罚制度,更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体制,是以维护特权阶级利益为目的的社会管理制度。
(二)赔命价习惯法的现代发展
不同于赎刑制度在中原地区被废弃的命运,赔命价制度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府的强制废止,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并且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藏区的适用愈演愈烈,被称为“民族习惯法的回潮”。杨方泉:《民族习惯法回潮的困境及其出路》,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 与古代赔命价的区别在于,即便现在的藏区各部落仍然存在制定法,有关青海中部藏族各部落习惯法,参见张济民主编:《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但是这些规则已不再是解决刑事冲突的实体法依据,“赔命价”发展成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的“调解”方式,命价的确定也不以身份层级为依据,而是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在司法实践中,自赔命价制度回潮以来,逐渐与国家制定法趋近,应用于正式的国家司法程序之中,并成为量刑的依据之一。例如下表所摘录的典型案件:案件来源于前引B30张济民主编书,第151—217页。
从上述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赔命价在现代的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命价的赔付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具有明显的影响。在通常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中,赔付命价后被害人予以从宽处罚的情形较为普遍,特别是在死刑案件中,是否支付“命价”成为了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是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执行的条件之一。可以说,只要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赔偿额都可以通过协商确定并得到犯罪人及其家属的认可,上述案件中的死缓判决判处都是双方就“命价”达成一致甚至是在判决前就已赔偿完毕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对于少数民族“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冲突的协调,刑事和解是较为可行的突破口。
第二,即使刑事案件纳入司法程序,赔命价的暴力、强迫、赔偿额高昂的弊病也并未完全祛除。被害人家属集结人马,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加害人及其家属支付命价,加害人被迫赔付,索要“命价”的情况依然存在。例如在闹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中,闹者被假释后,遭被害人亲属持刀追杀,闹者无奈又跑回看守所。闹者的母亲拿了100元现金到被害人家说情,后又请来宗教人士和原部落头人的后裔出面调解,赔偿“命价”6000元,被害人亲属才罢休。参见前引B30张济民主编书,第184—185页。 在这种情况下,“赔命价”是加害人在胁迫下非自愿支付的,成为人身安全免受威胁、摆脱被害人亲属纠缠的“对价”,虽然在客观上弥补了被害人家庭的经济损失,但不具有自愿性和恢复性。
赔命价制度对早期藏族法律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赔命价”作为一项对侵害生命健康行为的财产处罚制度,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和预防性;另一方面,“赔命价”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废除了早期法律中残酷、野蛮的肉刑与死刑,促进了刑罚的人道化、文明化发展。在现当代,藏区赔命价制度由具有实体规则意义的成文法,逐渐演变为民间处理刑事纠纷的调解程序,特别是随着国家制定法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赔命价习惯法逐渐发展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在藏区的特殊适用,正是由于赔命价制度本身所具备的被害恢复、轻刑化以及效率价值与刑事和解制度在价值理念上具有契合之处所致。
中原地区的赎刑制度对于大部分的刑罚种类都可以以金钱赎之,而藏区的赎刑制度更主要适用于伤害、杀人案件中,即所谓的“赔命价”、“赔血价”。更为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原地区的赎刑制度在大部分情况下,赎金是上缴国家的,类似于罚金刑;而藏区赎刑制度赎金的赔偿性质更加明显,虽有一部分“命价”要交给头人、宗教场所等,但是仍有大部分“命价”是直接付予被害方的,因而它更加亲近于侵权损害赔偿。
三、赎刑对于完善现代刑罚体系的制度性意义
梅因曾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的。”[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页。 以赔偿的手段解决刑事纠纷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我国古代以及少数民族的赎刑制度具有阶级性、不平等的一面,对这一点早在汉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另令民量粟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汉书·贡禹传》。 站在现代国家法的立场审视古代法律制度也通常容易放大其“不文明”的、与现代法治不适的一面,赎刑制度也是如此,其所蕴含的轻刑思想、人本主义观念包括制度本身的积极价值往往被忽略。对于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关系,日本学者千叶正士提出了“法律文化同一性原理”,即在一个民族的法律发展变迁过程中,不应让固有的法律文化完全消失,而应在重构与不断的选择中保持法律文化的同一性,并提出在对外国法的移植过程中应以其文化的同一性为标准指导、选择以及阐述。[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清末修律后,我国刑法的发展经历了移植西方—苏俄—西方的历程,这种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中,赎刑制度和它所代表的怜恤观念被人为革除。张兆凯:《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载《北方法学》2008年第6期。 并且在移植过程中始终欠缺对于本土资源的关怀,但民族的历史和其所创造的法律文化不应湮没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赎刑制度以刑赎罪、以赎代罚、以赎减罚等做法应当在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予以充分考量。由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赎刑制度的赎金流向两个极端,中原地区的赎金上缴国家,而“赔命价”中的“命价”则大部分是交予被害人的,因而这两种赎刑制度分别暗含着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刑事和解的属性,其具体规则对于我国完善刑罚体系以及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的落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借鉴意义。
(一)刑罚替代措施体系的建立
现代刑罚结构是以自由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但自刑事实证学派兴起以来,短期自由刑的犯罪标签效应、交叉感染现象以及惩罚与预防效果并不理想的弊端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与反思,短期自由刑的改革成为当代刑罚改革的主题之一。我国现行刑法并未规定刑罚易科制度,学者们多主张借鉴西方国家的易科制度、刑罚替代措施的立法经验,然而我国古代赎刑制度中的替刑理念和易科规则,对于现行刑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一,短期自由刑易科为罚金、劳役。易科罚金是国外法律实践中替代短期自由刑最主要的措施。例如《德国刑法典》第47条第2款规定:“本法未规定罚金刑和6个月或6个月以上自由刑,又无前款必须判处自由刑情况的,法院可判处其罚金。本法规定的最低自由刑较高时,在第1句的情况下根据法定的最低自由刑确定罚金刑的最低限度,30单位日额金相当于1个月自由刑。”《奥地利刑法典》第37条规定:“宣判罚金以取代自由刑……”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41条规定:“犯最重本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台币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罚金。但确因不执行所宣告之刑,难收矫正之效,或难以维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 通过考察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可以清晰地看出,沿袭了数千年的赎刑制度实质上正是以罚金替代正刑的替刑制度,清末修律大规模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赎刑制度被彻底废弃,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在我国建立并一直延续至今,对于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我国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主张引入国外立法中的易科制度,抛弃身份和阶级性色彩不谈,赎刑制度与易科规则本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在完善我国的刑罚制度时,古代赎刑制度的立法经验应当加以吸收和借鉴。
首先,自由刑可以易科为罚金。如前所述,罚金刑是替代短期自由刑最主要的方式,但为我国立法所否认。195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烟毒犯应坚决废止专科与易科罚金办法》中指出,易科罚金“只有利于不法分子用钱赎罪,危害社会,站在人民司法的立场,对此应予坚决反对……对于任何犯罪,也应禁止援引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对自由刑与罚金刑均可选择适用的案件,如盗窃罪,在决定刑罚时,既要避免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又要克服机械执法只判处自由刑的倾向。”现行刑法不仅没有规定易科制度,并且立法者的态度是,即便同时规定了自由刑和罚金刑的犯罪,也不能摒弃自由刑而仅仅适用罚金刑。在世界刑罚轻缓化以及短期自由刑改革的大趋势下,应当增加易科制度的规定,易科罚金是以财产刑替代自由刑的有利于犯罪人的做法,应当得到认可和适用,因而至少首先以罚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的尝试是可行的。
其次,自由刑可易科为社会服务。在世界刑罚改革运动中,以社会服务为代表的行刑社会化措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而早在我国秦代就有了以劳役赎刑的规定,《司空律》规定:“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赏(偿),以另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前引B10。 明代罚役的适用更加广泛,前期以罚役屯田为主,后来扩张为运输物品、造船、养马、种树、充当驿户等形式,罚役的规定既使犯罪人免于牢狱之灾,又满足了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劳役负担,可谓赎刑制度最有价值的部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服务源起于英国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适用于16岁以上实施了可以判处监禁的犯罪的犯罪人,在一年时间内应完成40~240个小时的劳动。如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大部分西欧国家都规定社区服务。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规定为一项刑罚执行方式,但适用于被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犯罪分子,主要功能在于对犯罪人监督管理、教育矫正以及帮困扶助。社区矫正的多年实践为易科社会服务刑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存在建立自由刑易科劳役、社会服务的现实基础。对此,应借鉴我国古代赎刑中的罚役制度以及国外立法中的易科社区服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短期自由刑易科为劳役、社会服务,以减少短期自由刑泛滥之弊病,同时强制犯罪人参加社会服务也是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的有效措施,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
第二,罚金刑易科为自由刑、劳役。罚金易科自由刑是基于罚金刑本身威慑力不足而导致的执行难的问题所提出的替代方法。我国古代的赎刑制度自唐代起就有罚金易科为杖刑的规定,如《名例律》规定:“应征正赃及赎无财者,准铜二斤各加杖十,决讫,付官、主。”前引B15,第84页。 明律中也规定了逆向赎刑,“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绑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明史·刑法志》。 上述规定是对无力缴纳赎金的替代方式,如此形成了以金钱赎刑、以劳役代赎金的连环易科模式。现代的罚金易科为自由刑与这种逆向赎刑模式相类似,都是针对罚金执行难的问题提出的。但是罚金刑易科的逆向转换模式受到了我国学者的批判,认为是对“有利于犯罪人”基本原则的违反,这种对刑罚种类的变更,脱离了据以确定原判刑罚的基础。于志刚:《关于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批判性思考》,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 笔者认为这种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剥夺人身自由的自由刑显然重于以缴纳罚金为内容的财产刑,将不执行罚金刑判决的易科为自由刑,特别是无力支付罚金的易科为自由刑,显然加重了对犯罪人刑罚,并且违背了罚金刑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的初衷。明律中“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的规定就比唐律中“赎无财者加杖”的规定更加人性,以劳役替代罚金较之于以正刑替代罚金更利于犯罪人,这种劳役赎刑的模式正是现代刑罚制度改革所提倡的劳役、公益劳动等社会化行刑模式的雏形。罚金刑易科劳役所具有的预防、教育作用以及经济效应当引起重视,我国罚金刑的执行实行定期缴纳、分期缴纳、强制缴纳、减免缴纳以及随时追缴制度,而未规定罚金刑的易科,对此有必要借鉴罚役赎刑制度,将劳役作为最后手段规定于罚金刑的执行制度之中,在对犯罪实行上述罚金等制度后,仍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可以考虑易科为劳役、劳动改造或是社区服务等措施。
(二)赎刑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封建法制的刑罚观一方面体现为严刑峻法,主张以重刑达到威慑民众不敢犯罪的目的,即以刑止刑,因而死刑罪名繁多,且同样是生命刑,根据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区分出多种痛苦程度不同的执行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德主刑辅”、“宽仁恤刑”,姜涛:《〈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载《法学家》2013年第3期。 对于死刑的适用在对象、疑罪以及执行程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其中,赎刑作为“赦宥”制度的一种,实质上起到了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并且这种限制模式形成了一项确定的法律制度。赎刑制度自产生伊始就是针对肉刑以及死刑的赎免,《尚书·吕刑》中“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就是以赎刑替代死刑的规定,秦汉时期死刑均为赎刑的种类之一,如《司空律》中“葆子以上居赎刑以上到赎死,居于官府,皆勿將司”。前引⑩。 汉初也规定“赎死,金二斤八两”。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唐律》中“死刑或斩皆赎铜一百二十斤”的规定也将死刑作为赎刑的对象之一等等。在一定情况下,对于特定人群死刑并不是必要的,对于他们赎金免死,既施以一定惩戒,同时也体现了法律和社会的恤刑和宽容。对生命的尊重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基本精神,赎死的规定正是法律的谦抑性、怜恤性、宽容性等人本主义价值理念的体现,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限制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应当为我国现代刑事司法所借鉴。
在藏区,宗教对于民众的生活具有强烈的指导作用,藏传佛教禁止杀生,倡导人们弃恶从善,在这样的宗教观念支配下,人们认为杀人本身就已是罪恶,以命偿命同样是在犯罪孽,因而主张以赔偿代替复仇,赔偿额的一部分用以填补被害方的损失,一部分捐给寺庙对死者进行超度以告慰亡灵,所谓的“命价”不仅使被害人家庭获得实际利益,而且维护了生命的尊严、满足当地群众的宗教情节。现代刑法以公共权力实施死刑来报复犯罪对社会利益的侵犯,而在民族地区则将犯罪视为对个人的侵害,因而被害方对加害人享有绝对的处分权,享有对犯罪行为予以谅解的权利。
我国古代中原地区的赎刑制度以及少数民族的赎刑制度都是通过支付财物的方式在客观上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其背后的人本主义理念对于立法、司法上的恤刑慎杀具有强烈的影响,我国现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与之一脉相承。此外,在制度上需要借鉴的是,犯罪人的赔偿能否作为罪后因素影响死刑的裁量。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即只能适用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侵犯财产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以及除渎职犯罪以外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所以死刑案件是不能够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上没有肯定赔偿对于死刑限制的影响,但在司法实践中这已成为通行做法,并且司法解释以及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也肯定了犯罪人的民事赔偿对于死刑裁量的影响,对此,学界和社会公众不乏批判和否定的声音,认为这是“花钱买命”。笔者认为,应当借鉴赎刑制度,对死刑的限制在司法层面打开一个突破口。在死刑裁量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要求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严”体现在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宽”不能理解为只能针对轻微犯罪,死缓的合理适用也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少杀慎杀政策的贯彻落实。被告人积极赔偿、认罪悔罪的行为属于表征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低、改造可能性较高的酌定量刑情节,因而,对于积极赔偿、认罪悔过的犯罪人,可以酌情适用死刑缓期执行。
可以说,与死刑的报复性相比,“赔命价”更接近于谅解、宽恕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在人类社会向废除死刑的文明发展中,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习惯法比国家制定法走得更远。“赔命价”制度在尊重被害人意愿以及排斥“杀人者死”这一传统固有的报复理念上,是有着积极的价值的。我国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的完善应当吸收其精华部分并加以充分利用,使赎刑制度在现代刑事法理念的指导下与国家制定法形成良性的互动,在对民族习惯法进行规范性整合的基础上,也对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Abstract:The redemption penalty is a unique leg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The redemption system in central plains has dual attributes of either an alternative penalty or an independent penalty during the Qin and the early Han Dynasty, which has developed into a general application rule of penalty since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laws in ancient China, the fines penalty is usually combined to be applied with the redemption penalty. The redemption penalty in minority regions can be well represented by the fines penalty of “compensation for life” applied in the Tibetan area, which was regulated as statutes in ancient times but indicates obvious nature of 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value and reasonable rules in the redemption system should be well learned and understood so as to improve the alternative penalty measures and the judicial control of death penalty in the present penalty system.
Key words:redemption fines of compensation for life penalty system
[作者简介]夏小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① 典型的文章如王涌:《中国需要一部具有商法品格的民法典》,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蒋大兴:《论民法典对商行为之调整——透视法观念、法技术与商行为之特殊性》,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赵万一:《中国究竟需要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兼谈民法典中如何处理与商法的关系》,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6期等。
② 2015年中国商法学会针对民法总则草案组织了多次研讨,重点讨论了商事法律关系、商主体、商行为等内容如何纳入到民法总则之中,而在既有的草案之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③ 例如王利明:《民商合一体例下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周林彬:《民法总则制定中商法总则内容的加入——以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一般规定条款的修改意见为例》,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蒋大兴、王首杰:《论民法总则对商事代理的调整——比较法与规范分析的逻辑》,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