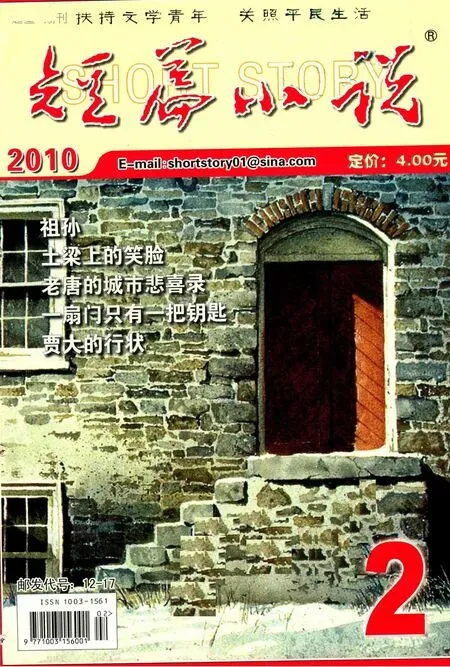针毙
◎肖德林
针毙
◎肖德林

1
龙二是我们沟头村最让人指望,又最指望不上的人。
1986年,我8岁,刚在沟头村上小学,浑身起疙瘩,发痒,流脓,结痂,散发着臭气,不得不一次次到村卫生室涂药抹水,挨龙二戳。龙二是这里唯一的医生。
在村人眼里,龙二是个废人,一条腿细得像芦柴——从小患上腿病,是个瘸子,连个老婆都没娶上。龙二除了会打针挂水,弄点药物抹抹,看不出他有什么大本事。那么多病人把希望落在他身上,然后还是一步步地走向死亡,最后终于茶水不进,埋进泥土。龙二孤独地坐在村卫生室里,几乎不敢抬头,他听着外面办丧事哇啦哇啦的唢呐声,仿佛是放大了的哭泣。他曾分辨过这些死者呼吸里哪怕细微的异常,为一线血丝焦躁不安,但现在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被抛在这声音之外。龙二落寞地在沟头村走动,有时像个鬼影,在河堤上徘徊。
每次去龙二那,我都希望是最后一次,可是下次还得来。
龙二的卫生室挂满了光屁股的人体图,那些箭头指着五脏六腑,令人害怕,闻到特殊的酒精味道,村里所有小孩都会胆颤心惊,怕挨针戳。
龙二的煤油炉上煮的是针头,酒精炉里传出丝丝的声音,龙二揭开铝盒,蒸汽“嗡”的一下散开来,透过这些蒸汽,我看到一盒子针头纪律严明地躺着。龙二用镊子轻轻拌一下,针头与铝盒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炒了一锅螺蛳。龙二细心地捏出一根针,装上针筒,对我说,屁股。龙二边说边用小砂片在细细小药瓶的脖子上划了一下,然后握在左手中,大拇指一掰,瓶子发出一声闷响,龙二伸出右手的长长针筒吸干瓶子的药液,“吱——”一声,像老牛喝干了槽中最后一口水。龙二向空中挤了挤,排除里面的空气。咦——龙二见我没动,又说:屁股——我呆呆地盯着那个针头的屁股,忘记了浑身的痒,我说:能给我一根报废的针么?打弯的或者用久的,一根就行。我特别想要那支针头,是想做我的炮纸枪。龙二轻蔑地笑笑,快,屁股——没办法,我撅起屁股,龙二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一针——酸死我了!
打完针,龙二昂着头,像要打喷嚏的样子,其实他是看窗外,看窗外那棵老杨树又遮住了屋里的阳光,他对那棵树毫无办法。几只苍蝇像喝醉了酒,在屋子里东撞西撞的,有一只一头撞死在玻璃窗上。讨厌的苍蝇!龙二说。我知道,他是在说我呢,我身上流的脓水,招惹的除了蚊子就是苍蝇,苍蝇就像我最亲密的朋友一样,我到哪,它们就嗡嗡地跟到哪。
龙二对我的病,好像不在意。他整天皱着眉头,好像在考虑全村人的病。他说,他脑子里有一张图,病号是黑点,像蚂蚁,天天吞噬他,一刻不得安,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托腮瞎想,是他的头疼病又犯了。村里卫生室原来是个老先生,赢得满村人的敬重,他不仅能治病,还能算命,当神匠。老先生干不动回家,龙二就到了村卫生室。因为龙二有文化,考了几年大学,没考上,回家,本来要去打工,老村长是个爱才的人,学过辨证法,说:废人用对了地方就是宝。
龙二每天痛苦地躲在角落看书,再不然,托腮数苍蝇。他的脸越来越苍白,我们皮肤的颜色都是硬邦邦的古铜色。苍白,在我们沟头村可不是什么好颜色,苍白就是一张纸,随时会被撕裂。我说:三叔,你不是病了吧,村里人病治不好,又把自己搞病,你还不如出去打工,城里阴沟里淌的都是钱。说到最后,我笑了。龙二有点恼了,挥挥手,你个小屁孩懂什么!我笑起来:是个屁,是个屁。我皱着鼻子搧风。我似乎闻到了一丝尿骚味,我想起昨天夜里尿床,现在内裤上还尿迹斑斑。
2
龙二最希望出现一个“田螺姑娘”。按道理,一个赤脚医生,即便是个瘸子,在村里找个姑娘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龙二就是个单身。这是个谜。村里流传着一个龙二的笑话。每年的大年初二,是沟头村新女婿上门拜年的日子,丈母娘款待新女婿总有一碗炒米蛋茶,放了蒜花,挑了猪油,还有鲜美的酱油,每个新女婿都以吃上丈母娘的炒米蛋茶骄傲。龙二某年大年初二,突然心血来潮,冒着严寒,做了一碗炒米蛋茶放在床头,然后躺在被子里,估计蛋茶不太烫,假装有丈母娘送蛋茶到床头:龙二,吃蛋茶。龙二尖着嗓子叫自己,然后有模有样地应一声,来了——自己穿新衣,哪知道,袖口一甩,蛋碗哗啦着地,忙了半天,一口汤也没喝上。
没有人向龙二验证这个故事的真假,所有人都这么说,我们看龙二的时候,这个笑话就在脑子里翻跟头。
龙二是一个喜欢阳光的人,黑夜让他充满担心。相信阳光,阳光能治愈许多邪恶的病,龙二作为无能村医时常说。卫生室在沟头村的最高处,这里有沟头村最好的阳光,龙二突然有一天发现门前的大杨树长得太高,遮了阳光,他要把它砍掉,全村人都认为他犯了神经病。
反对最凶的是卫生室前面玉芳家。玉芳的妈,像软面条,瘫在床上。这是一个害怕阳光的女人。这对母女刚到沟头村的时候,带来了许多城市的气息,她们也给家家户户送上大城市里的好东西,后来东西送完了,新鲜劲过去了,终于没了上门人。玉芳妈天天躺在床上看杨树,听鸟叫。通过杨树上颜色的变化,玉芳妈就知道春天来了,夏天去了,特别是那些鸟,她几乎能通过声音辨别它们的名字。玉芳是个“杨辣子”,比男孩还嚣张,一听龙二要砍树,举着把镰刀,要把龙二的脑袋割下来。玉芳一看就不是我们沟头村土生土长的种,她面孔白皙,黄毛,重要的是她说普通话。龙二好脾气,受了气,自己在卫生室叹气,叹完气,还得收拾药箱,走进那个阴暗潮湿的屋子里,给玉芳妈打针。
但我们小孩被家人警告:不许上玉芳家门。玉芳妈是村里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她的来路糊涂。村里人说,玉芳妈从小就是一个不安份的女人,她16岁离开村子到大城市闯荡就没回来过,家里人死光了,她倒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女儿,可从来没有看过她女儿的爸。玉芳妈得了什么病,村里没人说得清,问龙二,这个蹩脚村医嘴里含了一只死老鼠,听半天,不知说的啥。龙二不断要去挂水,挂完水,玉芳妈就躺在床上看树叶,睁着一双空洞的眼。
有一天,我感觉龙二心神不宁,不断对我说:你这个臭味,到太阳下曝晒,晒出紫泡来,晒出紫泡来就好了。我心里说:你个没本事的东西,我要能晒好,还要你干嘛。
前屋突然传来摔东西的声音,我想是一只瓷碗在这个尖锐的声音里走完了一生,后来又传来一声更大的声音,可以肯定是一摞碗灿然碎成瓦片,玉芳毫无顾忌地哭起来,我想是不是有巴掌落在她脸上,想想她平时嚣张的样子,感到很解恨。龙二弹簧般跳起来,冲到前屋去,把我的半个屁股晾在空气里。我半提着裤子,扭着腰,伸头看那个黑乎乎的窗户,希望看到龙二如何平息这场混乱,可惜只是看到一个人影,然后玉芳止住了哭,一个悠悠扬扬的哭声,也终于止住。
一片寂静。
虽然我和玉芳互掷泥块,打得浑身疼痛,甚至互相打破头,但是我更害怕她家那个脸色苍白,来历不明的妈。她像黑暗里的一只猫,其他都可以隐形,只是那双眼睛,冷冷地发着光。
我像害怕一座坟墓一样害怕那座房子,走路尽量不看它。这个房子其实是座公房,原来是养猪的。因为玉芳妈得了怪病,村里的大先生说,犯了神邪,必须拆掉原来的老屋子。原来的老屋子在高高的河岸上,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大先生说,玉芳妈是被野鬼缠上了。村长一听,大手一挥,拆!于是养猪场成了玉芳的家。本来这卫生室挨着猪场也有为猪治病方便的考虑,也就是说,龙二还是一位兽医。此举曾遭大部分村民反对,谁不知道,兽医手脚重。村长飞着唾沫说:谁来当兽医?村里再养不起一个闲人,兽医人医,反正是个医,都要吃药打针,理就是那个理!村长的嘴是沟头村最宽阔的嘴,宽阔得能瞬间吐出世界上所有的真理。
反对的人只好闭嘴,在大杨树下扇扇子。猪场的臭味不断飘来,越扇越臭,只好扔了扇子对着村长的背影呼气。
猪场已经废弃,猪场烧食的屋子成了玉芳家住处的时候,也就是说,龙二已完完全全是个医人的村医了。
3
龙二气咻咻地回到卫生室,他很激动,面色潮红,不断搔头叹气,心事重重,对给我打针心不在焉。不断唠叨:叫你晒太阳,晒太阳,你就是不听!我白他一眼,你给针头帽,我明天就去晒太阳。
我终于知道龙二娶不到老婆的原因,龙二不仅腿不好,还会在深夜“画地图”,只是工具不一样,人家用的是笔,他用的是下面的东西——他尿床!这是我们干的事,现在,我已经红着脸跟我妈妈指天发誓,我绝不再干,我妈妈担心地说:你再“画”,就会和龙二一样成个光棍,蛋茶都喝不上一口。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突然很兴奋地说:他尿床,还治我?我鼻子里不屑地发出一个声音。我妈自知失言,慌乱地说:小孩别瞎说!
龙二喜欢晒太阳,原来也每天夹着湿漉漉的裤裆上班,晒的是内裤。
我想看他的床,更想知道他如何尿床。我想深夜,他的尿床会和老牛撒尿一样,排水量是我们的几倍,滴滴答答满地都是。龙二在卫生室有一张床,我特别留意打量一番,齐齐整整,被子叠成方块,比我狗窝似的床高尚了许多。
我那天犯了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晚上,我举着油灯翻看连环画时,不小心把我妈一件纺丝绸衬衫烧破了一只角,衬衫被我妈叠得像块彩色豆腐,一烤,这块豆腐糊了。这是我妈走亲戚时唯一的脸面,我妈的脸面破了,不撕破我的小脸才怪。
我吓得逃出家门,在村庄游荡。
天黑透了,虫子唧唧叫成曲子,我知道它们好心催我入梦,它们哪里知道我现在有家归不得。
我真的不是要听墙角,听墙角在我们沟头村不是光明磊落的事,但是现在我倚在卫生室的西北墙角上,这样我不得不准备听龙二的鼾声,重要的是我要验证龙二是否画“地图”。墙角的味道不好闻,我知道村里几只无家可归的狗经常叉着后腿在红砖墙上画“地图”,那些绿盈盈的青苔经常承受它们的润泽,它们你情我愿。现在熏得我一阵眩晕,好在我是一个能不断散发臭气的人,很快适应,以毒攻毒。龙二的屋里似乎没有声音,一点黯淡的光透出来。龙二不见了。“十”字药箱还在,龙二应该没有出诊。我本来想进屋去偷针头,现在真是一个好机会。
但是我听到前屋好像有声音,改变了主意。黑暗里,玉芳家鬼屋已经不那么可怕,大杨树倒成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
现在沟头村正沉沉睡去,走路的狗都小心翼翼。玉芳家屋里有微弱的光,我想玉芳早就睡得人事不省了。龙二坐在床头的一张木凳上,影子在墙上不安分地扭动。玉芳妈躺在一团黑暗里,输液瓶拖着长长的尾巴。
龙二说:今天白天耽误了,只能晚上给你挂水。
停顿一会,龙二似乎是没话找话说:城里真的很热闹,你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玉芳妈咳嗽一声说:外面虽然五颜六色,样样新奇,可也像个花脸魔鬼似的长着牙齿呢,不小心就会被吞掉。
停顿一下,玉芳妈说:我很早从沟头村出去闯世界,闯得头破血流,闯得一身怪病,去过多少大医院都没能治好,现在回到沟头村已是一床坏棉花胎。我本来想死在外面的,可是玉芳,我要把她带回来,替我好好活着,好好呼吸沟头村这些新鲜的空气。我不能给她一个爸,但是我还有根——
龙二说:你会好的,一定会好,晒太阳,阳光是一味灵药,能治百病。你怎能害怕阳光——
一声长长的叹息:我这个绝症,羞死先人,哪能在村里抛头露面!
龙二不吱声,拧着头,想一会说:村里没人知道,不会有人懂。这是一个秘密。
女人提高了嗓子说:别骗人了,这还能有不透风的墙?我现在就想死,你别给我挂这些盐水,没用的。
我心里一拧,以为她看到了我,迅速蹲下来,我闻到呛鼻的尿骚味。
龙二说:你挺一挺,这个坎就会过去。
女人动了动身子,药水管子晃了晃,盐水一滴一滴地注入她的体内。
女人说:你抱抱我,我冷,我冷呀——
龙二站起来,又颓然地坐下。
女人笑了,你怕了?怕了呀——
龙二也笑:我不怕,虽然我没啥本事,我还是医生,医生怎会怕病人。
女人说:你摸摸我。我孤单,当年也许嫁给你,我们……谁叫你是个瘸子呀,你那条腿……龙二坐着没动,说:我……我……不配。
龙二很慌乱,鼻音很浓,堵上了什么。
你给我把针头拔掉!女人命令道。治不好的,我现在骨头里爬满了千万只蚂蚁。
龙二不动。
也许我不该回来呀,我在外面喂狗也比在家丢人现眼强——
龙二搔耳挠腮,一个劲地说:要晒太阳,明天就出去晒太阳,你再不能窝在床上了,这……这,不好……
女人开始啜泣。
我浑身瘙痒,痒得不断蹭墙,泥块落地的声音终于惊动了屋内人,龙二惊慌地问:谁?
我比他还惊慌,一溜烟跑了,好在是黑夜,没人在黑夜的眼力比我好。我已经忘记我妈正在家里准备扇我的耳光。
4
现在我能理解龙二为什么一次次冲向那个可怕的屋子。大多数时候,他是沉默的,有时会烦躁不安地炒螺蛳一样炒那些放在钢饭盒里亮晶晶的针头,弄得满村子酒精味。我对他不抱希望,玉芳妈那病大先生作法祛邪都没治好,龙二给她治病,只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我现在同情这个女人,她的那个莫名病的苦痛似乎长在了我的心上,应该比我的痒痛苦百倍。
缠在玉芳妈身上无处不在青面獠牙的鬼它又在哪里?我时常痛苦地寻觅。玉芳告诉我,鬼可不一定青面獠牙,它可能变成一朵美丽的花,或者变成一只嗡嗡飞的蜜蜂,在你想也不想的时候撞上你。它们会喊你的名字,你千万别答应,你答应了,你的魂魄就被吸走了,你就变成鬼了。我一边奇怪地笑着,一边后退,然后拔腿就跑,玉芳不是鬼魂附体了吧?
我制作了一柄7寸长的木剑,老先生说剑上喷上猪血就可以斩杀厉鬼。我选的是村里最古老的桃树,桃树是吉祥的树,吉祥得妖鬼遁形。我对玉芳说:龙二真是个“屁”,他没本事治好你妈的病,挂上我的桃木剑,你妈的病也许就好了,大先生说的。玉芳对这柄桃木剑没有我期待的惊喜,这让我很受伤。为削这柄桃木剑,我用尽各种木匠工具,特别是剑锋,我在磨刀石上磨了又磨,用镰刀削了又削,它的锋利,在我眼里不亚于一把匕首。
玉芳说:我妈恐怕好不了了,她已经吃不下饭。
我说:你挂上这桃木剑,应该灵的。
现在对于是否在剑身上溅上猪血,有点为难,哪里去弄猪血呢?我想到龙二曾经是兽医,兽医的粗大针管可以不费力地抽猪血,这事我看龙二干过。
哪知道,龙二非但不借给我兽医针筒,还把我的桃木剑扔在一边:小孩子,搞什么名堂!
我去找大先生,大先生眯缝着看我,嘴边咧开一道断裂的笑纹:傻呆子,你撒尿就行,童子尿!
我站着没动,我不知道这个瘦削麻子说话的真假。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大人们的话。后来我问我妈,我妈奇怪地看着我:你问这干什么?我不答。但是从她肯定的眼神里我知道了答案。
虽然浇上童子尿,但是我还是不会作法,那时候我在看电视剧封神榜,笃信姜子牙,我看遍全村,老麻子就是我们的姜太公,我希望他能传点技法给我,谁知他愣半天也没给提供一句咒语。
我想放弃这柄剑。玉芳看看我,翘了一会儿小嘴,突然说:算了,看你好心,算不定真能砍死小鬼呢。我听着玉芳芬芳的普通话,开心死了,说实在的,比我们那个蹩脚老师的普通话强十倍。在班上,因为臭气,没人愿意跟我玩,我一个人一张桌子,躲在角落里,因为老师实在没本事找出一个愿意和我同桌的同学。
这样我的这柄浇了童子尿的桃木剑就挂在了玉芳妈的床头。走进阴暗的屋子里,我才发现,玉芳和她妈不睡在一起,远远地搭块破门板,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角落里。玉芳小声告诉我,她妈不许和她靠近,怕病传染。我心里一拎,虚虚看她妈妈一眼,拔脚就溜,她妈睁开眼,向我微笑,可我没敢细看。
5
我的剑挂在玉芳妈的床头,我的心就长在上面了,我随时希望它能飞起来,斩杀鬼头。女人确乎也在好转,最明显的变化是开始晒太阳了,当然这个太阳晒得很艰难,得躺上藤椅,然后抬到阳光下,人前人后忙得最欢的是龙二。
我等来的却是玉芳妈刺破自己的手腕,用的是这柄剑。玉芳妈的病太痛苦,她不想让这个病彻底爆发,她要用命来换这个病的秘密。幸亏龙二发现及时,龙二狠狠地瞪我一眼,把这柄剑扔到地上,剑狠狠地戳破地,立着。我六神无主,犯了天大的错误。我怨玉芳妈,你要自杀,用什么不好,非要用上我的桃木剑不可?这柄桃木剑从此下落不明。
就在这个夏天,我浑身的疙瘩被晒出紫泡,然后它们开始消退,臭气开始减少,我知道冬天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好,我去龙二那的次数逐步减少,终于不再去。
一天,村里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是那个苍白的女人死了。一定有鬼叫她的名字,她一定是答应了。玉芳现在是个孤儿,臂上戴起宽大的黑袖章,衬着玉芳小小白白的脸。玉芳不说话,她围着大杨树一圈圈转着。谁叫也不答应。我说:玉芳,你看天,你妈当仙女去了。我们看天,天上云飘云散,仿佛真有一个仙女踏着云朵衣袂飘飘,飘着转到一堆云山后面了。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一个讨厌的挂着鼻涕小伙伴,跳跃着说。
玉芳瘪着嘴说:她怎么不带我,怎么不带我呀?
我说:那你做梦,梦里想什么有什么,梦里你就可以腾云驾雾。
第二天,玉芳告诉我,夜里,她妈妈来看她了。
不久,龙二被逮了起来。龙二屁本事没有,把女人医死了。他用“阳光疗法”给玉芳妈治病,什么阳光疗法?村里人鄙夷地说,在女人挂的吊针里注入了好多空气。龙二说是满瓶阳光。尽管满针筒阳光,龙二因医术太差,过失杀人,坐上了大牢。好在是自首,没被毙掉。
2015年春天,沟头村最大的变化是村组合并,合并后村部搬到了另一个村上。村部搬走了,猪场推倒,移植了一片水杉,树影婆娑,卫生室更孤单,被笼罩在巨大的阴影里,成了一枚被抛弃的黑棋子,等待腐烂。我见龙二在太阳下挠头,头发稀疏花白,面皮还是白,与沟头村田地里求食的人到底还是不一样,那条瘸腿在阳光下不停颤抖。当年,刑满释放回到沟头村,作为一个废人,如何安置龙二,村里费煞脑筋,老村长说:还是给他安排在卫生室,不许医人,只许医兽。这时候,村子里家家户户养猪,大力发展畜禽业。这是老村长最后一次行使职权,第二天他就缴公章回家了。
龙二看到我来,说:我家玉芳说要回来的,可能明天吧,哎——这也说不准。
他现在是玉芳的爹。村里人都翘大拇指,可怜的玉芳跟着这个瘸子爹,走的是正路。龙二也到处说玉芳就是“田螺姑娘”呢。
玉芳现在在城里开店。我想起玉芳,似乎又看见她妈死的那天,她不说话,抱着一棵大杨树,孤独地一圈圈转,一圈圈转……突然抬头惊慌地对我说:天和地怎么都旋转起来啦……
我看见她满脸的泪水。
等玉芳在城里挣了钱,我就要在这砌房了——这里的阳光多好呀!
龙二手搭凉棚,指了一下天对我说。
踟蹰片刻,龙二向我招手,神秘地掏出一个报纸包,是那柄桃木剑,现在已是一截老木头,落满岁月的灰尘,我知道这灰尘下面曾经喂过我的童子尿,还有玉芳妈的……血。
沟头村没人知道玉芳妈得的什么病,人们早就忘了追究。
这年年底,卫生室彻底关了门,兽医要资格证,龙二也没得当,沟头村从此再无村医。龙二无家可归,自己的老屋早坍塌了,只能在村卫生室看门,龙二贴了副对联:“门庭冷落 关门大吉”。
不久,龙二病了,很重,他医不好别人,更医不好自己,一个人躺在卫生室的破床上,等死。其实,全村人都知道,他等谁。打电话给城里的玉芳:你爹没几天活头了,你回家看看。玉芳啜泣着说:……我哪里有爹,我只有妈,被他针毙了……
村里人没听懂“针毙”这个词,但意思是清楚的,没人敢告诉龙二。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