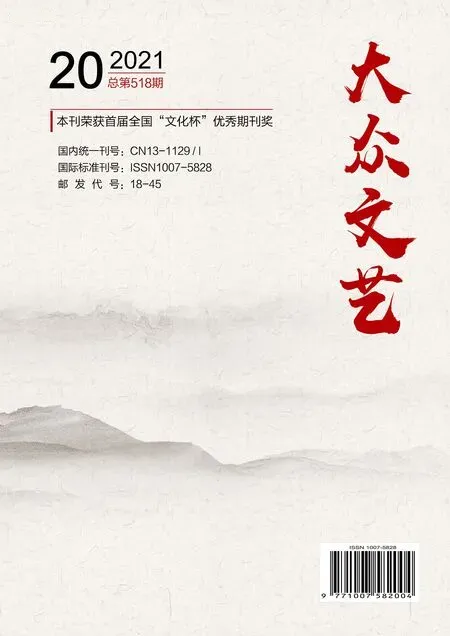博物馆的空间规训与空间权力
——以国家博物馆为例
何智文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100044)
博物馆的空间规训与空间权力
——以国家博物馆为例
何智文 (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 100044)
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致力于探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并从空间维度上探究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在空间上利用规训技术来对人体进行分解并施加微妙的强制从而体现对微观权力的生产。本文将以福柯的空间理论为出发点,以国家博物馆为例,探讨国家博物馆对于参观者的空间规训作用和对参观者施加的空间权力,以明确人在博物馆中的自觉形成参观行为的原因和人获取知识的过程。
博物馆;空间规训;空间权力
一、研究背景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博物馆内部布局的优化,展品的呈现方式日渐丰富,展品的布展结构也日趋满足观者的观展逻辑,人与展品的互动性也随之增强。但在人与展品的互动过程中,一种无形的力量和约束在影响着人的参观行为和文化认知,即福柯所提出的“空间规训”和“空间权力”。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博物馆快速普及发展、博物馆资源的极大丰富的时代,博物馆的“空间规训”和“空间权力”也通过博物馆本身的不同方面向参观者发挥着作用,规范着参观者的参观行为,并形成知识传播的过程。可以说,博物馆在文化传播和教育民众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国家博物馆对参观者的空间规训——参观者自觉形成参观行为的原因
(一)国家博物馆的空间设计、地理位置和意识形态对参观者个体的监视
与监狱的垂直化全景敞视的空间结构不同,博物馆基于展品的观看效果呈现出平面的空间结构特征。在这样的空间段落里,时间的空间化使得物的铺陈是一种线性的渐进链条。1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的内在的空间设计、展品摆放的顺序以及一些基础空间架构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参观者无限延伸的视野,对参观者的浏览行为具有细致微妙的强制,从而控制和引导着参观者的参观行动。同时,国家博物馆实际上是被精心建设的一个知识领域(权力领域),一个认知、行为和心理的教育场所,其空间内部设置的规章制度也在规范塑造者参观者。
此外,国家博物馆的空间位置处于北京天安门的东侧,其规划布局既顺应了中国“左祖右社”的传统文化理念,又具有强化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作用,可以说,国家博物馆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空间位置的设定赋予了国家博物馆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的审视视角,使参观者在参观行动进行之前便在思想上受到了意识形态的规训。
(二)国家博物馆空间对个体的改造
罗兰·巴特在游览巴黎铁塔之后写道“当我们望着它时,它是一件物体;而当我们去游览铁塔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目光,并因此构造着作为其注视对象的既 伸展于又收拢于其脚下的巴黎。”2同样,对于博物馆而言,参观者在主动观展的过程中,也已经处于博物馆的“监视”和“管理”之下,即观者已经被置入空间的规训过程中,他们必须通过改造自己的行为从而被动地接受这种规训。这在一定的空间之中,则表现在博物馆引入监狱的透视关系,即“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部人员、接等级体系的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3也就是说,参观者在不同展品面前逗留或移动,都受到博物馆内部管理人员目光的监视与潜在的约束和管理,从而实现对参观者个体的改造和监视。
在《乾隆南巡图》所处的展厅以及中国古代史展厅,每幅图或每个展厅空间段落之中,都存在国家博物馆配置的管理员,这些管理员的配置起到两种作用:第一,监视参观者的参观行为,即时刻注视参观者是否存在不当的参观行为;第二,实现对参观者个体的规训和改造,对参观者不当的参观行为进行管理,或起到对参观者参观行为的引导作用。
三、国家博物馆对参观者的空间权力——参观者接受知识的过程
(一)权力将知识构建为真理——权力实施的前提
博物馆作为重要的知识媒介,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的作用和权力首先外化于博物馆对文化资本的持有4和积累。正如福柯所提到的,知识与权力相交织的过程中,知识获得真理的地位,真理制度产生。真理以流通方式与一些生产并支持它的权力制度相联系, 并与由它引发并使它继续流通的权力效能相联系。知识的传播策略总是不断地自我调整 , 使得权力得以更完美的运作5。国家博物馆凭借着自身国家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地位,将大量的国家级和世界级的宝藏收藏与积累,并通过向社会大众开放或文化展览、文化活动等形式,将通过展品收集而获取的知识内容(即“真理”)与自身的权力地位相联系,发挥知识传播的权力效能,将汇集的文化藏品的知识内涵作为其知识构成的主要方面,向参观者传播,发挥博物馆权力。
此外,博物馆的权力还内化于对参观者的塑造。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厅对展品资源和知识内容的汇集和传播,其目的在于将参观者塑造成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增强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同时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和危机感,培养民众的公民责任,以此实现博物馆权力的实施。
(二)交往关系传播知识——权力实施的中介
交往关系是参观者个体间或群体间以符号传播为媒介的信息传递方式。权力关系介入交往关系,通过对符号的监视、控制、搜集和分析,把人变成知识的对象。6对于国家博物馆而言,参观者同博物馆施加的权力和博物馆的知识体系构成博物馆的权力关系。在参观者所处的权力关系与国家博物馆安排的专业人员的交往关系中,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对展品的形态、渊源等信息符号搜集后进行传播,将参观者设定为知识传播的对象,从而实现国家博物馆权力的实施。
(三)大众媒体加快知识扩散的进程——权力运作的推进器
福柯指出,“现代媒体与当代权力关系网络之间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社会控制网。”7大众媒介的应用,加快了知识扩散的进程。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对传统博物馆服务产生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为博物馆的升级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随着新媒体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在增加了人与展品之间的互动之外,还丰富了博物馆的职能与作用。在国家博物馆中,目前应用到的新媒体技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可识别智能标记的运用,帮助参观者实现对展品信息的捕捉和呈现,如中国古代史展厅中的展品信息二维码,参观者可利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获取展品全面的信息;第二,数字动画技术的应用,如《乾隆南巡图》展厅中的数字动画,将乾隆南巡图部分卷轴的内容利用数字技术拼接起来,向参观者呈现动态的历史再现;第三,国家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和官方微博的设置,将国家博物馆的高深文化“落地化”,并配合服务功能,拉近受众与国家博物馆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大众媒体在国家博物馆中的应用,起到了服务大众、加快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福柯致力于考察权力和规训如何在空间向度上发挥作用,这为国家博物馆的空间权力和空间规训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我们得出博物馆的空间规训作用(参观者形成参观行为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博物馆的规章制度对参观者的规范、博物馆的建筑结构、空间位置和意识形态对参观者行为潜在的约束以及展品前监视者的安排对参观者行为的改造。而博物馆的空间权力(参观者获取知识的过程)则体现在博物馆通过搜集归纳展品的文化知识、讲解人员的对展品信息文本的传播以及大众媒介技术的应用,从而向参与者传播展品知识,扩展展品知识传播渠道,普及藏品教育,实现空间权力的实施和到达。博物馆的展厅设计和结构建造对博物馆展品更好地呈现、博物馆文化的传播提供具体的外在条件,而博物馆的空间规训和空间权力则在约束参观者行为、构建参观者文化认知、向参观者传播展品知识、普及艺术教育方面则起到了抽象的本质作用。
注释:
1.张霖源.展示的秩序:现代博物馆空间的拜物幻象[J].云南社会科学,2015(03):172-178.
2.罗兰·巴特,李幼蒸译.《埃菲尔铁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
3.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等译.规训与惩罚[M].三联书店,2003:231.
4.徐梦可.博物馆的空间权力[J].大众文艺,2015(03):59.
5.李敬.传播学视域中的福柯:权力,知识与交往关系[J].国际新闻界,2013(02):60-68.
6.李敬.传播学视域中的福柯:权力,知识与交往关系[J].国际新闻界,2013(02):60-68.
7.高宣扬著.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22.
何智文,北京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