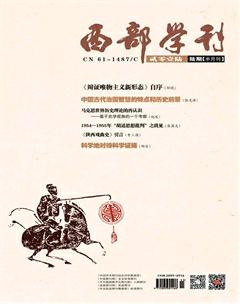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特点和历史前景
张茂泽
摘要:中国古代治国智慧内容丰富,有实践和理论两种存在形态。它们都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也有治国理政经验丰富而理性探讨国家、政府、君权的起源欠缺,君主治国智慧丰富而民主治国智慧欠缺这两大不足。其历史前景在于汲取全人类优秀文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革开放,将长期成为中国治国智慧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中国古代;治国智慧;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应该汲取古代中国治国智慧。中国古代治国智慧,存在于哪里?存在于5000多年中国政治史进程中,存在于记录这一政治史进程的史籍,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历代正史中的本纪、世家、列传等中,存在于儒、释、道和其它学派的政治思想学说中。研究中国政治史、政治思想史,总结提炼中国古代治国智慧,明了其特点和历史前景,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实践形态
作为实践形态的治国智慧,指我国古人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我国历史上前朝覆亡的教训和新朝兴起的经验。如殷商灭亡,西周建立。周初治国者周公等,汲取殷商灭亡教训,重视“德”的修养对于朝代更替、政权巩固和治国理政的意义,而提出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主张,在治国措施上,则制礼作乐、封邦建国等,形成礼乐文化治国模式,有力推动了中华文明史前进。这些都是西周初年改朝换代中产生的治国经验和教训,更成为后来儒、道等学派政治思想的重要渊源。在这种历史反思性认识中,蕴含着改朝换代的规律性因素。二是治国理政的经验积淀,其中也包含了国家治理规律因素在内,值得珍视。比如仅就改革而言,这些经验中既有改革成功的经验,如管仲改革、商鞅变法,也有改革失败的教训,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
王朝初建时期,治国者对朝代更替进行反思,产生的这些治国智慧往往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思想深刻,影响深远。如秦国横扫六国,军力强盛,建立起疆域辽阔、空前强大的王朝。秦始皇希望传之万代,不料却二世而亡。《资治通鉴·秦纪三》记载,秦二世时,“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汉初治国者针对秦朝仁义不施,而以孝治天下;针对秦朝严刑峻法,而约法三章;针对秦统治者大兴土木,严酷惨烈,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针对暴秦苛捐杂税,敲骨吸髓,而自己则厉行节俭,三十税一等。这些措施大多取得了成效。我国历史上出现三次“治世”,即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治国者亲身经历了前朝覆亡教训,故能有针对性地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得以取得成效。
概括起来看,这三次治世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治国者进行了以下努力:在指导思想上,虽说是家天下或私天下,但贤明的治国者有公天下的意识,与天下人共治天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理想,以民为本是基础,虚怀纳谏是途径;在经济上,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解决民众生活问题,节制消费,积累财富;仁爱民众,减免税赋,爱护民力,使民以时。在政治体制上,中央三公九卿或三省六部分职分权,力行谏诤,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地方实行郡县制和羁縻府州制,强化中央集权,维护中枢权威;在制度建设上,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建立健全礼法制度,克服治国理政中的随意性、非理性等因素;在思想文化上,和而不同,不禁绝不同意见,尤其是贞观年间,以儒为主,百家争鸣,三教并用;在思维方式上,朴素的辩证思维,或中道思维长期占主导地位,并落实为历史思维。政治上的极端思想或有产生,但一直受到中道思维抑制。中庸、中道、中行、中和等,是描述理想社会政治状态的常用词。国君、宰相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调理阴阳,抑制极端现象蔓延,防止对立局面出现。
我国古代更多的治国智慧则源于对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因为国家治乱、兴衰总是一个历史过程,治国者的使命正在于帮助国家拨乱反正、由衰而兴。在此过程中,治国者奋力改革特别重要,而改革者居安思危,厉行节俭,有弊必除,有错必究等,也是确保改革得以进行和成功的重要条件。历代成功的改革,使国家富强,如管仲改革齐国,如秦国商鞅变法,如西汉宣帝中兴,如武则天系列改革等,都是显著实例。如果治国者不知悔悟、改正,国家继续腐朽衰败,则兴起革命运动,用革命历史洪流洗刷污泥浊水,这样破而后立,也能求得兴利除害、拨乱反正的功效。可见历代治国者的改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也是产生和凝聚治国智慧的重要途径,是运用和体现治国智慧的重要平台。
我国古代治国者改革、中兴国家的经验中,也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治国智慧:治国者了解民间疾苦,以民为本,又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有志于圣王事业;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或“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或三教并用,但都重视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政治上,以朝廷政治清明、官员勤政爱民、民众安居乐业为目的,勇于并善于改革,大力整饬吏治,重拳整治贪腐,改革旧制,创立新制,抑制社会矛盾激化,避免衰败、亡国;经济上,重视发展生产,减免税赋等。
二、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理论形态
实践形态的治国智慧在贤明君臣处表现充分;以此为基础,也产生了理论形态的治国智慧,这就是学者们的治国思想。两种治国智慧有机统一,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完整形态。
在儒、道、法诸家中,治国智慧分别表现为礼治、德治、道治、法治等理论形态。礼治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封邦建国的治理模式,孔子提炼总结为“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的礼治主张。春秋末“礼坏乐崩”,孔子从“德”(人的本性)的角度反思礼的人性基础,而提出治国理论,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从提高治国者的人性综合修养着手,以身作则,是为德治;“道治”(《抱朴子·塞难》:“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则是道家进一步从宇宙本原高度寻求治国方略,体现出比儒家更抽象的政治理论思维水平;法治,即“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这是法家针对现实一般人的情况而为治国者巩固政权提出的治理办法。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礼治变成后人眼中的历史事实。儒家创始人孔子早年向往周初繁盛政治局面,常常梦见周公,将周公礼乐实践和礼乐制度纳入自己的政治思想中,提出“为国以礼”的礼治主张,要求治国者知礼、行礼、守礼,结合现实损益礼,希望在春秋末年再现周公开创的成康盛世。礼治的要点不在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在“礼”的践行;“礼”可以作为人们知行的程序、方法,获得和谐的心灵和社会秩序。故礼治的治国智慧,不知而信,不知而行,似乎是无知状态,老子“无知”论或受此启发而立论。但长期礼坏乐崩的现实情况,促使人们思考礼治不行的原因。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劳动工具改进,社会生产发展,各诸侯国兴起,中原政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礼乐秩序早已被打破,很难再恢复;另一方面,礼乐,尤其是礼制、礼仪的内在基础不明。换言之,照孔子看,礼乐崩坏也有人们修养不足的原因。从内在修养提高方面发展礼治,即是德治,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走的是这条路;顺此路再向前进一步,追到世界本原“道”处,就是道治。从外在制度方面发展礼治,即是法治,法家韩非等,走的是后一条路。
完整表述德治,即以仁义道德等人性为基础,以德治国,开创理想的道德政治局面。实施德治的前提是治国者人性修养不断提高,直到高如圣人。在这种修养中,认识不同于一般见闻之知,而是觉悟人性的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德治的治国智慧,是对礼治无知假象的驱离、明德真理的澄明。本此德性之知治国理政,即是德治。因为以人性修养为基础,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至善本性,故以民为本是德治的必然主张;而治国者以较高的人性修养治理天下,故能使人感动兴起,风教所及,如时雨之润万物,化成天下。德治在表现形式上是教化政治,总是强调教育和学习,而在实质上则是人性政治,用人性的光辉照亮人,使所有人都成为理想的人,由此使整个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
道治,即以道治国,是道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老子》、《庄子》及黄老的“无为而治”主张,是“道治”论的集中表现。“道治”论在西汉初年运用于治国实践中,取得了文景之治的显著成效。照“道治”论看,小知不如大知。大知近于“无知”,这是一种“知常曰明”的知,一种对道的认识、理解、体悟、直观。和一般清晰的认识不同,因为道混沌、恍惚,故人们对道的认识也恍兮惚兮,惚兮恍兮,有混沌、模糊性。清晰固然有准确的优点,但万物之间却有了分别,有了异同,万物就产生了特殊性,人们对万物的认识也会照猫画虎,亦步亦趋,有执滞、机械的相对性。这样的认识,难以如普遍的“道”那样高妙,无所不适,无往不利。将对道的体悟用于治国理政,就是道治。《老子》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治的主要内容,在道家那里就是克服小知,顺应自然,清静自正,无为而治。
道治和德治相同处在于,其治国智慧,是一种对宇宙本体、人的本性有所领悟的智慧,最好是治国者自己就具有这种悟道的治国智慧。用今天的眼光看,通常,修德、悟道都是哲学家的事情。故要求治国者闻道、悟道,近乎要求治国者做哲学王。闻道、悟道以后可谓圣人,故这种哲学王,也是圣人,圣王。
法治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明确提出的主张,即“以法治国”。其基础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主张一切政事“一断于法”,不容个人私情、私智、私意干扰,体现出政治的公共性;强化了某些社会规范的强制性,不可违背。在这些意义上,法家的法治主张是很好的。其不足有二:首先,其法的来源是君主个人意志,而非天下百姓公意。故黄宗羲谓三代以下无法,但人们都在说法,这只能是“非法之法”;其次,君主是法的来源,但君主并不受法的约束。相反,君主是法的主体,法为君主服务,为伸张君权、维护君主统治服务。这样的法,当然就成为君主专制的工具。故法家的“法治”治国智慧也有不足。
还要提到,除了礼治、德治、道治、法治外,我国历史上还出现过其它治国主张,如神治(殷商为代表的宗教政治)、权治(慎到的权势论、申不害的权术论为代表的权力主义政治)、自治(儒释道个人修养论为代表的政治主张,是一切“他治”论的逻辑基础)等,影响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各自起了一定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分别与西方神学政治思想、马基雅维利主义、自由主义等相沟通。但这些主张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没有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代表。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德治思想也先后汲取礼治思想(孔子)、自治思想(庄子、孟子)、法治思想(荀子)、神治思想(董仲舒)、道治思想(玄学)等因素,不断丰富发展,到宋明时期而集其成,被理学家熔铸成为古代中国理论形态的治国智慧的最大代表。
用今天的眼光看,上述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反映了治国理政的某些规律,构成了我国数千年政治史的优秀传统。我国现在作为疆域辽阔、多民族统一的世界大国,这种政治局面的形成,正可以看成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古代治国智慧的综合实践成就。中华文明持续不断自然发展,古代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治国智慧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三、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两大不足
但在根本上看,我国古代的治国智慧,存在着两大历史局限,不可忽视:
第一,这些治国智慧有时候虽然包含了建国智慧在内,但并不包含对国家起源、政府来源、君权本源等问题的讨论,国家、君主、君权等多被归诸神秘天命;即使有政治思想家理性讨论这些问题,也没有明确将国家和君主、君权分开进行探讨。周公、孔子开创了以“德”的修养来为国家、政府或君权产生提供正当性的优秀传统,后来政治思想家如孟子、董仲舒等,提到君权来源于民授问题,接续、弘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但流行的只是民本思想。民众作为国家主体、政府主人、君权本原的本质地位和作用,在古代君主专制时期一直未能发展为明确的理论形式;这使国家或政府的产生、朝代的更替、君主即位等重大政治活动,未能纳入人的理性认识范围,也未纳入理性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轨道,而从根本上摆脱神秘天命的制约。神秘天命假扮成国家、君主的护身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成为皇权的习惯语;朝廷甚至以天命的神圣性代替了儒家对皇权的道德正当性要求、抵制着近代民权人士对皇权合法性的要求。在政治思维方式上,一些思想家倾向于以神秘天命的运行解释朝代更替历史;在天命观念笼罩下,一些思想家则疏于理性思考,自觉或不自觉地习惯于承认国家、政府、皇权已经存在的既有事实,在此基础上认识治国理政活动,寻求治国良方而已。国家、政府、君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或合理性,似乎都不成为问题。
但近代以来,人们日益发现,国家学说的根本在于,不只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只是承认国家的现有存在,更重要的是要将国家的产生、最高领导人的诞生、权力的运行等,纳入理性认识和法制范围内,认识和改造国家,让国家机器为人民服务。即是说,要求在国家学说指导下,对国家进行理论设计、系统构建,使政府的建立和组织、权力的分割和运行、政策的制定和发布等,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建立健全法制,依法治国,成为近代以来治国智慧的重要内容。
第二,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大多只是君主专制下的治国智慧,是以君主为代表的治国者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深深打上了君主专制的烙印。在这种治国智慧里,君主以及追随君主的治国者集团作用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隐晦。即使礼治、德治、道治、法治等富有哲学智慧的治国主张,也无不仰赖治国者,尤其是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孔子“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说,就要求治国者为政以德,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后来思想家们也纷纷提出“君道”、“正君心”等,作为落实上述治国主张的前提条件、具体办法。治国之道往往与为君之道交叉混融。国家如何构建,权力运行的边界在哪里等,均来不及或不敢进行讨论。在明清专制皇权极端发展时期,臣民对君主的谏诤几乎被废除,连“正君心”这样的温和主张也不敢提了。可见,我国古代的治国智慧主要是君主智慧,而不是民主智慧。
当然,一些贤明的君主会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而有民本思想,在治国理政中也能尽量反映民心民意,得以取得显著成效。但我国古代这种贤明君主既少见,将民本思想贯彻到治国理政中,也难做到“一以贯之”,坚持到底。历史上治世少而乱世多,人们很容易将国家治乱和君主个人的品德修养相联系,如“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不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予以重点考虑、对待。中国古代治国智慧主要不是民主智慧,与人民群众无权力也无权利的低下政治地位现实是相应的。
近代以来,民主兴起。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为时代潮流,从而要求国家的建立和治理必须以民主、民治、民享为基础;必须遵循人民群众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原则。总的看,和我国近代以来民主政治历史短暂、发展尚未成熟相关联,我国现有的治国智慧,君主的多,民主的少;君主的系统、深入,内容丰富,民主的零散、粗浅,内容单薄。这需要当政者注意鉴别。
四、中国古代治国智慧的历史前景
客观看,治国智慧是我国政治活动中新出现的一个好词,应当纳入政治学中加以考察。“治国智慧”这个词,当然有从国家治理的政治现实出发,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考虑,但仍然有其重要理论意义。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关心正义的实现等伦理问题,关心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的组建和权力制约等。与此不同,我国几千年政治史,主要是治国理政的活动史;中国古代治国智慧,正是在几千年治国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结晶。所以,治国智慧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可以代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
在发达的历史学支持下,治国智慧的产生,可以从前代治国理政教训的汲取,扩展为对以前所有历史时期,无论中外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总结;治国智慧的内容,可以在君主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总结民主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可以从对现成既定国家组织的认识和解释,深入发展为对理想国家的科学设想、系统规划和理性构建。这正是当前我国政治学、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任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期治国智慧的充实和丰富,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人类优秀历史文化都是治国智慧的源泉
我们现在的治国智慧不仅是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应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治国经验的总结;不仅是对中国古代、近现代治国智慧的传承、弘扬,也必须是对其他民族治国智慧的学习和汲取。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业。现代化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书写。在社会化大生产方面,中国文化没有多少自己的历史经验可供汲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内容。比如一些在外国经过历史检验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办法、市场经济建设经验、管理制度、科学技术等,就可以大胆学习引进。这实际上正是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化西学为国学的表现,突显了中国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在科学时代,知识分子不仅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而且遍布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领域。他们凭借其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修养,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时,就范围而言,治国智慧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应成为全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具有世界性;不仅是前朝或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的历史总结,而且也应是近代的、现代的甚至当下社会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鲜活性和历史延续性;不仅是经验总结、教训汲取,而且也应成为科学的理论、系统的思想,具有普遍必然性。真正的政治智慧总是对政治活动规律的总结,有普遍必然性而又有现实力量。
第二,人民群众始终是治国智慧产生的肥沃土壤
通常,我们会研究历史上治国者的治国理政活动,从中发现其贤明处,概括、提炼治国智慧。这当然没有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国家治理主要由治国者进行,劳动群众无权,也无闲暇、无能力参与,在君主专制下更是如此。《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之类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作者虽然都有民本思想,但他们在书中重点描述的却是治国者的活动,人民群众在其中间或出现,也只是治国者治国理政的对象和点缀。
但今天我们关注治国智慧,眼睛不要仅仅看到治国者,尤其要看到劳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的主人,治国理政如何对待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需要、欲望,是治国理政的动力;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民心民意是衡量治国理政的现实标准。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是治国智慧的不竭源泉。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借助各个社会共同体的民主管理,聚天下之智,集众人之力,是掌握治国智慧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