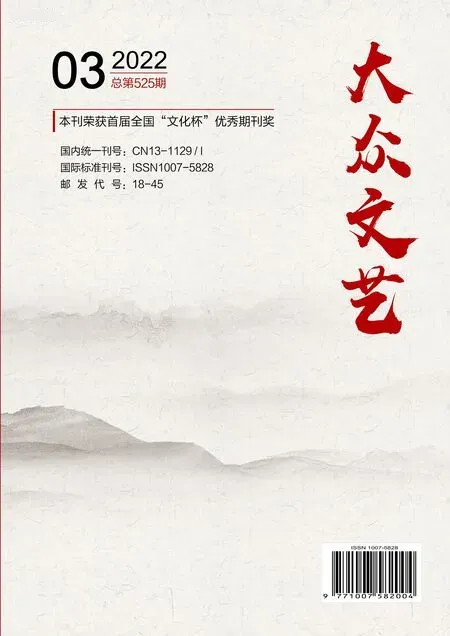浅析以“死亡美学”为突出特征的阿兹特克艺术
张勇毅 过宏雷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214122)
浅析以“死亡美学”为突出特征的阿兹特克艺术
张勇毅过宏雷(江南大学设计学院214122)
摘要:阿兹特克艺术是古代中美洲艺术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其艺术呈现出显著的中美洲地域文化风情,又以“死亡美学”作为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本文就阿兹特克艺术的形式美共性予以归纳,并着重结合特定历史时期探讨其“死亡美学”的产生缘由,反思基于当今时代语境如何正确认知艺术创作的方向。
关键词:峥嵘之美;死亡美学;仪式性;反相呈现
一、阿兹特克艺术的历史背景
今日拥有2000万人口的世界特大城市墨西哥城,建立在昔日繁华的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Tenochtitl City)的废墟之上。阿兹特克文明(Aztecs)是古代墨西哥文化舞台上最后一个角色,也是中美洲古代文明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依据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正三角需求层次理论,作为底层建筑的生存资料支撑起精神性建筑。在阿兹特克族族基本生存延续得到初步的保障,关于精神享受资料的需求获得了可行性条件作为支持后,建筑,手工业,绘画和雕塑艺术便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阿兹特克人被现代史学家誉为“伟大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其艺术立足于本民族丰富悠久的神话传说,信仰对生活的深入渗透,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与精湛手艺的互相配合,具有文化特色的视觉艺术得以呈现得淋漓尽致。著名德国艺术家杜勒曾高度评价阿兹特克艺术是“一生从未见过如此能使自己打心底欢呼的东西”。虽然由于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导致这一传奇文明迅速衰落,帝国200余年的繁荣已经为今天的研究学者留下了数量惊人的珍贵艺术品,以及一座座雄伟之极的金字塔和宫殿群遗址。欣赏阿兹特克艺术作品,会从中收获美的享受,并唤起对那个充满“峥嵘之美”古文明的探究之心。
二、阿兹特克艺术的诞生
阿兹特克艺术(The Aztec Arts)诞生的社会背景有以下两点:
1.多神崇拜。世界上不同地域文明的发源千差万别,又存在着一般共性。在基本满足第一层级的生存需求之后,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是“解释世界”,即从哪里来,在更大的外部环境中占据什么位置。阿兹特克文明所诞生的自然环境为中美洲热带雨林,生存与发展环境相对与世隔绝。阿兹特克先人从森林中获取一切生存资源,“多神论”是该类森林文明发源地的显著特点。阿兹特克的神话传说中创造出了数量众多的神灵(The Aztec Gods),据史学家统计大约有1600多个。不同神灵居于不同的载体,掌管不同的自然秩序,解释不同的自然现象。神灵之间亦存在着紧密的互相关联,并与特定日子产生错综复杂的对应。比如D.M.琼斯与B.L.莫里努(D.M.Jones/B.L.Molyneaux))所著《美洲神话(The Mythology of the Mericas)》一书中,有一段文字用于介绍名为阿卡特尔(Acatl)(“芦苇”可能是民间所起外号)的神灵,原文翻译为“……阿卡特尔是阿兹特克月(20天)的第13天,它是个凶日。保护神是泰兹卡里波卡(Tezcatlipoca,“冒烟的镜子”)或伊兹特拉扣里丘(Eztaqlisu)(狩猎之神米克斯扣特尔Mixcoatl的另一个化身);它的方位是东方。与之对应的日子是本(Feven)和魁吉(Qejir)(均无记载,推算也是两个神灵)(摘自《美洲神话》P96)……”对神灵的狂热崇拜贯穿着整部阿兹特克史。
2.神话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原始的耕种方式与雨林气候特征决定了不甚稳定的农业生产力,生产力的不稳定间接导致了不同部落间之战争频繁。阿兹特克先人为“解释世界”创造出诸多神灵以及相互关系,获得了族内大众认可之后,神灵信奉即作为了最有效链接全族的纽带,几乎渗透到了阿兹特克人日常生活每个方面。每个族人从出生到死亡,均有一套庞大繁复的规范礼仪作为指导行动的依据。阿兹特克人习惯使用与神灵关联的时间点进行占卜,尤为用于婚礼,祭祀,对外征战等重大社会活动,所以在各项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丰富的文化艺术产物。
繁杂的多神崇拜,以及神话信仰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均为阿兹特克艺术家的设计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三、阿兹特克艺术的形式美
结合相关文献和图集资料作为参考,从形式美的不同评价角度,有如下归纳:
1.造型之美。源于早期自然神形态诠释与加工工具的特性,天然,粗粝,古朴的造型设计使得阿兹特克艺术造型普遍可以概括为“峥嵘之美”。关于“峥嵘之美”的理解,可以类比李泽厚在《美的历程》著书中所介绍中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皿兽纹的造型及装饰:“……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狰厉的美……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情感……(《美的历程》P53)”。而这种原始的情感之所以为观众感同身受,是因为艺术家对于艺术品全身心的倾注,以思考与雕琢赋予了作品具有恰到好处张力的造型力量,充分传达出了创作意图。
2.线条之美。在阿兹特克的艺术中很难看到有长距离的直线与锐角。几乎总是会在折角处发生一些弯曲。直线与曲线和谐并存几乎是中美洲古文明的一个共性,一种可能是艺术家受到所处环境雨林中自然生长卷曲的植物形态所影响,并加以抽象利用。这种自然卷曲的线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石材料锐利,粗粝的视觉感受,同时极富地域视觉特征。
3.构图之美。艺术品构图通常非常饱满,繁杂。在对于人物及神灵造型的描绘上,其构图设计理念的本质是“求全”思想。忽略透视与比例的束缚,追求能使对象特点最明显化的“完美构成主义”,具有强烈的平面装饰艺术感。人物通常设计为正面视角的身躯,侧面视角的头部。通过比例尺寸的改变传达对象不同地位,身份的信息。同时大量堆积一些没有空间概念的陪衬物。
4.材料之美。阿兹特克文明又有“石头文明”一称,缘于其文明处于雨林深处,湿热多雨的气候导致木材料极易腐朽,使用寿命不长,同时阿兹特克的冶金业非常不发达。所以更加易于制取和驻留的石材料便成为了阿兹特克关于艺术材料的首选。在诸多石材中,绿松石是作为装饰最为重要的原料之一,阿兹特克人相信绿松石由最高主神奎兹尔扣特尔(Quetzalcóatl,羽蛇神,掌管风,降雨和农作物收成)所褪下的蛇皮所变成,具有强大魔力,佩戴其制成的装饰品会得到众神的保佑。故绿松石大量出现在出土的饰品和武器上,亦有磨成粉末,作为壁画的珍贵颜料。
5.色彩之美。常见以冷色作为“面”,暖色作为“点”与“线”性对比。颜色瑰丽多彩,来源为植物提取和矿物磨成的粉。主要有黑,青绿,青蓝,朱红,靛蓝,鹅黄。据统计其中青绿色作为富裕,尊贵的主色,是最常出现的使用颜色。同时阿兹特克人也大量使用磨成小圆片的宝石直接镶嵌于艺术品。娴熟的色彩搭配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被装饰物的形式美感。
6.艺术门类。可基本分为民间艺术与皇室艺术两大类。阿兹特克艺术的主要成就方面是皇室艺术,制作不计时间与材料成本,工艺非常精湛。而民间艺术则是主要反映劳动场景,饲养家畜等内容。较少使用名贵石料,多为麻布,陶土,骨等作为原料。工艺水平与艺术呈现上亦与前者差距较大。
7.阶级限定。通过不同的颜色和饰物区别,明确规范使用者的阶级。例如作为祭司阶级,只有最高祭司拥有同阿兹特克王相同的以大蓝孔雀长尾羽作为装饰,以及佩戴三层绿松石披肩的权力。中等祭司在举行人祭时,需要以朱红,鹅黄色的矿物颜料在全身涂绘出特定的符号。下等祭司及武士则只可佩戴一层绿松石披肩,无使用涂料的权力。平民则仅可佩戴极少量的宝石装饰。而用于人祭的本族奴隶或是捕获的他族武士,则以一种特殊制取的蓝色矿物颜料予以标记。在佩戴饰品方面,同样遵循着一套繁杂而严格的体系,从而非常直观地传达出某一类饰品所服务的阶级属性。这些明确的视觉标记区分有利于现代研究者对阿兹特克壁画,手工文物,建筑内容的迅速认知。
四、“死亡美学”作为突出特征的解
阿兹特克族被誉为“崇拜太阳与血的民族”。这里的“血”一词在今天则集中体现为艺术文物上各种直接表露的死亡符号呈现。比如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阿兹特克文物中,有被各种各样的绿松石镶嵌的殉葬者头骨,有像是纳粹“人皮灯罩”一样的人皮艺术品,羽蛇神金字塔基座的骷髅石雕墙,等等。类比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著名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中所提到古代日本武士对武士刀毫不吝啬的赞美,将飘散樱花比做武士的生命等行为。可怕的杀人凶器,骷髅,血腥的献祭过程,在阿兹特克人的眼中是美的。“死亡美学(The Death Aesthetics)”一词即是站在现代角度,用于归纳阿兹特克艺术最为突出的特征。阿兹特克“死亡美学”特性呈现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献祭习俗与蛮荒习性。源于不发达的知识系统,原始时期人类所看待的自然界被赋予许多拟人化的气息,有时“行善”,有时“作恶”;需要来自于人的管理。如果中断对自然界的警觉和引诱,自然的力量随时会吞噬人类。阿兹特克人认为,神灵向阿兹特克人提供帮助,并显示自己的力量使他们得以繁荣昌盛;而那些允许人类生存发展的神灵也应当得到报偿,阿兹特克族相信献祭出人命可以使神灵永葆慈悲心肠。据资料记载,除战俘之外阿兹特克人尤为喜欢拿孩子献祭,原因是孩子的眼泪能“带来雨水”:“如果他们不断哭泣,如果他们的眼泪不断下落,就会下雨了”。在种族的延续需求下,个体的牺牲是“必要的”。对于阿兹特克人而言,在战斗中(特指男人)和分娩时(特指女人)以及用于祭献的死亡都是非常高尚的。另外在古中美洲的文化中,战争和尚未从原始社会观念分离,导致阿兹特克人对于暴力结束人的性命看得非常平淡。这样的观念为“死亡美学”做出了铺垫。
2.关于“生”与“死”概念的认知。区别于同时期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并不害怕死亡。在阿兹特克信仰中,灵魂是永存的。“死”并非生命的终结,是一个新的起点,循环往复的过程。《美洲神话》一书中指出,循环性的概念渗透整个中美洲的文化与社会。在阿兹特克人的观念中,能够取悦神灵,维持种族繁衍昌盛的任何方式都是积极有益的,都是正面而“美丽”的。另一方面,因为拥有较为完善的生死循环神话诠释作为支撑,故对于个体“死亡”的看待要远远弱于种族延续的认知。
3.阶级统治的需求与强化。阶级统治关于“秩序”的长期灌输。阿兹特克艺术尤其是皇室艺术。几乎一切都围绕着神话传说中神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奉献方与被奉献方的基本矛盾关系而存在。比如献祭刀具所传达的观念符号是“光荣的牺牲”,即无条件的服从与奉献。在阿兹特克文明中,文化的传播是自上而下的单线式传递。民众相信并接受统治者关于神灵的“传话”,而统治阶级则从自身统治稳定出发,极力消除民众对于“死”的恐惧。将其作为“光荣”的行为予以宣传,鼓吹“神性至上”,强化作为“神的意志”的执政对外宣传,要求底层人民严格遵循所谓的“世界秩序”。所以在阿兹特克艺术中并不会规避死亡的直接呈现。因为死亡是“秩序”的另一面表象,是应当作为“奉献”被直观歌颂的。“美丽的死亡”实质上是阿兹特克统治阶级利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模棱两可之处,进行政治压迫与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
4.祭祀仪式赋予的群体自我暗示。“仪式性”是促进阿兹特克“死亡美学”发展的重要客观因素。人类需要从在参与群众共同目的事件中获得归属感,获得积极内心能量,增进所在群体的自豪感,抵御外在自然负面影响或侵略。而事件的仪式感与参与个体的自我正面暗示呈正比例函数。个体在仪式中所生的愉悦感是该仪式秩序美的来源,而涉及视觉要素的形式美也因为仪式和群体作用被放大。以阿兹特克最盛大的一项习俗人祭祀举例,依据统治阶级的诠释,神灵指令要用人类的血液去供给太阳,以提供它每日升起来的能量。在人祭祀的活动中,严谨的仪式感赋予是不可或缺的。阿兹特克祭祀在特定的金字塔上举行,祭司们披上用宝石串联制成的披肩,戴着珍禽羽毛制成的高高头饰和羽蛇神的狰狞木雕面具,手中紧握黑曜石祭刀吟唱颂歌。规范严肃的祭祀行为流程,颂歌的点缀,精美异常的祭祀用具,这些综合感官信息刺激均推动了仪式感的攀升。此时在场阿兹特克人在各种信息暗示的累积下,从专注的沉浸体验中感受到神灵真实的存在,相信这样的“仪式感”会得到神灵的愉悦,获得来年的风调雨顺。而心理暗示的愉悦经群体行为被统一迅速放大,产生美的感受。此时“死亡”的概念对于仪式本身,实际已经不是重点。所以,“死亡美学”一词应当来源于现代的捆绑式解读。
综上所属,今天我们所认为可怕的“死亡”过程,在阿兹特克人的视角中是美的,因为被赋予了赖以信服的诠释和极其庄重的形式感,使得个体从“死亡”的相关过程中削减了关于外界的恐惧。正如颜翔林在《死亡美学》一书中所说,死亡的意境“在给人以痛感与丑感的同时,也给人以某种价值观念的领悟和情感取向的满足,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旨趣(P84)”。“死亡美学”恰恰是从关于种族延续和阶级维护的恐惧中诞生,其既是阿兹特克人以保护自身种族生存作为目的的艺术产物。更是为统治阶级所需要,进行包装后的一种反相呈现。“死亡美学”虽然代表着落后的文化观念,但是基于特定时期的客观视角,其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增强了阿兹特克社会的凝聚力,并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从当今的视角,阿兹特克的死亡现象呈现具备有严谨规律性的逻辑抽象,成为具有历史记录意义与艺术价值的特定时代产物,所以能够上升成为一种美学。
五、结语
扎根于中美洲雨林深处的阿兹特克人,在奴隶制与早期农耕生产方式并存的原始的社会形态下,竟然拥有着如此超前的艺术创造力。阿兹特克人将向神灵效忠的狂热信仰作用于艺术,也正是因为“死亡美学”的突出特征,赋予了“阿兹特克式”艺术独特的魅力。在今天的文化研究工作中,我们对于阿兹特克艺术的解读应当一分为二,尊重特定历史语境的影响,以理性尺度客观看待与评价。既看到阿兹特克艺术对于本文明所起到的正面推进力,也认识到其内容中落后,消极的一面。立足于当今时代,文化作用于艺术设计与传达的过程中,艺术家应当时刻注意文化艺术的内容需要与时俱进,将有利于广大受众精神文化水平的真正提高作为目标,创作具有时代先进性,开启民智的先进文化艺术。
参考文献:
[1](英)D.M.琼斯/B.L.莫里努,余世燕译.美洲神话[M].山西出版集团,希望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2](中)李泽厚.美的历程[M].三联出版社,2014年3月版.
[3](美)鲁思.本尼迪克特,一兵译.菊与刀[M].武汉出版社,2011年3月版.
[4](法)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马振骋译.阿兹特克:太阳与血的民族[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8月版.
[5](中)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中)张家骝.论古代国家恐怖主义的缘起与嬗变——基于亚述,商王朝及阿兹特克的对比分析[J].民族论坛,2012(07).
张勇毅,硕士,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