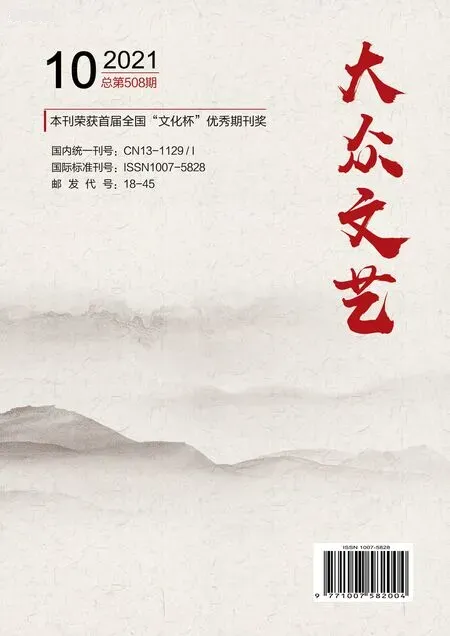《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身份确立”问题
支丽蓉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710000)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身份确立”问题
支丽蓉(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710000)
摘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本雅明通过波德莱尔对现代性观察和研究的成果。诗人田园式的抒情已存在危机,抒情诗描述的对象转向人群,诗人作为人群中的人,使自己无所事事,同时又对人群进行追踪和描述。抒情诗是诗歌的规范,诗人的抒情方式关系到诗人的身份确立;诗人的抒情对象——人群,同时也存在着身份确立的问题。社会的生产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反应机制,在现代性中无论是诗人还是人群都存在主体性的丧失,本雅明通过波德莱尔的阶级属性来确立诗人的身份,通过社会的生产关系来确立大众的身份。
关键词:现代主义;身份确立;诗人;大众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是现代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它指出了一个大环境,资本主义要发达,必然是在大都市。抒情是指以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的表现个人内心情感,是诗人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感触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抒情者还是抒情对象的主体性缺失,都与现代主义的形成密切相关。
一、现代性致使主体的丧失
影响现代主义的重要思想家很多,例如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弗雷泽等。1很多理论家在界定现代主义时往往强调它的反传统精神,以尼采和马克思为例,尼采在他的手稿《疯人》中写下上帝之死,“疯人”就意味着人类权威和秩序的缺失,意味着上帝的死亡,上帝一死,人就从中心滚向X,这样就可以对一切传统准则:权力、理性和道德进行重估2。在哲学思想上,人类开始去中心化,在实践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也昭示着现代主义,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人与人之间形成利益竞争的关系,人们之间变得疏远和敌对,甚至人与自身的本质也异化了,疏远了。波德莱尔在他的论文《现代论》中明确指出:“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与传统相对立的文明方式。”
波德莱尔的好友皮埃尔杜邦说:“诗人‘交替地把耳朵伸向森林和大众’,大众则对他的关注给予了回报。”波德莱尔离开田园,走向城市,他从城乡差别的消失中觉察到了抒情诗的危机。本雅明在讨论波德莱尔的一首诗《拾垃圾者的酒》时提到:“当然,人们不能将拾垃圾者归为浪荡游民,但每个属于浪荡游民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者身上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者与那些动摇这个社会根基的人们会有同感。”3拾垃圾能够成为一个职业,暗示着大都市的生产过剩,诗人同拾垃圾者一样,属于朝不保夕的闲逛者,波德莱尔用拾垃圾者来隐喻诗人的创作活动,诗人描述的是机器和机器运作下的人群,而拾垃圾者捡拾的是这两者的产物。诗人的身份是尴尬的,他从传统的高于人群转变为置身于人群。
生活在巴黎的人群,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他们对于事物不是慢慢体会而是快速做出反应,这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有关,城市的面貌比一个凡人的心还变得快,机器的齿轮带动每个人的脚步。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劳动,工人对于产品的意义无需关注,只要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就行,街上的行人对于人群的反应也如同在机器旁一样。这种存在方式是生产制度强加给人群的,一个人作为劳动力或者是商品,他就没有必要在商品中再置入自身的东西即人不会移情于人群,休闲逛街者即诗人整日面对着“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的那种不关心他人的独来独往”而带来的空虚。
这种反应机制,直接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主体性的丧失,二是从众。人们对于一件事物的反应只是匆匆一瞥,而不是深入了解,这直接反映在人们对于图片浏览和文字阅读的态度上。图片浏览是快捷直观的,不用主体去深入观察和思考,本雅明说:“复制技术引发的推断性意愿记忆的不断就绪缩减了想象力的活动空间,人们在赏析一件艺术作品时,它在人们身上引发的思想和行为反应根本不能穷尽它或者处置它,但是对于一个复制时代的摄影作品来说,眼睛却像饥饿面对食物或者焦渴面对饮料一样。”个人感知被公约的他律所代替,那种被实际需求不断激活的、生活离不开他人的感觉逐渐被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行磨平了,这种机制每一步的完善,都消磨着人们以前特定的行为方式和情感,对于惊颤的反应逐渐机械化,个体的思考和反应是怪异的,大众的反应才是最正常、最安全的。
二、从诗人到大众的身份确立问题
在巴黎拥挤的人潮中,无论是抒情诗人还是普通大众,主体的丧失成为趋势。身份的确立更多地与人的社会位置相关。
对于诗人的身份确立问题,本雅明从波德莱尔所属的阶级来回答。波德莱尔属于小资产阶级,他对现代性是摇摆不定、态度暧昧的,波德莱尔诅咒进步,同时又欣赏工业带给现代生活的特殊风味。他站在大城市和资产阶级队伍的门槛上,二者都还没有使他愿意真正进入,二者中的不管哪一种都还不能使他感到自在,因为身份确立有些时候来自立场问题。本雅明说:“波德莱尔真正需要克服的东西,就是他对撒旦的信仰与自己拒斥任何信仰之间的冲突”。波德莱尔早期诗作里有一首诗是写街头卖身女的:“为了一双鞋她卖掉了她的灵魂,老天爷耻笑了这个羞辱。我进行乔装打扮,效仿者贵人的高傲,为当作家我出卖我的思想。”4对于波德莱尔所属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刚刚走下坡路,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劳动的商品性质,社会将这他们作为诗人的乐趣引向现实,对商品的移情成为必然,他们必须无论是快乐还是别扭都尝试这种移情,这样的移情源自一个阶级对自己命运的预感。
大众身份的确立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人群,而机器对人的异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片段化、瞬间化。人一方面易于辨识的,一方面又难以寻找的。易于辨识是因为私人空间的减少,人把自己暴露在大众中,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大城市为了方便管理,采取现代身份确立制度,巴尔扎克他在《平和的米农老爹》中写道:“可怜的法国女人们。为了织就你们那小小的浪漫故事,你可能喜欢不为人所知的去生活,可是,在这样一个文明社会中,你何以做到这一点呢?公共场所的马车往来都要注册登记,信件也要登记,寄信时要查清邮戳,住房被编上牌号。这样整个国家的每一小块土地都被注册登记了。”而难于寻找是因为人群是流动的,变化的,形色匆匆的。如果你在城市街道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一个人,这也许会变成你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相遇,因为这个人会立马消失在人群中,人群是大众的藏匿之所,所以一些不文明现象才会赫然出现,例如偷盗,卖淫,凶杀等等,人群的藏匿性更是促进了侦探小说的发展。密集的人群必然招致快速的前进,置身于人群之中,使人无暇顾及世界,眼前的情景一闪而过,波德莱尔一首诗《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女人》就是这种体现。如果在一个发展缓慢而且生活规律的乡下,你有可能会通过熟人打听或者在乡村间再次遇到这位妇女,你们可能会交谈,以致成为朋友。
三、结语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就可以深切体会到现代性转变如何在社会生活和审美艺术领域发生。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有一个较为广泛的表述“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似乎就是这一现象的写照,诗人所处的小资产阶级由于历史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要对商品和人群进行移情,而大众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中,身份被社会生产的机制界定。书中讨论的现代性问题和身份确立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国社会新兴的大众群体和大众文化已经站上历史的舞台。本雅明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他对现代主义现象的披露,为我们观察和思考身边的环境提供了视野。同时也提醒着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灵韵的回归,对人与人关系的重视,对未来更合理的制度的建设。资本主义是全球的趋势,对现代主义的思考也必将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思考。
注释:
1.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652.
2.(德)尼采著,威仁译.上帝死了·尼采文选[M].三联书店上海分,1989: 267-272.
3.(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4.
4.(法)夏尔·波德莱尔著,胡小跃编.波德莱尔诗全集[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265.
作者简介:
支丽蓉(1991-),女,汉族,陕西宝鸡人,文学硕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西方文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