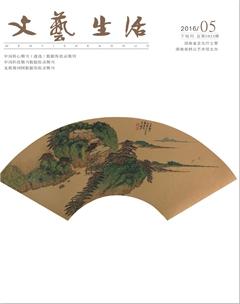威廉斯笔下的女性形象
赵春花
摘 要:田纳西·威廉斯是美国南方文学中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他以刻画南方淑女形象而闻名于美国剧坛。文章通过分析田纳西·威廉斯作品中的四个典型的淑女形象,向人们展现了南方妇女在精神上的倍受摧残,人性上的压抑和灵魂上所遭受的迫害,体现了作家对整个南方命运及进程上的极大忧虑与关注。
关键词:田纳西·威廉斯;南方淑女;幻想;现实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5-0051-02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年)是二战后美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他曾先后四次获得纽约剧评奖、两次普利策奖以及其他各类戏剧奖,为当代美国戏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威廉斯生长在南方对南方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他和同时代的剧作家亚瑟·密勒不同,他并没有放眼于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是以他熟知的南方为背景,向人们描绘了作为弱小个体的个人,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恰恰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这是因为威廉斯是怀着深切的爱来完成对人物的临摹。他的创作仿佛一阵清新的春风吹遍了美国剧坛。
有的评论家称田纳西·威廉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所出现的最杰出的美国剧作家”;有的评论家则认为他是“当代的奥尼尔”。由此可见,威廉斯在美国剧坛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与同时期剧作家不同的是,他的作品继承了从埃德加·爱伦·坡到福克纳以来的南方怪异传统,集中反映了美国南方的没落。尤为要指出的是,威廉斯把他对南方女性的了解融入到他的作品中去,着力刻画了南方淑女处于北方工业文明与南方种植园文化碰撞的尴尬境地之下的无奈和无助。她们是一群孤独、失意、脆弱而又心灵扭曲的女人,有的与世隔绝,有的疯狂,有的堕落。她们既无力抵挡势不可挡的北方工业文明,也不愿放弃旧南方赋予她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这群女人就是美国著名的评论家罗杰·博克西尔在评论威廉斯的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南方淑女。
美国南北战争后,随着蓄奴制的废除和北方工业化的冲击,南方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体系逐渐走向崩溃。在历史的动荡变革中,南方贵族庄园主阶级留恋昔日南方的乡绅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以及维系这种生活的社会、道德体系。面对衰亡的命运,却不甘心,拼命想扼守这一切。而他们精心设计出来的举止风雅、谈吐得体的南方淑女为了固守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为了不违背虚伪而又无人性的道德观念、为了维持种植园时代的生活方式或陷于幻想,或摇曳于幻想和现实之间,但也不乏勇敢面对现实者。本文旨在对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中的姐妹:布兰奇和斯黛拉以及《玻璃动物园》中的母女:阿曼达和劳拉四个淑女形象进行分类及分析,向人们展现南方妇女在精神上的倍受摧残,人性上的压抑和灵魂上所遭受的迫害,表达了威廉斯对整个南方命运及进程上的极大忧虑与关注。
一、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女性形象
从小在女性成员占多数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威廉斯,颇具女性的性格特点,而且也使他对南方女性有很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威廉斯的笔端下生出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南方的“最后的贵族”。本文认为他笔下的南方淑女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淑女沉湎于幻想而拒不承认现实;第二类淑女则摇曳于幻想和现实之间;第三类淑女则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对现实采取积极的态度。
《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便是第一类淑女的代表。她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不敢直面生活,只能以沉湎于美好的幻想,逃避现实这种生活方式来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
作为一个旧南方典型的大家闺秀,布兰奇美丽温柔,仪态万方,是众人心目中的女皇。像她这样的贵族女子可以永远依靠如骑士一般潇洒富有的贵族绅士幸福地生活。古老美丽又宁静的美梦庄园是她应该生活的地方,高贵优雅又富有的绅士应该是她理想的丈夫。于是,布兰奇把丈夫艾伦看成是自己最美好的梦想。然而,这一梦想的破灭粉碎了布兰奇的一切美梦,也粉碎了她对人生的一切希望。
接踵而至的是她的亲人的去世以及庄园的逝去,布兰奇独自一人经历了这一切,没有人给予她安慰或替她分担。布兰奇无法忍受这种孤寂和悲伤,她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怀和保护。可是,她却把投入一个又一个男人的怀抱当成是庇护自己、填补内心空虚的唯一途径。男人们根本不在乎布兰奇的精神和心灵,仅仅把她当成泄欲的工具。最终她声名狼藉被赶出本市。无家可归的她只好到新奥尔良投靠她的妹妹斯黛拉。布兰奇既无法面对冷漠的人群,也得不到一点关怀和保护,从而,她选择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她掩饰自己酗酒的恶习;她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用胭脂与昏暗的灯光掩盖脸上的皱纹;她炫耀她那一大衣柜俗丽、廉价的晚礼服;她经常洗澡来缓解受压迫的神经;她不断地编造谎言来麻醉自己的心灵—她挣扎着要维护自己的体面与高雅,但却又忍不住与自己的“没教养”的妹夫斯坦利调情。遇到密奇后,她告诉自己密奇才是她真正的绅士。为了能与密奇结婚,她重新把自己伪装成一位高雅的弱女子。但她却无法掩盖自己内心真实的欲望:她用密奇听不懂的法语调戏他。在与密奇交往的同时,她竟然送给收电话费的小伙子一个吻。当布兰奇的谎言被揭穿,她只有选择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我不要现实,我要神奇的梦幻!”。但其实她的内心深处却忍受着社会道德的谴责,欲望无以释放,直到最后斯坦利通过强奸,对她的脆弱神经以致命一击,使她精神错乱,完全陷入幻觉的世界。
在饱受着浓烈的南方情怀和残酷的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布兰奇无所适从,无法与自我和谐相处,灵与肉的分离导致了她人格的异化。因而,幻想成为她规避一切的唯一武器。尽管幻想注定破灭,布兰奇仍就紧紧抓住:“我不要现实。我要魔幻!是的,魔幻!我努力将魔幻给予人们。我歪曲事实,我没有告诉他们真实,但我告诉他们的是应当如此的“真实”。”这虚幻的世界像麻醉剂一样使布兰奇获得了暂时的平静,为她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第二类淑女如《玻璃动物园》中的母女:阿曼达和劳拉均被现实所迫,试图逃避却又无法逃避。所以,她们只好徘徊于幻想与现实之间,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虚幻。
阿曼达,作为南方种植园主的女儿,举止优雅,谈吐得体,脑子里满是浪漫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念。同时,在她的内心深处,也受到严格道德准则的约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女子遭到了丈夫无情地抛弃。她独自一人将儿女养大,过着贫困而又枯燥的生活。关于那段充满鲜花与舞会的时代的记忆却时时涌入她的脑海:17个翩翩少年在同一个下午向她求爱。尽管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但阿曼达却不愿接受目前拮据而窘迫的生活现实。她喜欢咬文嚼字,竭尽所能保持其端庄与娴静,以保持她的淑女风度。她的居住条件已无法使其接待客人,但当汤姆把同学邀到家里时,她居然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少女似的,带着风情与羞涩的微笑接待小伙子,仿佛又重返少女时代,沉浸在往昔的浪漫情怀之中,却忘记现实中的小伙子的到来是为了女儿劳拉,而她却喧宾夺主地扮演了一个应该由女儿扮演的角色。
阿曼达本人执着于早年的回忆,她还将这种回忆和思想灌输给她的子女。然而,面对苦痛的现实,她却一直在逃避,抑或将现实与回忆相融。于是,她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她的孩子身上。她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一位成功的男士,成为家庭强有力的支柱,女儿劳拉能找到一位事业有成的男友,却不愿承认现实中儿子不过是一位普通工人,而女儿身有残疾。阿曼达刻意地逃避现实,生活在被美化的虚幻之中,她企图用回忆与幻想来填补生活中的空虚,试图在现实中寻找过去的光荣与浪漫。可是,她的不切实际却使得自己的儿子离家出走,自己的女儿蜷缩在更加狭小的虚幻空间里。
至于女儿劳拉,一场儿时的疾病使她成了残疾,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稍微短一点,绑着支架。由此,她对自己的身体缺陷过于敏感和关注,变得内向和自卑。终于,劳拉中途辍学,整天呆在家中摆弄那些玻璃动物,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她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一遇到困难就采取逃避的态度,脆弱得犹如她珍藏的那些玻璃动物。为此,母亲阿曼达焦虑不安。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弟弟汤姆把他的同事吉姆介绍给劳拉。吉姆的到来对于劳拉来说是件好事—他正是劳拉以前一直暗恋的对象。他开朗、热情洋溢的谈话感染了劳拉,使她慢慢地从她自己封闭的虚幻世界里走出来—在柔和的烛光下,劳拉容光焕发,美丽无比。她与吉姆跳舞,并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吻。然而,被打碎的独角兽把吉姆拉回到现实—他已经有了未婚妻,同时也使劳拉对生活刚刚燃起的希望破灭了—她重新退回到自己的玻璃世界中。如果劳拉敢于正视人生,即使她身体上有残疾,那么她也会是生活的强者。可是,现实的残酷—父爱的缺失,暗恋的人心有所属以及弟弟的离家出走和母亲所灌输的思想都使得劳拉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综上所述,这两类淑女不仅是南北战争的牺牲品,更是南方旧传统的牺牲品。她们对南方价值观的固守和执着是她们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症结所在。但威廉斯在他的剧中还描述了另外一类淑女形象,她们在骤然变化下的社会大背景下勇敢地褪去南方社会为她们戴上的光环,挣扎努力着要融入到美国妇女的主流中去,成为美国主流女性。《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的妹妹斯黛拉就是这一类淑女的代表,她采取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不耽于幻想,不为过去虚伪的社会道德所累,主动适应突变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体现出了敢于追求新生活的崭新的南方女性形象。
布兰奇的妹妹,斯黛拉在十八、九岁的时候离开密西西比,前往新奥尔良,跳离了南方那艘即将沉没的大船,抛弃了南方淑女需要遵守的道德规则。恪守南方传统道德准则的淑女是举止文雅、谈吐得体的;她们不食人间烟火,是云天之上闪耀着炫目光辉的雅典娜;传统清教主义下的淑女是精神的化身,必须掩盖自己的欲望,成为贞洁的象征,顺从的典范。然而,斯黛拉的行为都与人们心中的典型淑女形象大相径庭。在新奥尔良,她嫁给了来自社会底层的斯坦利,享受着野蛮的感官上的快乐。斯黛拉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的合理追求,虽然她的那种追求违反了清教统治下的清规戒律,可她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准则。当布兰奇对来自社会底层的斯坦利,尤其是对他的波兰血统表示不屑时,斯黛拉告诉布兰奇,斯坦利和她在家乡碰到的男人不同,南方绅士冠冕堂皇,而斯坦利讲求实际,这一切都深深吸引了斯黛拉。而且,她还和新奥尔良贫民区的居民建立了友谊。由此可见,早年就跳离南方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的斯黛拉,已经勇敢地抛下南方道德准则施加给她的压力和约束,她积极寻求对生存方式,并接受了代表北方文明的斯坦利,适应了现实。
二、结语
威廉斯曾说过他从来不写他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是怀着爱来写南方的,我知道南方社会意识到我对他们的描写是一种爱的表现。我正是对这个不再存在的南方的怀念,才写了那些导致它毁灭的力量。”正是基于这种创作宗旨,威廉斯真实地再现了南方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强烈谴责了南方旧传统观念对南方妇女的摧残和压抑。同时,这些南方妇女的悲惨境遇也映射出现代美国人物质满足之外的精神困惑与苦闷,展示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冲突,揭示出现代人耽于幻想规避现实的社会本质。体现了作者对整个南方命运及进程上的极大忧虑与关注,寄希望于南方人可以今早走出历史的阴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敢于面对现实,尽快地适应新南方。
参考文献:
[1]凯瑟琳·休斯.当代美国剧作家[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2]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3]张耘.现代西方戏剧名家名著选评[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 Williams·Tennessee.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M].New York:Penguin Books Press,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