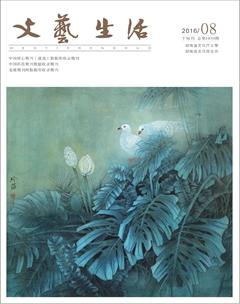言说与实践
王永鹏
摘 要:《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但在其生活的18世纪,理学权威已因种种原因受到各种挑战,其中尤以重视考据的汉学带来的冲击为最。汉学发展引发的学术话语革命,不仅提供了重新认知儒家经典的学术范式,更直接导致了理学权威的瓦解。通过研究夏敬渠在《野叟曝言》中重构理学权威的努力,我们不仅能了解那个时代“道学先生”的心理,而且可以一窥当时各种学术思潮的碰撞与摩擦。
关键词:《野叟曝言》;理学;言说;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4-0006-02
夏敬渠(1705-1787年),江阴人,著作宏富,却因未刊刻且遭战乱而散佚颇多,幸得其子祖燿搜集整理成《浣玉轩集》,部分内容得以传世,又著有小说《野叟曝言》,实以其主人公文素臣自况。夏敬渠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18世纪,这一时期正是汉学学术话语逐渐形成,“空谈性理”的理学(本文所用“理学”一词皆指狭义之程朱理学)受到学者们普遍怀疑的时期。而江阴所处的江南地区,正是这一学术话语革命的核心区域。以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学者倡导通过考据复原儒家经典的原貌,反对宋明理学把一切问题都诉诸“义理”并试图通过思辨寻求答案的做法。①从抽象思辨到文本考证,学术范式的转变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这对宋代以来确立的理学权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受家族传统和江阴理学风气影响的夏敬渠,仍然坚定地维护程朱理学,这在他存世的诗文中多有体现。②而长达一百五十四回、洋洋百万余言的小说《野叟曝言》亦成为其试图重建理学权威的工具。
一、言说: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
与大多数中国古代小说以事件为中心、多主角的特点不同,《野叟曝言》以人物为中心,只有一个主角即文素臣,且整部小说几乎以文素臣的游历为线索贯穿全书,加之夏敬渠有意识地避免使用说书人套语及小说中习见的韵文,这使得《野叟曝言》具有了鲜明的叙事特征——限制视角的广泛使用及说书人口吻的淡化。在叙述人在文本中缺席,作者放弃了无所不能的全知视角的情况下,书中人物言语的可靠性又依仗什么来保证呢?夏敬渠选择了论辩这一形式。
《野叟曝言》中有着为数不少的谈经论史与辟佛斥老的内容(往往是长篇大论),而这些内容往往以论辩的形式展开,最后以主角在这场论辩中的胜利作为结束。在无法借助叙述人权威的情况下,主角维护理学权威的言语的可靠性似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得以显现。小说第二回,在素臣大谈佛教之害与辟佛之必要性之后,“未公听得颠头播脑,把酒都忘记。伏侍的家人小子止顾在窗外窃听,无心换酒上菜。连那船家亦觉入耳会心,津津有味。满船中除了素臣的话头,寂声无息,并雨声全不理会”。③第五十九、六十二两回中,素臣两次与东方侨议论儒、道优劣,最终“东方侨如梦方觉,如醉方醒,忙起身离席,连连打拱,道:‘弟沉溺于苦海者已垂十年,今乃得援手而上。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老先生也。自此当发愤于孔孟之微文、程朱之正解,倘有所得,皆先生之赐也。”④第七十一回,素臣以孝道说服飞娘弃绝不婚不育之念,“说得飞娘面赤鼻酸,心惊肉跳,额汗津津,眼泪簌簌,大叫一声,蓦然倒地”。⑤可以说,理学的权威通过其在论辩中的胜利得以重建,另一方(崇信佛、老或背离传统儒家行为规范的人)在辩论结束后的反应则增强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
在层出不穷的论辩中,以贬斥佛、老的次数最多,言辞也最激烈。佛、老成为文素臣心中的儒教的头号敌人,不仅因其学说与儒家观念相左甚多,更是因为程朱理学被汉学家认为掺杂了佛老思想,并非是纯正的“儒学”。⑥因此,夏敬渠不得不在小说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在小说中,以道学家自居的文素臣不遗余力地抨击佛老,在第五十九回与东方侨议论时说道:“圣人之性是仁义礼智之性,扩而充之,以保四海,此圣人尽性之事也;老庄则以仁义礼智为贼性之物,而以清净为尽兴矣。圣人之命是理宰乎气之命,殀寿不贰,终身以从此圣人至命之事也;老庄则以格致诚正为害命之事,而以昏默为至命矣。故圣人之主静,以敬戒惧恐惧,其静也常惺;老庄之主静,以忘去知离形,其静也常槁。……子朱子云: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惟弥近理,故学者惑之;惟大乱真,故儒者惧之。”⑦强调佛老与儒教之“性”、“命”、“静”名同实异,指出佛老看似近理、实则乱真,无疑是试图划清理学与佛老之学之间的界限。
但是仅仅与佛、老之学“划清界限”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清初)学人把明亡归因于道德沦丧、伦理秩序崩溃,并认为它是由空洞浅薄的理学思辨引发的。”⑧面对理学“空谈性理”的指责,夏敬渠在其小说中亦借人物之口对此做出了回应。第六十二回水夫人讲“格物致知”说道:“故欲成其意,必先致知;欲致其知,必先格物,格得一物,即致得一知。事事真知灼见,不同禅悟支离恍惚。”指出理学思辨不同于“支离恍惚”的“禅悟”,而是由“格物”的实践中得来的。第八十七回素臣为东宫讲解《大学》与《中庸》之关系:“《大学》由意诚而至治国平天下,顺而推之也。《中庸》由为天下国家而至诚身,逆而推之也。顺逆虽殊,而俱归重一诚。其入手工夫,则《大学》之格物致知,即《中庸》之学问思辨也,由学问思辨以力行,弗得弗措而尽百倍之功,则愚者必明,柔着必强,而可进于诚。”⑨在文素臣看来“格物致知”与“学问思辨”本是一体,而“由学问思辨以力行”可“尽百倍之功”。这种对“思辨”的维护无疑意在证明理学方法论的合理性,从而重塑理学的权威。
二、实践:矫正理学的空谈之弊
清初汉学家们对程朱理学“空谈性理”的职责并非言过其实。“‘理学(按:指程朱理学)把伦理原则提高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虽然使古典儒学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本体论基础,但在道德实践上,把伦理原则更多地作为外在的权威,忽视了人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能动性。”⑩夏敬渠亦注意到了理学的这一弊端,并试图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的实践对之进行矫正。因此,虽然文素臣以“道学先生”自居,并以捍卫程朱理学为出发点对佛老、陆王之学进行攻击,但纵观其一生行径,却有越过程朱,直追原始儒家“修、齐、治、平”之道的意味。
《野叟曝言》第一回便谓“素臣常思遨游名山大川,以广见闻,且遍览山川形势,物色风尘,以为异日施措之地”,后其足迹几遍宇内。赖其天生神力与辟邪正气,并得旅途中结识的英雄好汉之帮助,素臣先后于福建革除男风之弊、攻取黄海诸岛、平息江西民变与苗疆之乱、诛杀景王与靳直并亲征北虏。如果说素臣的足迹仍限于明朝疆域之内,其子孙平倭,灭日本、印度、安南、西域等地佛教及其好友景日京征服欧洲二十余国,使之亦独尊孔圣则无异于替素臣践行了其“平天下”的理想。
与其过于重视“内圣”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外王”的理学前辈相比,夏敬渠无疑认为二者应当并举。但是不同于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内省”,“外王”的实践活动无疑会产生广泛的政治、社会影响。怎样确保这种会带来巨大声望和政治资本的行为的动机是出于维护儒学道统,而不是为个人谋求权力与财富呢?尤其是在叙述人几乎在文本中缺席,无法依靠叙述人权威来保证主人公的动机未掺杂个人因素的情况下,怎样处理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夏敬渠在处理这一问题方面所做的努力。
首先,小说主人公文素臣的形象迥异于传统儒生,他不仅精于诗、医、兵、算,更拥有天生神力与辟邪正气——他可以徒手搏蛟、飞檐走壁,他的随身物品和所写的字有辟邪的功效。作者甚至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可以水中取银的“不贪泉”(只有文素臣及水夫人能够取用)。一方面,“不贪泉”的出现意味着素臣已经无需利用其“外王”的实践来获取财富;另一方面,素臣为此泉取名“不贪”更说明了其对待财富的态度。而且,文素臣在游历过程中用其理学家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大批英雄好汉的支持与拥护。这些都使得其可以无需借助官方力量(如军队等)便可以实现其“外王”理想。而对于这样一个全能的儒家超人,功名利禄似乎失去了其应有的吸引力。
其次,通过文素臣怎样面对功成名就之后的加官进爵与诸多赏赐,我们亦可以管窥夏敬渠是如何试图保证主人公实践动机的“高尚性”的。如果文素臣面对封赏选择急流勇退、挂冠而去,无疑会有悖于其一直宣扬的儒家伦理,尤其是面对孝宗这样的明君,“不仕”难免“无义”。但若心安理得地接受封赏,则难免会使其“外王”实践的动机受到质疑。夏敬渠亦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在小说中进行了相应处理:面对封赏,素臣对水夫人说道:“说起天子隆恩,宠逾非礼,恩过其分,孩儿畏如烈火,竟不知何道可以消弭,望母亲训示。”111436水夫人回应道:“至汝能履盛美而恐惧,乃君子之道,但一味恐惧,便将成患得患失之鄙夫。汝遇此明主,受此殊恩,当朝夕纳诲,启沃君心,夙夜靖共,勤劳王事,登斯民于三五,臻治术于唐虞,此即持盈保泰之道。一切计较祸福之心,皆私心也。”12面对荣宠,素臣并未志得意满,而是心有惶恐,水夫人的训示则意在说明作为臣子只须尽心辅佐明君,为民造福,至于富贵,无须计较其“失”,亦不必在意其“得”。夏敬渠意图通过这样的阐述,表明一切封赏与恩宠皆是天子单方面的行为,素臣对此是无任何希求的。
三、结语:结果与目的的背离
可以看出,文素臣为了重建理学的权威做了多方面的许多努力,主要体现在其言语和实践两个方面。但当我们重新审视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他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理学家,而其所宣扬和捍卫的“理学”,不仅与“程朱”之学面目迥异,而且亦超出了正统儒学的范畴。文素臣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抛之脑后,其在历险过程中展现出的“异能”似乎与其所不齿的佛道之徒并无二致。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夏敬渠一方面借小说人物之口大力宣扬传统的儒家两性观,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地大肆描写主人公行旅中的艳遇,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通过文素臣在面对这些诱惑时表现出的正气来塑造其理学家的形象,但频频出现又异常具体的淫亵场面的描写却不得不说是夏敬渠本人潜意识中对类似性行为的渴望。除此之外,虽然文素臣面对天子荣宠能谨守臣子之礼且心有惶恐,但小说中不只一次出现用太阳这一僭越意味明显的意向来指代文素臣的情节,以及素臣好友景日京征服欧罗巴诸国建立起冠以素臣之姓的“大人文国”等内容,无一不显示出夏敬渠对权势的渴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会发现,尽管夏敬渠希望通过小说中文素臣的言语与实践重建理学的权威,但是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其所塑造的理学家的形象的虚伪。即使我们忽略小说文本中反映出的作者的潜在意识,小说主人公的言行所带来的结果仍与其出发点是相背离的。贞妇黄铁娘死后得为香烈娘娘无疑有道教“羽化登仙”之意味,素臣所上治国之策有不少与颜李学派主张相合之处,类似的内容表明,即使说理学的权威通过文素臣的言行得以再一次确立,我们也无法称其重建,而应说其重构了理学的权威——一方面,小说中理学的内容已超出了程朱之学的范畴,另一方面,这种权威更多的是通过“外王”的实践所树立的,而非是通过程朱更为重视的“内圣”之道。
夏敬渠试图在18世纪的学术话语革命中捍卫理学的权威,但其在小说中所做努力的结果却与其目的背道而驰。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看出这一时期理学衰落的必然性,更能管窥这一学术话语革命中各种学说与主张是如何碰撞并相互影响的。通过对类似《野叟曝言》这样具有鲜明特点的文人小说的解读,我们不仅能把握小说发展在这一时期呈现的新特点,更能从一个侧面去了解这一时期学术思潮的变迁。
注释:
①⑧艾尔曼(美).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②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③④⑤⑦⑨1112夏敬渠.野叟曝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2,751,862,11,1055,1436.
⑥余英时(美).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初论[A].人文与理性的中国[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⑩陈来.宋明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