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海雕
郑德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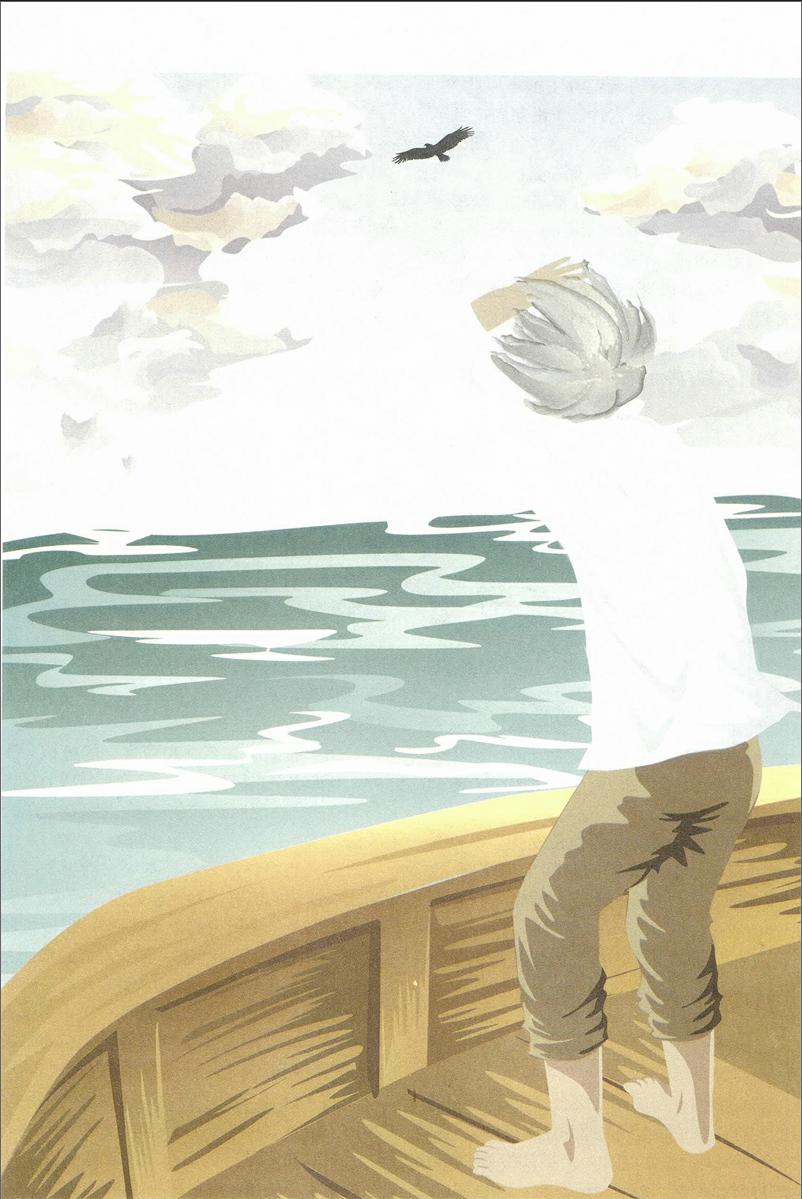
一只鸷鸟在空中盘旋。这鸟,似鹰,翅膀却没有鹰的长,似鹫,头又不秃,更不是那猫脸猴脸的枭类。它体型硕大,体羽的大部分呈油亮的黑色,翅羽的尖部和尾羽却是雪白,通体形成强烈的黑白反差,加之金黄的喙和爪子,一如印象派油画色彩淋漓的涂抹。这鸟翔在空中,发出“呼——鸥——”的啸鸣,那声音开始时好似虎啸,后又如海鸥低咽的长鸣,苍凉悠远,勾人心魄。
鸷鸟围着两条海匪船盘旋,距离也就是三五十米。两条船上的三十来号人感到好奇,都抻长脖子,头颅仿佛被绳牵着,随着乌的飞行轨迹转动。看着看着,有人猜测:“是海雕吧!”
“对,白头海雕。”有人附和。
“你看那鸟的头上有白色吗?”一位老者冷冷的一句。老者长着几根稀疏的红黄胡子,神情内敛,看那股不怒自威的架势,不用说,他就是这两船海匪的老大了。
众人再看,鸟的头部果然没有白色,却是夺人眼球的乌黑,呈现虎的条状斑纹,还真有虎的威风,于是都沉默不语。只有海浪不紧不慢地拍打着船舷,和着天空那鸟振翅的扑拉声响,偶尔便是那鸟暴戾的啸鸣。
“是虎头海雕。”老者又似乎不经意的一句。
虎头海雕在渤海一带为旅鸟或迷乌,极罕见的,难怪众人不识。
其时是农历的七月初一,海潮退得大,两个看船的人一时没注意,船就搁浅了。等到老者带着一行人逶迤回来,大伙连推带撑,无奈潮水太浅,船还是动不了。
绺子帮里,一个失误可能断送整个队伍的性命。本来,刀条脸的军师早赞画好的,这趟买卖还是海上来,海上走,趁着伪满洲国气数将尽,狠狠干他一票,弄些枪弹和钱物,留作日后的打算。哪承想,这趟出来还真不顺,踏线的连问两个地名,一个是“南营”,一个是“范屯”。“南营”即难赢,“范屯即犯事的屯子,都犯忌讳。于是,老者领着人马加了十二分的小心,在线人的内应下,很快砸开了熊岳城边满铁的熊岳票房和果木株式会社,弄了长短二十多棵喷子和一批飞子,另加两箱子黄的白的和绺子里叫做“萝卜片儿”的袁大头。回到海边上船,却走不了,这是什么时候?气得老者掏出二十响的驳壳,打开机头就要搂火,被旁边的刀条脸和手下死死抱住。无奈,只好等涨潮再起航了。
老者一脸的沉郁。他知道此时的危险,而这只乌的出现,更让他心头一凛,猛地想起早年在海参崴听到的一位老人的说法:“这虎头海雕,游荡的孤雕不仅吃海物,连天上飞的乌,地上跑的狐狸、山兔、蛇,乌龟,它都抓吃,甚至是小孩儿。更邪性的是它嗜爱人的血腥味儿,能预先知道哪里将有杀戮……”
当时还很年轻的老者听了很不以为然,“不就是一只鸟吗,这么神?”没想到,当年的传说似乎成了现在的谶语。绺子里,阅历和智慧是顶重要的。打打杀杀倒在其次。
海浪仍不紧不慢地拍打着船舷,船却还是漂不起来。
在绺子里被称作红光子的太阳开始有点偏西,照着海面和船上的人,不动声色。老者眯着眼睛瞅去,脖子上的血管就成了蚯蚓状。一时间,他望着太阳,两船的人又都望着这位绿林道上赫赫有名的老大,忽然之间,他们就发现他老了。
“千里草,带一个弟兄,把两个箱子扛岸上找地方埋了,做好标记。”老者依然看着太阳,不紧不慢地说。千里草叫董三,董字拆开,土匪黑话里就是千里草,是有名的炮头,听到老大吩咐,就问:“带谁去?”
“你定吧!”老者仍是不紧不慢的,似乎小事一桩,边说边坐到甲板上,用两手揉着眼睛。其实,这正是他的驭人之术,给手下的人充分信任,再说情况越是紧张,越要镇定,不能自己先慌了。
千里草就带一个弟兄,扛了箱子,一人一把短把锹,跳到船下。“记住,万一有什么动静,你俩就不要回来了,慢慢地转回老营。”老者嘱咐。
半个时辰过去,什么都没发生。船也渐渐漂了起来,埋完箱子回来的千里草两人,离船还有二三十步的距离了,眼瞅着就要上船……
正在节骨眼儿上,岸上的歪把子机枪爆豆般响了。
二
这一股绺子,江湖上报号“海蛟”,明的暗的计有近百号的弟兄,原为辽南抗日义勇军中的一股。绺子里的老大,当年曾在海参崴一代的绿林里混过,绰号“巡海雕”,和座山雕等这个雕那个雕的相沆瀣,以狡黠闻名。救国军的大队溃散后,他就领着这一股蛰伏在辽河的入海口一带,平日里种地,打鱼,寻到机会就啸聚起来,干一票。
而辽南的盖州、熊岳一带则是“海蛟”活动的重点区域。伪满洲国的十四年统治期间,这股绺子到这一带闹得沸沸扬扬的“大买卖”就有好几次。“绺子”行动时爱走高岗,为的是视野开阔,先发先动,免中埋伏。村民们远远看着,越怕越想看,极富刺激。
第一次,响动最大,事发却是偶然。绺子里一位踏线的来到熊岳附近的南满铁路芦屯站,正赶上唱野台子大戏,人山人海的。当地的一位姜巡捕无端毒打一位乡亲,踏线的实在看不过眼,上前劝了几句,也遭到毒打。踏线的回老营向大当家的讲了情况,弟兄受辱,绺子的名号就栽了。于是“海蛟”绺子兵分两路,一路从陆路潜入,一路乘船,攻占了芦屯火车站和警察局,掐断了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
火车站的几个日本人吓得跪地求饶,那日本人也不是传说的不怕死的武士道,有的都吓尿裤子了……警察局空无一人,那惹事的姜巡捕也溜了,捡了一条命。
绺子收缴了火车站和警察局的枪械、钱物,到海边坐船扬长而去。等到瓦房店的日本援军到来,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片汪洋无际的大海。
这一次事件过后,日本人大动干戈,从盖州城西边的西套,到熊岳城西南的龙王庙,沿海边修了一条所谓的“海防道”,以便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又在西套,鲅鱼圈西山和仙人岛修了三个海防监视哨,由伪警察和棒子队驻守监视海面;并从日本九州岛的佐世保航空队调来三架水上飞机,驻在鲅鱼圈的海边,每天起飞监视海面……
而“蛟龙”绺子也从这一次的“买卖”趟出了路子,瞅准机会就来熊岳一带干一票。
第二次,是抢伪满洲国实业厅孙厅长的老爹家。那孙家,是连在一起的三座四合院,占了半条街,四周建有炮台,看家护院的加上拿枪的长工有三四十号人。本来谋划是里应外合的偷袭,却出了纰漏成了砸响窑。那孙家身穿一身红双手使枪的十八岁大姑娘甚是骁勇,接连打伤绺子里的两个弟兄,到底被不露声色的“巡海雕”觑个机会,一枪放倒。
第三次,是绑投靠了日本人的原东北军教导团何大团长儿子的票。几个伪满军装束的人来到何大团长儿子上学的学校,说是何大团长接儿子到城里上学,就把人领走了。双方讨价还价,“蛟龙”绺子急了,就把票撕了一块一一割掉了何大团长儿子的鼻子。直到解放后好多年,熊岳一带的人还常看到露着两个黑鼻孔的这位,当然,孩子们看了都疹得慌。
第四次,踏线的进营口带回消息,一些日本人的机构开始焚烧档案什么的东西,神色凝重,而一些妇女更是哭咧咧的,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巡海雕”寻思,这伪满洲国是要黄了,将来是谁的天下还不知道,得趁乱弄点儿本钱,队伍就四下辽南。哪知,七月天里的这一次罕见的大潮,使队伍陷入了绝地。
岸上的歪把子机枪至少是两挺,互相配合,简直是弹密如雨,围绕着往船上跑的千里草两人,发出啾啾的死神呼啸。但那弹着点不行,没准头,多是从头顶飞过,倏忽一下又一连串地打到海里,扯出一片水花儿……“巡海雕”就判断岸上的对手是新手,没多少作战经验,他就让船上的弟兄都趴下,躲避枪弹。同时命令:“岸上的人不下海,谁也不要开枪。”他知道此时弟兄们的短枪够不着对手。
千里草两人趟在茬裆深的水里,跑不起来。
歪把子的子弹就围着两人打,渐渐地,岸上的枪手经过校正,子弹就开始靠近他们的身边跳动。突然一下,千里草后面的弟兄中了 弹,一下僵住,似乎摆了一个造型,再慢慢倒下,鲜血顺弹孔汨汨而出,在海水里形成一朵硕大的生命牡丹,呈现着最后的辉煌。
千里草回头看了一下,忙把身子压得更低,脸几乎贴到海面,但他还是缺少决绝的果敢,没一下扎到水里,就这一犹豫,也被打中了。千里草身体还努力向着船的方向,拼劲力气地喊:“歪脖树一一西一一五、五一一”鲜血和气体混成的血沫子从前胸喷出,喉咙里的声音就几乎听不到了,人倒在离船不到十步的海水里。
“巡海雕”眼睛都红了,但还显得很镇静,告诉弟兄都趴到船舱里,或跳到海里转到船的另一侧,躲避子弹。
歪把子机枪的子弹就集中到两条船上,很快,船的迎弹面被打出很多弹孔,密集之处简直如同筛子,海水汨汨流进船舱,间或有人中弹倒在船上,或大叫着蹿起掉到海里。
“巡海雕”就明白眼下整个绺子面临着灭顶之灾。这样熬下去,不用说弟兄们一个个被打掉,就是这船被打得这样,也走不远了。他就决定,哪怕是鱼死网破,也得闯一闯。
其实,这一次绺子刚回到海边时,“巡海雕”边走,就边把周围的地理环境察看了一番,这也是他多年绿林闯荡养成的习惯。这些年,他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毫不起眼的老头,进营口,一不赌二不嫖,就到俗称的“小天桥”坑洼甸的茶馆听评书。时间长了,他也就自己琢磨,逐渐摸索掌握了一些实用的的天文地理甚至是阴阳八卦的知识。
刚上船时,“巡海雕”一看船不能动了,盛怒之后,他马上就察看地形,甚至想把队伍带回岸上抢占地形,隐蔽起来等待潮水上涨。只是看到船的斜后方有一条白花花的涌浪,和海岸呈大致的平行状,逶迤通到远远的岸上,他明白近海处凡是翻滚浪花的地方都可徒涉,这是一条别人看不出的通道,他也就下决心把队伍就留在船上了。哪知,就是这一决定铸下大错。
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了。
“巡海雕”喊过二当家的黑话称作“二龙戏”的朱二,和三当家的马三,抻长脖子,张了好几下嘴,才说:“绺子就要哗哒了,你们两个领着弟兄,就顺这条翻白浪花水线冲出去。我闯荡江湖一辈子,现在,就跟着千里草几个留这里吧……”
朱二和马三急了,要背着“巡海雕”下水,“巡海雕”便朝天“啪啪”两枪,喝道:“你们不走,我先死。”说着,那二十响的驳壳就指向了自己的脑袋。
队伍只好下船,一人跟着一人,躲避着子弹,行动敏捷。“巡海雕”看着这二十七八个人的背影,暗暗地为他们祈祷。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他的子侄辈,跟了他多年的子弟兵,现在却生死未卜。海风吹来,他忽然感到脸上的眼泪,舔一舔咸咸的……
四
海岸上对绺子射击的队伍是熊岳城日本人的什么少年义勇军。
别看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孩伢子,那武士道的精神还挺足。他们明知时局不利,还是靠着那种胸中戾气纠集起来,从军马场弄了三十多匹大洋马,每天在城西北的死火山上冲锋劈杀,射击操练,比那正规的关东军还关东军,以图最后的顽抗。当听说满铁的熊岳站票房和果木株式会社被抢后,就一路尾随到海边。趁着两条绺子船要走却走不了的机会,两条歪把子机枪就响了。
当看到绺子开始顺翻浪花的水线往岸上跑时,一个年龄较大留着一撮卫生胡的小头目就笑了:“吆西,大大的好!”边说边和旁边的一位击掌。
歪把子机枪调整枪口,开始对绺子的队伍扫射。无奈距离太远,没什么杀伤,倒像是一路欢送的鞭炮。
朱二和马三带着绺子上了海岸,眼瞅着队伍就要没进树林里,远走高飞了。一队人停住脚步,回望海里的那两只形影相吊的船,大伙都惦记起他们的大当家的。
哪知,一场血腥的拼杀开始了。
离海岸不到百步的一道沙岗后面,埋伏着三十来匹大洋马和三十来个小鬼子。那马训练得极好,都卧着,静静地一动不动。每一匹的马旁,都趴着一个小鬼子,一只腿搭到马的后背上,等待第一时间冲锋。小鬼子结束利落,各握一把雪亮的骑兵马刀,有几个头上还缠了白布,布上写有血红的日本字,显得杀气腾腾的。
绺子的队伍正向沙岗走来,散散落落的。那沙岗后面一声呼啸,伏发,小鬼子就乘马发起了冲锋,人喊马嘶,黄尘滚滚,逞极一时的威风。
绺子的弟兄哪见过这个阵势,大多的人开始本能地躲避,几个有战斗经验的立刻卧倒射击。交锋中,小鬼子有两个从马上栽了下来,一匹马也被打倒,咴咴长嘶……但转瞬间小鬼子就冲到眼前,刀劈马踏,又一阵风似的冲了过去……
小鬼子的马队远远地停住,兜回,整队,再次发起疯狂的冲锋。仅仅两个回合,上岸的绺子全都被砍杀了。小鬼子们一个个带着满身的血污,发出歇斯底里般的欢呼,又跃马挥刀,向千米之外的歪把子机枪阵地奔去。
原来,小鬼子那留着一撮卫生胡的小头目挺有军事素养的,研习过中国的《孙子兵法》,今天带人追到海边,细细地观察一番,判断往海里冲不行,而僵持下去等潮水上来绺子船就远走高飞了。于是,就采取“围师必阙”的方式,虚留一条生路,然后用骑兵冲杀。绺子果然中计。
但是,他高兴得似乎早了点。
两只船还在海里。看得出潮水上来了,船随浪起伏,旁边远远近近,隐隐的还有千里草等几人的尸体,鲜血扩散,远远地望去,海水中形成一团团暗红的阴影。
小鬼子们嚎叫着,欢呼着,有的挽起衣裤,有的干脆脱掉了长衣长裤,大多数的把长枪放到岸上,蜂拥着向两只船奔去。他们知道,船上有绺子刚刚从熊岳票房和果木株式会社抢的钱财和枪支弹药,另外,可能还有别的贵重东西。这机会,不拿白不拿;正是享受胜利的时刻。
留着一撮卫生胡的小头目开始还有戒心,但此时哪还能阻止这疯狂的队伍,于是也加入到蜂拥的人群中。
小鬼子们边走边撩起海水,洗刷身上和马刀上的血污,得意狂妄之极。
两只船还在漂着。其中的一只一侧的甲板上,并排放着两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那枪叫一个新,阳光下枪上的烧蓝闪着幽蓝的光芒。而绺子里的大当家“巡海雕”却不见了身影。
眼看着小鬼子们就要上船了。倏的一下,“巡海雕”猛地从船舷旁的水下蹿出,跳到船上,拿起两把驳壳,疾如鬼魅。小鬼子们大惊,随即便一拥而上。
“巡海雕”却神情自若,先对带枪的,再对带马刀的,最后对徒手的,一枪一个开始点名。一个身手敏捷的家伙跳到船上,被“巡海雕”一脚踩住,枪顶着后脑壳给爆了头。
小鬼子就剩了一个,却被眼前的场景吓傻了,站在海水里一动不动。停了好一会儿,那神情才缓过来,哇哇地哭喊着,双手抱住脑袋向岸上跑去。
“巡海雕”举枪的手缓缓放了下来。有顷,重又举起,瞄准,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小子,回你的东洋老家吧!”
两阵余一人。“巡海雕”下船,把千里草等几个弟兄抱到一只船上,停放好,把船推到深水区,那船就漂洋而去,渐渐消失于天际。
“巡海雕”独自奔向岸上。
那只虎头海雕仍在天空盘旋,间或发出“呼一一鸥一一”的戾鸣。
五
仅仅过了七天,就到了1945年的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也随之垮台了。
作为日寇侵略的殉葬,渤海边上也多了一盔硕大的“鬼子坟”,战死的小鬼子的长枪短枪,马刀,包括那两挺歪把子机枪,和那些高大的战马,都散落到民间。甚至,一些小鬼子脚上的皮靴都被扒走了……
离“鬼子坟”不远,则是一盔同样硕大的“绺子坟”。
不多天,这两盔坟就芳草萋萋,似乎述说着曾经的故事。
那只孤傲的虎头海雕仍在两盔坟的附近徘徊。村民讲,这雕吃人肉吃上瘾了。
六
第二年的春天,这海边来了一位慈眉善目的捕雕人,手提一个紫铜丝编就装着机关的大鸟笼,笼内有两只咕咕叫唤的鸽子。他在海边的沙滩和林中转悠了一天,傍晚,敲开了海边林家的网铺。
开门的是林家的“大龙王爷”。捕雕人就对他讲:“我是捕雕的,找口水喝。”于是边喝水边聊。
“捕雕?干什么用?”
“啊,天津卫的一家珠宝店老板要制作一把雕翎扇,对,就是诸葛孔明手中那样的。我就盯上了一只虎头海雕,追来追去,就追到这了。”
“这雕是去年过来的,可凶了,也不怎么怕人。”
再谈,捕雕人就拿出一块金灿灿的怀表,递给“大龙王爷”,说算是准备下一段在渔窝棚吃住的费用。
于是,捕雕人就在林家的渔窝棚吃住,天天独自一人,起早贪黑,提着那鸟笼子出去转,追捕那只虎头海雕。
围着捕雕人头上盘旋的虎头海雕看到笼里的鸽子,两个眼睛滴溜溜乱转,脖子上的翎毛都扎煞开,喉咙里咕咕乱叫,扇动三尺多长的翅膀,猛扑到笼前,眼瞅着就要进笼了却被捕雕人猛地一下甩出的木棍打飞。
原来,他此行真正目的不是捕雕,而是寻找去年埋下的那两只装着财宝的箱子。捕雕人不是别人,正是“海蛟”绺子的大当家“巡海雕”。
明里捕雕,暗里找宝。一晃半个多月过去,那千里草临终说的歪脖树却没出现,把个捕雕人急得嘴都起泡了。一天傍晚,他和“大龙王爷”的十二岁的儿子云龙坐在网铺前,一老一小拉呱,老的眼睛不经意地那么一扫,就看到了柴火垛前的歪脖树。
“哎,小云龙,这棵死树从哪抠来的?”老的有一搭无一搭地问。
“就那边二道洼子旁的岗上。”小的也随嘴一说。
第二天一大早,捕雕人就出了渔窝棚,顺着二道洼子的岗上寻找起来,很快发现了那残存的树坑。以树坑为基点,向西五步,立体斩开土层,仔细观察,竟与旁边的别无二致,远非紧急情况下所能做到。“歪脖树一一西一一五、五一一”昨天的大当家的,今天的捕雕人,想着千里草生命中最后的话语,又向西确定一个五十步的位置一一洼子里一簇茂盛的河柳。捕雕人四下看看,小心地铲开草皮,就看到了那两只箱子。打开看看,东西原封未动,捕雕人就原样儿盖好。
捕雕人长吁一口气,他知道现在就是千里草两个弟兄活过来,也找不到这两只箱子了,因为标的物歪脖树没了。
捕雕人就开始一心一意捕那只雕。
然而那虎头海雕真有灵性,虽然还是常围绕着摘雕人盘旋,却绝不再接近装着鸽子的笼子。捕雕人就用烟熏弄了只獾子作诱饵,虎头海雕靠近,当看到那紫铜丝,一下产生了条件反射,还是不进笼子。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捕雕人急了,当着那盘旋的虎头海雕的面,用匕首从自己的腿肚子剜下一块鸡蛋大的肉,割下一小块抛到空中,虎头海雕敏捷地俯冲过来,空中接住,一抻脖吃了……
捕雕人把剩下的一块肉放到笼中。自己给腿上了金疮药,包扎好,就大摇大摆坐在鸟笼的旁边,静等虎头海雕入笼。
虎头海雕还真品出人肉的滋味儿,那种贪婪的欲望就被激发,盘旋两圈落在笼前,一声长叫,发疯般钻进笼子。
回到渔窝棚,捕雕人给虎头海雕戴上眼罩,开始拔那做雕翎扇的尾翼。边拔,边给一旁好奇看着的小云龙讲解:“不管什么雕,尾羽都是十根翎,就这虎头海雕独,是十二根,因此数这雕飞得稳,竟能停在空中不动。”
捕雕人拔了九根雕翎,给虎头海雕留了三根,其中一边留一根,中间留一根,为的是让它还能飞,能自己捕食儿。拔完后,就把雕放了。捕雕人说:“等到明年拔掉的翎毛还能长出来。”
小云龙就认了捕雕人当干爹,写了生养死葬的字据,给干爹磕了三个响头。那干爹也不白当,过了些日子,就把那两箱子黄的白的给了林家,林家就发了一笔横财,买房买地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等到土改,林家就相当于用这横财买了顶富农帽子。
那九根雕翎一直保存在林家。
解放后,林家人曾到天津的古玩店打听,根本就没听说有收雕翎做雕翎扇的。也许,这就是捕雕人当年为寻找财宝箱子编的一段故事,一个由头。
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通过当年的小云龙的儿子看到了那雕翎,结果大失所望,跟鹅的翎毛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又听说拿一根压到鸡架旁,黄鼠狼就不敢来偷鸡,雕的翎毛有特殊的气味儿,黄鼠狼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