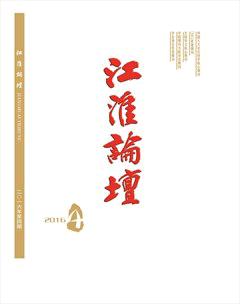梭罗的中庸之道:读《瓦尔登湖》*
王玉明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
梭罗的中庸之道:读《瓦尔登湖》*
王玉明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230036)
摘要:在瓦尔登湖畔,梭罗与山野虫鸟为邻,筑屋耕种、自给自足,呈现出一幅幅悠然自得的诗意图景,与中国传统中远离尘嚣的隐士生活颇为相似。但梭罗厉行简朴、修身养性的同时,还在田园牧歌中践行农事,在隐居山林中依然心念尘世,直至回归俗务。贯穿全书,梭罗努力在浪漫与现实、自然与文明、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借助中庸智慧,给世人指明了一条回归本真、诗意栖居的道路,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如此解读,该部经典将为中西生态文学及文明提供新的对话空间。
关键词:瓦尔登湖;自然;出世;入世;中庸之道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亨利·大卫·梭罗是美国著名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20世纪初,梭罗在美国声名鹊起,到了30年代,他已被推崇为美国经典作家、自然文学之父。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以下简称《瓦》)被誉为“绿色圣经”,迄今已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阅。该书之所以有如此魅力,主要是因为它是一部有关自然的书,一部有关修行的书,一部有关如何实现人的内在平衡及与外在和谐的书。在心灵迷失、生态失衡的现当代社会,《瓦》自然熠熠生辉。
1845年7月4日,梭罗走进自然,践行一项伟大的实验:探究自然之美与生命的本质,并借以修身养性,警示世人。梭罗栖居自然的场所是在康科德小镇郊区的瓦尔登湖畔。他自建小砖木屋,就近垦荒,开辟了豆园,自产自销,自得其乐,颇有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蕴。然而,在自然中追求简朴以修身养性并非其终极目标。梭罗倡导简朴但并未苦行,身处自然却一心梦想建构新型的城镇。梭罗走进自然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俗世。梭罗并非二元对立的矛盾体,暗涌其内心的其实是中庸的智慧,这种智慧即孔子所言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合乎时宜”与“随时变通”之间的平衡。[1]意在“中的”、“和合”,致力于“有用”,即有利,时时事事付诸行动。很显然,梭罗孜孜追求的是一种适度的状态,一种德行,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亲近自然,返璞归真,内外兼修。实践精神乃其要义,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及“天人合一”观念不谋而合,隐含其中的是东西文化的共性以及人类精神的内在互通性。就其渊源、特质及现实意义作一番探究,必将为当下全球生态问题的反思与解决提供一条绿色的文学对话通道。
一、回归本真:在自然中修身至善
“中庸之道”实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简朴、修身,在与自我及自然的和谐中追求均衡、动态的差异共存状态,它是周遭存在和发展的定律。梭罗正是在自然万物与日常景致中寻找其踪影并加以吸收的,与“中庸之道”强调的修身养性观产生共鸣。
梭罗所处的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值工业化起始阶段,人们日夜操劳,为物所役。在梭罗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实则工业化对人性的侵蚀与践踏。但可悲的是,人们深陷其中却又浑然不知。“欺骗和谬论被尊为最可靠的真理,而现实却成了虚构。”[2]96人们把想象的事情归纳为真知,在一种错误的追求下劳作,人生目标日渐迷失。梭罗在《瓦》的开篇就借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醒世人,人们应该遵循适度原则,避免极端,并实时对自己的生活加以反思,而这种自省最好在自然中完成,因为梭罗认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只有亲近自然,才能完善自我,进入更高的境界。
梭罗历来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在瓦尔登湖畔独居的两年多光景,梭罗专注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他认为:“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2]82以房产为例,“当农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不见得因此而更富有,反而会是更穷了,是房子拥有了他。”[2]33唯有降低物质需求,追求内心的宁静,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过简朴明智的生活,养活自己不是件苦事”[2]70。
梭罗搭建小砖木屋总共花费28美元多一点,14平方米的居住面积难以满足一个人正常的生活空间需要,但在梭罗看来,重要的是居住者及其生活方式。梭罗每个星期平均的食物开销只要0.27美元,即便在那个时代也少得可怜。但梭罗却能自得其乐,他就是想让人们知道,生活是可以很简朴的,“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使生活舒适的东西,非但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定阻碍人类的崇高向上”[2]13。梭罗的简朴应该理解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某种目的。[3]他以湖畔生活验证着自己的主张:唯有在简朴而真诚的生活中,人们才能真正地发现自己,超越自己,生活的真谛并不能从城镇的喧嚣忙碌中得到。基于此,梭罗试图对康科德居民那种虚伪浮夸、漫无目的的生活方式进行批评与反思。
作为梭罗的精神自传,《瓦》是一本有关修身的书,整部作品从不同层面围绕修身这一主题展开。在瓦尔登湖畔,梭罗通过寄情山水以获得精神层面的提升,寻回生命的本真。梭罗的修身养性是在他与自然荒野的完美融合中悄声无息地完成的。正如美国自然文学家奥尔森所言:“荒野之于美国人而言,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现代生活高度压力的矫正法、一种重获平衡和安宁的方式。他们走向荒野是为了心灵的健康。”[4]梭罗选择暂居湖畔、临近荒野,是因为他深信,湖是大地的眼睛,荒野则是最美丽的风景。在《瓦》中,字里行间浸透着梭罗对自然深沉的爱。他甚至建议每周只需工作一天,剩下的六天皆可用真心去探索、体验自然之美,因为靠近自然这片不息的生命之源,与其和平共处,融入其中,就能产生最大的愉悦,激发伟大的思想。梭罗总在感慨自己是绿叶和草地的一部分,与脚下的大地息息相通。这与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境界颇为相似。
梭罗注重从个人道德良心的角度阐发自我修养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被喻为“瓦尔登湖畔的孔子”。在小屋独居的两年多时间里,梭罗以文学的、超自然的方式探测湖水,感悟自然中的一切。“有时我感觉到,可以在大自然的任何物体中找到最为甜蜜温柔、最为率真和令人鼓舞的伙伴。”[2]132梭罗深信,融于自然的人,只要感官仍然健全,就不可能孤独,更不会抑郁,他所能体悟到的只会是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绵绵细雨飘落下来,我突然感到和大自然为伴是这样甜蜜,受益无穷,就在雨点的啪嗒啪嗒声中,在我房子周围的每一声音和景象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难以言表的友善,像一种氛围支撑着我。”[2]133在这里,瓦尔登湖不仅仅是一个湖,而且还是梭罗的精神家园。
梭罗重精神而轻物质,一生探索并追求更高尚的精神生活。在湖畔隐居期间,梭罗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床后要洗澡,以达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状态。梭罗同样信仰“德不孤,必有邻”,因此,他毅然选择暂离城镇的喧嚣,独居林中而丝毫不畏惧孤独。当然,与自然相亲相近同样不是梭罗的最终目的,修身养性才是其真正的追求。《瓦》中处处流露着梭罗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对生命价值的珍视。梭罗走近瓦尔登湖,试图重建一个新伊甸园,一个道法自然的理想国,通过简朴实现精神的超越,以达到修身养性的境界。梭罗亲近自然、反思自我的场所既非真正的荒野,也不是喧嚣不止的村镇,而是一片位于小镇郊区、荒野边缘的中间地带。
二、栖居于中间地带:在田园牧歌中回归农事
《瓦》中虽然弥漫着诗意、浪漫的田园情怀,但始终围绕农事展开,与美国的农事传统关系紧密。梭罗还大量引用维吉尔的农事诗,罗马的农业书写等,该书甚至对建筑村舍也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梭罗所主张并亲历的农事并非一种单调的、奴隶式的劳作,而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农事活动,致力于在浪漫诗意和田间实务之间寻求平衡。梭罗在村镇和荒野之间选择瓦尔登湖畔这一中间地带暂居,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农事与牧歌之间来去自由、游刃有余。
首先,梭罗极力为农事传统正名。一般来说,农事伦理注重实践的价值,认为劳动就是生活,与崇尚闲暇就是生活的田园牧歌式伦理不同。在梭罗看来,农事重在实践,而农业的文学想象总是有意无意地掩盖其本质特征,自维吉尔以后的农事书写近乎是诗意、田园、牧歌式“景观”的代名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虽摈弃了工业文明的丑陋,却置身过于理想化的自然之美。梭罗退守瓦尔登湖畔,独居小屋,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浪漫的、田园牧歌式的做派。其实不然,梭罗是试图通过某种博弈以唤醒人们对农事的尊重。作为一名超验主义知识分子,梭罗反思人们对农事的偏见,认为上帝为人类创造双手是用来劳动的,农事活动是上帝对人类的教化。修复农事的声誉是19世纪多数美国超验主义者致力完成的一项大业。
梭罗所推崇的农事并非卑微低下的劳作,殷实的物质生活亦非其追求的目标。古代诗歌和神话至少已经表明,农畜牧业是神圣的艺术,但是当人们因贪婪和私心而追求扩大生产,追求高产量的时候,农事已经不再,景观也随之贬值,农夫也就过上了最为卑鄙的生活。梭罗深入研究了农事活动的历史,他认为在人类文明之初,各种有关农事活动的庆典、仪式和节日凸显农事活动神圣而虔敬的意义。但是在19世纪梭罗所生活的时代,乡村自给自足的小型农场多半已被商业化农场所替代,农夫变成了农业产业经营者,在梭罗看来这是一种堕落,农场主们如同乞丐一般,不满足于既得的享受。
在《瓦》的开篇,梭罗便已表明,现代农夫比古代的奴隶还要卑下和不自由。“我在康科德做过多次旅行。所到之处,无论是在商店、办公室、田野上,我都感觉居民似乎是在以千种非凡的方式苦行赎罪。”[2]2当农业商业化或产业化的时候,它即失去了原有的魅力,这是梭罗在自己开垦的豆园上耕作后的一番感悟,“由于贪婪和自私,以及我们大家都具有的把土地视为财产,或用来获得财产的主要手段的卑下习惯,风景被破坏掉了,农耕和我们一起堕落了,农民过着最卑贱的生活。他只是作为一个掠夺者了解自然的。”[2]167因此,梭罗在第一季将略有盈余的农产品用于出售之后,随即缩小规模,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种植,进而将自己的田地保持在一种半开垦状态。他也一直告诫自己:“我不会在又一个夏天花这么多的力气种豆子和玉米了,而要种下真挚、淳朴、信念、天真这样的种子。”[2]165这就是梭罗在《瓦》中不止一次呼吁人们所要遵循的适度原则,他坚持在精神及审美健康与身体及土地健康之间取中间点,因为适度,人们会有时间散步、阅读和写作,生活就会变得充实而又高尚。
梭罗研究学者蒂尔曼认为,《瓦》是农事理想和诗意田园的糅合,既有对诗歌和沉思优哉游哉的享受,又有着对劳作、艰辛、农事科学和常识的尊重。与爱默生将农夫视为联系人类与自然的“中间世界”一样,梭罗倡导美国人做一个在城镇与荒野之间的小农场上耕地的农夫,既不受文明的奴役,又可逃脱荒野带给人类的孤独与恐惧。[5]
通过重构“略有余粮的农场经营模式”,梭罗在农事之余留出一点闲暇以享受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以求处于自由状态。在《瓦》中,梭罗所追求的田园并未脱离现实基础,他所亲历的农事也没有变味,虽为垦荒耕植,但细腻、润泽,不失泥土味和浑朴的风格。就是在这样一种中间状态,梭罗精心构筑牧歌式的家园:诗化的村庄、农场和农事。这种中间状态实为令人尊重的观念抑或无法撼动的隐喻,一种道德境界,近乎完美地隐含于既不太荒野也未过城市化的乡村秩序的意象之中,充当调和的力量,在实用的进步主义和浪漫的原始主义之间建立有益的平衡。
农事传统的景观化或劳役化都会让梭罗深感痛心。在瓦尔登湖畔,梭罗希望做一位“高尚的野人”,古老农事传统的守望者,努力呈现农事活动的原初面貌,因为唯有在农事中,梭罗才会感觉与生活及大地联系密切。在瓦尔登湖畔这片中间地带,梭罗既可以田园放歌、优哉游哉,又可以躬身田地,自给自足,在诗意追求与尘世俗务之间来去自由、悠然自得。他如此生活的目的恰恰在于为农事传统正名,并通过唤醒麻木劳作的人们,恢复农事的神圣性,希望美国人成为 “诗人般的农夫”抑或“农夫般的诗人”。
三、经世致用:在“出世”中寻求“入世”
在瓦尔登湖畔,梭罗选择与山野虫鸟为邻,以孤独为伴,以阅读四季及山林为乐,像一位遁世者,远离尘嚣,安于一隅,自得其乐。但是稍加探究,我们便会发现,梭罗并不像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隐士,仕途受挫后,被动无奈地出世,归隐山林,独善其身,甚至终其一生。隐居抑或出世对梭罗而言,只是一种生活实验,回归社会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梭罗的“出世”和“入世”都是主动的,他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的同时,终究不忘以出世时获得的顿悟启发世人。
梭罗虽被誉为美国独处的先哲,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的小屋离最近的邻居只有1英里远,大约20分钟的步行路程;离他妈妈居住的康科德村镇也不远,为的是能够时不时回家取甜饼;离瓦尔登湖对面运输冰块和农产品的铁路只有半英里远,以至他经常沿铁路边散步;离通往波士顿的那条公路也就只有300码的距离,当有运输农产品的马车队伍经过时,马具的铃声在顺风的情况下,会自然飘进梭罗的耳中,他常常乐于倾听,其乐无穷。更重要的是,经常会有拜访者进出湖畔的小屋。梭罗的研究者威斯莱尔曾坦言,有人误认为梭罗是一位隐士,对他人漠不关心,其实,梭罗关心邻居的需求,经常替人请愿,他关注社区事务,和爱默生一样反对蓄奴制,不止一次帮助黑奴逃往美国北方或者加拿大。对于黑人,梭罗充满了同情和欣赏。梭罗对时事弊病的批判更是一针见血,丝毫不会含糊其词,更不会以图自保。梭罗虽然不是一个爱群聚的人,但是他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已。
梭罗选择独居湖畔林边为的是能有一处安逸栖居之所,以及来之不易的闲情逸致,以期从湖畔的实验中真正获益。但是梭罗并没有将荒野与城市对立起来。他痴情荒野,同样热爱城市周围被开垦过的林地,以及在土地上耕种的人们。《瓦》并未宣扬消极的“出世”观念,而是为世人指出更积极的“入世”道路,即通过回归自然、培养独立的人格和简单的生活方式来抵抗繁杂的物质文明,这就是梭罗践行的世俗的超验主义。
在《瓦》的第一章,梭罗就向世人表明,他在瓦尔登湖畔开垦种植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不必过长。“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里的过客了。”[2]1在结尾,梭罗重申:“我在林中第一年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年和第一年很相像。1847年9月6日,我最终离开了瓦尔登湖。”[2]321既然梭罗已经完成了他的实验,就不必继续独居湖边,因为他从不执意要做一名隐士。他注重的是生活的自由,而不执着某种外在的生活方式。梭罗一开始就声明,他到林中居住,因为他希望生活得从容一些,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他不希望过那种不是生活的生活,除非必须如此。或许唯恐后人发生误解,梭罗在“来客”这一章再次表明:“我认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社交。我天生不是个隐士。”[2]141在瓦尔登湖的生活也并非超凡入圣、至高完美的,梭罗以批判者的身份,唤醒人们对现世不足的关注。“我不打算写一曲沮丧之歌,而是像一只黎明时的雄鸡,站立在鸡棚上引颈高歌,哪怕只是为了唤醒我的邻人。”[2]85由此可见,梭罗“出世”的终极目标是“入世”。
梭罗是带着感悟“入世”的。他再三提醒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只会给自己戴上一副镣铐,只不过这镣铐是金子的。“当人如此低贱之时,自然之美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走向湖边,是为了看到自己宁静的精神映照在湖面之上,可是当我们的精神不能得到安宁时,到湖畔去是没有意义的。”[6]梭罗非常清楚,精神的宁静只有在自然荒野之中才会获得,所以他首先选择来到湖畔。然而,梭罗又没有完全否定生活的物质层面,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这两者他都很尊重,这等于实践了中庸之道所隐含的“不偏不倚”的观念。如前所言,瓦尔登湖距文明世界只有一步之遥,他并没有脱离他厌恶的世界。他走向湖畔时没忘了拿上一把斧子,一把锋利的斧子,用以筑屋。这一点至关重要。梭罗躲进伊甸园的时候,没忘了随时可以再回到他批评的这个世界中来。[7]
在《瓦》中,梭罗隐居湖畔的同时还向世人展示了作为斗士的一面。对于社会弊端,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梭罗对人类社会中他认为是恶的东西的憎恨程度不下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梭罗身上,有着隐士和斗士的奇妙结合。[2]代序:8-9作为一名超验主义者,梭罗努力超越物质世界最终是为了改变它。《瓦》记录的恰恰就是其改变物质世界的方案。很显然,湖泊山林并不是梭罗的最终目标,而是实现自我救赎与复兴的场所。经过自然的洗礼,梭罗期待重建一个精神更加高尚的有机社会。在一个因商业化而变得冷漠的时代,带着这份神圣的使命,梭罗亲历自然,实践其中,然后再回归世俗,从一个高尚的野人的视角,给世人展现一种“更高的精神法则”。而梭罗这一伟大理想的规划与想象化的实践均在自然荒野中完成,因为他深信,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存这个世界。唯有保护好自然荒野,人类才不会丢失自己的心灵。“入世”后的梭罗肯定不会忘却那一片湖泊山野,因为那儿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下一次出征与洗礼的发生地。也正因此,梭罗被后人誉为美国自然文学之父、环保主义的先驱。
四、东西互鉴:生态视域下的对话想象
梭罗在《瓦》中表现出来的中庸智慧在本质上是他对自然本真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生发于他对东方经典的阅读与思考,抑或两者的杂糅,蕴含其中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与丰富的生态情愫。在生态危机日渐蔓延的当下,这种智慧为中西生态文学和生态文明对话、构建全球生态话语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学真正产生深度碰撞应该始于19世纪,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对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所产生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爱默生接触到了欧洲学者翻译的《孔子的著作》和《中国古典:通称四书》,书中的思想深深打动了爱默生,他甚至称后者为“我的中国书”,足见他对该书的喜爱程度。爱默生把孔子与基督耶稣并行比较,然后论证说孔子提出“中庸之道”的时间比耶稣提出“金科玉律”的时间早了整整500年。[8]在《经验》一文,爱默生说:“中间世界最好,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乃上策。”作为梭罗在哈佛大学的一位重要导师,爱默生对于梭罗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梭罗虽早在1838年就在日记中提及孔子,但对东方经典的系统了解大致始于1841年,当时其导师爱默生赴国外讲学,梭罗搬入他家居住,真切地接近儒家思想并逐渐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亲切感。1843年他选登在超验主义俱乐部喉舌杂志《日晷》上的21条语录就出自他此前的读书笔记。在哈佛求学期间,梭罗潜心研究修辞的同时广泛阅读欧洲及东方经典。学习古代典籍,凝思于久远的伟大而不朽的思想,大大提升了梭罗的心智,使其视野豁然开朗。他呼吁人们重视东方文明,认为西方世界尚未从东方取得它注定要接受的全部光亮。[9]
在梭罗看来,在道德堕落、人心迷失、物欲横流的年代,重温古代东方贤哲的思想不无益处。梭罗参阅东方著作的目的是透过东方智慧来省察西方世界。很显然,梭罗在《瓦》中表现出来的人文情怀及生态情愫与儒家思想不无关联,林语堂曾言,在所有的美国作家中,梭罗的人生观该是最富有中国色彩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与梭罗心心相通。在日益遭到工业文明破坏的自然面前,在寻求精神独立的时代,急于摆脱欧洲文化羁绊的爱默生和梭罗等悄悄地将目光转向东方。他们希望从异质的古老文明中找到不一样的智慧,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布伊尔所言,梭罗身在地方,却着眼全球,从某种意义上讲,梭罗及其导师爱默生是世界哲学家、作家,他们的思想没有地理和历史的国界,与东方哲学家不无共通之处。[3]23-24
《瓦》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与互建的典范。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行孔子之道的时代,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时代,最令人向往的时代。”[10]当今社会,在人与自然,以及多元文化之间开展对话是必然趋势。而儒家思想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各种对话提供丰富的资源。[11]《瓦》中或多或少蕴含儒家智慧,在19世纪人为物役的美国,这种智慧曾是一剂良方妙药,治愈了美国人的工业病,教会他们学会仰望天空,敬畏大地。在当代,这种智慧又重新回归东方语境,被慢慢挖掘,为重审我们的传统,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找寻一条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路径带来一种似曾相识的启示。[12]这一过程实则东西互鉴的过程,是两种话语和哲学体系进行建设性对话的过程。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两个月后就离开了,但是他与自然亦或儒家的对话却远未结束。在《瓦》中,梭罗也是这样暗示的,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只要自然尚存,两者之间的对话就是未完成的,因为对话是一种理想,是对人与自然以及文明之间冲突的充满现实意义的回应。唯有对话,才会带来无限生机和希望。
五、结 语
在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之间,现代资本主义在美国逐渐形成,商业和工业资本开始掌控一切,日益征服人的肉体和灵魂。人们追逐物质、唯利是图,贫富悬殊日渐加大,形成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有良知的人都在寻求超越政治的解决方法,要么是地理的,要么是历史的,要么是精神的,要么兼而有之。
梭罗就是这么一位仁人志士,一直致力于记录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异化状态,努力追求一种警醒与昏睡之间的平衡,以期修身养性,涵养并留存其道德观的精髓。梭罗崇尚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对这种价值的认可是一种有道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融入自然、反思自我,记录点滴感悟以期警示世人。梭罗将单纯的自然日志书写提升到一个更崇高、更精神化的境界,其中梭罗集中呈现的是一种适度的准则。在瓦尔登湖畔,梭罗将简朴与修身放在首位,以探究人生最基本的、得体的需求;梭罗在恢复农事传统的同时又在告诫世人千万不可成为劳作的奴隶,但梭罗的农事又不失田园牧歌的意味、诗意的向度;梭罗隐居湖畔小屋却不忘俗务,直至回归村镇;梭罗走进荒野,终究是为了感悟并回归尘世。
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中点”,一种基于数值分割的“黄金中道”,梭罗在权衡各种可能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做出明智的判断与选择,其理想的境界是“和”:一种平衡的、发展的和求同存异的状态,一种宁静的,更接近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庸之道,梭罗及其作品的伟大之处可能就在于此。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种“伟大”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今天看来,梭罗及其《瓦》的意义主要在于,当人类一路高歌,不择手段追求物质财富,并将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有一个声音终究会回响在他的耳旁,提醒他停下脚步,回望原初,放慢节奏,换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健康的、不失诗意的栖居方式。
在19世纪中期,环境问题自然还未凸显,梭罗隐居湖畔也许并非为了什么环保,但这并不妨碍当下的我们对梭罗进行生态解读,因为他在《瓦》中走进的是人类共同的自然,反思的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努力构建的是一种普适的伦理价值体系。因此,该书关乎人类乃至生态的整体,及未来与发展,没有地理、历史或文化的界限。[13]在瓦尔登湖畔,梭罗与其内心及自然开展对话,获得了对人生深切的体悟,由此形成的文本已经沉淀为超越时空的、实现价值践行与意义追寻的自然书写典范,可以直接同世界范围内身处心境及环境危机的广大读者进行对话。要想使得这种对话更加深入,更富成效,更能启示人类未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学者同样也要展开多元对话。由此,我们才能更加充分地发现该书的人文内涵及生态意蕴,更好地理解并享受这本伟大的书。
参考文献:
[1]阮超群,陈选华.论和谐源于规则——一个基于《论语》的视角解析[J].江淮论坛,2013,(4):113.
[2][美]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M].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3]Robinson,David.Emerson,Thoreau,Fuller,and Transcendentalism[J].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2007:25.
[4]转引自:张冬梅.寻归荒野——论自然文学佳作《克罗斯小溪》中的心景[J].江淮论坛,2016,(1):188.
[5]姚桂桂.美国重农神话与美国农业政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29.
[6]转引自毛亮.“疏离”与“参与”:梭罗与《公民的不服从》[J].外国文学评论,2013,(2):30-32.
[7]莫天.东方伊甸园 西方瓦尔登湖[J].绿叶,2015,(1-2):96.
[8]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6-19.
[9]杨金才.梭罗的遁世与入世情怀[J].南京社会科学,2004,(12):74.
[10]转引自左言东.人类危机呼唤孔子智慧[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66.
[11][美]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彭国翔,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6.
[12]张造群.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根基[J].社会科学战线,2014,(11):24-28.
[13]冯天瑜.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当代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2014,(1):77-83.
(责任编辑无逸)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157-006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SK2015A344);安徽农业大学学科骨干培育项目(2014XKPY-77);安徽农业大学繁荣哲学与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012zs01zd)
作者简介:王玉明(1970—),安徽天长人,副教授,2009年赴美国麻省州立大学阿姆斯特分校和罕布什尔学院访问学习,主要研究方向:美国生态文学及美国文学生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