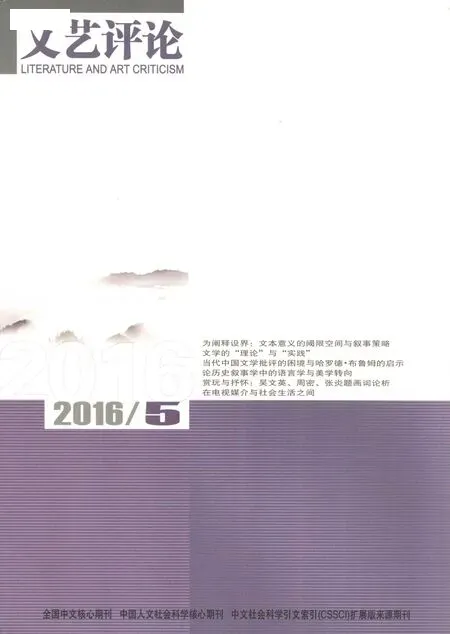赏玩与抒怀:吴文英、周密、张炎题画词论析
○陈琳琳
赏玩与抒怀:吴文英、周密、张炎题画词论析
○陈琳琳
有宋一代,词是“一代之文学”①,绘画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二者皆是当时最富生命力的艺术样式。词是一种时间性的音乐文学,绘画是一种空间性的平面艺术,题画词②将词、画紧密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题材,为观察词与绘画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与层出不穷的宋代题画诗研究相比,宋代题画词较少受人关注,相关的研究论著较少。③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注重宏观考察,深入到题画词的文本内部,具体探究题画词的情感内蕴与艺术风貌并不多见,题画词特殊的创作技巧甚少被提及,这一方面的空白值得填补。
通过翻检《全宋词》④发现,相比题画诗的普遍繁荣,题画词的创作在宋代并不是十分发达,但是,绝大多数的宋词名家都曾参与题画词的创作,如苏轼、秦观、辛弃疾、吴文英、陆游、刘辰翁、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有题画词存世,足见“以画入词”这种艺术方式在宋代已获得较普遍的认同,尤其在南宋后期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创作高潮。风雅词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英、周密和张炎三人共创作了59首题画词,占据宋代题画词创作总量近四成。南宋后期的题画词创作臻于成熟,代表着宋代题画词的艺术高峰,且宋元易代的历史背景为题画词注入了特殊的情感内蕴。笔者以这三位词人的题画词创作为论述中心,具体分析南宋后期风雅词人独特的审美趣味与思想情感,探讨词与绘画如何在题画词中突破各自的局限,进行充分的对话与融合,以此透视宋代词与绘画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
一、南宋后期题画词创作的勃兴
题画词在南宋后期的勃兴,与风雅词人的生活趣味有密切关联。吴文英出身虽不显赫,但长年曳裾王门,交游显贵;周密、张炎早年成长于书香贵族之家,饱受浓厚的文化氛围熏染。安逸的生活使词人醉心于诗酒优游,琴棋书画成为其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词人以绘画作为遣兴抒怀之余事,周密“善画梅、竹、兰、石”⑤,张炎亦工水仙。绘画实践促使词人更加熟悉绘画技法,为品鉴画作打下了专业功底。而且,伴随着宋代书画收藏风气的兴盛,书画的品题鉴赏成为词人吟社唱和的重要内容,张炎曾多次写墨水仙赠答好友,周密“以鉴赏游诸公”⑥,题画题材更频繁地进入文学唱和之中,成为词人切磋词艺、交流思想的一种常见方式。
与此同时,历经近一个朝代的积累,绘画与词这两个艺术门类在南宋后期皆进入成熟期。在绘画方面,宋代绘画逐渐朝着文人化的方向发展,画工的文学修养有所提高,绘画的文学性不断加深,文学主题越来越受到画家的关注。花鸟画科的繁盛,与题画词创作的勃兴关系颇为紧密,王朝闻《中国美术史》称:“一般而言,人物画科更近于叙事诗,山水画科更近于抒情诗,而花鸟画科更近于为‘诗余’‘艳科’的词。”⑦工笔重彩的院体花鸟追求工细秾丽,暗合传统艳词的摹写风格,为词与绘画的结合提供了直接素材。伴随着文人画发展的深化,兼以当时禅理学之兴盛,水墨写意花鸟画在南宋后期广为流行。这种新型的花鸟画多取材于林木窠石、梅兰竹菊,作画方法类似书法,适宜文人操练,且往往被寄以清高萧散的情致,既契合吟玩墨戏的风雅闲情,又符合文人孤芳自赏的时代心理,是激发词人创作题画词的一个重要动因。在文学方面,吴文英、周密、张炎皆师承周邦彦、姜夔一脉的“雅词”传统,追求“格高调雅”的审美风格,重视词的音韵谐美与修辞技巧。词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已经接近尾声,常见题材多已被充分发掘,难以翻新,词人的创作重心渐由拓展词的题材内容转移到强化词的审美价值上,极尽能事锤炼字面。精细化的描摹技巧为词人题画提供了技术支持,层层铺叙、细细勾勒的语言技巧更易于淋漓尽致地再现绘画,尤其擅长再现精巧细腻的画作细节,带给读者逼真的视觉想象。
词的地位提升亦是“以词题画”的一个重要前提。祝振玉在《略论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几个原因》中说道:“像绘画作品这样具有高雅身份的表现上,可以用诗写之,才能使画家满意,被看作是锦上添花,如果以词题之,那简直是轻慢不敬著粪佛头了。”⑧绘画在中国古代被赋予了教化的社会功能,唐人张彦远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⑨,绘画享有与诗文同等的崇高地位,若以早期被视为“小道”的词来题画,便显得不够庄重了。然而,经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革新,词逐步摆脱遣兴娱宾的单一娱乐功能,充分吸取诗文的审美趣味和创作技巧,逐渐变得士大夫化,被赋予了与诗文相类的言志功能。在此基础上,南宋中后期的风雅词派更通过“复雅”为词“尊体”。词的雅化使其具备与诗文同等崇高的精神品格,词体的地位得到大力提升。至此,词既能充分抒写自我怀抱,又具备高雅的审美特质,自然也就能与绘画相提并论了。
二、题画词的情感内蕴:赏玩风调与遗民心绪
考察现存的宋人题画词,纯粹摹写画面、重现画境的作品并不多见,大部分作品以再现画面切入,重在表达审美感受,或借画怀人,或以画言志。限于词的文体特征,题画词甚少通篇阐发绘画理论或剖析画作所蕴含的哲思,多将词人独特的个体情感融入审美体验。风雅词人的题画词尤其如此,诗意的生活方式赋予他们赏玩的闲情逸趣,画卷成为他们把玩的对象,“细玩”“展玩”“清玩”等词眼屡次在其题画作品中出现。他们善于观照画中形象,反复把玩画意,提炼画作精神,借题画词传达一种风雅情调。如张炎词《卜算子·黄葵》:
雅淡浅深黄,顾影欹秋雨。碧带犹皴笋指痕,不解擎芳醑。休唱古阳关,如把相思铸。却忆铜盘露已干,愁在倾心处。⑩
这是张炎为友人伯寿题四花词的一首。词人先点出黄葵花瓣清雅的颜色、花枝孤立的姿势,接着把视线移至瓣下绿叶,绿叶托起黄葵,犹如纤纤素手擎住金盏。黄葵酒盏似的别样形态,迎风微荡的动人之姿,仿佛超越了画幅而回归自然,散发盎然生意。词人宕开画面,由花的形状联想到铸相思的酒杯,贮满词人的相思与愁苦。通过这一番展玩,画中之花所寄寓的精神内涵被阐发出来。
创作题画词时,风雅词人反复琢炼字句、雕刻形象,试图营造清雅朦胧的意境,将真情深隐其中,使得题画词也成为读者的把玩对象,须反复赏玩才能有会于心。这一特点在吴文英的题画词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吴文英在再现画面形象时,常常赋予画中形象多重情感内涵,含蓄地传达幽微的情思。如《望江南·赋画灵照女》词:
衣白苎,雪面堕愁鬟。不识朝云行雨处,空随春梦到人间。留向画图看。慵临镜,流水洗花颜。自织苍烟湘泪冷,谁捞明月海波寒。天澹雾漫漫。
灵照女一事本是一个富有喜剧性的佛教故事,⑪在吴文英笔下被赋予了悲剧气息。“自织苍烟湘泪冷,谁捞明月海波寒”,以湘妃与李白的故事暗喻灵照女投水而亡。大概吴文英所题画卷或是灵照女画像,或是白衣女子徘徊江际的片段。吴文英为她安排了投江的命运,但为何投江,是效仿湘女殉情,还是失足落水而亡,还是另有缘故?吴文英借“灵照女”的悲剧形象,是对佛学观念的质疑,还是对生命凋零的哀伤?是对坚贞不渝的爱情的怀疑,还是因其曾错过如此女子而抱恨终生?其中意味只能留待读者细细把玩。正如邓乔彬先生所述:“这种欲露不露,不落言筌的情志,正是反复缠绵,深加锻炼的结果。”⑫词人细细把玩的审美心理恰恰促成了这种含蓄多歧的情感表达方式。
在赏玩性的审美趣味的驱动下,在各类画作题材中,风雅词人尤为青睐情趣盎然的花鸟画。⑬南宋后期,偏安享乐的生活被战火打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步入晚年的吴文英已经感受到王朝大厦将倒的亡国气氛,周密和张炎的生平横跨宋元两代,对国恨家难更是刻骨铭心。在这个敏感的朝代更替期,有些词人选择为民族兴亡奔走高呼,有些词人则跳开激烈的外部矛盾,回归自我内心世界。所谓“一花一世界”,词人从一花一草中感受心灵的微小波澜,感悟整个世界的变迁。此时,南宋主流绘画的表现重心亦由“大山堂堂”转移到“半边山水”,画家在一丘一壑间寄寓自我情怀,从边角化的山水中寻求内心世界的平和,醉心于内心世界的开拓与独立精神的建构。风雅词人的创作精神与宋末画家相通,这是他们在画幅上进行情感对话与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前提。于是,北宋中期由苏轼等文人掀起的“墨戏”画法在宋末成为一时风尚,这种游戏笔墨极为契合宋末词人的赏玩心理,如张炎词《临江仙》:
甲寅秋,寓吴,作墨水仙为处梅吟边清玩。时余年六十有七,看花雾中,不过戏纵笔墨,观者出门一笑可也。
剪剪春冰出万壑,和春带出芳丛。谁分弱水洗尘红。低回金叵罗,约略玉玲珑。
昨夜洞庭云一片,朗吟飞过天风。戏将瑶草散虚空。灵根何处觅,只在此山中。
张炎创作此词时已走到生命的尾声。平生坎坷难以娓娓道尽,不如付诸游戏笔墨,与挚友吟赏展玩,一笑置之。结句“灵根何处觅,只在此山中”既是对水仙幽独品格的赞美,更是其孤高人格的自我写照。在元初的文化高压之下,文人只能借“墨戏”浇心中块垒,显然,“墨戏”并不是真正的游戏,而是文士寄托情志的一种既高雅又安全的创作方式,其中的清高与无奈含蓄地透显出来。
周密与张炎俱成长于钟鸣鼎食之家,早年过着诗酒优游的富贵生活,安逸的生活被蒙古铁骑踏碎,他们的社会身份由高贵的士大夫跌落为异族奴隶。词人经此重大的家国变故,今昔盛衰之间不禁产生人生幻灭之感,周密《武林旧事》云:“曳裾贵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⑭繁华的过去,痛苦的当下,迷惘的未来,词人无法从残酷的现实解脱出来,反映在题画词中便是不断地流连过往,为失落的心灵寻求安慰。
昔时宴饮聚会的欢乐被定格在画卷之上,现实却是山河残破、繁华难再。前代的画作或绘画题材被置于当前的生活语境之下,呈现出巨大的今昔反差,譬如《雪溪图》《渔乐图》《倦耕图》等传统画作题材,进入到词人的审美视野之内,往往勾起他们对故园的怀想,从而燃起创作欲望。张炎《湘月》词小序云:“余载书往来山阴道中,每以事夺,不能尽兴。戊子冬晚,与徐平野、王中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萧飒。中仙有词雅丽;平野作《晋雪图》,亦清逸可观。”赋画雪景本是绘画中的一个常见题材,因其呼应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常寄寓晋人的风雅情调。借助题画,张炎称颂晋人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的生活方式,而回归现实,“堪叹敲雪门荒,争棋墅冷,苦竹鸣山鬼。纵使如今犹有晋,无复清游如此”,战乱毁坏了湖光山色,山阴道上难以复现往日清游的雅兴,晋人风度只能交付画面寄托,高蹈出尘的隐居理想被现实残酷地销蚀,强烈的失落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复如张炎《如梦令·题渔乐图》词:
不是潇湘风雨,不是洞庭烟树。醉倒古乾坤,人在孤篷来处。休去,休去。见说桃源无路。
渔乐、桃源亦是绘画中的常见题材,画家借以抒发隐居理想,词人却在结拍末三句直接表明对桃源世界的质疑。伴随着异族的入侵,能够寄放词人灵魂的精神“桃花源”已不复存在。他们或迫于现实出仕,隐忍奉事于异族统治者之下,或试图隐居山水,然国破山河的易代之感始终萦绕心头。精神家园的今昔之别,为题画词蒙上了一层悲剧意味。
绘画往往蕴含着画者个体的生命体验,遗民画家试图用线条与水墨传达自身的心绪,具有类似经历的词人观之,如有切肤之痛,促成了题画词的创作。张炎有两首题写郑思肖《墨兰图》(图1)⑮的词作:
黑云飞起,夜月啼湘鬼。魂返灵根无二纸,千古不随流水。香心淡染清华,似花还似非花。要与闲梅相处,孤山山下人家。——《清平乐·题处梅家藏所南翁画兰》
三花一叶,比似前时别。烟水茫茫无处说,冷却西湖风月。贞芳只合深山,红尘了不相关。留得许多清影,幽香不到人间。——《清平乐》

图1 郑思肖《墨兰图》
个体的生命体验牵动着宋末遗民敏感的神经,对于当代画作的题写,张炎将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付诸其上,尽管在艺术技巧上,这两首题画词与一般咏物词并无多大差异,但其情感内蕴将“题画”的特殊性揭示出来。宋亡之后,郑思肖隐居深山,义不仕元,坐卧不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于“穴”下则为“大宋”)。每画兰而不画土,根无所凭藉,或问其故,则云:“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邪?”⑯从其现存《墨兰图》(图1)可见,兰花失去了抚育的土壤,显得弱不禁风、孤苦无依。故国的灭亡,亲人的离世,理想的破灭,异族的压制,于笔墨之间隐隐透露出来。这种遭际与张炎何其相似!张炎在梦中幻想“孤山山下人家”的隐逸生活,现实却是连栖身之土俱已被异族夺去,唯能以残年眷怀旧国故家。不过,可贵的是,这种追昔情怀并不是一味的哀叹,更有对昔日品格的坚守。张炎将兰花比作屈子:“黑云飞起,夜月啼湘鬼。”既赞美郑思肖不屈不挠的气节,又隐约传达与画者志同道合的政治情志。
三、题画词的艺术特点:文学语言与绘画技艺的交融互补
关于诗画关系的探讨自古有之,苏轼尝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大多数中国古代文人反复强调诗、画在艺术表现上的相通之处,但是诗、画毕竟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属性,各有其特长与缺陷,吴文英和周密等词人对绘画的表现局限有着清醒的认识:“亭上秋声,莺笼春语,难入丹青。”(吴文英《柳梢青·题钱得闲四时图画》)“自玄晖去后,云情雪意,丹青手、应难写”(周密《龙吟曲·赋宝山园表里画图》)。因此,在题画词的创作实践中,词人必须打破词、画之间的界限,既引入借鉴绘画的理论与艺术技法,又以语言特长弥补绘画的局限,充分发挥文学的独特优势。吴文英、周密、张炎这三位以锤炼词工出名的词人,在题画词的时空安排、设色造境、形象塑造等方面俱有精深造诣,引领着题画词的创作风尚。
(一)错综的时空安排
绘画运用线条和色彩,一般只能处理物体“在空间中的并列静态”,而诗歌运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多表现全体或部分本来“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⑰。在题画词的创作过程中,词人首先面临着如何把空间意象转换为时间序列的问题。为了逼真地再现画面,词人在将绘画意象转换为语言文字时,总是尽力保留图画原有的空间感。将图画的层次感引入词作是题画词空间布局的一大特点。宋代画家郭熙提出著名的“三远”说⑱,“三远”要求画家不能仅仅描摹眼前的表层现象,还应以一种俯仰的姿态来观山水,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观照山水。词人有意识地吸取了这种取景构图方式,赋予词作丰富的层次感,如周密《龙吟曲·赋宝山园表里画图》一词,将宝山园景色视为一幅山水图赋写,谋篇布局上吸取“三远”理论,词人仿佛娴熟地操控着一台摄像机,在景色之间往返推拉,远近交错,富有层次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三远”之中,词人似乎更偏好于“平远”。“落日沙黄,远天云淡,弄影芦花外”(张炎《湘月》),“平沙流水,叶老芦花未,落雁无声还有字”(张炎《清平乐·题平沙落雁图》),词人由眼前之景逐渐向远方推移,最终将读者的视线带入苍茫的云天之际。衣若芬曾指出,“平远构图的山水画,往往因其水平视域的观看角度,暗示退隐江湖的愿望”⑲。观者随着平远的视向眺望无尽的空间,那阔远苍茫的远方既可能是另一个桃源世界,又可能暗喻着渺茫的前途,恰恰契合了周密、张炎等词人的遗民心绪。
在吸收绘画的空间布局之外,题画词还保留了文学的时间意识。画面只能定格一时,再高明的画家也难以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内展现时间的流动性,吴文英云:“辋川落日渔罾。写不尽、人间四并。”(《柳梢青·题钱得闲四时图画》)纵使是王维的佳作《辋川图》也难以将人间变换的四时景色囊入画中。宋人沈括言:“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⑳更是一语点出绘画作为空间艺术的表现缺陷。为了弥补绘画的局限,词人在题画词的创作中大量运用流动性的时间意象,例如吴文英词《浣溪沙·题史菊屏扇》:
门巷深深小画楼,阑干曾识凭春愁。新蓬遮却绣鸳游。桃观日斜香掩户,苹溪风起水东流。紫萸玉腕又逢秋。
首二句勾画一个春日凭栏的凝愁少女,进而转为夏日新蓬遮映下的鸳鸯戏游,末句又以“紫萸”点明秋意。明里是题画,暗里却是以季节的流动来结构画意。春、夏、秋三季显然不能同时出现在扇画之中,词人却以联想来弥补图画与文字的空隙,丰富画作的意蕴。复如吴文英《暗香疏影·夹钟宫赋墨梅》下阕:
何逊扬州旧事,五更梦半醒。胡调吹彻。若把南枝,图入凌烟,香满玉楼琼阙。相将初试红盐味,到烟雨、青黄时节。想雁空、北落冬深,澹墨晚天云阔。词人连用典故来赋画梅花,依稀可见其中的时间线索。因梅花将要凋零,将其图入画中,留住她的美丽。梅花凋零之后在烟雨时节结梅子,故“相将初试红盐味”。结尾荡回冬季,又是梅花凌寒绽放之时,历经重重的时间想象之后再度回归画面。单一的画图只能写一时的梅花,题画词却能题写四季梅花,化静态的画面为动态的想象,令梅花形象更丰满立体。
(二)写意的设色造境
中国传统绘画历来注重意境,寥寥几笔即可传达绵长的情韵。到了南宋,马远、夏圭等画家更将湿润的墨感带入绘画创作,以水墨淋漓引导观者感受湿润的云雾缭绕之美。这种“渲染”技法启发了题画词的创作,词人常常渲染一种氛围,为山水画增添悠长的意韵,如张炎《南楼令·题聚仙图》末句“隔水一声何处笛,正月满,洞庭湖”,突然宕开了画面的往昔热闹与词人现实心境的悲凉,定格在一个静谧安宁的空镜头中,余韵绵长。题画词或者渲染一个背景,映衬画中人物,如张炎词《踏莎行·卢仝啜茶手卷》“清气崖深,斜阳木末。松风泉水声相答”;或者渲染宁静幽雅的氛围,为主人公卢仝的出场铺设一个清雅的环境,侧面烘托其品格之高雅。
清初画家笪重光云:“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㉑虚实相生是题画词最为突出的造境方式。画作是实体的存在,它的思想旨趣与情感容量只能在固定空间内呈示,且一般只能再现实境;题画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则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充分摆脱图画的空间桎梏,不断跳转于虚实之间。虚境在题画词的创作中具备多重功能,它为追昔怀人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如吴文英词《梦芙蓉·赵昌芙蓉图,梅津所藏》上阕:
西风摇步绮。记长堤骤过,紫骝十里。断桥南岸,人在晚霞外。锦温花共醉。当时曾共秋被。自别霓裳,应红销翠冷,霜枕正慵起。
此词开篇即绘芙蓉图景,紧接着突然中断对画面的题写,转而回溯一段往昔的甜蜜情事,又以想象中别后女子的惨淡形容作结。这段追忆显然不可能存在于真实画面中,但却为画中芙蓉染上了浓浓的人情意味。词人没有完全抛开画面凭空想象,而是将过往的虚境与画面的实境结合起来,写别后女子的憔悴,与真实芙蓉的“红销翠冷”相映照,又以真实芙蓉的“红销翠冷”反衬画作芙蓉的鲜艳夺目。画中之花尚娇艳,如花的女子却形容枯槁,怀想之悲油然而生。词人在叙写中交糅着画芙蓉、真芙蓉和女子三个意象,构筑了“花中有人,人中有花”这一意象叠现的词境,人是虚写,画芙蓉是实写,真芙蓉又是虚写,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为全词增添了朦胧的审美意味。
有时候,虚境则是一个超现实的梦幻意境,记录下词人观画时飞动的思绪,赋予词作浪漫的意味,形成了与现实的对照。例如张炎词《疏影·题宾月图》,词人体察画幅中“千峰独立”的宾客形象,精心用文字制造了一个缥缈的想象空间:“海镜倒涌秋白。”宾士仿佛漫步于月宫之中,与嫦娥脉脉对视,然此番神游终要回到现实,宾士似不甘心,直唤“是几番、飞盖追随”,久坐桂树之下,任月夜的露水打湿衣襟。漫步月空、得遇嫦娥的神游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力,仿佛带领读者进入远离尘嚣的幻想世界。不过,这种缥缈奇幻的神游最终回归现实的残山剩水,伤今的遗民情绪百转千回而见出。
尤具特色的是,题画词常常渲染一个虚境作为花鸟画的背景。中国传统花鸟画常在白纸白绢上作画,无任何背景。宗白华先生云:“尝见一幅八大山人画鱼,在一张白纸的中心勾点寥寥数笔,一条极生动的鱼,别无所有,然而顿觉满纸江湖,烟波无尽。”㉒只要画作中心的花鸟足够生动,空白的背景也能被调动起来,分得几分花鸟的动感之美。题画词则不同,尤其是不直接题写在画卷上的词作,读者无法通过阅读文本直接获取花鸟形象,词人有必要铺设一个虚境作为背景,将画作的中心形象置于一种氛围之中,更好地引导读者观赏画作。例如:
小雨新霜,萍池藓径生寒。——周密《声声慢·逃禅作菊、桂、秋荷,目之曰“三逸”》
烟水冷,传语旧沙鸥。——张炎《小重山·题晓竹图》
烟水茫茫无处说,冷却西湖风月。——张炎《清平乐·题处梅家藏所南翁画兰》
空江晚,长笛一声吹。——张炎《小重山·烟竹图》
优美的意境一方面从侧面烘托了画中之物的高贵品格,一方面又给读者以立体的观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特定环境之中欣赏花鸟,而非对着一幅冷冰冰的平面图像。这种对画作背景的填补,往往带有极强烈的主观色彩,显示出题画词“写意”的艺术特点。
题画词的虚写成分,除了词人精心营造的虚境之外,“虚色”亦别具特色。关于“虚色”,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中说道:“写一个颜色而虚实交映,制造两个颜色错综的幻象,这似乎是文字艺术的独家本领,造形艺术办不到。”㉓传统绘画在设色上常常只采用符合生活逻辑的颜色,文学却可以配置实色外的“虚色”,传达更新颖的画面效果。南宋时期,水墨花鸟图大盛,墨色勾画花鸟足以传神写意,然题写水墨花鸟图,则面临着棘手的设色问题。宋人刘敞《微雨登城》诗云:“雨映寒空半有无,重楼闲上倚城隅。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诗人有意在前三句回避任何色彩描写,并以“浅深”“高低”暗示着水墨画的构图方式,营造淡雅的水墨意境,使结句的“水墨图”比喻浑然天成。㉔刘敞以贴切的文学描述将实景转化为水墨图,然水墨画的题词是一个逆向的创作过程。词人可以通过对画作运笔浅深与用墨浓淡的观察,分析水墨画的构图层次,重点避开表现色彩的字眼,再现雅致的水墨意境,这一处理方式较为真实,问题在于,读者阅读题画词时常常缺乏一个预设情境(基于人们丰富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较固定的视觉感受,如“微雨山色”),对于不甚了解“墨戏”趣味的读者而言,单一的色调似乎略显枯槁。于是,有些题画词便采用了另一种处理方式,如:
相将初试红盐味,到烟雨、青黄时节。——吴文英《暗香疏影·夹钟宫赋墨梅》
谁分弱水洗尘红。低回金叵罗,约略玉玲珑。——张炎《临江仙》
记珠悬润碧,飘飖秋影,曾印禅窗。——张炎《甘州·题曾心传藏温日观墨蒲萄画卷》
在这些词作中,词人运用某种“虚色”为水墨画设色,这种“虚色”避免了画面色彩的单一化,更传神地摹写了画中之物的色泽、肌理、光亮等细节,这种“虚色”往往符合现实的视觉经验,产生更为逼真生动的画面感。
(三)立体的形象塑造
莱辛在《拉奥孔》中曾提出一个观点:绘画擅长表现静态的物体,而诗歌擅长表现持续的动作。当诗歌描绘物体时,常常要把静态的画面转换为动态的语言序列,要借助暗示的方法。词的创作与诗有一定的相似性,若以题画词的实际创作来检验这个观点,莱辛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吴文英《梦芙蓉·赵昌芙蓉图,梅津所藏》开篇以“西风摇步绮”传神地揭示画中芙蓉摇曳生姿的动态美感,周密以“曳雪牵云”(《声声慢·逃禅作梅、瑞香、水仙,字之曰“三香”》)拟花,沉寂的画中之花顿时活跃起来,可见“以动写静”确是题画词的常见技法。以“美的效果”侧面烘染的写法也很常见,如“画图重展,惊认旧梳洗”(吴文英《梦芙蓉·赵昌芙蓉图,梅津所藏》);“太白醉游何处,定应忘了沉香”(张炎《清平乐·为伯寿题四花牡丹》);“引得传情,恼得娇娥瘦”(张炎《蝶恋花·题未色褚仲良写真》)等,皆是通过叙写图画产生的强烈效果,间接烘染画面之逼真、画者技法之高超。
然而,中国古典诗词的描写艺术远比《拉奥孔》所述的更为复杂。钱钟书先生称:“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自己的彩色碟破产,诗歌里勾勒的轮廓、刻划的形状可能使造形艺术家感到自己的凿刀和画笔技穷。”题画词一面借鉴传统绘画的白描、点染、勾勒等技法,一面又充分彰显文学语言强大的摹写状物能力,通过运用多种文学技法立体化地塑造画面形象,从而打破了绘画单调的平面效果,甚至赋予画中形象人格化的精神内涵。
立体化的形象塑造方式,最普遍地体现为“以美人意象喻画中花草”的表现模式。在同一幅画卷之上,画者可以将花与美人并置,却难以展现二者合一的幻觉与美感。平面的画幅极难直接呈现美人与花的映衬与互动,但在古诗词创作中,“美人比花”却是一个传统。词人在题画词创作中沿袭这一传统,达到“人花一体”的效果。周密词《声声慢·逃禅作菊、桂、秋荷,目之曰“三逸”》,开篇以“妆额黄轻,舞衣红浅”赋画花蕊、花瓣的颜色与质感,又以“粲星钿、霞佩珊珊”赋画花朵迎风招展的形态。吴文英词《燕归梁·书水仙扇》,先以女子的发型簪饰比喻花朵的形状:“白玉搔头坠髻松”;接着以“翠裙”喻绿叶;再以女子的衣饰赋画水仙的身姿:“青丝结带鸳鸯盏”;最后再以女子步态的轻盈写水仙迎风飘摇之美,仿佛美人从画中向观者迎面走来:“绿尘湘水避春风。步归来、月宫中”。为了全面铺陈女子之美,词人还突破了单一的视觉效果,借助听觉、触觉、嗅觉等多感官的综合描写,对画作图像进行全方位的表现,造成“通感”效果,令读者在阅读时充分调动多种感官,融入自己的亲身体验,从而拉近了与画作之间的距离。
在以美人喻花时,题画词比其他题材的词作更注意到了美人的造型方法。画面上的鲜花或有百般姿态,但词的体量有限,如美人有万种风情,若要选取一个最能令人砰然心动的瞬间,需煞费一番心机。题画词往往选择画中的某个瞬间加以阐发,或者是无心理妆的慵懒无聊,或者是瘦弱堪怜的楚楚背影,或者是凭栏拈花的凝愁神色,或者是衣带飘飞、若往若还的曼妙身姿。有学者认为,这些画面吸收了传统仕女画的构图方式㉕,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基于对大量画作的深刻印象之上,词人把握画作神髓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图画典型化:这些美人形象往往处于最富有包孕性的一刻,能够给观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当然,风雅词人更重视挖掘花草的内在品格。一方面,词人以侧面烘托的方式赋画花草的高雅品性,如以“梅兄矾弟”烘托水仙的精神品格:“应恨梅兄矾弟远,云隔山阿”(张炎《浪淘沙·余画墨水仙并题其上》);以“炎天梅蕊”与“雪里芭蕉”烘托竹石的高洁(张炎《风入松·溪山堂竹》);以“山间闲梅”作比,表现兰花的隐逸品节(张炎《清平乐·题处梅家藏所南翁画兰》)。另一方面,词人以女性的独特气质与人生命运赋予花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以历史上的美人拟花,融入历史典故,如“五湖水色掩西施”(吴文英《浣溪沙·题李中斋舟中梅屏》);“素女情多,阿真娇重,唤起空谷”(吴文英《蕙兰芳引·林钟商,俗名歇指调赋藏一家吴郡王画兰》);“香雾湿云鬟,蕊佩珊珊,酒醒微步晚波寒”(张炎《浪淘沙·作墨水仙寄张伯雨》)等。将梅花比作西施,牡丹比作杨玉环、神女,水仙比作洛神,这些经典的美人意象为题画词添上了历史韵味,而这种美人意象又是敞开的,可以容纳不同观者的不同想象,从而丰富了画作的阐释可能。作比的美人通常是闻名史册的薄命女子,她们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词人的身世之悲,婉转地抒发了词人国破家亡的悲凉情绪。
四、词与画的互文与对话
当词被题上画卷时,词的文本与画面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参与画作意义的建构,词、画之间呈现出鲜明的互文关系:画面提供直观的视觉美感,文字间接阐释画意、延展画境,二者互为阐释、互为映衬且互为补充。除了再现画面与艺术批评之外,宋代题画词往往融入了词人独特的审美视角与人生体验,构成对绘画艺术的“再创造”,并以文字符号的书写形式积极参与到绘画整体艺术形象的构筑之中。于是,在同一幅画卷上,出现了绘画、词、书法三种不同艺术的相互映照。观者的鉴赏过程既是一次感性的审美体验,又是一个理性的思维过程,极大地拓宽画作意义的阐释空间。例如,周密词《夷则商国香慢·赋子固凌波图》,明代汪珂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录在赵孟坚《赵孟坚水墨双钩水仙长卷》之下,㉖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藏赵孟坚《水仙图》(图2),㉗其后题有周密词,较为直接地体现词与画的互文关系:
玉润金明。记曲屏小几,剪叶移根。经年汜人重见,瘦影娉婷。雨带风襟零乱,步云冷、鹅筦吹春。相逢旧京洛,素靥尘缁,仙掌霜凝。国香流落恨,正冰铺翠薄,谁念遗簪。水天空远,应念礬弟梅兄。渺渺鱼波望极,五十弦、愁满湘云。凄凉耿无语,梦入东风,雪尽江清。

图2 (传)赵孟坚《水仙图》(局部)
若只是观画,可见长长一丛水仙,顿生繁乱之感,不知何处停驻视线。若只是读词,较之其他宋季咏物词并无多大新意,若无词题,较难设想词人实在赋画水仙而非咏水仙。在题词的画卷上,观者一方面可以借助题画词引导整个鉴赏过程,一方面通过赏玩画作细部获得对词作的深层了解。词的上阕从外形、意态、品格、神韵各个方面,全面再现画中的水仙形象,发挥了导览与诠释的作用;下阕跳开了画面,由水仙凄冷寂寞的气质联想到北去的妃嫔,寄托对故国的怀想。若是仅有图画,观者只能从草草的水仙丛中感受一种凄凉的心境,却不能明确这是一种追昔伤今的遗民心绪,特别是“水天空远,应念矾弟梅兄”一句,既是画家赵孟坚的人格注解,㉘又是词人遗民心志的写照,被赋予了超越画面的文化意蕴。词的结句更是渲染了空濛凄冷的气氛,这种气氛难以透过一纸空白的背景透显,词人便将观画者由封闭的画作引向更为空阔的时空,语尽而意无穷。
绘画的阐释空间经由传统诗词的唱和活动获得了进一步的延宕。词人在自题自画时面临着不同创作角色的转换,是围绕不同艺术形式而展开的一次自我对话。处于同一时代的词人与画家之间发生着精神互动,隔代的词人与画家之间亦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多重对话关系之中,画作意义不断地叠加丰富,逐渐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化元素流传下来。宋代画家扬无咎㉙曾创作《四梅图》(图3),㉚并自题四首《杨柳青》于卷后,在一卷之内彰显词与画的互文关系,对后人影响甚大。饶宗颐先生认为:“不能作画的词人,则和他的词;能画又兼词的,则依样题作‘词画’。”㉛据其卷后跋语,画作四段分别截取了梅花绽放过程的四个节点:未开、欲开、盛开、将残,所题《柳梢青》四首分别对应四段画面,充分体现词画互文的特点。

图3 扬无咎《四梅图》(局部)
周密以同调的四首《柳梢青》追和扬无咎,词作如下:
约略春痕。吹香新句,照影清尊。洗尽时妆,效颦西子,不负东昏。金沙旧事休论。尽消得、东风返魂。一段真清,风前孤驿,雪后前村。
万雪千霜。禁持不过,玉雪生光。水部情多,杜郎老去,空恼愁肠。天寒野屿空廓。静倚竹、无人自香。一笑相逢,江南江北,竹屋山窗。
映水穿篱。新霜微月,小蕊疏枝。几许风流,一声龙竹,半幅鹅溪。江头怅望多时。欲待折、相思寄伊。真色真香,丹青难写,今古无诗。
夜鹤惊飞。香浮翠藓,玉点冰枝。古意高风,幽人空谷,静女深帏。芳心自有天知。任醉舞、花边帽欹。最爱孤山,雪初晴后,月未残时。
周密在小序中盛赞扬无咎的《双清图》,此图或以梅花为绘画中心,是否即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扬无咎之《四梅图》,似尚未有确切的证据。周密和作承袭扬无咎词的艺术技法,将画中之梅当作现实之梅加以描摹,体现词人对“折枝式”构图的借鉴:画者并不暴露梅花的根部,其枝干总是由画外入画,与自然隔而不断,气脉相连,有一番自然天成的韵味。此外,周密还常常跳出画面,欲携“水部”“杜郎”等古人一同品画,体现雅士情趣。作为品评者,周密一语点出绘画与文学的艺术特性:“真色真香,丹青难写,今古无诗。”尽管不能将此组词与《四梅图》一一对照,但经由此词,扬无咎绘画的阐释空间获得了极大的延展。杨、周虽处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却有相似的品格追求,足见宋代士人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在这一追和过程中,词、画的互文性再一次得到强化。
除了周密,据饶宗颐先生的统计,徐禹公、陈允平、张雨、虞道园、柯九思等人先后和过扬无咎此词,文嘉、马扶羲二人仿效扬无咎作“词画”,既写梅又题词于其上,实现了词、画的二度转换。扬无咎据梅填词,文、马结合词意再作新梅并自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几经转换与演绎,原诗和它的这一系列衍生品已经形成一种富含深意的文化符号代码”㉜,以画作为中心的题画词唱和,促使词、画进入二度转换的流程,成为一种文化的累积,一方面丰富了梅图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为《四梅图》的经典化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复如张炎作词题温日观《墨葡萄》画卷,刘沆、沈钦以同调和之。㉝温日观是宋末的僧人画家,有多种《墨葡萄图》传世。张炎《甘州·题曾心传藏温日观墨蒲萄画卷》词如下:
想不劳、添竹引龙须,断梗忽传芳。记珠悬润碧,飘飖秋影,曾印禅窗。诗外片云落莫,错认是花光。无色空尘眼,雾老烟荒。一剪静中生意,任前看冷淡,真味深长。有清风如许,吹断万红香。且休教夜深人见,怕误他、看月上银床。凝眸久,却愁卷去,难博西凉。
此词大抵翻不出上文所述的题画词的艺术特色。“记珠悬润碧,飘飖秋影”,将葡萄比作一个温婉女子,刻画其在秋风下摇曳的身姿,借以再现画中葡萄的婆娑姿态。“一翦静中生意,任前看冷淡,真味深长。有清风如许,吹断万红香”摹写葡萄的香气,侧面烘托葡萄的清雅品格。“且休教夜深人见,怕误他、看月上银床”从引得观者无法入眠的画作效果切入,侧面烘托画工之精湛。值得重视的是,词的末句暗示此词或作于张炎北游为元政府修金子《藏经》时期,弥漫着一种清高而哀伤的情绪。张炎倾慕“无色空尘眼,雾老烟荒”的禅意生活,然现实的家国变故、迷惘的未来前途都造成了身处异乡的漂泊不安之感,故借题写墨葡萄,传达微妙复杂的遗民心绪。沈钦与刘沆的和作吸取了张炎的创作方式,对画中葡萄多加描绘,并着意烘托葡萄所寄托的禅意,对画者的品性加以称赞,尽管词句的修辞不如张词蕴藉工致,但所流露的思想情绪与张炎如出一辙,俱是罢卷之后回归现实,反映遗民群体迷惘不安的心理状态。
在此次关于《墨葡萄》画卷的文学唱和活动中,词人从鉴赏的角度讨论温日观画葡萄的艺术技法,对后世葡萄图的创作具有示范意义。更重要的是,以题画词的创作为媒介,北游文人展开了一次精神交流,他们通过文学唱和呈示了遗民文人迷惘不安的心理状态,并共同表达了遭受家国变故的重创之后凄苦悲凉的心绪。通过文学唱和,词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相互慰藉与支持。
还有另一种唱和方式值得关注。张炎与陆行直交好,曾为其画作题《祝英台近·题陆壶天水墨兰石》词,另有为陆行直家妓卿卿作《清平乐》(候蛩凄断)。多年之后,陆行直创作了名画《碧梧苍石图》㉞,遂将张炎此词题于画上,自述道:
此友人张叔夏赠余之作也。余不能记忆。于至治元年仲夏廿四日,戏作《碧梧苍石》,与冶仙西窗夜坐,因语及此。转瞬二十一载,今卿卿、叔夏皆成故人。恍然如隔世事,遂书于卷首,以记一时之感慨云。
传统意义上的题画唱和,以一幅画为中心,由多位词人在卷上围绕画意题写,间或有相互应答,既构成文本与图像之间的互文关系,又形成多个历时性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陆行直的这种唱和活动,是以好友之词题于自己的画作之上,以绘画创作的实践来回应词人的赠词。由于张炎已经过世,这幅画承载着对友人的深重追念,以及对往昔友谊的怀想。张炎词幽折的遗民情绪在画卷之上复活,激发了画者对自我身世经历的重新审视,成为画者感伤情绪的另一载体。虽然张炎已故去,陆行直仍能在画中与他进行精神对话,而陆、张的精神对话更是通过物质性画卷直接呈示于后代文士面前,引发了他们长久的共鸣,据《珊瑚网》所录,此画卷有大量后人的题跋,而这些层出不穷的追和题画之作,又构成一场穿越历史时空的精神对话。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①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宋元戏曲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页。
②题画词的定义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题画词”指直接题写在画作之上的词,或自题,或他题。广义的“题画词”指题写在各种画面之上或以绘画作品为题写中心的词,除了题写在画卷上的词,亦包括题写在画屏、画扇之上的词。本文以广义题画词为论述对象。
③关于题画词的研究,较早的成果为饶宗颐先生的《词与画——论艺术的换位问题》一文,这篇文章从“词画的出现及其影响”“以词入画”“以词题画”“词人生活与画卷”“以词证画史”“以画法喻词”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述,较全面地阐明词与画的关系,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苗贵松的《宋代题画词简论》《宋代题画词的主要贡献和后世影响》探讨宋代题画词的定义、分期、兴起背景、后世影响等基本问题。河北大学吴文治的硕士论文《宋代题画词论说》厘清了题画词的定义,重点论述题画词兴起的背景、题画词的分期与分类等问题,并探讨了题画诗与题画词的异同。彭国忠的《唐五代北宋绘画与词》关注词人与绘画的关系以及题画词兴盛的现象,论述绘画对唐五代北宋词的深层影响。谭辉煌的《论风雅词人题画词的文化意蕴和艺术手法——以张炎、周密和王沂孙为中心》具体分析了题画词的画意与画技。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均有一定启发意义。
④翻检依据为词题与小序。对于题扇面词,如果据标题、小序及词意均无法确认扇面是白面还是画面,为统计方便,一律不计入。吴文英词《蝶恋花·题华山道女扇》,无法确认是否为画扇,吴蓓《梦窗词汇校笺释集评》倾向于扇中有画,笔者据词意亦认为画面感较强,故将此词计入。通过翻检,共统计宋人题画词147首,创作数量前三位分别为张炎(36首)、吴文英(12首)、周密(11首)。
⑤夏文彦《图绘宝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7页。
⑥袁桷《袁桷集校注》[M],杨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1534页。
⑦王朝闻《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M],济南: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⑧祝振玉《略论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几个原因》[J],《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
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⑩引文均出自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下多处同,不再出注。
⑪宋人释道原《传灯录》记:襄州居士庞蕴有一女名灵照,“居士将入灭,令女灵照出视日早晚,及午以报。女遽报曰:‘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居士出户观次,灵照即登父坐,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锋捷矣。’”参见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八[M],《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涵芬楼影印。
⑫邓乔彬《论南宋版风雅词派在词的美学进程中的意义》[A],收于邓乔彬《词学廿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⑬与宋画的题材分类相一致,宋代题画词在题材上主要分为山水、人物与花鸟三类,吴文英、周密、张炎三人的题画词以花鸟题材占最大比重(约占70%)。而周密现存的21首题画诗,仅有2首是花鸟题材。
⑭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⑮郑思肖《墨兰图》,纸本,墨笔,纵25.7厘米,横42.4厘米,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⑯程敏政辑《宋遗民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4页。
⑰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2页。
⑱宋人郭熙云:“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参见郭熙撰、郭思编《林泉高致集·山水训》[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⑲衣若芬《观看、叙述、审美:唐宋题画文学论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版,第13页。
⑳沈括《新校注梦溪笔谈》[M],胡道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69页。
㉑笪重光《画筌》[M],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9页。
㉒宗白华《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A],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㉓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40页。
㉔参见张鸣《宋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㉕彭国忠《唐五代北宋绘画与词》[J],《学术研究》,2008年第11期。
㉖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58页,第913页。
㉗(传)赵孟坚《水仙图》,绢本,墨笔,纵33.2厘米,横374厘米.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画有专家质疑为伪作,如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上有文章《关于“赵孟坚〈水仙图〉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此画为明清人利用十二家题跋作伪。
㉘周密《齐东野语》记:赵孟坚曾自制一舟,作为宴游之所。舟中所置,除留一榻以为晏息之地外,皆为图书及雅玩之物。“兴致所至,使左右取之,吟弄以至废寝忘食。时人一晚便知此为赵子固书画船。”他曾于酒饮之酣时,“脱帽以酒淋发,箕踞歌《离骚》,旁若无人”。参见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九[M],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
㉙《全宋词》作“杨无咎”,据唐圭璋《读词札记》,当为扬雄之后,本姓扬,本文从之。参见唐圭璋《读词札记》[J],《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㉚㉛扬无咎《四梅图》,纸本墨笔,纵37.2厘米,横358.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饶宗颐《词与画——论艺术的换位问题》[A],见饶宗颐《画[宁页]——国画史论集》[C],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22-223页。
㉜赵晓涛《游于艺途——宋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㉝据杨海明《张炎年表》考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张炎在途中或大都后,作《甘州》,题为“题曾心传藏温日观墨蒲萄画卷”。参见杨海明《张炎年表》[A],附于《张炎研究》,见《杨海明词学文集》卷二,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页。另据清人吴升《大观录》记载:温日观葡萄墨迹,题词凡三人,调《甘州》。玉田首倡,和者州刘沆、汴沈钦。参见吴升《大观录》卷十五[M],见卢辅圣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465页。
㉞陆行直《碧梧苍石图》,绢本设色,纵107厘米,横53.2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