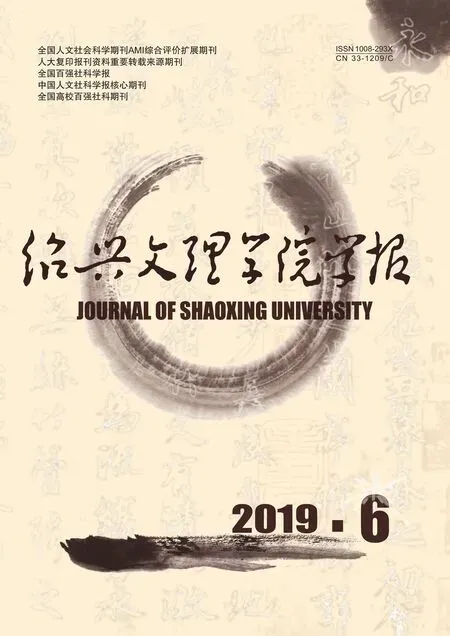定调之功:论张炎的当世接受
何 扬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文学史上,一位作家得以确立典范,往往离不开特定群体的接受,而当世人的描述往往最接近作家本来面目。张炎(1248—1321?),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为宋末著名词人,有词集《山中白云词》和理论专论《词源》传世。张炎论词崇尚“清空”“骚雅”,注重声律意度,创作与理论桴鼓相应,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张炎一生交游广泛,据孙虹先生《张玉田年谱》考证可知,与张炎交游者多达九十余人。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试图呈现宋元之际张炎交游者对其家世生平、雅士人格以及词与词学思想的认知,并探讨这一初始接受阶段的意义。
一、张炎其人的当世接受
当世者为张炎所做的序跋、题辞是研究张炎极为重要的材料,其丰富的信息量,为了解张炎家世生平与雅士人格提供了许多参考。
(一)家世
张炎家世问题曾经扑朔迷离,关于张炎是南宋“中兴名将”张俊(字伯英,追封“循王”)的五世孙还是六世孙,以及张炎与张镃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张炎交游者的记载密不可分。首先,可以明确张炎父亲为张枢,邓牧《山中白云词序》提到:“盖其父寄闲先生善词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传者。”[1]165“寄闲”乃张炎父亲张枢之号。其次,可以确定张炎为张俊后代,郑思肖《玉田词题辞》称:“吾识张循王孙玉田先辈。”[1]164袁桷则直接指出“玉田为循王五世孙”[1]164。由于袁桷与张炎时代相当,又同张炎交往密切,后世大都认可这种观点,如厉鹗《山中白云词题辞》称:“叔夏于功甫为三世,于循王为五世。”[1]16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循王之五世孙。”[2]然而,袁桷实遗漏了张炎祖父张濡。至于张炎与张镃的关系,袁桷说是“古梅千槛,空怀玉照之风流。……诗书娱晚岁,还名祖父之青毡”[1]163(玉照,袁桷自注“张镃号约斋,堂名玉照”)自然也就不成立。但这里需了解一件事,张炎祖父张濡的部曲曾误杀元使廉希贤、严忠范,宋元易代后,张濡遭到报复,为元人磔杀。在异族统治下,张炎很可能会受到株连威胁,故而,袁桷在谈论张炎家世时应考虑到了当时的政治因素,所以故作迷离之辞,他对张炎“祖父问题”的回避也就可以理解了。又如舒岳祥、戴表元赠张炎的序皆模糊其词,或出于相同考虑。当代学者杨海明先生经过详细考证,确考张炎为张俊六世孙,并梳理出张氏谱系:俊—子厚—宗元—镃—濡—枢—炎,邱鸣皋先生在《关于张炎的考索》一文中又对其进行了确认与补充。今世学者固有正本清源之功,但也不可忽略宋元之际张炎交游者们提供的线索。
(二)生平
张炎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深受家族高雅奢侈风气影响,年少时期过的是承平贵公子生活,试看戴表元的《送张叔夏西游序》与郑思肖的《玉田词题辞》:
玉田张叔夏与余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于时风神散朗,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也。[1]162(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
吾识张循王孙玉田先辈,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数千里,一片空狂怀抱,日日化雨为醉。自仰扳姜尧章、史邦卿、卢蒲江、吴梦窗诸名胜,互相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飘飘征情,节节弄拍,嘲明月以谑乐,卖落花而陪笑。[1]164(郑思肖《玉田词题辞》)
两段文字生动描绘出张炎年少时期的悠游生活。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剧变,张炎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舒岳祥《赠玉田序》记载:
宋南渡勋王之裔子玉田张君,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饮,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一日,思江南菰米莼丝,慨然襥被而归。不入古杭,扁舟浙水东西,为漫浪游。[1]165
舒序谈到了张炎初次北行之事,同时涉及词人南归后的足迹(1)据孙虹先生考证,张炎一生两次北游大都。张炎初次北行在临安沦陷之际,时间约为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此年五月宋端宗改元)或景炎二年(1277)。初次北游归杭,往来于杭州、山阴、四明之间,即所谓“扁舟浙水东西,为漫浪游”。第二次北行时间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次年春南归杭州。再次北游归杭后,先游浙江东路(山阴、四明、台州),十年后改游浙江西路(苏州、常州、江阴),即戴序所谓“改游吴公子季札、春申君之乡”。戴序“犹家钱塘十年”,再有“西游”之行。见孙虹.张炎北游事迹发覆[J].文学遗产,2018(2).。宋亡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张炎第二次北上大都,此次北行为应召缮写金字《藏经》,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记载:
垂及强仕,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愈不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1]162
戴序对张炎第二次北行与南归后的行踪皆有所说明。此次南归,迫于生计的张炎四方奔走,陆文奎《玉田词题辞》记载:“客游无方,三十年矣。”[1]166面对这种漫游生活,张炎颇为无奈,戴序记载:“适与相值,问叔夏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叔夏曰:‘不然,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虽少有遇,无以宁吾居,吾不得已违之,吾岂乐为此哉!’语竟,意色不能无沮然。”[1]162辗转奔波的张炎本想寄食于他人,不料故人或处境窘迫、或零落不存,偶有所遇,也只能仰人鼻息。戴序又言:“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钟鸣鼎食,江湖高才词客姜夔尧章、孙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馆谷其门,千金之装,列驷之聘,谈笑得之,不以为异,迨其途穷境变,则亦以望于他人。”[1]162张炎由青少年时的富贵公子,历经南宋覆灭,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北行南归后,萍踪浪迹,乞食漫游,晚年生活更是牢落困苦,这些都可从张炎交游者的记载中看出。
(三)雅士人格
张炎家世清华,自幼受门风濡染,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与不凡的艺术修养,前引戴表元的《送张叔夏西游序》与郑思肖的《玉田词题辞》已大致勾勒出入元前张炎的“承平公子”形象,其时他赏花饮酒、吟诗唱曲,“风神散朗”地生活在西子湖畔。舒岳祥对张炎的卓异才情的描述最为具体,称其:“诗有姜尧章深婉之风,词有周清真雅丽之思,画有赵子固潇洒之意。”[1]165在舒岳祥看来,张炎诗、词、画都足以与当时的一流名家相提并论,可见其学养富赡。张炎的雅士人格还表现为气节之耿介,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承平时代的张炎风流儒雅,而在历经战祸兵燹、国祚改运后,张炎仍未改变其清介品性,邓牧称他:“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孙公子蕴藉,身外穷达,诚不足动其心,馁其气欤。”[1]165舒岳祥以年迈之躯为张炎词集作序时,也谈到“(张炎)未脱承平公子故态,笑语歌哭,骚姿雅骨,不以夷险变迁也。其楚狂与?其阮籍与?其贾生与?其苏门啸者与?”[1]165“楚狂”“阮籍”“贾生”“苏门啸者”皆用来形容张炎品格之清贞。张炎以不与世俯仰的人格魅力,成为当世士子文人心目中的雅士典范。
宋史、元史等正史皆未给张炎立传,小说笔记也鲜有涉及,而张炎除词集《山中白云词》和理论专论《词源》外,只留下一首诗,可以说研究张炎本体的文献十分匮乏,故而,这些当世者对张炎家世生平、雅士人格的描述,无疑为后世研究张炎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材料。
二、张炎其词的当世接受
张炎有词集《山中白云词》传世,存词约三百首。《山中白云词》律吕协洽、清空骚雅,并能博采众家之长,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当世交游者对此也有一定认知。
(一)律吕协洽
张炎习词受父亲张枢与师友影响,自称:“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尝知绪余,故生平好为词章,用功四十年。”[3]255“守音协律”也体现于张炎的创作中,仇远《玉田词题辞》云:
读《山中白云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不特可写青檀口,亦可被歌管、荐清庙,方之古人,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世谓词者诗之余,然词尤难于诗,词失腔犹诗落韵,诗不过四五七言而止,词乃有四声五音均拍重轻清浊之别,若言顺律舛,律协言谬,俱非本色。或一字未合,一句皆废;一句未妥,一阕皆不光彩,信戛戛乎其难。[1]164
在宋元之际词体逐步案头化,渐渐成为与诗无异的一种抒情体裁时,仇远特别提到张炎词“可被歌管”,实际上是强调《山中白云词》回归了词体的音乐属性。仇远认为诗词间存在严格区别,其不同处主要在于音律,而与诗相较,词律无疑繁杂许多,他又将张炎与精通音律的前辈词人姜夔相提并论,可见对张炎词乐成就的认可。
(二)“清空”与“骚雅”
张炎在《词源》中多次揭橥“清空”“骚雅”理论,并将其视为最高艺术旨归,《山中白云词》主体风格也不外乎是。郑思肖《玉田词题辞》谈到:“能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不容半点新愁飞到游人眉睫之上。”[1]164强调张炎词的艺术渲染效果为“清”。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流丽清畅。”[1]162解说基本点由“流丽”和“清畅”组成,在“清”基础上明确了“丽”。舒岳祥认为张炎词“有周清真雅丽之思”[1]165,由“丽”到“雅”,诠释者对张炎词艺术特征的把握逐步深化。邓牧对张炎词评价较为具体,谓:“知者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近玉田张君无二家所短,而兼所长。”[1]165邓牧和舒岳祥皆肯定张炎词具备“丽”的特点,且分别明确“骚”与“雅”的特质,而“骚”与“雅”又有关联,“骚雅”一词出自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序》,置于词学领域,则要求作词应追求典雅与庄重。由上可知,当世者对张炎词风格的认识与阐释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过程,但基本不出“清空”“骚雅”范畴,与张炎推崇的理论高境相符。
(三)博采众家之长
为张炎所推崇的词人不在少数,《词源》提到:“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作词者能取诸人之所长,去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象而为之。岂不能与美成辈争雄长哉。”[3]255张炎在创作中也能实践其主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前引邓牧《山中白云词序》谈到“知者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近玉田张君无二家所短,而兼所长”,即强调张炎词兼具周邦彦词“丽”与姜夔词“骚”的特点。陆辅之作为张炎弟子,深谙其师用心,《词旨》曾谈到张炎心目中习词取法的对象,“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诀”[4]301-302。陆辅之的总结与张炎推崇的典范相符。直至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仍谈到:“张玉田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5]可视为对张炎词博采众长认识的一种延续。
张炎词律吕协洽,清空骚雅,并能博采众长,这些重要特征为张炎同时代交游者所体认,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定评,他们的观点也深深影响到后世特别是清代词坛对张炎的论说与评判。
三、张炎词学思想的当世接受
宋元之际较为系统的接受张炎词学的要属陆辅之的《词旨》,陆辅之言:“予从乐笑翁游,深得奥旨制度之法,因从其言,命韶暂作《词旨》。”[4]301《词旨》对《词源》词学进行了多方位阐释,涉及“清空”范畴、雅俗理论与创作上的谋篇布局。
(一)“清空”范畴
张炎词学最具原创性的是“清空”理论。《词源》“清空”条:“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3]259他将姜夔与吴文英作为“清空”与“质实”风格的代表,并且明确标举“清空”境界,推崇姜夔。陆辅之十分认可张炎的“清空”理论,《词旨》云:“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尽,《指迷》(《词源》旧称《乐府指迷》))之妙,尽在是矣。”[4]303
在张炎看来,“清空”须自立新意,如“词以意趣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3]260,“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3]255。陆辅之则提出“命意贵远”[4]301,又言:“学者必在心传耳传,以心会意,当有悟入处。然须跳出窠臼外,时出新意,自成一家。”[4]303“清空”又需对字句深加锤炼,达到泯灭斧凿痕迹出以自然之语并具备敲金戛玉的艺术效果。《词源》“字面”条谈到:“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3]259“句法”条:“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3]258《词旨》则阐释为:“用字贵便,造语贵新,炼字贵响。”[4]301《词旨》还举了这样一则例子:
蕲王孙韩铸,字亦颜,雅有才思,尝学词于乐笑翁。一日,与周公谨父买舟西湖,泊荷花而饮酒杯半。公谨父举似亦颜学词之意,翁指花云:“莲子结成花自落。”[4]303
杨海明先生对此曾有分析:“张炎教人学词,曾说过‘莲子结成花自落’的话头。意思便在于‘雕琢至极’另外要出以‘自然’(有些类似乎‘绚烂之极,乃造平淡’一样),而他的学生陆辅之一方面主张‘造语贵新,炼字贵响’,一方面又提出‘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这说明他们通过实践,已经觉悟到了把研炼与‘自然’结合起来的道理。”[6]可见,陆辅之所理解的“自然”并非等同于不假雕琢的“清水出芙蓉”之态,而是经过反复锤炼后出以自然,这从《词旨》所列的“奇对”“警句”“词眼”等例句也可看出。陆辅之接受了张炎的“清空”理论,其对“清空”内涵的阐释与《词源》相一致。
(二)雅与俗
“崇雅”乃张炎词学思想的核心,他曾谈到《词源》创作意图:“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僭述管见,类列于后。”《词源》对不符合骚雅规范的作品也有论及,“节序”条:“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3]263李清照此词写于宋室南渡后,词笔沉重,饱含家国之感,但用语俚俗,在张炎看来不符合雅词标准。为情所役的软媚侧艳之词同样受到张炎批评,如“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3]266。《词源》中还有两段话值得注意,“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3]263,“康、柳词亦自披风抹月中来,风月二字,在我发挥”[3]267,张炎认为词的抒情作用胜于诗,但需远俗,言情要有节制,以含蓄蕴藉为美,以雅正清丽为追求。陆辅之接受了张炎的“雅俗”观点,《词旨》卷首开宗明义:“夫词亦难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4]301又谈到:“词格卑于诗,以其不远俗也。然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矣。”[4]301“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脱出宿生尘腐气,然后知此语,咀嚼有味。”[4]302这里多次提到“雅”与“俗”,“雅”是指体制规范,“俗”则是指词在内容表达上更适合言“风月性情”,而非指语言俚俗,应当说,陆辅之的看法与张炎是接近的。
《词源》以雅论词,涉及的词人有苏东坡、秦少游、周清真、姜白石、吴梦窗、史邦卿、杨守斋、周草窗、施梅川、李筼房等人。《词旨》以例为证,列有“乐笑翁奇对”23则,“乐笑翁警句”13则,“属对”和“警句”所选也多为姜张一派骚雅词人作品。“属对”38则选录姜白石4则、吴梦窗4则、史邦卿4则、施梅川3则、李筼房2则、张寄闲2则、周草窗2则、高竹屋2则、孙花翁1则;警句92则选录吴梦窗9则、姜白石7则、王碧山5则、史邦卿4则、周草窗4则、李筼房4则、张寄闲3则、高竹屋2则、孙花翁1则、李莱老1则,所举词句深婉蕴藉,颇能反映陆辅之的“崇雅”思想。
(三)谋篇布局
慢词经北宋柳永、周邦彦等人开拓发展,于南宋蔚然成风。相较小令,慢词字数增多、篇幅扩大,适合描写更为复杂多变的生活与情感,作法自然也就殊异于小令。《词源》下卷谈到词的谋篇布局,“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调,而后述曲。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3]258。《词旨》则云:“对句好可得,起句好难得,收拾全藉出场。”[4]302明人胡元仪笺释:“谋篇之妙,必起结相成,意远句隽,乃十足之品。”[4]302《词旨》又言:“制词须布置停匀,血脉贯穿。过片不可断曲意,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4]303陆辅之的观点与张炎如出一辙,二人都认为作词当全篇匀称,既要注意起结,也要留心过片,唯有起结相成,意脉不断,方为佳作。陆辅之还以相当数量的起句、结句及过片之句来说明,据笔者统计,《词旨》列举了31则起句,涉及张炎的有15则;46则结句,涉及张炎的有2则;起结皆见于《词旨》的词作有5首,过片例句有3则。
要而言之,《词旨》是承续《词源》词学的一部专论,它对《词源》重要的命题基本都有阐发,正如胡元仪所言:“《词旨》为书,皆述叔夏论词之旨,与叔夏《词源》同条共贯。”[4]343
四、小结
张炎的接受正是从宋元之际张炎交游者的品评开始,虽然他们的话语较为散漫零碎,缺乏理论深度与整体性,属于词学批评中较为原始的形态,但他们与张炎生活的时代相当,对张炎家世人格、词以及词学思想诠释大体恰当。这些当世者开启了自宋以来的张炎接受,并为后世评说张炎定下基调。考察张炎的当世接受有利于把握张炎接受的最初生态,继而构建完整的张炎接受史,而一直以来,有关张炎的文献十分匮乏,这些交游者提供的片语只言,其史料价值亦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