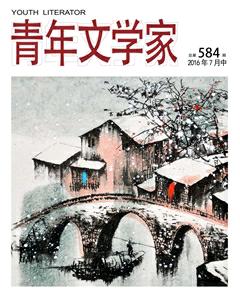贵州民族文学的构建与流变
作者简介:李家禄(1967.4-),中共黔东南州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及长篇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2
贵州世居33个少数民族,在全国仅次于新疆和云南两省区,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深厚,丰富多彩。贵州民族文学受惠于原生态文化土壤滋养,得天独厚,作家人数众多且文学表现异彩纷呈,研究贵州民族文学的构建、发展及其流变,对于把握多民族背景下区域民族文学发展特征,促进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繁荣,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重要参考价值。
一、新文化运动催动了贵州民族文学萌芽
新文化运动中,将贵州世居民族带入新文学视野的是骞先艾,他以汉族作家的眼光观察少数民族生活及苦难命运,创作了《水葬》、《贵州道上》等优秀短篇小说,鲁迅归入乡土文学范畴,称“在我们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里面”,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作为贵州新文学开派者,骞先艾作品题材和风格成为后来者竞相仿效的样本,影响了贵州民族文学发展轨迹。发掘历史资料,在新文化灿烂群星之下并不缺贵州民族作家身影。苗族作家吴绍文1936年于北京与王西彦、曹靖华等筹建青年文艺社,创办《青年文艺》,自兼社长和总编辑,发表《旅伴》等小说多篇。侗族作家王先平在《青年文艺》发表短篇小说《生活》及《活在记忆中的一位亡友》,袁仁琮在《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侗族卷》中说:“侗族创作小说的第一个人是锦屏的王先平。”《侗族文学史》认为:“他和他的作品在侗族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抗战爆发,“文军”西征,把新文化气息带入偏远封闭的云贵高原。巴金、张恨水等大家在贵州撒播了新文学种子。沿海报业纷纷西迁,贵州报业出现过几十种报纸,有民营也有官办。《革命日报》、《贵阳晨报》、《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等报纸副刊、及《文艺周刊》等专业文艺刊物提供文学阵地,各民族文艺青年围绕抗战,发表了大量诗文,以丰富的文学实践充当了探路者角色,为贵州民族文学发展铺垫了基石,提供了文化参照。
二、民间文化整理与观照激发了作家创作热情
解放与建设大西南,大批知识分子随军第二次西征,深入各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收集整理和研究贵州内容丰富、形式纷繁的民族民间文化。苗族古歌、侗族大歌、优秀民间故事等大批文化典籍相继出版面世,引发了贵州民族文学的觉醒,并铺垫了较高起点和基础。
新社会翻身作主人,作家思想上和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迫切需要为时代鼓与呼。苗族作家伍略、侗族作家滕树嵩、谭良洲、刘荣敏、袁仁琮、张作为等、彝族作家苏晓星等,纷纷在文坛上展露头角。他们自觉地将思想根须扎进民族历史与文化深处,生根发芽,作品的民族历史文化气息与时代特征同样鲜明。伍略的文学创作是从整理民间故事开始,将苗族叙事长诗《曼凤多曼笃》记录发表,被改为京剧和舞剧,又拍成电影《曼萝花》。又将《仰阿莎》、《金难和野鸡》等苗族神话叙事长诗和童话故事诗整理发表。58年创作并发表《高山上的凤凰》、《芦笙老人》等短篇小说,走上文坛。滕树嵩以短篇小说《侗家人》一鸣惊人。苏晓星创作了《乃康年》、《黄花之歌》等大批短篇小说,赞扬新社会民族地区的新变化,反映新人新气象。中篇小说《良心的中伤》通过描写五十年代乌蒙山彝族地区的一场叛乱,展示一个受蒙蔽欺骗的农民车后的心理冲突,揭示了人物心理发展的痛苦历程及思想的复杂变化。
他们的作品在思想艺术上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新社会诞生的青年作家追求阶级平等、民族大团结,极力迎合现实,抹杀人物的民族性格特征;受新时代文化气息鼓舞,身为少数民族一员又极力追求文化个性,彰显民族性格,宣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这种矛盾促成作家纷纷跨界、跨民族写作,苏晓星不少作品以苗族文化及人物为主题,伍略、滕树嵩小说中也是多民族人物共存,努力体现大同社会理想;作品思想艺术与时代精神特征趋于一致,反映了民族作家为跟上时代步伐所作出的努力与探索。即或如此,随着“反右”运动和“文革”相继到来,滕树嵩因《侗家人》被打成右派,伍略、苏晓星等作家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与迫害。刚刚露出峥嵘、呈现创造活力的贵州民族文学遭遇严重寒流而冰封。
三、文化开放推动文学创作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造就了八十年代文化大发展,贵州民族文学经历寒冬后逐渐复兴。五六十年代展露头角并很快偃旗息鼓的作家,迎来了创作黄金时期。滕树嵩继中篇小说《侗家人》在全国广受关注后,又出版长篇小说《风满木楼》,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侗家人形象,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袁仁琮、张作为、谭良洲、刘荣敏等纷纷推出重要作品。一时间,贵州侗族文学创作蔚为大观,形成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侗族作家群。伍略发表中篇名作《麻栗沟》、《绿色的箭囊》、《贫土》等重要作品。《麻栗沟》是一部动人心魄的人间悲剧:在极左思潮迫害下,苗族农民富老大、花妹、麻风病患者等被抛出了正常生活轨道。在麻栗沟与世隔绝的恶劣环境里,来自三个不同民族的弱小者,自尊、自重、自爱,相互同情、互助友爱。富老大在遭受一连串沉重打击后,怀着“转世”投生到一个“成分好”人家的冥想,自埋祈福。作品通过弥漫在闭塞山区阴暗而恐怖的文化氛围,以人性被压抑被毁灭的大悲剧结局,透视出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理上的厚重积淀。苏晓星发表了《人始终是最可爱的》、《呜呐与宝马》等大量优秀作品。讴歌新时代、歌颂民族团结成为作品经典主题。不过,所经历的复杂运动和思想斗争,丰富了作家生活基础,扼杀了作家的思想,作品缺乏思想洞见,多数停留在对过去作品类型复制与内容扩展,艺术表现手法较过去更成熟,文学上却没有取得更大突破,缺乏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作品。
青年作家异峰突起。受到世界文学潮流影响较大,文学风格变得复杂多样。以这一时期涌现的苗族作家而论,石定受黔北作家群影响较大,小说紧跟时代潮流,体现强烈的现实特征。《公路从门前过》反映改革开放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改变;《天凉好个秋》通过现代意识的观照,对农村愚昧顽固的封建宗法思想进行深刻剖析与批判。强调人们只有剥离封建残余意识,才有可能轻装前进,获得幸福生活。韦文扬发表《蛊》、《山》、《水》等中短篇小说,对传统民族风俗进行浓墨重彩描绘。苗族作家赵朝龙受到寻根文化影响,在乌江上行走、行吟,推出“乌江文学”主题系列作品。侗族作家潘年英立足于都市反思侗寨传统,写出了《落日回家》等系列作品,小说集《我的雪天》、《伤心篱笆》以浓郁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产生较大影响,成为这一时期侗族文学的重要收获。
四、反思传统催生了神秘主义文学特质
当下,新一代民族作家另辟蹊径,在求异中突围,立足于山地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中,寻找贵州文学的区域文化地位,探索建立具有喀斯特高原特征的文化:一类作家立足于当下社会情态,用现代眼光去看待社会变革,描绘一幅幅贵州特色的现实风俗画卷。仡佬族赵剑平、肖勤是其中代表。肖勤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暖》、《金宝》、《霜晨月》、《寻找丹砂》等作品,《暖》描写了一位十二岁留守女孩小等的苦难遭遇及对于爱的强烈渴求,心理描写非常细腻,真诚生动。民族文化符号在她的小说中也时有体现,但游离于形象之外,仅是人物披挂的外衣与标签,说明民族文化对于新生代作家的影响逐渐递减。另一类作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冲突中,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构建与精神缺失。民族文化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内部自我循环的亚文化体系,成为自给自足少数民族社会的精神基石。仡佬族作家王华在《当代》发表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花河》引起外界关注。在《桥溪庄》,刚出生的雪豆被抽打脚心,跟着抽打的节奏喊了一串“完了”,“他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来自于冥冥之中的不祥。”这种不祥伴随着整个叙事过程。故事最后揭示,不祥原来是人为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有意思的是,贵州作家冉正万也在《人民文学》发表《银鱼来》,他说:“这是贵州传奇,人神共处,在神性与人性缠斗与融合中暗示了人永远的孤独。”他们的目光同时指向了贵州传统文化的神秘性,形成了一个相互观照的文化状态。奇特的自然环境、奇异的民族特征、诡异的巫文化风俗紧密结合,在现代语境下营造出一种神秘多变的意象,成为贵州民族作家的主要创新手段和探索方向。
参考文献:
[1]熊艳妮:《抗战时期贵州报业概观》[J].《当代贵州》2013年35期。
[2]王华,《桥溪庄》[M].《当代》,2005年第1期;《傩赐》[M].2006年第5期。
[3]韦文扬:《苗山》[M].华龄出版社,200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