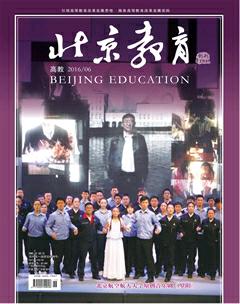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意义
张翼星
摘 要:“通识教育”的名称和实施,虽然源于西方,但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舶来品”,我国从古代到现代也有着相近的丰富资源有待我们深入发掘。“通识教育”是一种自由、通达的教育,一种重视文明、人才传统的教育,一种拓宽基础、培养高端人才的教育。近十年来,各大学在本科生教学中设置通选课,开展通识教育。但究竟为何开展通识教育?如何合理设置通选课?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通盘考虑、合理安排的问题。
关键词:通识教育;通才;现代大学;通选课程
美国现代“通识教育”踪迹
现代研究型大学,究竟主要培养专才还是通才?古典人文教育与各门科学内容和方法的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它们的关系和位置应当是怎样的?现代通识教育的尝试,出现于1917年—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逐渐形成哥伦比亚大学本科通识教育的体系与制度,随后在美国各大学通行起来。
美国关于通识教育的阐述和部署,有两个基本文献。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原校长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在193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在美国》,其中第三章专讲“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尖锐批评了当时在美国的中学与大学只为升学考试服务的应试教育倾向,批评了大学里的功利主义和唯市场取向的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使研究型大学日益变成职业培训的场所,这只会导致大学理念的消失。在哈钦斯看来,现代大学的教育应当首先是一种“共同教育”(Common Education),即“通识教育”,才能有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在专业上互相沟通。现代大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教育理念,培养共同的精神与文化根基。现代大学若要成为现代科学的创新之所,应当首先成为“文明传承之所”,这就要求探讨人类的“永恒问题”,即“共同人性”与本民族的族类特性问题。哈钦斯还主张把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教育两年制扩展为四年制,通识教育的学分占全部学分的一半。但他的这种观点和主张首先在芝加哥大学内引起激烈争论,甚至遭到尖锐批评,直到1942年才被正式通过,从此芝加哥大学便建立了强化通识教育的本科体制。虽然后来又将四年制改为前两年通识教育,后两年向专业方向分流,但哈钦斯奠定了本科阶段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传统,芝加哥大学也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典范。
另一个基本文献是1945年哈佛大学在校长科南特(James B. Conant)领导下发表的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一般称“哈佛红皮书”),对美国和国际上许多大学都有持久的影响。在科南特看来,通识教育关系到国家高质量人才的成长,更加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与哈钦斯的理念密切联系,科南特关于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要为美国现代社会奠定共同的文明基础,为此就必须开设各种形式的“西方文明”课,并以西方经典的阅读为中心,这便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最基本的内容与方式。
总的来看,现代美国流行的通识教育的显著特点有四个:一是通识教育的宗旨,是取得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认同,以求奠定美国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基础,因而通识教育的主线,便是西方文明史,或有关西方文明的各类课程。虽难免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缺陷,但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寻求文明传统的共同体认,增强对人类和民族文明的社会责任感,是值得借鉴的。二是通识教育的教学方式,是以对西方文明经典著作广泛而深层的阅读为中心。这贯穿在各门课程和各种教学环节中。三是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是经过专门机构通盘考虑、反复研究和精心设计的。四是通识教育课一般都由一流学者亲自讲授,并以多种形式组织学生讨论。
我国通识教育的资源
我国教育界将英语中的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译成“通识教育”,包含民族传统教育思想的成分。儒家经典《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文献,其中指定的九年计划要求“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中庸》所概括的学习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由此可见,儒家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求“博学”,讲究“会通”或“贯通”,或称“知类通达”。孔子也说:“吾道一以贯之。”早期儒家的教育项目称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已大致包含我们今日所说的“德、智、体、美”育,或“文科”与“理科”的内容。儒家要求培养的人,是“士”“君子”以至“圣人”,应当是一种完善的人格:学与思结合,知与行合一,德、仁、勇兼备的人。当然,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偏执的“独尊儒术”,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远远落后于西方。明清之际富于民主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大都反对文化专制,批评科举制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中便有“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规定,这显然继承了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优秀遗产。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于1917年任校长以后,着重吸取德国教育家洪堡的教育思想和柏林大学的办学经验,并且对西方各大学博采众长,结合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提出一系列改革的主张与措施,把一所充满官僚腐败习气的旧学堂改造成一所现代型的研究型大学。他鼓励“顺自然、展个性”,主张“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塑造一种“健全的人格”,并且主张沟通文、理,要求理工科的学生也学些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备人文情怀;学文科的学生也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具备科学精神。特别是他明确提出并坚决贯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这在中国现代科学、教育、文化领域开一代新风。
在北京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都曾兴起过通识教育和学术繁荣的高潮。实际上主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作的梅贻琦曾著《大学一解》一文,论及“通”与“专”的关系。有人认为,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大学毕业生应为一通才,也应为一专家,即通专并重。梅贻琦指出:“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因为通识为专才之基础,在大学本科几年的时间内难以通专并举、同时达到。造就专才,可另有大学研究院、高级专科学校或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去完成。关于治学中的“通”与“专”或“博”与“约”的关系,胡适曾比喻为埃及的金字塔,“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底子宽,才能上得去。endprint
曾任清华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的潘光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首先是教人做一个“人”或做一个“士”。这种“士”的教育,从理智方面说,就是“推十合一”。他指出:“泛滥无归的人患在推十之后,不能合一;执一不化的人,患在未尝推十,早就合一。”潘光旦可能是我国教育界中最早翻译和使用“通识教育”的人。他融会中西,既吸收和借鉴了中西教育思想,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与其他专科学校的教育不同,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通才,而不是专才或“匠人”,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的内容应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方面。这就要求我们将自然、社会与人视为一体,融会贯通地思考人生与世界的各种问题,从而为更高的专深研究奠定基础。参照西方和美国的大学制度,潘光旦明确主张大学不要过早划分专业,至少延缓到本科第三学年,第一学年可以考虑设置“自然科学通论”“社会科学通论”“文化概论”“宇宙与人生”之类的通识课程。
综上所述,“通识教育”的名称和实施,虽然源于西方,但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舶来品”,我国从古代到现代也有着相近的丰富资源有待我们深入发掘。总的来看,“通识教育”是一种自由、通达的教育,一种重视文明、人才传统的教育,一种拓宽基础、培养高端人才的教育。如果说,美国现代大学的 “通识教育”更加侧重于西方文明史、文明传统的话,我国历来强调的通识教育,更侧重于“博学”“会通”“合十推一”,培养“健全人格”与通才的一面。
我国当前实施的“通识教育”,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教育的经验与长处,但不能是美国现代“通识教育”的单纯“移植”或照搬,应当结合我国的传统与现实,走出一条富于时代和民族特色、培养高质量人才的路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照搬苏联模式,强调“专业对口”和“专才”的培养,把专业和教研室划分得很细、很窄,设立屏障,互不介入,造成“隔行如隔山”的“隧道效果”。这使学生、教师的知识和视野备受限制,缺乏深造的基础和条件。这种模式对我国教育的影响颇深,至今并未完全清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随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势头又骤然兴起。应用型、时尚型、赢利型的学科与专业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大大削弱了基础学科、基本理论与基本训练的地位,人文基础学科(文、史、哲)和人文精神呈现衰退趋势。这两种倾向,正是十年来我国大学很少出现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强调博学和知类通达、强调文明传统和人文精神的通识教育,既是补偏救弊、培养杰出人才、实现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觉与共识。
当前我国通识教育的问题与建议
十多年来,我国大学大致设定前一年半侧重通识教育,后两年半为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并允许学生在前一年半内重新选择专业。门类与科目多样的通选课可供学生选修,一般很受欢迎,也比较有利于学生个性与兴趣的发展。由此可见,通识教育是有成绩的,但仍存在若干重要问题,迫切需要加强研究、得到及时解决。
通识教育是国际现代教育的一大潮流,也符合培养现代化、高质量人才的需要。但当前通识教育仅限于采取划分学习年限、设置通选课程(包括设置几类科目、分别规定学分等)、在试点学院安排导师制、可改变专业、学习年限有一定弹性等。但这些都还限于表面,对于通识教育的意义与要求并未充分研究和讨论,缺乏自觉的共识,存在某些盲目、误解和阻力。实施现代通识教育,既要汲取西方的先进经验,又要继承我国的优秀遗产,融合中西,走出自己的路子。因此,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掘我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教育资源,而这方面的工作尚未认真开展,应当引起我们重视。
通选课究竟应该如何合理设置?怎样达到通识教育的要求?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通盘考虑、合理安排的问题。当前的通选课,确实有一批水平较高、反映教师学术专长、受到学生欢迎的课程。学科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每年能开出一大批各类名目的课程,供全校个性各异、兴趣多样的学生选修,可谓是大学里的一种进步。但当前的通选课,经常呈现自发状态,缺乏统筹规划和严格的评审制度。课程虽然较多,但也显得比较杂乱,像是一个“大拼盘”,而且有些教师与学生对通选课并不重视。有的教师由于课时短,授课内容往往前紧后松,很少有阅读经典和组织讨论的时间;有的学生把通选课视为“附属课”“辅助课”,对内容贫乏的课称为“水课”,但却乐于轻松取得学分。若年年如此重复,不作规划与改进,便难以达到通识教育的应有效果。
对于通识教育的基本含义与要求是什么,学界存在不同观点。而笔者个人理解其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拓宽基础、沟通文理,为专业深造创造条件;二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提升学生的个人气质。通选课的设置和建设,可考虑沿着这两个方面进行,而为了达到这两方面的要求,主要依靠对中西文明史上各种经典读本的深层阅读与探讨来完成,而不是依靠通选课程的设置数量来实现。这是通识教育最薄弱的环节,迫切需要有关部门从长计议,广大师生狠下功夫。
合理的通识教育,绝不是削弱或排斥专业教育,恰恰是要在更高层次上推进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培养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中学是基础教育阶段,笔者个人理解,中学的教育就是一种初级阶段的通识教育,它应当与大学的通识教育相衔接。因此,笔者不主张在中学实行文理分科。在课程设置上,如何正确而恰当地处理通选课与专业课的关系,通选课与文化素质课、传统政治课的关系,都需要作适当调整,尽量避免重复、节省时间、提高质量、注重效果,尽力调动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山东大学曾着力建设两门课程:一是“中国民族精神”;二是“中国文献经典”。由于其富于开创性,质量高、收效大,深受学生欢迎。这种课程是适合通识教育要求的,而且可以与文化素质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熔于一炉,事半功倍,岂不是很好么?当然,西方的文明史与经典阅读,也应当着重安排。
以上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心机构,组织一批有热情、有水平的学者,定期研究、讨论,进行总体的规划与设置,只有这样才能使通识教育名副其实地向前推进。有的国外大学早已成立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并定期出版刊物,这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卜 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