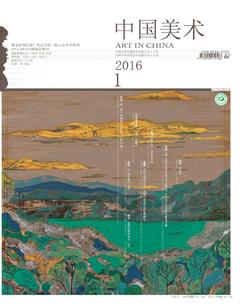土山清夜一灯红
薛永年
王逊(1915-1969)
中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曾先后在北京师大附中、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1957年,在他的主持下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为培养美术史、美术理论人才做出出了要贡献。
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亲自主持并参与了清华文物馆创建、雁北文物考察、景泰蓝工艺设计、国徽设计、建国瓷设计、敦煌艺术遗产整理、故宫书画征集鉴定、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美术学科)、永乐宫壁画考证等重要工作,在哲学、美学、逻辑学、美术考古、古代书画鉴定、工艺美术、民间美术、中外艺术交流、敦煌学等领域卓有建树。
为纪念王逊先生的学术成就,他的学生和晚辈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国美术史》(1985)、《王逊学术文集》(2006)、《王逊美术史论集》(2009)等论著。
我从1960至1965年在中央美院的美术史系学习,那时候,王逊先生只有四十多岁,比今天中央美院人文学院的郑岩先生还小几岁,主持美术史系的金维诺先生当时30多岁,比今天的人文学院的黄小峰老师还年轻。那时的美术史系,是全校最年轻的系,如果不算编制在图书馆的常任侠先生,王逊先生是系里年纪最大的老师。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王先生还戴着右派帽子,身体也不太好,但已经给我们上《中国美术史》课了,这当然离不开当时院系领导的敢于担当和知人善任。后来,在1962至1963年,王先生又给我们60级学生讲授《中国书画论》。他不是按问题讲,是按历史发展讲,讲书画论的名篇,以及书画美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广州美院陈少丰教授的听课笔记,在李公明教授和梁江先生的协助下,内部刻印多份,流传很广。
比起别的同学来,我接触王先生多一些,先是他主动指导我的专业写作,后来我的毕业论文也是王逊先生指导的。当时他没有成家,住在校尉胡同老美院西侧靠着东安市场的小土山上,内外两间屋,在晚问我经常去找他请教,也经常碰到去请教的李松涛先生和孙世昌同学。王逊先生是来者不拒,不厌其烦,放下手中的工作,耐心地接待,细致地讲解,有时还找出自己的藏书给我看。
在大学五年期间,无论在做人上,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迎接毕业后工作的准备上,王逊先生都言传身教,循循善诱,都使我受益良多。我主要谈三点。
细微关心与学术引路
我是1965年毕业的,毕业分配时,美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有结束。这个运动,作为“文革”的前奏,已开始贴大字报,批判院系领导和老先生,有些老先生首肯的学生,变成了“修正主义的米苗子”。之后,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但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临行前,我到北京站附近的美院宿舍,向王先生辞行,他已经知道吉林省博物馆来要人,不是为了补充书画研究人才,而是要搞陶瓷的人。
他出于对学生的爱护,一见面就指着书架上的宋代瓷器,问我时代和窑口,接着对我说:“陶瓷史也是美术史的一部分,也很重要,我在清华大学文物馆负责日常工作的时候,就接触了大量的器物,对后来搞美术史很有帮助。”他还说:
“你们一直在学校学习,可能以为工作单位也会像学校一样单纯,其实在实际工作中,事务性的事情很多,要学会适应,在工作中学习。”
我当时请教王先生说:“如果到吉林省以后,我有机会研究书画,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他的回答和金维诺先生一样,说一个是高句丽壁画,一个是故宫流散书画。正是由于先生的指引,我才在1972年文物工作上马后,在收集和研究故宫流散书画方面做出了点滴成绩,发表了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循循善诱与理论启蒙
那时候,美术史系的美术理论课,偏重于讲方针政策,有点忽视美术的基础理论。在艺术规律的理解,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方面,我倒是深深受益于王逊先生。有两个例子,一是意境问题,那时有门课叫专业练习,内容是著录古画,王先生带着去故宫看画,李松涛先生具体负责,我著录了罗聘的《山水册》,尝试着以文学语言描述视觉形象,尽可能传达画中意境,王先生可能觉得我写的不错,就找我谈话,指导我在意境问题上阅读和思考,引导我从理论上去认识艺术规律。我在广泛阅读李泽厚、程至的和叶朗等家的论文之后,才理解了意境不仅是美院老画家常讲的情景交融、还是“意在画外”的“空间境象”。
接着他又引导我思考意境与典型的关系,我当时也觉得意境很难用典型论来解释,就问王先生怎么办?他说,不能按现实主义的典型论来诠释意境,典型属于现实主义,意境可能属于浪漫主义,你再去深入思索。毕业那年,他直接指导了我关于意境问题的毕业论文。第二个例子是对于书法美的认识。那时故宫举行了《邓石如书法展》。我开始做邓石如研究,从文献、图像、年谱、考证入手,他则从书法美角度开导我去思考,告诉我他的老师邓以蛰是最早从美学角度研究书法并且发表文章的,说邓以蛰把书法分为意境与形式。有一次,我问他。有的书法刚健,有的书法柔婉,怎样的书法是美的呢,他说关键在于对立因素的互相渗透,不同的书法美在于相反因素组合中的不同比例,对于比较抽象的问题,他分析讲解得的特别深入透彻,一下子使我茅塞顿开。精品基础与教材楷模
王先生研究哲学出身,从邓以蛰修习美学和美术史,新中国成立后又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编写的美术教材书,与众不同,比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美术史,更有高度和广度。那本《中国美术史讲义》,开始没有公开发行,新时期美术研究所的第一班研究生,也就是郎绍君和他的同学,专门用钢版刻印作为学习资料。这部讲义在有限篇幅内,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绘画、雕塑、建筑等多种美术门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和艺术成就,既重视了美术赖以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重视了美术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关系,又没有忽视美术本身在审美能力(题材)与表现能力(艺术技巧)上的自律发展,尽管今天看来已经有些不足,在当时是公认水平较高的一部著作。
20世纪60年代我阅读他编写的《中国美术史讲义》之后,曾问他王先生怎么看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他特别向我推荐了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说《中国画学全史》是近现代所有美术史和绘画史中最好的,而且从书架上拿给我看,我发现有不少眉批小注,就借回来研究,发现他是批判性地阅读,有肯定,有思考,也有质疑,从中学到了东西。也理解了《中国美术史讲义》,是集各家大成又有新的学术构架和系统理论见解的著作,
这部书以及薄松年、陈少丰先生补充修订的《中国美术史》,也正是1989年我主持美术史系时组织大家编写的《中国美术简史》的基础。在发凡起例的过程中,我和李树老师先细读了包括王逊先生在内的多种美术史读本,其中还有:滕固的、郑午昌的、李浴的、阎丽川的、黄宾虹的,最后决定还是按王先生编写中国美术史的体系框架,自律与他律结合的方法、重视考古新发现的特点来编写。后来在又经过修订,至今已印了30余万册,被评为精品教材。参加编写的老师都付出了辛劳和智慧,但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就是王逊先生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讲义》。
是不是可以说,王逊先生是滕固之后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开拓者,是筹建我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的带头人,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是我这一代美术史学者的引路人。他是从美学思想史角度开设中国书画论的第一人,也是在美术史研究领域重视文物考古、重视哲学美学,对于古建、书法和工艺都研究有素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学者,更是史论结合、贯通古今而积极古为今用的美术史论批评家。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来缅怀王逊先生,并抄写出来送给家属留念:
门墙隔代郁葱葱,辟路开山第一功。记得传经与解惑,土山清夜一灯红。
责编/刘竟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