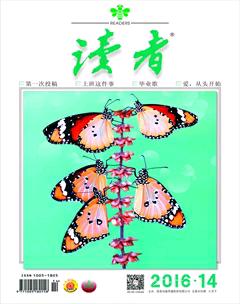一个王朝的挽幛
吴光辉
一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1898年7月8日这一天,整个江南山景就如同一幅黑白相间的书法作品,被“开缺”免职、遣送回乡后去祭祖的翁同龢,一路悲伤地向着这幅作品深处跌跌撞撞而去。一片墨黑的天空正下着细雨,刮着阴风。69岁的翁同龢早已脱下一品朝服,穿上一件玄色长袍,全身被阴风吹得瑟瑟发抖,雨水早已淋湿了他花白的头发。
风黑。雾白。雨清。
常熟虞山西麓,祖坟四周的垂柳飘拂着无奈,祖坟前新插的白幡飘展着悲苦,白色纸钱在四处飘飞着惆怅,焚香的青烟从土坟前升腾起忧伤。白发玄衣的翁同龢还没走到父母的坟前就痛哭流涕起来:“父母大人呀,儿子不孝,对不起你们呀!”他是一路喊着、哭着,踉踉跄跄地奔到坟前的。他流着泪在坟前供上祭品,点烛烧纸,乐手们吹起了唢呐。一曲凄凄惨惨的苏南民间悲调便从坟间传出,呜呜啦啦,凄惨动人。
翁同龢跪倒在黑白相间的水墨山景里,跪倒在撕心裂肺的绝望中。
一夜的漫天阴雨随风扫过,留下了点点愁苦;一夜的孤雁在林间盘旋,留下了沙哑的长鸣;一夜的寒霜无声地洒落,留下了一片揪心的惨痛;一夜的无边悲愁,使翁同龢白了一尺胡须。悲苦、惆怅、绝望,这便是翁同龢挥毫写下的《祭祖》手札的情感由来了。这恐怕也是我翻开翁同龢的《松禅老人遗墨》,就感到从那一幅幅白纸墨迹的字里行间,流泻出无限的愤懑与忧伤的原因吧。
我觉得那本在他去世后出版、现已发黄、陈旧斑驳的书法作品集,早已不仅仅是翁同龢被削职为民、归隐山林时的艺术结晶,而是一种封建知识分子理想破灭时的情感发泄,又是一种封建王朝从兴盛走向没落时的历史笔录,更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时代挽幛。渗透纸背的不仅仅是翁同龢晚年的墨迹,而更多的是翁同龢报国无门、忧国忧民的无限惆怅。
我不知道翁同龢是不是色盲,但他肯定将他的归隐地江苏常熟虞山那原本五颜六色的景物,全都精简成黑白照片似的图像,然后用他的书法思维,将这远离县城的寂山静水,勾勒成黑白相间的泼墨,从而写下了《黄昏犹作》《虞乡续记》《山居闭门》《春江渌涨》等一幅又一幅书法佳作。他让眼前的世界全都变作笔下和黑白与线条,又让线条和墨色在白纸上化作一种无奈与叹息;同时,他还让世间的刁钻乖滑全都变作笔下的朴拙敦厚,又让人世间的忠奸是非化作一种黑白对比强烈的独特形态。翁同龢就这样将自己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化作永恒。
我敢断言,翁同龢选择书法是他人生的一个必然。因为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非白即黑思维方式,才能得以充分地表达,而他的人生又一步一步地迫使他选择了这种表达。然而,正是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方式,成为大清王朝的国家悲剧和翁同龢个人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翁同龢在甲午战败后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私访康有为,随后又在光绪帝面前举荐“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百日维新”的序幕。然而,在“百日维新”的第四天,他就被以“言语狂悖,渐露跋扈”的罪名“开缺回籍”了。这恐怕便是非白即黑思维方式造成的结果了。正是这种非白即黑、非忠即奸、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认定了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能一下子由忠变奸,他也就逃脱不了被削职为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下场,后来一大批维新人物也惨遭血腥镇压。
墨黑。纸白。泪浊。
他当日挥毫写下手札一幅:“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献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骫骳之辞,尚不致贻羞先人也。”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幅《祭祖》墨迹了,他在字里行间倾诉着一代精英忠心报国却被黜回乡的无限悲伤。
一笔长横是风。一笔斜点是雨。一笔卧钩是泪。
二
孤寂。黯然。神伤。
翁同龢踟蹰在残阳西斜、枯叶乱舞、哀鸿长鸣的山景中,沉思在100多年前晚清王朝的那个悲伤季节里。良久,满怀怨恨的翁同龢,缓缓地提起那支饱蘸悲愤的狼毫,渐写渐快,渐写渐浓。我在想他笔下的这幅墨迹《一笔虎》岂止是书法作品,分明就是一代文化精英在经历“甲午”“戊戌”打击后的最后企望,分明就是一个王朝在甲午战败后垂死挣扎的时代梦想。
翁同龢一生的分水岭就是甲午战争。翁同龢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下子变成了“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由此,翁同龢的人生也“从白而黑,从忠而奸,从好而坏”了。
如果按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来判断,翁同龢的大半生是白的、忠的、好的,一直到69岁,突然就变成了黑的、奸的、坏的。他20岁被选为拔贡,22岁中举人,26岁中状元,从此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成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被皇上和太后誉为“讲授有方,入值甚勤”。他与光绪皇帝的感情达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成为光绪皇帝最亲近的股肱大臣。他曾积极赞同开设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文馆,曾奏请停止圆明园工程建设,曾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曾在中法战争中积极主张抗争。在甲午战争中,他又声斥李鸿章的软弱求和,力主“以战求和”。在甲午战败后,他又积极组织和参与了戊戌变法,想通过变法来探求中国富强之道,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势。也就在这时,他一下子变成了“言语狂悖”的奸党,被“开缺回籍”,原本“难舍难分”的光绪皇帝,这时居然一下子变得“上回顾无言”了。
可怕的是这种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官场上形成的忠奸之辩。在朝野里将大臣们划分为忠臣、奸臣,在甲午战争中划分为主战派、主和派,在戊戌变法中又划分为帝党、后党,翁同龢的人生就是因为这种思维模式而兴衰起伏。当翁同龢被认定是个奸佞之臣时,他原本几十年的政绩也就被一笔勾销,结果也只有被“开缺”免职了。
因此,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武力拼搏,而且是一种体制与另一种体制之间的政治对抗,更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另一种思维模式之间的文化较量。慈禧、光绪就是运用这种思维,翁同龢、李鸿章就是运用这种思维,国人同样运用这种思维。这样,甲午战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翁同龢被开缺罢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正因如此,翁同龢选择书法作为他人生的最后寄托,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在书法的黑白世界里,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思维模式,才能得到充分地表达与展示。
从此,翁同龢“此去闭门空山里,只须读易更言诗”;从此,大清国少了一位权臣,却多了一位书法大家;从此,他日临汉碑,勤摹图画,他的书法日渐老辣,臻于化境,成为《清史稿·翁同龢传》所言“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他成为《清稗类钞》谓之“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之书法宗师。
苦雨。草堂。枯灯。孤居山野,了此残生,唯有书法相随。
三
一捺侧锋是风。一横中锋是雨。一点回锋是泪。
1904年7月4日夜,江南山林,溽热烦闷,一片墨黑,唯有一盏枯灯随风摇曳,似翁同龢即将飘逝的生命。
弥留之际的翁同龢已经不能提笔,枯槁瘦弱,满脸愁苦,气若游丝。他自知大限已到,便断断续续地口占《绝别诗》:“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与汝曹弹……”他气喘吁吁地说完最后一句,就再也克制不住,两行老泪纵横而下。经历一阵痛苦痉挛之后,他又以《论语》集句给自己撰了一副挽联:“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他睁着泪眼看着自己给自己撰写的挽幛,让人代笔高悬于堂前,白纸黑字,黑白分明,他这才仰天长叹一声,闭上了双眼,饮恨长逝。就这样,一代爱国老臣抱着无尽的幽怨和孤愤,从此长眠于江南虞山尚湖之间,长眠在大清国岌岌可危的命运里。
其实,他是在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殉情。他岂止是死在了非白即黑的思维模式里,他还死在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皇权思想里,死在了垂死挣扎的封建专制体制里。
一笔长横写清苦。一笔斜点书悲伤。一笔卧钩画凄凉。
翁同龢就这样带着满腹怨恨离开了人世,也给后人留下了是非成败、功过忠奸的无数话题。他那绝笔的挽幛高悬在山间草堂里,也高悬在晚清王朝的天幕上。
然而,他给后人留下了《松禅老人遗墨》,也给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一座艺术高峰,更给晚清王朝走向最后灭亡写下了一个时代的挽幛。
一路纸钱飘飞,就是遣散他飘逸超脱的艺术灵魂。一路唢呐长鸣,就是高扬他质朴拙涩的书家境界。一路挽幛翻舞,就是高悬他悲怆厚重的爱国思想。 <
(晓 荷摘自《北京文学》2016年第3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