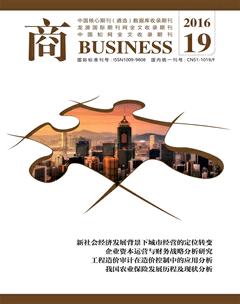论科技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谢静茹
摘要:自然在欧洲中世纪被看作一个有灵的世界,人是微观自然,与自然关系天然和谐。启蒙之后,特别是科学革命以来,自然被看作是一个机械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同时人有了认识、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和自由。后启蒙时代,现代科学试图将人与自然视作同等的客体。科技发展引发的环境、伦理问题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人类最终能否迎来理性、和平、繁荣的尘世天堂。重塑启蒙之前的有机自然观,或许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优途径。
关键词:自然;文明;科技时代
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欧洲思想家孜孜不倦探讨的主题。在西方传统思想中,自然被看作跟人一样有生命的世界。这个世界跟人体一样,由土,水,气,火四大基本元素构成。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最早提出四元素说,①其后的西方哲学家们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将之发扬起来。进入中世纪,人、地球和宇宙成为体现上帝神性的三个世界,它们不仅组成元素一样,而且运行规律相同,都是在神的理性意愿的安排下按照既定轨道通往完美。人被看作是体现整个自然的“微观世界”,正如歌德在其名著《浮士德》中称人为“这世界的小神”②。
这个世界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到极致。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相信人、地球、宇宙分别对应微观世界、地理世界和宏观世界,三者和谐融洽。这种融洽关系的根本原因是人与自然本质相通,不可分离。这样的世界观直到十七世纪在欧洲还颇为主流。在这样的世界观下,神的预见是保持世界运转的第一原因,人处于这样的不可改变的自然序列中,只需虔诚地接受自然规律并在履行神规定的义务时体现神的意志,无需也无力改造自然。所以在这一时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安无事。
人们因为相信这样一个有机、有生命、与人本身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自然,故而对自然始终怀有充满敬畏的态度。在这样和谐的关系下,自然和人一样拥有一种神性的美,万物比例适度,运行有序,均是上帝理性的反映。
十七世纪初伽利略基于实践观测的天文学发现证明了哥白尼的猜想——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从此中世纪那个在上帝的理性引导下秩序井然的宇宙观逐渐坍塌。培根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提出新科学的里程碑式的宣言:人类并不需要被动接受自然,相反,通过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探究,人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认识、改造并最终征服自然。对培根眼里的人来说,自然是客体,不再是与人休戚相关经脉相连的主体。人类认识自然这个客体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它。人在最开始面对自然的时候可能是谦卑的,但一旦掌握了自然的奥秘,人就会成为自然主人,驾驭自然。而这样的工作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完成的。人将上帝从伊甸园里驱逐,为随心所欲大刀阔斧地改造自然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从哲学上讲,在后启蒙时代,现代科学试图完全消除人和自然在存在论上的差异。用吉莱斯皮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中的观点说明就是,在传统的神——人——自然这三个特殊形而上学领域里,我们驱逐了神,又试图把人与自然视作无甚差异的存在。③这也在现代化学、生物学、物理学以及近年来非常热门的认知科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得到证明。科学革命带来的是一个去魅化的世界,自然失去了生命,失去了灵魂,变成了一个机械运动的世界。在科学革命之后的世界观里,自然和人的运行规律是相似的,组成人和自然的基本要素也是相似的,这似乎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世界观颇为相似,但其实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中世纪世界观里人与自然均是有灵的主体,而科学世界观里人与自然均是机械的客体,是人认识和利用的对象。除此之外,科学世界观是一个没有目的论的世界观。机械运动受规律支配,并无目的可言,万事万物的发展并不是顺应着上帝的理性趋于某种完美。不过,现代科学确有试图为人们展现一幅美好、积极的图景:人类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断认识自然、驾驭自然,迎来理性、和平、繁荣的尘世天堂。
当然世界观的转变并不是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一声炮响就一蹴而就的。开普勒、牛顿等处在新旧世界观交替时期的科学巨匠,并不是泾渭分明地“抛弃”了中世纪的世界观,接受了科学、无神的、机械的世界图景。例如哥白尼虽然推翻了地心说,动摇了中世纪世界观的神学基础,但在他的世界观里,太阳是一个类似基督教中“圣父”的存在,他跟开普勒一样,几乎可以算作是以宗教的虔诚崇拜太阳的人。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人类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高奏凯歌,似乎逐渐可以在无神的世界中站稳脚跟了。但真的如此吗?如今我们享受着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现代科学的世界观为我们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困惑甚至灾难。既然自然只是人类活动的对象,是认识的客体,是资源的来源,那么向自然举起的屠刀就不需要展现任何怜悯。亚马逊丛林面临的森林砍伐屡禁不止,雨林的消失威胁着诸多生物;大量电子垃圾被发达国家低价出售到发展中国家掩埋,成为危害环境的定时炸弹,而全球70%的电子垃圾流向了中国……④各国的核军备竞赛威胁着整个地球的明天……自然是为人提供资源的母体,是倾泻废物的垃圾场,在这样一个人与自然分离甚至根本利益敌对的世界观下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人自身也成为了科学认识的客体。人的身体,意识,认知都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越来越接近破译人之为人的最后秘密,以创造人、改造人为己任。人的情感、精神可以用化学物质的相互作用解释,爱情不过是多巴胺的分泌,至于灵魂,在这个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迷信概念。
以上种种,使得人类面临着自产生以来最大的生存和伦理危机。To be, or not to be. 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自然观,那么人类将无可避免的面对自然和文明层面的末日审判。相反的,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重塑启蒙之前的有机自然观,或许就能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二十一世纪的哲学需要找到某种途径,让人与自然从被认识和驾驭的客体重新变回有生命有头脑的主体,让人类对自身、对自然都更加的仁慈和和善,在此基础上,人类文明或许可以走得更远。(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注解: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77.
② (德)歌德.浮士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14.
③ 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58-60.
④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77.
[2](德)歌德.浮士德[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14.
[3]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58-60.
[4]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