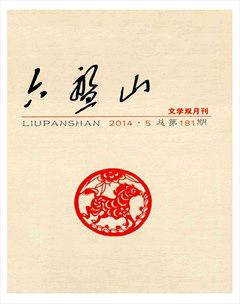一棵大柳树
牛红旗
2014年5月17日下午,从上窑村的峡谷里出来,远远望见几只白鸽在河沟对面的上空盘旋,鸽子久旋不落的弧心是一棵古柳。于是我决意这次一定要去那里看看。那里曾经是海原县杨明乡的老庄村,两年前村里人迁到了银南的黄灌区,农宅也陆续拆除了,但还有一两户人家依旧住在那里。想去那里看看的原因不是我近年在专意走访西海固即将消失的山村,而是不久前李成福老师的女儿李敏告诉我,她家的老宅还没完全拆除,她二爷爷和二奶奶还住在旁边的院里替她家照看着。
老庄村,背靠乡村公路,面对干枯的河沟,从村名看,它或许比周围的老山村更古老,可现在,它除了一片人烟稀少的废墟,就只剩几处残旧的农家土院和几棵古树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可行的窄路,没行几步,车子又被一条浅沟拦挡住了,不得已,我只好下车步行。前面独立存在的土院是否李老师生长过的旧居呢?古朴的大门楼子,两侧墩着两块大青石,院外还挺立着一棵古柳。稍一思量,我肯定自己的疑问:是的,在西海固乡下奔走多年,非读书人一般不会如此构建自己的家院。
白鸽还在盘旋,它们在我的头顶留下了羽翼挥舞的簌簌声。不知哪来的一股风,吹得前面的古柳哗哗作响。在这几近荒芜的所在,若不是脚下的残砖和破瓦,我肯定会记住风的来意和去向,然而,就在此刻,我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李老师病情转危,住进了重病监护室,他们许多人正在赶往银川医院探望的途中。我确实不知道刚才那股风是去向何处,木然中,只见那棵古柳向后倒去,缓缓地跟着悬浮的、西去的红日。然而,等我收起电话弄明白怎么回事,再定睛注视眼前的情景时,却见那棵古柳依然枝叶茂盛地挺立在原地。我摸不准刚才是进入了幻觉,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心灵感应。
李成福老师退休前是《六盘山》杂志执行副主编、资深编辑。他早年在海原县一所乡村中学当语文教师,由于他文笔出众、功底厚实和对文字有着严谨热忱的态度,后来被选调到了固原市文联《六盘山》编辑部。西海固文学在国内有今天的声誉和成就,离不开李老师当初的贡献。在他潜心指导和人格魅力潜移默化下,西海固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这是有目共睹和众所公认的。我步入文学创作行列较晚,虽未在李老师做编辑时亲受指教,但仅后来不多的几次接触,就已受到了难得的教益。其实,要学习一个人的品德,感知一个人的学养,领悟一个人的境界,获得一个人的经验,不一定非要他来面授机宜,只要是有心人,从他所行的路、所做事情、所写的文章,乃至从他所居住过的地方和他的背影里都能得到信息,受到启迪。
李老师故居前的古柳有一怀粗,树叶密密地婆娑着,树阴有两丈许。李老师的二叔母说,“成福是我们老庄最有学识的,是品行最好的人尖尖。”抑或是灼热的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她撩起衣袖拭了拭眼角,用手理了理苍白的头发,又戴上了遮阳布帽。从她口里得知,他和老伴没有随村里人一同搬走的原因是她的老伴不能生活自理,尽管黄河灌区什么都方便,尽管在这里点着煤油灯照亮,但总觉得老根在这里扎深了一时半会儿还拔不掉。她指着李老师的故居说,“成福调到固原工作都几十年了,可没害病的时候还时常回来”;她指着古柳说,“这树那时候还是个小伙子,现在阴凉都快扑到院子里了”。
她打开大门,我走了进去。这是一所荒寂的农家四合院,从院内人行道的碱土看,已经很久没人走动了。院内几棵苹果树开着与往年相同的白花,没有翻种的菜畦除了一畦韭菜还绿绿地长着,其余的园地都生满了荒草。我见苹果树旁有块石头,便走了去。我仔细端详着那块似磨刀石又似坐墩的石头,记起李老师在他的文章中提说过他早年读《文天祥》从中得知文天祥的父亲激励文天祥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和他听爷爷讲乡村故事的事来;我猜想着李老师放学回到家中的情景,或许他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看书、听爷爷讲故事。我知道,每一座老宅都有它的神奇和神秘,每一样古老的物什都有它的由来和过往,每一块砖石都有它的成因和人留在它身上的烙印,每一株草木都有它存在的生命意义。李老师的二叔母声音颤微微地说:“这几棵果树是成福栽的,年年结果子。”她佝下腰捡起一根木棍,絮叨说:“好人得的病,咋偏偏都那么难缠呢?”她见我瞅着北房支吾了一气没说出话来,忙又说:“这阵子过了,成福病好了,一定会回来看看的。”
我自言自语说:“是啊,李老师怎么会忘记这里呢。”我定定地望着北面的上房,山墙和后背墙伫立着,屋顶陷了,房心空荡荡亮着。这时,鸽子们扑棱棱落了下来,落到东面土屋的山墙上,有的咕咕不止,仿佛哀诉着什么,有的鼓起胸膛咕嘟着,仿佛焦灼地呼唤什么?
又有一股风吹过来。不知为何,我告辞后又把头脸探出车窗回望了一阵。古柳在风中呜呜抖动着,它的主干粗犷又结实,枝叶舒展而不张扬。我想,它有倒下去轰然巨响的身形,也有倒下去沉闷不语的气度!再看墙头上的鸽子,它们侧眼望着我,个个心神不宁、心事重重。
我是2012年秋天请李敏带我到她家去才见的她父亲第一面,且后来见面次数不多。但我敢断言,我也是受其教益最深的人。李老师是个温文尔雅、谦卑敦厚的人,他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也没摆一点老师的架势。他沏茶之后便和我促膝相坐开门见山谈起文学创作来。当时,我正为《失守的城堡》各篇章的书写雷同而一筹莫展,也是读过他的《追寻大先生》深有感触后一心要登门拜访以求指点迷津的。这次造访正如我在《失守的城堡》中所写的那样,通过李老师的指点和李老师一家人的亲和,是他们的《微笑中让我转了一个弯》。这弯不仅转在文学创作上,也转在对待人生态度上。李老师通过实例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写文章和做人一样,贵在平静,贵在干净,贵在真实和真诚。我难以形容当时的惬意,记得为了表达悉心受悟的过程,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茶杯里的茶叶活了过来,悄悄地舒展,悠悠地翱翔,缓缓地栖落,相互间还不时碰一下,一碰,随即又各自矜持,各自沉静,没一会儿,茶水就慢慢有了颜色,渐渐淡绿,渐渐金黄,茶香也跟着热气飘出水杯,仿佛生了双翅,飘满了整个屋子。”
甚为遗憾的是书稿写完后没能请李老师帮我校对一下。李老师退休在家,重病在身,还一直在不间断地帮一些单位和朋友整理、编纂书稿。李老师患病后我和几位文友去家里探望过,他没一点重病患者的沮丧和哀怨。我们谨小慎微地说着每一句话,强装笑脸吃着熟透了的西瓜,生怕哪一个字眼或哪一个眼神撞着那根暗自绷紧的神经。他似乎觉察到了,反而淡然、舒缓、乐呵呵地谈说着病变的过程,讲论着人在磨难面前应该持有的坦然态度和从容对待生死的观点。谈到书法,他取来朋友为他题字篆刻的几枚图章让我们观赏,为了安慰他,我还贸然给一枚图章估了高价,他一高兴,像小孩一样唤来李敏炫耀说,别以为我只有几本书,现在看看,这些石头疙瘩也是宝贝,也是一笔遗产。李敏站在他的身后笑着,应承着,可所有在场的人没一个心里不是酸的。
是啊,有些人喜欢给后人留下金银珠宝和钻石玛瑙,可这位朴朴素素的读书人,却把一块刻有自己名字的石头当做珍宝。他掬着那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端详了许久,其神情和一位母亲对着镜子笑看自己的面容,对着襁褓欣赏自己的婴孩,对着农田检阅自己耕种抵御病虫战胜旱涝茁壮成长起来的庄稼没什么两样。而后,他依依不舍、小心翼翼地把那块石头放进盒子,交给了李敏。他还对我抱歉地说,原本想抽点时间帮你校对书稿的,可手头接承下的活儿多,没能帮上这点忙。我忙说,以后我还要写东西,到时候再请您帮忙,时间长着呢。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过去了一年多。自第一次见过李老师后,后来还见过李老师两次。一次是在座谈会上,他像学生一样认认真真地听着,座谈时,他结合西海固的文学现状交流了不少自己的看法,会后我开车送他回家,他又重复交代了第一次对我讲过的话,还叮嘱我要多看名家作品,多体验底层生活,多思考。另有一次是在一家小餐馆,他正和一位老朋友吃饭,看见我,笑声朗朗。他还向他的老朋友介绍我并加以赞赏的语言。那次我们相谈甚欢。吃完泡馍他和老朋友走出餐馆后餐馆老板问我,你如此尊敬这位老人,他是哪一级干部?我说,他不是干部。老板不信,不是干部是大老板?我说,也不是大老板。老板疑惑不解地说,不是领导不是老板,那他一定是一棵大树喽!我说,是的,他是一棵大树。
虽则,这是我见李老师最后一面,然而,在生命的亲历中我将时常记起那棵叶落叶生、守望家园的古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