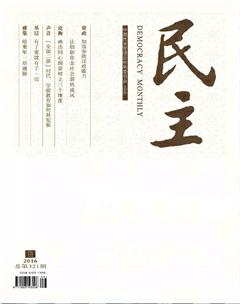眷村子弟江湖老
苏木
亲情写作渐成两岸文学创作的一门“显学”,赵刚教授在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的序言里援引陈映真的话“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写作”,对亲情写作容易出现的问题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他对该书的评价“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的书写,而是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似乎也成为对写作者的要求与责任的企盼。倘以此来衡量袁琼琼女士关于眷村及家人回忆的散文集《两个父亲》,未免只能将其归入“私人书写”一类,但细细读来,那些对眷村生活的回忆片段,既是对邻人的观察,何尝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观察;既是追忆,何尝不是对回忆的再度回忆。这位善讲故事的眷村第二代,在狭小的书写空间里表达对眷村生活的颇有个人特色的感受,既具故事性,又去故事性;既具历史性,又去历史性,糅合说书人的起承转合与个体观察者的柔软体悟,虽少有“反省”之努力、大江大海的历史悲情乃至“拒绝遗忘”的铿锵宣言,却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蕴发出了几许“异色”与“亮色”。
1949年年底,“国民政府”将“行政院”由四川成都迁往台北,正式宣告大陆弃守,陆续迁台的人员达百万之众。除去少数权势人物,多数军公教人员身无长物,辗转流离。1956年,宋美龄发起“军眷筹建住宅计划”,至1967年结束之时,共建成3万余栋眷舍,分布全台11个县市,据不完全统计,共计888个眷村。五湖四海、不同性情之人在统一规划下共同生活,相互影响、渐融一体,眷村生活的历史悲情难免成为共同经验,袁琼琼引友人之话,“眷村是长了毒瘤的母亲,你不能不爱她,又不能不恨她”,其冲击感可谓强也。然而,时代变迁终究是由每个个体来真实承担,共同经验并不能排斥个人经验,袁琼琼说,友人对眷村的回忆充满不堪和痛楚,“我对眷村一直有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我没吃过眷村生活的苦,只享受到眷村生活的好处”。没吃过苦,无妨视为耳顺之年作者故作天真烂漫之语;眷村生活的“好处”却实打实来自母亲、生父和继父的关爱,或可说是母亲和两个父亲给予了作者一种异于邻人的生活感知,终衍化成为她体悟眷村与人生的底色。
作者生父响应国民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离家从军,随迁台湾,后因病去世。生父去世时,作者年已及笄,已是颇知事体的年纪,如何处理对母亲改嫁的认知和对两个父亲的感情纠葛,端看作者的笔法和功底。《两个父亲》文中,作者不惜“丑化”美丽母亲的形象,以“母老虎”比之母亲的护犊情深,从“与其嫁掉小的,不如嫁掉老的”的后知后觉中感恩母亲改嫁作出的牺牲 ;写继父之处,则从肢体接触的触感、嗅感落笔,“过去的他跟我们完全没有肢体接触,甚至没有眼神接触,但是最后十几年,我们开始习惯见面或离开时拥抱他……他那年已经八十来岁,身体非常清凉干净,抱着他时感觉他有种香气,青草似的,阴凉干爽,完全没有所谓的老人味”。年少时的几多龃龉、牵牵绊绊,唯自己的成长老去才能体会父辈在无言中的关切。作者在《两个父亲》一文结尾时,想象两个父亲的相逢,“一个胖胖的,浓眉毛大眼睛,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是本书最深情的一处。
在第二部分《眷村》中,作者追忆眷村生活,以《在塞尔维亚》一文显出观察之独特,不在生活的困窘、成长的烦恼,而在青年男女之间流动的情意——每月一次分发米粮的士官长和某个年轻妇人之间可能存在的“隐秘心事”。作者写到,“一个月一次,不需要更多了。只要一个月一次,在人群里彼此对视,二十秒或三十秒。那一整个月便因此丰富起来。可以如同粮食一般,慢慢咀嚼,一天三次,每次烹调或进食时,那个秘密便被提醒一次,被咀嚼。从喉头,滑过呼吸的位置,滑过心的位置,进入胃里”。发乎情而止于礼,岁月静好之时如是,动荡颠沛之时如是。这种“思无邪”的美好穿越白云千载、穿越大洋海峡、穿越政党更替,在海岛一隅扎根结果,不妨视为农耕文明基因的强大遗传力。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长大的眷村子弟终究会离开眷村。袁琼琼在《身在此,魂魄在彼》一文里叹道,眷村子弟离开眷村,并不是开枝散叶,而是汇入社会洪流中,就此无影无踪。她以说书人戏谑的口吻解释缘何加入影视圈和黑社会者为多,“在群众里生活,要被重视,必定要夸张自己的行为和感受,眷村成长让人容易有戏剧性倾向。这大约就是这两种‘行业特别吸引眷村子弟的理由”。但前路茫茫,来者犹未可追。作者继续说,眷村生活的封闭性,使眷村子弟比一般外省人更不容易融入台湾社会,在被保护也被隔绝的眷村里生活,使我们融入外界的时间推迟至少二十年,等到我们出来融入社会时,许多优势早已丧失,许多眷村子弟沦落到台湾底层,成为二或三等公民。以《一百年漂泊》中杨渡父亲的例子作对比,这位台中农民家庭的儿子投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转型,亲身参与台湾“短工业化年代”,克难前行,终成为如赵刚教授所言“轰轰烈烈”群体里的一员。尽管并未具体刻画某位眷村子弟的腾达或沦落像,相较于眉目分明的非眷村子弟的外省人或本省人,如何在被忽略、遗忘的现实之上前行,是袁琼琼作为“返来的女儿”对同侪、也是对自己的发问。
眷村子弟只是台湾外省人的一部分,眷村生活史只是台湾外省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台湾外省人生活史也只是近现代台湾史的一部分。在《宝岛一村》等作品挟来的强势“眷村热”下,同是眷村第二代的朱天心说,“如今眷村书写或演出,显得悠哉自在、甜美怀旧,我以为是因为它已死透了,它再没有想象和描述中的有影响力和可怕”。外省人第二代的蒋晓云也说,“台湾不仅仅有眷村,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的”。为谁代言发声、选择何边站队、无意或有意美化或丑化,在这个本来可以越来越开放的时代,仿佛超越叙述本身,成为越来越难以摆脱的羁绊。感谢袁琼琼柔软而模糊的小作,摆脱羁绊,着意追忆,有这样一群人,生于眷村,老于江湖。
眷村子弟江湖老。
——以《台北人》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