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四季(外一篇)
□ 那 耘
一年四季(外一篇)
□ 那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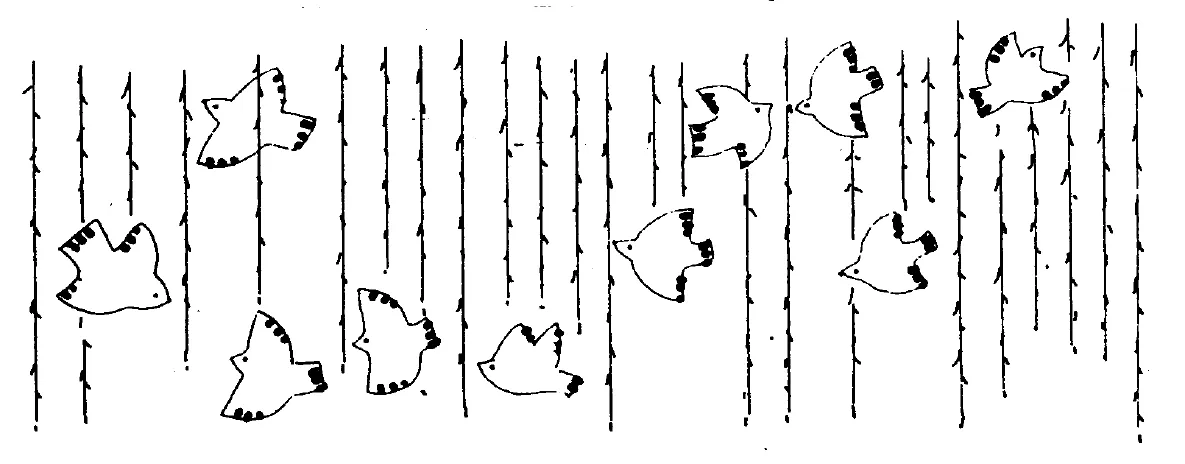
如果要用一个字,概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十年间对食物的感觉,那便是:馋!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花生种是拌上农药下种的——不是防虫,而是防人。
播种的农民经不住诱惑,会大把大把吞下花生种。即使拌了药,也会偷冷掸掉药渣,用衣袖蹭一蹭,或用水涮一涮,便虎咽了下去。如果这几天哪位闹了肚子,大家都知道,他肯定偷吃了花生种。
大豆口感不如花生,就不必拌药了,急了眼的人也有吃的。
花生种顶出了生命小伞时,临近路边,会有若干缺席者——这是上下学孩子们的作品:他们扒走了刚种下的花生,又狡猾地将地垅复原。
花生们的厄运,其实远未结束。快要成熟时,也会有一只只大人或小孩的手,扒开土壤,将率先成熟的取走,然后也是狡猾地将地垅复原。
收获花生时,干部们只得告诫大家:小命可是自己的!那几天,自家的口粮肯定节省了,如厕的次数也会倍增。
摔花生时离年关不远了。干部们知道管不住大家的嘴,索性不管,他们严盯死防的,是大家的口袋。上厕所免不了要盯着,关键的关键,是收工的时候。男社员容易对付,妇女们要复杂些。大姑娘们矜持,不会太出格。老娘们儿就令干部头疼了。她会充分利用身体优势,把花生携带回家。即使花生被从隐私部位强行掏出,也只是臊红了脸,大家嘎嘎一笑,便拉倒了。
炒花生就要过年了,这是杀猪外最令人雀跃的时刻。远处传来稀疏的鞭炮声,炊烟和火药的气味,红红的春联,行人脸上的匆忙和喜色,更衬托了这花生的香美。
平日里沾的荤腥少,能吃上一顿肉,便是所有美梦里最美的梦了。
杀猪只有一回,得是过年。杀鸡鸭鹅,有数的几回,须逢非常的节庆。
此外能解馋的,便是生产队里老弱病残的牲口了。哪一头垂垂老矣,或病入膏肓,大家都掰着指头数,期盼它快些咽气。有等不及的,便提前数天有了结果。更有违法的,还能工作的牲口,便莫名其妙地死了,吃了肉。宰杀耕畜是很重的罪,也有人因此获罪。
分肉那一天,大人小孩都过年般兴奋。肥瘦不等,骨肉不匀,分肉成了苦差,须由村中长老承担,要么过秤,要么只凭肉眼,反正就这么分了,似乎也没起什么纠纷。头和四蹄,按惯例,属于几位刀斧手的。牛和马,头很大,据老人们说,其实也很出肉的。因为他是专家,享受这个特权,大家只是妒羡一点而已。
和吃肉比起来,吃蛋似乎要容易一些。
家家都立了计划,将鸡鸭鹅一代代培养起来,先选种蛋,再选乳娘——有不少不合格的乳娘,或孵到一半便撂了挑子,或闹个鸡飞蛋打,前功尽弃。
有的母鸡似乎很有激情,涨红了脸,扎煞着羽毛,不生蛋了,甚至不吃不喝,非要担起哺乳的重任。主人不同意它的想法,便僵持,逼得主人天天用冷水浇它,以期早日恢复产蛋。
每天早晨摸家禽们的屁股,是主妇们的要务,孩子们往往也乐于参与。如果硬硬的,便是今日的蛋了。如果连续硬硬的,便要享受劳模的礼遇,甚至伙食也要比同伴好。
那时的家禽,还有家畜,对粮食格外敏感。它们会机敏地捕捉住机会,分食主人的食物。它们的眼神,总有一种偷食者的余光,那是觊觎,也是饥渴,是一种无奈的贪婪。
八十年代省亲见到的家禽,直眼白搭在稻谷上走来走去,似乎在寻找什么。
父亲说,他们在找虫子吃。
我诧异,不是有现成的稻谷么?
这令我恍如隔世。
饱饱地吃上一顿米饭,几年前,还是一种很大的奢望——看来,我们的生活中,是发生了某种质变。
如今,我和周围许多人一样,长出了三层下巴,腰上也佩带了救生圈——减肥,已成为生活中的必修课。
面对一道道消受不尽的美味佳肴,我总会想起一个人——那个深情地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他的名字叫邓小平。
舅 姥 爷
瓜尔佳,汉语音关,满族大姓也。我伯母姓关,她那支关姓又特别庞大,我就有了数不清的远房瓜尔佳舅舅,当然舅姥爷也是数目不菲。大部分舅姥爷都无缘得见,惟独五舅姥爷忘也忘不掉。
印象中大家都怕他登门,最怕的是赶集那一天,而五舅姥爷最好的一口便是赶集,一般他是空着手去,再空着手回来,往往是快吃饭的时候,五舅姥爷姗姗而来,上座早已留好,须再三恭敬延请,才坐。如果吃过了饭,并且主人竟无重新开宴的意思,后果将十分严重,看在伯母只是他侄女,侄女去世我堂兄只是他堂外孙,他留足了面子,那也少不得拍桌打凳,严词训斥,然后拂袖而去,须再三虔诚挽留,才重新回屋上炕。饭菜的内容也须十分讲究,概而言之,得用最好的孝敬他,比如说有三只公鸡,你竟杀了次大或最小的,那也要震怒且拂袖而去的。父母他们笑谈说,赶集那一天,家禽们都很紧张,院子里很少见到它们的踪影。
五舅姥爷家离集市二十里,我们约十五里,清早顺路经过时,他也不进门,只在门外咳嗽两声,大家便知道五舅姥爷赶集来了。一般他都很准时,清早咳嗽两声,午饭时赶回。没听到咳嗽声,大家弹冠相庆了,往往也会出错。杯盘狼藉之时,五舅姥爷会紫涨着长脸,怒发冲冠出现在面前。惟一的化解,便是去抓最大的公鸡了。往后清早便会格外留心,须知五舅姥爷声带出点故障,或竟偶尔忘了出声,那也是可能的。
五舅姥爷真的不能赶集,一定是健康出了问题。开始偶尔一次两次,后来日见其多。大家说,五舅姥爷老了迈不动腿了。他活到七十多岁,在他那支瓜尔佳里,算是高寿的。
五舅姥爷和他的兄弟们都不爱种地,靠什么营生,说不上来,只见他们溜溜达达,活得写意。到了舅舅这一辈,能干活有出息的很少。因邻村而居,便对大舅和老舅多一些了解。
文福大舅是家族里少见的勤快人,因其近于愚忠的操劳,竟一直做着生产队里的干部,开始是小队长,后来是大队的贫下中农协会主任,群众最无法忍受的便是他的演讲,而他是绝不会放过每一次折磨听众的机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开头是一连串的这个,中间还要插上数不清的这个,不胜其烦的听众实在抓狂,难免扬去一把沙子,或甩出干粪蛋。这也休想中止大舅的重要讲话。舅母矮且黑,不擅家务,饭做得不好吃,孩子也穿得褴褛,儿子白里透红,却有些低能。女儿呆滞,几近不能自理,也嫁了人家,据说丈夫也有些残疾。大舅殉公后,这一家人就不知哪里去了。那一年水患频仍,深夜时大舅播报汛情,雷击身亡。第二天尸体停放在拖拉机库房里,上面盖着两张麻袋片,地上满是油渍,围了许多人观看。大舅耳朵里有点干血,双目紧闭,神情却很宁静。大舅得到的最后奖励,是一副薄薄的棺材板。村校派去一批小学生,为他做悼念仪式。我猜想,这足以告慰大舅那忠厚的灵魂了。
文波老舅是三邻五村仅有的几个光棍之一。别人光棍的原因,多因残疾或体貌陋琐,他却完全因为懒惰。印象中的老舅,细高的身材,面皮白净,穿的也很整洁,说话细声细语,待人接物温和得体。惟一的美中不足,是头上有几个浅疤,毛发肯定要缺几小块,于是一年四季帽不离头。只要还有一口吃的,老舅绝不会去上工。他的主要食物,便是玉米糊咸菜,有时咸菜也没有了,便往糊里撒点盐,喝得文文绉绉有滋有味。据说老舅一辈子没沾过女人。他见了她们总是躲。尤其她们扎作一堆,不怀好意盯他的时候。这时他会面红耳赤,飞也似逃掉,在嘲笑声中绕出许多冤枉路。
老舅死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自己吊在门框上,脚下的小凳踢翻了。吊死者死相一般都很狰狞,惟独老舅却有几分笑意,平静中带着欣慰。大家都说,这是遭够了尘世的罪,到另个世界享福去了。惟一的炕柜,载着恬淡的他,于稀疏的贺岁鞭炮中,抬到乱坟岗,冻土上刨个浅坑,埋掉。弃世那一年,老舅大约不到四十岁罢。
(摘自《满族文学》2015年第15期)
父亲笑着说:人家现在吃米了,最好做熟了给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