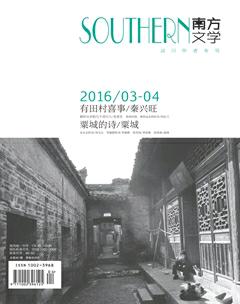树生的故事
卢子
这个温暖的初冬,我慕名来到位于海洋山脉的大弯村。大弯村遍地白果树,每年一到秋冬交替时节,这些前阵子还是青里泛黄的白果叶,在一两阵凄风苦雨的渲染下,铺天盖地的黄透,一下把岭南的冬天给点燃了。
我谢绝了有关方面的安排,只身一人到大弯村写生创作。或许是得到上面的交代,村长学正、村主任来苟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亦步亦趋带我参观完整个村庄。
初冬的阳光柔软地包裹着这个遍地矗立白果树的古村落,一树树金黄的白果叶,像小扇子又像张开粉翼的蝴蝶,扑落在泥砖墙头,黑色瓦片缝隙里,青石板路上,有薄薄的一层了。如果有风,它们还在飘落,直到枝头干净,直到地面成毯,它们还会张开翅膀飞起来,挪了另外一个地方跌落,可惜没有风,它们只好乖乖地躺在原地,任人践踏。我们兜了一圈回到村头,村头一棵古拙苍老巨大的白果树,像玉帝专用的帏幔一样,庄严的张开在那里,一树金黄,夺人眼目。树下几个孩子骑在草垛上翻滚,旁边有一堵泥砖墙,墙根一只花公鸡在啄食。我被这一幅乡村野趣图所感动,心里有了灵感,我决心画眼前这幅乡野画卷。
我的身后不一会就围上来了一群村民,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大家都很兴奋,在村长学正一番警告之后,变得鸦雀无声。村民显得很有耐心又充满着好奇心,所有的眼珠子都牵在我手中的画笔上,随着画笔在画纸上转动。他们屏息凝神,表情肃穆专注,时不时发出一声惊叹。大弯村正处于旅游的黄金时间,来此观光的游客很多,如果碰上周末这里更像赶庙会一样人山人海,人满为患。我特意挑了一个不是周末的时间,但游人依然不少,有省内省外的、港澳台的、甚至还有外国人,他们像鱼一样一群一群地游来又一群一群的散开。他们围在树下拍照。他们也会围到我身边来看稀奇,却都在村长村主任的眼神和手势的示意下离开,村人自觉地帮我肃清了这些外在的干扰,他们心里认为我现在不是在画画,而是在为村里做一件神圣的事情。
这幅画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地上树叶响起嚓嚓的响声,一串脚步由一个拐杖拖过来,在我身旁站定。不一会,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画家,你的画没画好——
我悚然一惊,这话怎么听起来有当头棒喝的警省。我不得不停下笔,回过头来端详这个声音的来源。最近这二十年来我再也没听到有人当面说我的画不好,我的画被各大馆厅收藏还经常被作为国礼赠给国外领导人或贵宾。今天居然有人说不好,我脑海里冒起第一个念头便是此人定是不懂画,但这话里有话,绝不那么简单。
话是从一个五十多岁看起来似乎比实际年龄更老些的半百老头的嘴里冒出来的,他的头发斑白凌乱,黑布棉袄油渍发亮,他拄着一个竹竿,背有些佝偻,右脚居然是瘸的。他从左边蹭到右边,眼睛转悠在画里的白果树、泥砖墙、一群孩子追着一片树叶上,最终他还是轻轻地摆头,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画是画得不错,可惜还是少了点什么。
所有人都回头来看他,显然为他惊人的言论所惊讶,这个一直在村里不显山露水的低调角色,此时此刻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村主任来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揶揄了一句,板栗,你哪只眼睛看出这画不好。
板栗似乎没听到来苟说话,或者压根眼里面就没有这些人。他眼里面只有这幅画。
你想听听吗?他从画上移开了目光,盯着我的眼睛,突然问我。
想呐,你倒是给我说说看。我认真地看着他说,放下身段,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他似乎感受到我的诚恳,语气变得柔软了许多。
他顿了一顿语气,不容置疑地说,这幅画,少画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又着重强调了一句。他的瞳仁从眼角瞥了一遍旁边这些人,接着说,学正,来苟你们说是吗?你们每一次带领上级领导或者客人来参观,都没有说起他,你们真把他忘了吗?
村长学正村主任来苟脸上有些微微变了颜色,他们欲说又止,最终咽了咽喉咙,保持缄默。
画家,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可要耐心听完——半百老人清了清嗓子,没有等我置可否,也没有作开场白,开门见山直接说了下面这个故事。
他叫树生。六零年在村口这棵白果王树下生下来的。那天他母亲还在帮生产队割茅草,割着割着,突然肚子一阵剧痛。她便丢了镰刀腆着大肚子急急忙忙往家里跑。刚刚跑到这棵树下,树生就生了下来。
母亲找人帮他算过生辰八字,说父母带不住他,需要给给他找个寄娘,于是拜祭这棵老得不知道年龄的白果王做寄娘。严格的说应该是寄爹,因为白果王是棵公树,不结白果,只产花,花粉让蜜蜂蝴蝶采去给其他白果树授粉。村里那些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白果树都是他的子女,也是树生的兄弟。
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加上母亲的千嘱万咐,树生对这些白果树像神灵一样敬着,绝不允许别人对它们进行冒犯。那时候,树生,学正,来苟,还有我,我们都是同龄人,每天都黏在一起,追鸡撵狗,上屋掀瓦,什么都做。我记得那天学正提议攀爬白果王,树生突然翻脸,恶狠狠地站在树下,一个也不许爬树。最终树生被学正和来苟放倒在地上,大伙纷纷爬上树,一字排开骑在树枝上嘲笑树生。
树生从地上站起来,悻悻跑回家。不一会提着一把镰刀往白果王冲来,边跑边说,砍死你们,我砍死你们。我们惊慌失措地往下跳……我的脚——你看看我的右脚,就是那天跌在石头缝里,把脚筋给折断了,从那时起我的脚就落下了这个毛病。
我当时恨死了树生,大伙也不再跟树生玩耍,把树生当怪物,当空气,从孤立到忽略,树生在人眼里变得可有可无,比一根鸭毛还轻。树生没有了玩伴,他整天整天跟白果树玩,从早到晚,自言自语,把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向白果树诉说,白果树成了他世界的全部。
村上的白果树后来分到各家各户,白果王由于是公树,又是大湾村标志性的村树,所以它依然是村集体所有。九十年代白果突然身价倍增,一夜之间由原先几毛几块一斤,涨到了三四十块一斤,一棵白果树多则收获上万,少则也有几百。大弯村因这些祖宗树而提前跑在小康路上。这时候,我们这一茬人,也都为人父母,只有树生光杆司令一个。树生没有老婆,只有这些白果树,尽管树分到各户,成为私人财产,但他仍然视它们为自己的亲人,把它们当兄弟,白果王是他的娘。看到家家户户富裕起来,村人对白果树爱护有加,树生心里奔流着一股幸福的暖流,时时哼着几个简单明快的音符,别人听不懂内容,却听得出其中的快乐。
可是,世事难料。几年之后,白果炒作效应一过,无人再来收购,白果变得一钱不值。大弯村依赖白果富起来,又因为白果陷入困顿。这时候,来苟第一个卖起了白果树,果不值钱了,树却慢慢越卖越贵,一棵百年老白果树可以卖到两三万的价钱。看到来苟卖树得钱,全村争相效仿,掀起卖树热潮。这场突如其来的空前“灾难”,简直是要了树生的命,好像村民卖的不是树,而是他的兄弟。
树生不再哼小曲,他白天黑夜给我们讲道理,说着说着,眼里流出悲伤的眼泪。他甚至给我们下跪哀求,可是这群“疯”了的人慢慢把他当成了“疯子”。树生无计可施,只好打电话给政府,政府派人来处理,这些倒腾古树的行为收敛了一些。大家不敢明目张胆白天挖树,转到晚上进行。树生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兄弟”被卡车装起,横着拉出村去,心里火燎火燎地痛。他阻止不了卖树的,他就阻止买树的。他把村道挖出一个个深坑,让卡车走不了,可是深坑不一会又被填平,树照旧给拉出去。树生只好回家抡起镰刀跑出来,往买树的前面一站,大义凛然。买树的胆怯了,纷纷退场转移到别村,还放话说,大弯村只要有树生这个“疯子”在,就不会再来大湾村买树。
村里人彻底急了。学正、来苟轮番来找树生做思想工作,可是树生一根筋犟到底,油盐不进。接着村里把我和九十岁的东芬奶奶推举出来找树生动之以情,树生说,那些白果树是我的兄弟,我的妈,你说,你们要卖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妈,你们肯吗?大家见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在学正来苟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把树生绑在树上,然后当着树生的面挖树卖树。树生破口大骂,整夜整夜的骂,直到声嘶力竭,嗓门过度使用,导致发声功能丧失,只发发出嚯嚯的声调。
买树的后来打起了白果王的主意,直接甩了十万树款。村人给这十万甩红了眼,开始在白果王根部动土。树生声音瞎了,眼睛可不瞎,叮在地上的铁镐,在一镐一镐地挖着树生的心。树生爆发超乎寻常的力量,他不惜蹭破皮肉挣脱了绳索。他不顾一切地往村外跑去,深沉的夜色埋没了那沉闷的脚步声。
大家有些心慌,十万树款还接在来苟手里。大家不怕树生闹,怕的是树生跑去报告乡政府。他们停止了挖树,村里每个出进口都派人盯稍。天亮的时候,一个身影急匆匆地靠近村子。村人发现了树生,树生身后没有带来政府的人,确定了树生只是一个人。挖树的把提起的心搬下来放实,大家开始继续未完成的工作,不想夜长梦多。
来苟发现树生嘴里嚯嚯地比划个不停,树生嗓门坏了,现在树生就是一个哑巴。来苟不理会他,抡着铁镐对他说,你再捣乱又把你绑起来。他的镐头刚刚落地,就听见身后哧哧的响,接着飘来一股呛鼻的火药烟味。所有的目光汇聚到树生身上,树生敞开衣服,肚子上缠满着导火线。我日你祖宗,来苟当时骂了一声,丢下铁镐撒腿就跑,大伙也跟着跑,跑得比兔子还快。来苟边跑边说,树生,我们不挖树,你赶快弄熄导火线。
树生听到来苟说出的话,他把导火线扯断了。他早在导火线上割了好几个切口,就是为了便于扯断。挖树的几个心突突跳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缓过劲来。他们不敢上前,可是又不甘心离开,其中学正试图慢慢靠近,树生大喝一声,打开打火机作势要点燃。学正吓了一跳,停住脚步向树生摆手说,我就拿我的锄头,拿起锄头就回家。他同时挪了一步,两步,三步……第十五步。学正心里数着数,第十五步的时候离树生的距离约两米,他趁着树生举棋不定之间,猛然翻身一个虎跃,他抱住了树生的双腿,用力把这危险人物掀起,重重地摔倒。来苟等人蜂拥而上,钳头的,掐脖的,骑腿的,动作迅速有效,树生像一块生鱼片被死死地钉在砧板上。来苟把树生身上的导火线一圈一圈地解开,解到最后连火药雷管的影子都不见,只有一个十米长的导火线。
大家啼笑皆非,仿佛受到了愚弄和侮辱,抬起树生四肢,抛饺子一样,抛起,扔下,又抛起,又扔下,直摔得树生天旋地转,眼冒金星,连嚯嚯都叫不出了。最后大家玩腻了,直接把他扔坡坎底下去了。
这场闹剧让众人心情愉悦,继续举镐抡锹,不知谁带头唱起革命歌曲,大家齐声附和:团结就是力量……
谁也没有留意到树生又站在了他们面前,悄无声息地点燃了肚子上的导火线,身上郝然绑着土制炸药装置。大伙看清炸药的时候,腿脚都软了,踉踉跄跄跑几步,全都趴倒在地上。
树生只留下一句含糊不清的话,接着他从容地跑离活人和“寄娘”,随着一声闷雷一般的巨响,火光四射,泥石冲天。活着的树生一瞬间化成碎片。
因为树生的死,再因为上级对挖古树采取了严厉惩治措施,大湾村停止了挖树卖树行为。可以说,游客今天来大弯村参观的所有的白果老树,都是树生用生命换来的。经众人后来仔细回忆,树生留下那句话是:不要挖树。原来树生早偷来了炸药,那炸药是隔壁村采石场上丢失的。众人始料不及的是树生为了一棵树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大家只找来树生的身体碎片,碎片和泥土粘连在一起,几乎无法分辨,最后只好把“树生”掩埋在炸出来的坑里……
板栗像抽尽了全身的气力,终于把故事讲完,他乌黑的嘴唇在抖抖索索,两条腿和竹竿也在颤巍巍的抖动。大家沉默,没人把气喘得大声一点。
画家,我们今天踩着的这块黄土,就是当年埋葬树生的土地……你是位大画家,就算我们的白果王老死了,你的画也会永久活下来。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拜托你让树生一直活在你的画里。
所有人都点着头看着我。我也郑重地向着埋葬树生的这块土地点点头,这块土地还留着炸药烧焦的颜色。我的眼里一些热热的东西在涌动,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没有画好这棵白果王,因为我少画了一个人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