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子的箴言
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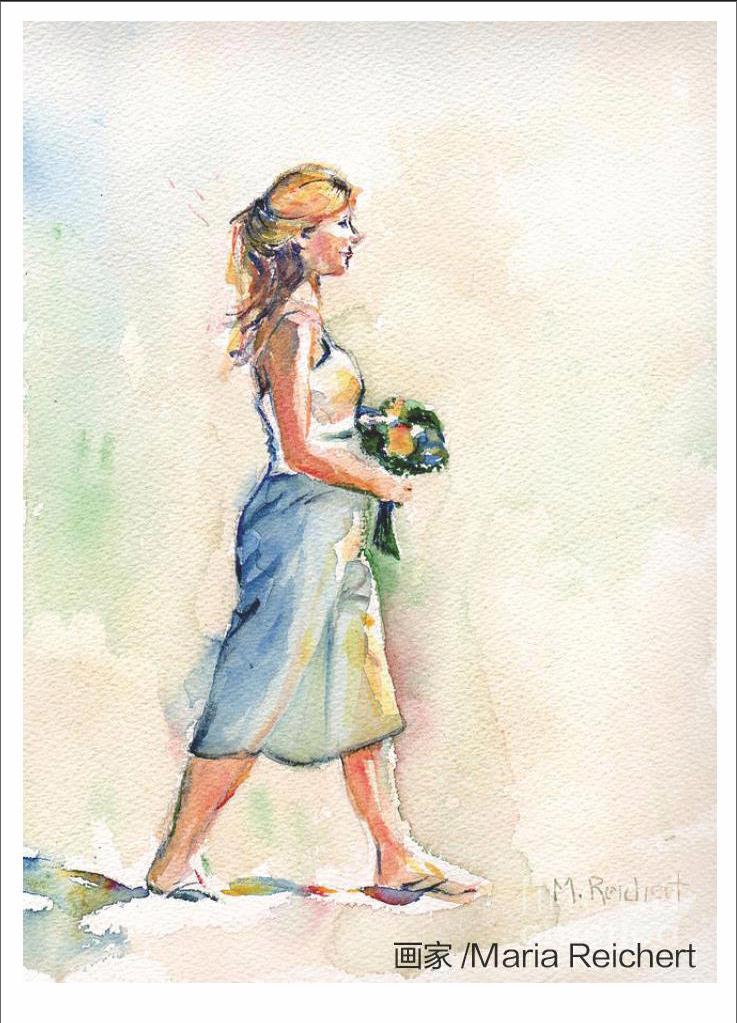
1989年 16岁
栀子花的箴言是:敢把自己的喜恶表达出来
午后的风很暖,若有若无地送来栀子花的芳香。
耳边传来邻居宋阿姨的声音:“囡囡,不要去闻花!”我循声望去,邻家孙女站在一丛绿篱下,绿叶中夹着白花,缕缕芬芳正是从这里荡开。“快回来!栀子花太香招虫子,你凑得那样近,虫子会咬你!”
我莞尔。幸好邻居没说栀子花的坏话!不然我怕是要跟她理论一番——喜欢栀子不足为奇,见不得人贬损它,非要为它说话,这略微偏执的态度里,则藏着我少女时的一个秘密。
那时我念高一,下学期刚开始,我毫无征兆地喜欢上了罗君。他又高又瘦,笑容温和,言谈潇洒,跟那些下了课就在操场上疯跑,上课铃响了才大汗淋漓奔回教室的男生不同,罗君称得上儒雅。
那天在校门口,我和罗君遇上了。一股馥郁的花香飘来,快步掠过我俩的那个女生,束马尾辫的发圈上系了一朵洁白的栀子。
真香啊!我心神一震。但凡香花,多半花小低调,栀子花却不然,花朵大,香气浓郁。每年这个时节,母亲都会为我摘许多半开的栀子,泡在盛了清水的杯中,看它们绽开花瓣,洁白端丽,清香四溢。
“这种花,俗不可耐!”罗君的评语却吓我一跳。我想反驳他,罗君又轻蔑地说:“花和人一样,各有各的气质。栀子花就很乡气,像村姑。你说呢?”
替栀子花辩解的话,被我硬生生咽了回去。谁会承认自己格调低俗呢?我低声附和:“是啊!栀子花,香得太浓烈了。”
那晚放学回家,茶几上清水浸着的一捧栀子,被我挪到了阳台上。母亲问我缘故,我嘟哝道:“香味太刺鼻,闻着头昏。”
太喜欢一个人,脑子就会发昏,会以他的喜恶为标准吧?罗君喜欢用纯蓝墨水,于是用惯蓝黑墨水的我,也爱上了纯蓝字色的明媚、醒目;他喜欢一位诗人的作品,我虽嫌那诗人矫情,还是买来诗集,将每首诗都背得滚瓜烂熟;他说他最喜欢荷兰足球队的“三剑客”,我便迅速变成荷兰队的球迷。
但我和罗君的关系却像这季节撩人的风,扑朔迷离。掩饰自己,投其所好,是我和罗君的相处模式。但我并不快乐。有时我特别欣赏他,有时我听到他在教室后面突然发出的笑声,又感到莫名惊诧——他笑得太张扬,以至于我总怀疑那不是他。
这种疑惑,在一个闷热的午后得到证实。罗君的自行车和初中部一个男生的车擦了一下,我眼看着罗君将车推倒,冲那矮个子少年骂出一句又一句粗话、脏话。少年的道歉声被罗君一连串污秽的脏话给淹没。我瞥一眼路边并无损伤的自行车,再瞟一眼满脸怒容的罗君,骤然间,我也怒了。
说好的气质呢?说好的格调呢?罗君在我心中的形象瞬间倒塌。那个学期结束,罗君选了文科,我俩分别在两幢教学楼上课,渐行渐远。除了被我轻慢过的栀子花,谁也不知我曾痴痴地恋慕过这个男孩。
下一个初夏来临时,我常常带几朵栀子花在书包里。管别人怎么说?我知道自己打心眼里喜欢这清雅美丽的花儿。我还知道,下一次喜欢上谁,怎样也不会随意丢弃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力。能彼此相容,才能交往下去呀!
后来我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提到栀子花时,他这样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我击节赞赏,却想到了罗君,遗憾他没读到这段话,遗憾我没在他面前说出自己的观点。
其实,回想起来,罗君原本就是个普通的男孩,既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完美,也不是我听到他爆粗时那样粗鄙。我为之放弃自我,不敢表达真实想法的,不过是我想象出来的、单薄肤浅的一个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