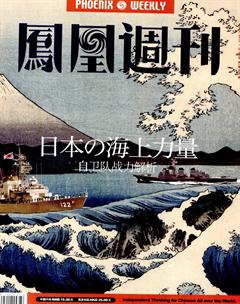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吴海云

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内,杨奎松是极少数得到海内外公认的学者之一。他今年推出的著作合集《革命》,成为中国学术出版界年内的一件盛事。
《革命》精选了杨奎松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的研究,分为《“中间地带”的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四册。其中前两册着重讨论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亦即受到强邻苏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而第三册着重讨论中国近代两大政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大陆近30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每一册,都是原创性研究与分析的典范。
在同行的眼中,其卓越之处,在于他能从实事求是的治学立场出发,但又拥有观察历史的独特角度。在发掘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和俄罗斯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他把中国共产革命放在国际关系的脉络中进行梳理,最终写出超越政党斗争和政治宣传、合乎史料检验原则的著作,呈现了远比一般海内外党史论著更加合乎历史真相的中国革命史叙事。在他看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
走上学术之路,是想要回答“中国怎么了?”
《凤凰周刊》:当我向人提起你的时候,一个很常见的反应就是:“做党史,不容易!”说“不容易”,自然和中国的政治环境有关。因此我首先想问的是,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中共党史”这个研究领域?
杨奎松:这是很偶然的。我学中共党史,纯粹是因为高考时考分不够理想,第二拨录取时被分了过去。毕业后,又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新材料。那段时间也好,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之后新一波的思想解放时期,视野一下子开放很多,资料条件也变得非常有利,这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当然,能坚持这么几十年,是因为这个研究有助于解决我心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凤凰周刊》: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杨奎松:中国究竟怎么了?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让今人难以理解的反复与冲突?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革命总会吞噬自己的儿女?为什么大家都主张革命,却“只许我革命,不许你革命”,动辄还要将别人打成反革命?为什么革命的结果和理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今天中国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又会向哪里去?……这些问题,不止是我一个人在想,在问,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从“文革”后期开始,很多人都在这样想,在这样问。记得“林彪事件”发生后,北京许多干部子弟都在读理论书,西方的、马列的,什么都读。大家都在反思,都在问:共产党到底怎么了?毛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等等。很多疑问是我当年就已经在问,却总也解答不了的。
《凤凰周刊》:许多历史学者在做研究时,喜欢选择一个断代、比如“文革”,或是某个历史人物、比如陈独秀,做那种比较具体的微观研究。而你做的是那种跟着时代走的宏观研究,为什么?
杨奎松:我不喜欢那种—上来就钻到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思想中去的专题式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我们研究的历史通常不过是人类社会的某一部分沿着时间线索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要搞清楚任何一段历史,哪怕是一个人的某—段历史,在弄清楚这段历史的具体史实经过以外,特别需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我们要解 释清楚任何一段历史,哪怕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不把前面的各种影响因子梳理清楚,不了解构成事件各方的具体情况及其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动因,我们可能连具体解读说明这个事件的微观过程都有困难。
你刚刚提到了“文革”。确实,从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学者,包括民间历史爱好者,都对研究“文革”史感兴趣。但是,“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它其实和整个共产党的发展历史相关。如果你把它放在中共党史的整个进程中来看,“文革”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独特的事件,更不是毛泽东在晚年脑子一热突发奇想的东西。
举个例子: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就一度发生过内讧。因为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大家互相揭发、批判、贴小字报,向苏联安全部门检举告密,靠外力介入抓“反革命”等等,当年就整了好多人,后来还因此弄死了一些人。这件事跟毛泽东毫无关系,甚至跟苏联人也没什么关系。事实是,无论有无毛泽东,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一直在发生。像苏维埃时期的中共肃反,除了富田事变和毛泽东有关外,其他根据地的肃反同样死了很多自己人,都不是毛泽东在起作用,当时斯大林也没有搞大清洗,也不是苏联人在那里瞎指挥闹的。这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己其实就有问题,不过是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容易使之发酵而已,并不简单的是哪个人的问题。如果不更深入地去考察、了解、弄清楚历史上的、社会文化上的种种原因,单纯做“文革”史研究,我们就只好围绕着大量微观史实来下功夫,回答不了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那样惨烈的一场自我相残的政治大动乱何以会发生?
《凤凰周刊》:但这样一步步地往下走,很慢啊!
杨奎松:是很慢。我研究了30年,做到今天,才从20世纪初做到1950年代,还没到1960年代。我—直希望能够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但现在看,即使中国的政治进程不会发生严重倒退,我怕我还没做到“文革”也就不在了。
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
《凤凰周刊》:那让我们回到你的研究——“革命”——上。我想请问,在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后,你对革命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杨奎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论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专制统治或腐败政府的造反行动,还是以武装反抗的形式改变本民族屈辱地位的激烈行为,都不是近代中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20世纪的特殊产物。我赞同汉娜·阿伦特对革命的阐释,即“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平等自由意识的觉醒及其由此产生的对压迫平等自由的反抗心理。只要这个问题存在,无论是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还是经济上的平等自由受到过度压迫,革命的爆发都是不可避免的。你没有办法去“告别”过去,也未必阻止得了今后的革命。
《凤凰周刊》:问题在于,革命虽然有暴力、血腥的一面,但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公正、自由与进步。且不说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就说不久前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不仅很少受到谴责,甚至还占据国际政治道德舆论的制高点。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从官方到民间,对革命都有一种“告别”的情绪。在你看来,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杨奎松:首先,我想指出,国人中对革命的“告别”情绪多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生长起来的。至少,在毛时代,“革命”还是许多中国人以为骄傲的一种政治符号:那里面既包含着一种“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自豪感,也包含着对中国可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能够实践平民政治的制度、体制的政治自豪感。上世纪60年代末的几年里,中国这种革命理念甚至一度曾经风靡世界,1968年遍及全球的“红色五月风暴”就是一个证明,如今一些人对于毛时代的怀念多半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感受。
任何历史的发生都有其相对的逻辑和原因,中国革命也是一样。问题在于,如果革命没有一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普世的价值观作为支撑,打破旧制度之后,不能建立起一套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基本制度,这种革命带来的未必是历史的进步,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历史反复。因为,就像马克思讲过的,泼脏水是对的,但把澡盆里的婴儿一起倒掉,就过犹不及了。
具体来说,任何社会文化,都是精英文化在起着主导作用,并规范着社会上一切人的言行举止。旧的制度文化的确有束缚人性,甚至是“吃人”的一面,但也有其总结人类几千年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维系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与道德。革命自有打破旧制度、旧文化的功效。但是,破旧未必能立新。特别是依靠民众造反的底层革命,—旦把旧的制度文化打破,把原有的阶级关系摧毁掉,那种底层的、原始的、人性丑陋野蛮的东西就会抬头。如果这种革命不是顺应历史发展步伐而来,新的法律制度、道德文化没有能够在旧社会中自然生成并在新社会中成长起来,新社会势必会被更落后的制度文化所统治。
《凤凰周刊》:革命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你觉得这和民族性有关么?
杨奎松:是的,不同的民族,其民族性及其国民性很不同。民族中人的性格特点多半是受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乃至于环境影响作用形成的。中国人,或者我们说汉人的性格特征就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条件。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小农经济的社会,自耕农多,小地主多,大地主少,最重要的是农民和地主、和土地,都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这和西欧、日本的古代社会完全不同。欧洲、日本的庄园地主经济因为农民与贵族或地主休戚与共,贵族、地主不仅经济要靠农奴,保卫庄园乃至与外部关系,包括出粮、出丁、出兵、打仗,也都要靠农奴。农民因为依附于贵族或庄园主及其土地,他们的命运也与之息息相关,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庄园地主经济很容易造就出一个内聚力较强的民族来。而中国式小农经济恰恰相反,农民本身没有依附性,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可以自由迁徙,甚至多数农民自有少量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生存,这种经济制度很容易造就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散漫个体。从早年孙中山,—直到今天海外华人中的知识精英,几乎无不感叹国人的这种特性,即一盘散沙,且内斗不止。
所以,中国人特别爱讲“平等”,甚至于要讲“均平”,但出发点却多半是着眼于自私的目的。中国人讲的“平等”和西方概念中的“平等”不完全是一回事儿。西方必须要讲个人主义,是因为不处理解决好“公”与“私”的关系,就会带来整个依附关系很强的经济体的解体;中国小农经济中因为很少个体“私”对“公”依附关系,多半只有“大私”和“小秘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形成人人“只管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中国汉人通常个人生存能力很强,群体意识及团结力却很弱,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凤凰周刊》:一盘散沙、内斗不止;但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啊?为什么奉行利己主义的中国人会那么容易内讧呢?
杨奎松:那就必须要说阶级斗争了。它是中共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也是今天的中国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表面上,阶级斗争是有利于集体主义习惯和理念形成的,对克服国人自私自利的国民性有好处。实际上,中国人自引入阶级斗争以来,从来就不是严格按阶级划线的。并不是你是工人,你就是革命的;你是地主,你就是反动的。几十年来,中共的阶级政策—直在左右摇摆,今天讲斗争,明天讲团结。讲斗争的时候,你是知识分子都可能要被划入另册;讲团结的时候,你是地主也可以变成统一战线的对象。不仅如此,农民中间也是要分阶级的,工人中间同样要查异己分子,要分左、中、右。无论俄国,还是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共产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表现在根本无法简单地依据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占有的有无多少来划阶级,通常要看一个人的政治言论、行为、情感、立场,甚至要看他的社会关系,看他的家庭出身,看他以往的历史,包括读书上学的经历,来认定他的敌我属性。因此,哪怕你昨天还是共产党员,今天就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由此可知,中国的阶级斗争并不能真正推动国人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反而容易更进一步强化国人不顾是非善恶,唯上唯权,从众跟风,落井下石的利己心理。
《凤凰周刊》:它被工具化、扩大化了,最终成为了一种很可怕的意识形态。
杨奎松:是的。因为阶级斗争是敌我斗争,敌我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因此碰到这种问题必须选边站,站对了就万事大吉,站错了就万劫不复,有几个国人还敢独立思考,去判断什么对错是非呢?改革开放了,今天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但是,我们今天政治观念及其处理问题的方法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还是非我即敌,你死我活式的。凡被视为敌对者,不管确否,一定要被看成是坏的、恶的、反动的,在政治上必须仇恨、防范,甚至于打击和消灭之。影响到大部分国人今天在看问题时,也仍旧摆脱不掉非黑即白的极端立场,很少能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更谈不到保持客观态度了。
中国文明进程会走得比理想中慢得多
《凤凰周刊》:我发现,虽然你是个历史学者,但很注重现实的关怀。
杨奎松:那当然,我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因为我关心我们今天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来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是,离开了真实、客观、全面的历史史实的研究与披露,任何讨论和看法都只能是望风扑影的空谈空论。而还原史实,非要历史学家出来做这方面的基础工作不可。
《凤凰周刊》:那作为一个现实的关注者,你在系统地梳理中国革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抱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奎松: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我既是宿命论者,也是乐观主义者。从历史的长程来看,任何国家、民族都在发展中前行。何况,就我们生活的这几十年来看,中国的进步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比如,在1980年代,“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还遭到批判;而今天,主张人权、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主义,固然习惯于敌我思维的国人的接受和认识程度还不一致,但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已经是一种社会共识了。在我看来,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对人、对人的生命和权利是否高度重视与尊重。西方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进步,就是让欧洲人越来越多地认识了人性的价值,从而使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人权平等的意义。中国社会的历史进步,也一定会从对人权平等和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变化上逐渐体现出来。
但是,今天还有几亿农民的中国社会进步得再快,也还是存在太多的一时无法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文化意识方面的进步。人类文明进步从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任何人为地超出历史发展阶段,另创新文明的努力,结果多半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主观上想要超越资本主义,事实上反而可能会跌回到中世纪野蛮文明的水平,甚至于更惨。
举一个例子。人类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人吃人的记述。而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这种情况已越来越难见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原本就慢,但史书记载为复仇食人之事至少在清史稿中已不复见到了,为食补而食人的记载也鲜能见到。想不到,历史发展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因为在农村用仇恨宣传的方法鼓动农民搞你死我活的土改和镇反,底层民众中野蛮落后的文化意识沉滓泛起,各地接连发生了并非因饥饿而食人的丑陋现象。这种情况1960年代末还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在落后地区打击所谓“反革命”敌人的过程中,又一度发生了更严重的人吃人的事件。仅此一点即说明,以中国底层文化之落后,城乡文明差距之大,要让历史文明倒退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真要想让历史文明进步,则难上加难。
《凤凰周刊》:但你还是选择乐观。
杨奎松:当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无非是快与慢的问题。我们背负着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的沉重历史遗产,又经历了俄式阶级革命的历史反复,这注定了我们国家的文明进程势必会走得比理想中慢得多。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马上提升全国民众的文明道德水准,而是要设法改变长期以来支配着我们社会政治文化的敌我观念,以避免人相食的惨剧在中国重演。当然,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这种危险,愿意自觉地帮助推进文明的进步,哪怕大家只是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方面多做一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讲人性、重人权的事情,中国的社会进步也都会加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