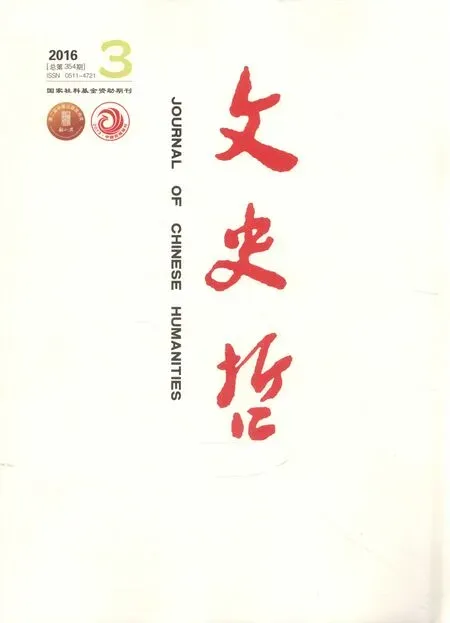“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宇宙无意识
——禅宗及禅悟的本质新解
顾明栋
“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宇宙无意识
——禅宗及禅悟的本质新解
顾明栋
摘要:“禅”这一本来是东亚特有的宗教哲学思想,现今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虽然世界上众多思想家对禅宗和禅悟发表了很多见解,但所持的共识仍然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通过对禅宗从历史、心理、语言、哲学和主体间性的多重视角进行深度探索,可以对禅悟的本质提出一个为前人所未道的见解:禅悟是主体对出生前的身心状态的某种回归,胎儿在母体中感知世界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最原始的无意识,但这种原初的无意识却是宇宙性的,其心理状态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物我为一的出生前感知堪称“宇宙无意识”。人一旦出生就无法回到出生前的身心状态,但通过修炼可以达到向这一身心状态的瞬刻回归。禅悟的本质就是宇宙无意识在特殊情况下的瞬间回归,因此,禅悟不是深刻认识自我和世界的大智慧,而是一种回归生命原初本真的无智慧。
关键词:禅;禅悟;涅槃;佛教;宗教哲学;宇宙无意识
“禅”(Chan/Zen)本来是东亚特有的一个宗教哲学传统,但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禅”早已不是一个囿于东亚的宗教哲学思想,而成了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仅以西方为例,从20世纪之初禅宗在西方开始出现,到196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禅吸引了无数西方人的注意,其中包括当代众多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艺术家①这些人士包括卡尔·荣格(Carl Jung)、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卡伦·霍妮(Karen Horney)、麦斯特尔·艾克哈特(Meister Eckart)、爱伦·沃茨(Allan Watts)、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梅尔福特·斯皮罗(Melford Spiro)等。。如今,许多西方大学开设了禅宗课程,禅甚至成了许多西方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一位学者的观察,在欧洲、大洋洲和北美,成千上万的西方人正在修禅②参见Stephen Batchelor, The Awakening of the West: The Encounter of Buddhism and Western Culture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1994).。尽管如此,世人对禅宗尤其是禅悟持一种神秘主义的共识,即使是铃木大拙也不例外。这位毕生致力于向西方推广禅学的先驱和集大成者,始终坚持认为禅是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的。至于禅悟这一修禅的最终目的,铃木大拙在其众多的演讲和著作中一再重申,是人类理智所不能穿透的③D. T. Suzuki, Living by Zen (London: Rider Books, 1986), 20.。颇为有趣的是,几乎所有对禅宗感兴趣的人都同意铃木大拙的看法,这些思想家包括荣格和弗洛姆,还有西方研究禅宗的著名学者如亨利·杜姆林(Henrich Dumoulin)等*例如荣格就曾声称,禅悟是“一种获得启示的技艺和途径,欧洲人几乎不可能领会。”他赞同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即:“任何企图解释或分析禅为何物,开悟为何物的行为皆是徒劳。”(参见C. G. Jung, Psychology and the East, trans. R. F. 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140, 142);弗洛姆虽然不同意荣格关于西方人无法理解禅的看法,但他完全附和铃木大拙的看法,认为禅悟绝对是一种不可用理性言传的体验(参见Fromm, “Psychoanalysis and Zen Buddhism,” in Zen Buddhism &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119);杜姆林是西方研究禅宗的大家之一,他撰写的禅宗历史是禅宗研究者的必读,但他认为:“像所有神秘的体验一样,禅悟是不可言喻的。”(参见Henrich Dumoulin, Zen Enlightenment: Origins and Meaning, trans. John C. Maraldo [New York: Weartherhill, 1979]).。
笔者认为,上述看法仍然没有超脱视禅宗为不可言喻的东方神秘主义的窠臼,是一种完全否认人类主体之间可以存在相互理解的不可知论。在本文中,笔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并通过对禅宗从历史、心理、语言、哲学和主体间性的多个层面进行深度探索,试图从多元综合的角度对理解禅宗和禅悟的本质提出一些拙见。
一、禅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
谈到禅宗,第一个问题就是:禅宗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解答。铃木大拙一再强调禅既非哲学,也非宗教;要么就是一种普世哲学和宗教。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禅既非哲学也非心理学*参见C.G. Jung, Psychology and the East, 140。。笔者认为,正如儒家和道家既是哲学又是宗教,更是生活方式一样,禅也是在东方哲学、历史心理和生活基础之上创立的一种形式独特的宗教、哲学和生存方式。事实上很难区分禅的哪些部分与宗教有关,哪些部分与哲学思想有关,哪些部分与生活有关,因为禅与这三者都息息相关。禅之所以是哲学是因其主要关注的对象正是基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哲学家所研究的存在主义的课题。如海德格尔所言,人生的特征就是对无家可归的存在的个人感知,伴随着不安全和恐惧(焦虑)的感受。焦虑(Angst)不是害怕某一具体的事物,而是虚无的难以名状的恐惧。禅也可说是宗教,因为就像世界上其他各种宗教一样,它具有填补人们精神空缺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禅和强迫性神经症作一比较,来理解它既是宗教也是哲学。强迫性神经症本质上是人类的存在给主体造成的问题。构成强迫性神经症的问题关系到一个人存在的偶然性。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可用哈姆雷特的名言来表达:“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或换种方式来问就成了:“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存在?”强迫症患者对这类有关存在的问题的反应是狂热地工作或不断重复某种行为仪式,从而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缓解其难以名状的焦虑。他们之所以从事这些强迫性的仪式,是因为认为这有助于逃避罪恶感和焦虑感。这些仪式的形式和内容都使弗洛伊德得以将强迫性神经症的结构和宗教的结构进行颇有说服力的比较*Freud, “Obsessive Action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 ed. Peter Gay, The Freud Reader (New York: Norton, 1989), 435.。其他一些思想家也作过类似的比较研究。笔者并非指禅是能够治愈神经症的宗教,也没有暗示修禅者都是神经症患者,尽管心理学家们通常认为所有人多少都有些神经质。笔者认为,禅所面对的并不是一组症状,而是一个深层心理结构。
一言以蔽之,禅与人类存在的问题有关,笔者愿将此问题描绘成“生命焦虑”(anxiety of life)或“生存焦虑”(anxiety of living)。从佛陀(Buddha)到今天的普通禅宗信徒,所有人修禅的首要动机都是在围绕存在问题而挣扎的过程中寻求真谛。折磨他们的生存焦虑可能呈现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寂寞和恐惧,有的是认为生命无意义的感受,有的是无来由的内疚和悔恨感,有的是内在的不安或外在的威胁,或者是对人生无常和死亡的无奈。在巴利文大藏经(Pali Canon)中有一段描述佛陀看破红尘的著名段落,乔答摩(Gautama)问自己:“我遭受着生老病死、悲伤和污秽,为什么还要寻求同样遭受这些痛苦的东西呢?我遭受着这些痛苦,假设我去寻找摆脱生老病死、悲伤和污秽的束缚的至高无上的涅槃(Nirvana),会怎样呢?”*Bhikkhu Nanamoli, The Life of the Buddha (Kandy, Sri Lanka, 1978), 10.很少有人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乔答摩这个养尊处优、曾经声色犬马的王子竟能体会到生存焦虑。他接触到出生、衰老、病痛和死亡的残酷现实这件事,一直都被解释为是他脱离尘世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这些历史事实只是表面的原因,因为一个人接触到这些残酷的人间事实之后可能会更珍惜生命和生活,或者采用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和“花开堪折直须折”的人生态度纵情声色,用当下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过把瘾再死。佛陀的生存焦虑中还有更深层的含义,有些人可能会把它看作是逃离自我和世界的病态的冲动,英国著名思想家及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将这种欲望描述为灵魂最基本的渴望,是非凡的精神活动和意识状态的主要刺激物*Aldous Huxley,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这一更深的层次是普通哲学或心理学无法看穿的,要认识它,就要从宗教(禅宗佛教的历史)、表现(禅学和禅修)、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弗洛伊德和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心理学)和语言(语言与主体的关系)等综合视角探讨其本质。
二、“欲望”和四圣谛
既然禅是佛教的一种,要理解它,就不能忽视佛教的四圣谛(The Four Noble Truths)与以上笔者提出的几个哲学、心理学的层面的关系。佛陀宣称四圣谛是一种根本的方法,它们能够真正理解造成人类苦难的无可争议和不可否认的真相。四圣谛可被视为包含了佛陀对人性顽疾的诊断,提出了理解人类存在的四个相关联的步骤:1.生命是苦难;2.苦难来自欲望或渴求;3.要解脱苦难,必须消除欲望或渴求;4.要消除欲望或渴望,必须修行八正道(the Eightfold Path)。在四圣谛中,最重要的(或有害的)因素是欲望或渴望,因为它是人类所有痛苦的根源。欲望或渴望通常被认为是对物质利益或感官享受等无休止的追求。然而这种理解既不符合佛陀特有的生命焦虑,也不符合人类一般性的生命焦虑。正如笔者先前所述,乔答摩在弃绝尘世之前拥有一切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他的欲望或渴望并不在于这些实在的东西,一定还有其他的不可名状的对象。在此,我们了解一下法国思想家雅克·拉康关于“欲望”的概念将会有所启发。

拉康还区分了欲望和内驱力(drives)的差异。尽管这两者都属于他者的范畴,欲望是唯一的,而内驱力有很多。换句话说,内驱力就是所谓欲望的单一力的具体表现。欲望的对象只有一个,即小他物(objet petita),由不同的部分驱力中的各种局部对象体现。但小他物不是欲望所趋向的对象,而是欲望产生的原因。欲望不涉及对象,而是涉及缺乏和丧失。欲望是填补缺乏和重获丧失的对象的无意识渴望。

三、欲望的产生和涅槃
根据佛陀的教导,摆脱渴望或欲望的唯一方法是修行通往涅槃的八正道。那么,涅槃就是人免受欲望攻击的最终归宿。因此涅槃与禅悟密切相关。从很多方面来看,悟就是涅槃。但什么是涅槃?即使到现在,它仍是众说纷纭、充满误解的谜一般的概念。下面是《禅门三柱》一书的禅宗词汇中“涅槃”的定义:

这个定义只涉及涅槃的某些方面。涅槃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而且因为这一点佛教常被指责为一种虚无主义、消极悲观和厌世绝望的宗教和哲学。这种指责基于对涅槃词源学的理解。在梵文中,涅槃意为“灭绝”。这个定义长久以来被一些西方学者看作佛教教义消极性的证据。佛教徒和禅宗信徒当然反对这种解释。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对于指责其为虚无主义的看法,他们的辩解是软弱无力、并不很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们迄今还未能向大众确切地展示涅槃到底是什么。在此有必要引用下面一段话:

笔者必须指出,这段引证的辩解并不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涅槃。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只有首先用哲学和心理学的话语对欲望、欲望的起源和欲望的对象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正确地理解涅槃。

在《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一书中,弗洛伊德分析了罗曼·罗兰首先提出的“宗教情感的真正根源”,并受其启发详细探讨了罗兰所说的“海洋般浩渺的感觉”(Oceanic feeling):“他想要把这种感觉称为对‘永恒’的感觉,对无边无际、无拘无束的存在的感受——可以说,如同‘海洋般广阔无垠’。这种感受……完全是主观的事实,不是信条;它不能使人长命百岁,但却是宗教力量的源泉,各个宗教派别和宗教体系都利用它。”*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New York: Norton, 1961), 11.弗洛伊德并不认为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是宗教情感的真正根源,而将其解释为我们现在所称的自体与客体分离的危机。最初婴儿没有察觉自身与哺育自己的母亲的区分,这是我们所谓的婴儿期母婴共生的心理状态。后来,婴儿知道了母亲与自己是独立存在的两个主体。这种自体客体分离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创伤性事件,虽被压抑到无意识中,但绝不会完全消失。成人之后,在某些情形下会重现这种“无边无际的、与宇宙相连的”“海洋般浩渺的感觉”,这事实上曾经是与母体共生的存在。在压抑的状态中,它会带来存在的问题,即生存焦虑。在很多方面,禅的觉悟或启示非常类似于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正如许多修禅者在对他们开悟的体验的描述中所显示的那样。

拉康的欲望理论进一步证实了人类的这种无意识愿望。根据拉康的观点,欲望的对象就是“他者”。这很难实现,因为真正的他者就是子宫这个失去的天堂。胎儿享受子宫里无与伦比的极乐,在那里它的生活应有尽有,无忧无虑。出生带来了创伤,当脐带被割断后,胎儿之乐也随之而去。这也许可以解释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从未感觉过轻松自在……我们不断地被推向存在……我们没有故乡,躁动不安地存在着”*引自Arne Naess, Four Modern Philosophers, trans. Alastai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174.。
子宫里的胎儿漂浮在羊水中,感觉与母体和宇宙合而为一,不受外部刺激的侵扰。这就是罗曼·罗兰所描绘的真正的“海洋般浩渺的感觉”。胎儿无欲无求,万事俱备。子宫是天堂和老家的原始模型。出生意味着永久的无“家/宫”(home/womb)可归。婴儿出生时没有一个是开心微笑的——都是在哭泣。哭泣是不适和失落的标记。海德格尔坚信,哲学严格地说就是乡愁*参见Arne Naess, Four Modern Philosophers, 174.。中国历代诗人也不断描述这种莫名的“千古愁”。笔者试图指出,生命焦虑严格来说是那种乡愁的表达和再现。涅槃就是与“原始失落”达成妥协的最终方式。归根到底,涅槃原则可能就是笔者所称的胎儿之乐,它消灭了无可名状的躁动不安,给人一种回“家/宫”(return to home/womb)的幻觉。正如笔者稍后会说明的,禅力图唤起的最终的精神状态,正是一个人曾在子宫中感受到的没有刺激、痛苦、紧张和欲望的状态。胎儿无欲无求,它享受着无欲、宁静和满足。这种生存状态可能曾经激发道家构想出了“无”(nonbeing)的概念,而佛教则创造了空(void)或涅槃的概念。在梵语中,涅槃意为“熄灭、寂灭,自我内驱力对尘世欲望的完全湮灭”。非常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借用了“涅槃原则”(nirvana principle)来解释他提出的死亡本能:


笔者不揣冒昧地提出,涅槃的心理状态近似于胎儿在母亲子宫里享受的宁静的心理状态。笔者的观点得到了婴儿心理学研究和禅悟者认识的有力支持。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如此描述新生婴儿的自我的状态: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庄子·齐物论》)
可以认为,这段陈述可视为一种直觉性的思考,表现了婴儿最初单一性的存在状态、随后发生的自体客体分离,以及语言的产生。时常出现的回到子宫中的无意识愿望重现在无生(unborn)的欲望中。日本的禅宗大师道元(Dogen)对佛法本性的理解正是如此。他说:“身心与草木并存。佛法(Dharmas)无生,一心亦无生。万物本相,微尘亦本相。故一心为万物,万物为一心,共为一体。”*引自 Shobogenzo. 转引自 Dumoulin, Zen Enlightenment: Origins and Meaning, 104.
盘珪(Bankei)禅师是日本近代的禅宗大师之一,他传授无生之道,并将其认同于悟。铃木大拙在这一点上与他看法一致,但将其解释为一种形而上的道义:
盘珪的无生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不仅包括我们日常经验的感觉领域,还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实在的整体,它充塞十方世界的尽头。……无生是一切创造的可能性的本源。由此就产生了,当我们吃饭时,不是我们而是无生在吃;当我们疲乏睡眠时,不是我们而是无生在睡。*Suzuki, Fromm, and Richard De Martino, Zen Buddhism &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19.
换句话说,无生是先验的存在(Transcendental Presence)。笔者认为,铃木大拙并未能完全领会盘珪的本意。无生的终极所指是没有出生的状态。中国禅宗大师临济义玄对无生作出了恰当的解释:“进入无生法界,他[佛陀]游历四方。进入华严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他看到一切皆空,没有实在。”*转引自Suzuki’s translation in Zen Buddhism & Psychoanalysis, 34.
在很大程度上,原始失落(失去子宫)和次级失落(失去共生)的概念可用来解释涅槃两个相关但迥然不同的方面,笔者将其称为初级涅槃和终极涅槃。初级涅槃可理解为一种“超越时空的绝对存在”。这种涅槃代表了安宁空寂的精神状态,在这里人能超脱所有尘世的苦恼。伴随着禅悟的精神状态与这种情况相似,笔者定义其为胎儿之乐。伴随着禅悟的精神状态类似于胎儿之乐。无论它有多接近胎儿之乐,它终不是胎儿享受的最初的愉悦。它是一个替代品,一个“他者”。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拉康和巴特都同意愉悦能够用语言表达,而极乐不能。“极乐是无法言传的,内隐于语言的”,巴特如是说。他引用拉康的话:“一个人需牢记的是,单就极乐而言,它是禁止言说的,要有也只能在字里行间闪现……”法国学者勒克莱尔(Leclaire)也认为:“无论是谁在说,言说本身就阻止了极乐,或者相应的,任何人极乐的体验,都会造成文字及所有可能的语言在他欢庆之时崩塌与无形。”*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5), 21.巴特谈论的是文学文本,但是他所提到的极乐令人惊讶地接近悟禅者被唤醒时体验到的精神状态。终极涅槃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自我毁灭的本能,它力图回到无生命的无机状态。这种形式的涅槃也可被称为消极涅槃(negative Nirvana),因为它确实表达了看似虚无主义的否定的含义:终极涅槃是他者最终的领域——他者的迷醉,即死亡。但在关键的一点上,笔者与弗洛伊德的看法不同,终极涅槃并不是生命的无机状态,而是出生前的身心存在状态。反驳虚无主义看法只需一个反问即可击中要害:对于佛教徒和修禅的人来说,回归无生命的无机状态有何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死亡驱动或死亡本能并不是要回归如泥土砖石等无机物的存在状态,而是主体对完善圆满的欲望的追求。在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佛教对死亡的用语——圆寂,其字面意是“圆满的沉默”,沉默是前语言的状态,圆满指的是主体欲望的目标——再次与想象中的自体与客体的融合得以实现。主体欲望的目标首先是子宫,然后是母亲,但是这个母亲又常常为在自我和他者互动中产生的替代性的母亲意象所取代,如山川,峡谷,海洋,大地,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
四、禅悟与宇宙意识
修禅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开悟。如铃木大拙所言,“悟是禅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 ),没有悟的禅就不是禅”*D. T. Suzuki, 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4), 95.。问题是:开悟或禅悟是什么?人们很少停下来思考,严格说来,悟或启示其实是用词不当,因为它恰恰表达了相反的含义:禅悟的本质是丧失意识、知识甚至是认知。它用于表示失落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可能在于,它使人们意识到在生命焦虑之外还有一种选择方式。这种领悟就是禅悟。
对于局外人来说,禅悟可能是修禅最神秘莫测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日本的禅的历史中,讲述了很多大彻大悟的修行者,但是很少告诉我们禅悟体验的细节。只有到了现代,那些获得禅悟的禅师们才开始向我们描绘他们的体验。在一段叙述中,一位日本比丘尼记录了她顿悟的体验:“我忘记了自己。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是虚空,这是虚无。天地在一瞬间变得明亮;我的身体突然变轻了。我感觉好像我能飞上九天。一切都是虚无;我双手交叉,敬畏着虚无。”*T. Iizuka ed., Sanzen Taikenshu (Tokyo, 1956), 152.一位在家中实现禅悟的工程师这样描述他的体验:“我自身所系的自我最初变得虚无缥缈。但是[佛经]的文字没有改变:‘诸天上下,独我圆满。’难道禅堂的滑门不圆满吗?草席没有在圆满的脚下舞蹈吗?红枫叶没有在圆满的光下闪烁吗?宇宙被圆满包围;圆满就在宇宙中。”*Ryuko Yasutani ed., Kyudo no tabi: Gendaijin ga katru Zen no sator no taikendan, first series (Tokyo, 1959), 215.另一女性修禅者报告更有启发意义:“我和广阔宇宙融为一体。无论我仰望头顶还是环顾四周,宇宙都是无限广阔,一片浩渺。最终我跌倒在地。”*T. Iizuka ed., Sanzen taikenshu, 115.不必引用更多顿悟的体验。所有这些体验似乎都有共同的特征:主客体间屏障的打破,自我的消失,对现实的直接体验,对虚无的感受,以及融于宇宙的感觉。

理解禅悟的宇宙体验有多种多样的说法。有人曾使用加拿大精神病学家理查德·R·巴克(Richard R. Bucke)的 “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来描绘与禅悟类似的神秘体验*Richard R. Buckle, Cosmic Consciousness: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Mind (New York: Dutton, 1923).。美国著名思想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宗教经验之种种》(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一书中,认识到巴克的宇宙意识和东方神秘主义现象之间有着密切关系。R·C·扎纳(R.C. Zaehner)认为,巴克的宇宙意识相当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弗洛姆也将巴克的“宇宙意识”看成“正是禅宗佛教中开悟的体验”。但笔者认为,他们所说的宇宙意识并不是禅悟的本质,这是因为“宇宙意识”正如其字面意思所示,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可以用清晰的语言来描绘;而禅悟无论是“无念”还是“忘我”,都是一种前语言的无意识,因而无法用清晰的语言来描绘。禅悟的本质接近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海洋般浩渺的感觉”,亦即胎儿在母体内与万物融为一体的身心体验,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由于胎儿在母体中尚未有认知和语言,因而只可能有感觉,但不可能有意识,因此,笔者认为用“宇宙意识”来理解禅悟颇为不妥。禅悟获得的那种体验与其说是“宇宙意识”,倒不如说是“宇宙无意识”(cosmic unconsciousness)显得更为恰当。

道元在就如何开悟提出建议时,说:“修行佛道就是了解自我。了解自我就是忘记自我。忘记自我就是感应诸法,感应诸法就是达到解脱自己和他人的身心的目的。”*Masao Abe and Norman Waddell trans., “Shobogenzo Genjokoan,” in The Eastern Buddhist vol. 5, no.2, 134 ff.在对道元这段话的评论中,杜姆林恰当地指出:
人通过遗忘而学习,也就是说,摆脱自身一切有意识的自我……在这种体验中,所有对立和区分——甚至是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都消失了。在道元的话里,身心意味着整体的人所拥有的肉体和意识。身心的解脱(datsuraku)就是超越自我,在觉悟中得到解脱。*Dumoulin, Zen Enlightenment: Origins and Meaning, 22.
禅悟,恰恰是通过突破不同层面的意识的和理性的思维,成为跨越客体的存在,自己真正体验到了本我。
禅宗六祖惠能关于禅悟的论述更证明笔者的看法。在谈到开悟的时候,他主张“见性成佛”。但是一个人的本性是什么?《六祖坛经》有云:

杜姆林对此评论道:
根据南宗惠能的解释,开悟与终极现实(ultimate reality)的经验有关,因而也与超验和存在(Transcendence and Being)的经验有关。这种形而上的观点与北宗开悟的方法形成对比。在其对手南宗的解释中,北宗力图达到心灵纯洁的状态,即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与此相反,惠能悟禅方法的特点是无宗旨性,新的存在层面的突破,以及对超验的经历。*Dumoulin, Zen Enlightenment: Origins and Meaning, 50.
杜姆林把禅悟视为一种终极现实,但什么是终极现实?杜姆林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因而并没有触及禅悟的本质,笔者认为,禅悟的终极现实就是胎儿体验到的现实。因为惠能的悟的方式触及了人类普遍的返璞归真的无意识愿望,它是对人类存在状态更真实的反映。
在禅宗传统中,惠能的无念(no thoughts)说构成了禅宗快速开悟的方法。美国宗教学者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在比较西方宗教和禅宗的神秘体验时将“无念”称为“终极精神”,与“先验无意识”相同。默顿解释说:“其命运在其赖以生存的存在之光中显露。……它与神之光成为一体,圣约翰(St. John)表示的‘启示每一个世人的光’(John 1: 9)似乎与般若(智慧)(prajna)和惠能的‘无意识’密切相关。”*Thomas Merton, Mystics and Zen Masters (New York: 1967), 25.默顿用基督教语言解释无念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仍然没有摆脱“大智慧”的理念,而禅的无念是建立在佛教涅槃和道教返璞归真的概念之上的。老子的《道德经》第十六章明确提到回归本源的无意识欲望:“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想象界是人类主体与动物心理联系最密切的方面*Lacan, The Seminars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trans. Russell Grigg with not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253.。因此,它代表了人类主体性和自然最近的接触点。然而,人类的想象界是由象征构建的。这意味着人想象中的关系与自然有极大的偏离。象征界是人类建立在规则和结构基础上的、完整的、包括一切的体系。既然规则和结构离开了语言的使用是难以想象的,象征界本质上属于语言的维度。然而,象征界不能等同于语言。因为语言除了象征维度,还包括想象和真实维度。语言的象征维度属于能指,在此维度中,元素不是确定项(positive terms),而是体现区别的关系。语言在这三界中的调和功能对我们理解禅悟有极重要的意义。
禅宗的精髓由十六字概括:“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根据这十六字诀传达的信息,笔者认为,禅悟就是在语言的超语言形式的调解中,从象征界经过想象界进入真实界的一瞬间的通路。在本质上,它是通过忘却语言,忘却意识,甚至是摒弃无意识,从而产生了重获失去的子宫的幻觉和与母体共生的自我存在状态,它是一种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身心感受,但不是许多学者思想家所说的“宇宙意识”。
五、禅悟的本质:“宇宙无意识”

日本道元禅师开悟的故事可以说明问题,他得以实现了大彻大悟,是因为成功地抛弃了有意识的自我。根据记载,一次道元正与其他修禅者一同在中国师傅如净的禅房里打坐。有一位弟子打起了瞌睡,被师傅当头棒喝。师傅训斥道:“抛弃你的身心,打瞌睡不能使你开悟!”一听到这些话,道元立即大彻大悟了。抛弃身心的状态正是自我从意识中完全消失的状态,从而使主体能够进入无拘无束、无牵无挂的存在。
禅悟表明,主体真正的存在是完全脱离有意识的思考,这与笛卡儿就此话题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正相反。铃木大拙认为笛卡儿关于存在的观念与禅宗存在的观念有区别,但是他认为人的智力无法解释这种差异:
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宣称“我思故我在”,但是我们必须把它反过来。存在是第一位的。通过坚定地主张“我在”,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了。我将“我”和“无我”区分开。当我说“我在”时,我已离开我自己。“我在”是出发点,但是我们从“我在”出发,到达了“我思”。这个部分很难解释,因为人的智力无法解决这个问题。*D.T. Suzuki, The Field of Zen, ed. with a Forward by Christmas Humphrey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18.
实际上,这并非像铃木大拙说的那样不可能理解。从思考过程中的主体的自我意识里,笛卡儿发现了其“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基础”:“我思故我在。”但是,禅宗刚好相反。修禅者认为,一个人一旦思考,他就异化于自身了,因为他的思想具有了在自我和客体之间调解的双重身份。因此,笛卡儿观念中的存在是意识和语言构成的存在,而修禅者观念中的存在是语言习得之前,甚至出生之前的原始存在。因为它是一种无中介的存在,它就是修禅者所称的“真正的存在”,完全不同于虚假的、社会的、语言的存在。由禅宗所表示的真正的存在令人吃惊地类似于拉康关于主体的概念:拉康认为,语言不仅先于主体存在并决定了主体思维发展的走向,而且使主体从一出生起就沦为语言的奴隶*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148.。沿着这一思路,拉康挑战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认为情况刚好相反:“我思故我不在”(I think where I am not),并提出截然相反的论断:“我不思故我在” (I am where I do not think)*见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166.。在拉康的观念中,主体不是由思考决定的,恰恰相反,思考导致主体的消失:“我不在故我思,因此,我不思故我在……人们应该说的是:当我是思考的玩偶之时,我是不存在的;我不想到思考之时,我就想到了我的真实身份。”*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166.关于真正的存在,拉康的原理和禅悟的原理能够互相解释。在概念上,拉康的“我不思故我在”与《金刚经》中使惠能开悟的“应无所住,而生此心”核心观念是相通的。在禅修实践上,坐禅最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摆脱思考。只有这样做修禅者才能进入无中介的、非异化的、真正的原初存在。
修炼者获得的这种原初存在不是宇宙意识,而是宇宙无意识。宇宙无意识既不是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也不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更不是巴克的宇宙意识。铃木大拙受盘珪(Bankei)的“无生”启发,曾用宇宙无意识来描绘禅,但他所说的宇宙无意识与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并无多大差别,因为他声言:“只要无意识是本能的,它就没有超出动物和婴儿的无意识,就不可能是成人的无意识。属于成人的无意识是培育出的无意识,它把成人自婴儿时起所经历的一切有意识的体验都包含其中而构成了其全部存在。”*Suzuki, Zen Buddhism & Psychoanalysis, 19.铃木将宇宙无意识看成是一种成人的、培养的无意识,因此是一种后天的无意识,其着眼的方向与笔者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笔者的宇宙无意识探讨的是出生前以及前语言的身心状态,因而是一种出生前的无意识。此外,铃木将禅宗的目的及禅悟看成是与精神分析的目的并无多大差别:“禅宗的目的在于获得探索事物本质的新视角……无论如何定义,禅悟指的是处于二元思维的混乱中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新世界的展现。”*见其由荣格为其作序的书,D. T. Suzuki, An Introduction to Zen Buddhism, 88.而以笔者的“宇宙无意识”概念视之,禅悟不是发现新大陆,而是失去的“乐园”的失而复得。
至此,我们应该归纳一下禅悟的“宇宙无意识”。当胎儿在母体中感知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其感知外在于自身的心理活动是一种最原始的无意识,但这种原初的无意识却是宇宙性的,因为,对胎儿来说,其生存的子宫,就是其感知的世界,也就是整个宇宙。在这个世界中,胎儿的感受就是庄子的名言所描绘的心理状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一言以蔽之,胎儿在出生前感知的物我为一的存在就是“宇宙无意识”。
六、结论:“宇宙无意识”的瞬间回归
1925年,弗洛伊德写过一篇文章,“关于神奇的书写板”,用儿童玩具说明其有关大脑是如何处理记忆的理论。神奇的书写板由两层可以相互分开的塑料薄膜遮盖着一层蜡板组成,人们可以在上面用一支特制的笔书写。如果要消除写下的字,只要揭开遮盖蜡板的塑料薄膜即可。但是,如果揭开上面两层塑料膜,可以看到蜡板上留下曾经书写的痕迹。书写板提供了一种可以不断书写并不断消除字迹的装置,同时,又保留了写过的痕迹。弗洛伊德利用此板的原理说明大脑接受感知的工作原理。大脑通过两个不同的系统记录永久性记忆痕迹:一是接受感觉但是并不保留永久痕迹的有意识感知系统,另一个是保留从外界接受的刺激、使其留有永久痕迹的记忆系统。神奇书写板刚好表现了大脑的这两个功能。这一具有三层结构的玩具刚好与弗氏关于大脑的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层位相模式相对应。诚如弗氏所言,“书写板上字迹的出现与消失”与“感知过程中意识的突然出现和逐渐消失相似”*Freud,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Standard Edition) vol. XIX, 230.。
在《弗洛伊德与书写场景》一文中,达里德认为,弗洛伊德使用神奇书写板并不是借用其作为一种比喻,而是因为感知机制真的是像书写板那样的一种书写机器。作为支撑其观点的一个步骤,他指出,书写板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不是因为书写笔在塑料膜上留下了痕迹,而是因为蜡版接触了塑料膜的反面。这与感知的过程如出一辙。达里德认为,没有人能够直接认识世界,而总是事后追溯性地感知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以前记忆的结果,或者用另一个说法,是以前书写的结果。他认为:“书写在感知甚至没有出现之前就对感知起了辅助作用。”*Freud,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X, 224.达里德的本意是用弗洛伊德的神奇书写板确认书写的重要性,我们欲理解禅悟也可借用神奇书写板的原理。
在其对弗洛伊德的文字所作的评论中,达里德写道:
神奇书写板在其结构中含有康德描绘的三种经验的类比中存在的三种时间模式:永恒、连续、共在。*Derrida, “Freud and the Scene of Writing,”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25.


[责任编辑李梅]
作者简介:顾明栋,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
※ 本文原为英文,承蒙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冯涛老师译出初稿,笔者对译文作了校订和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