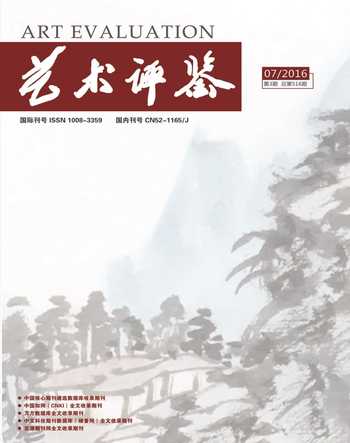从广西壮族传统民歌的曲调结构论其民族心理特征
摘要:广西壮族传统民歌是壮族历来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其民歌本身就蕴涵着壮族人民的心理认知特性。而且经过千百年的沉淀与积累,这种群体心理特质已经完全融入到歌曲之中。这就给我们研究壮族族群的心理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原料。尤其是民歌的曲调结构深刻地反映出壮族人民在事物认识、理解甚至表达方面的心理模式。同时,这些民歌曲调反过来对壮族族群的心理构建又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壮族 民歌 曲调结构
广西壮族的传统民歌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不仅仅是因为其歌曲的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壮族文明与文化的传承。事实上,壮族人民长期没有统一的文字,“人们只能用这种易于掌握和便于记忆的歌唱形式,按一定的惯例和仪轨来进行思维和感情交流,传播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并依此达到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从而构成了壮族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素质及人生观、美学观。”因此,壮族传统民歌本身就蕴涵着壮族人民的心理认知特性。而且经过千百年的沉淀与积累,这种群体心理特质已经完全融入到歌曲之中。这就对我们研究壮族族群的心理特征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原料。
一、壮族传统民歌中的调式调性转换所带来的“物我合一”的循环辩证思维特点
广西壮族传统民歌主要是以单声部旋律为主,部分地区有多声部形式。除部分多声部的民歌在调式调性上有一定的变化外,①其主要的调式调性在一首歌中基本上都是统一的。这样的一种调式调性结构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单线性的思维模式,缺少空间感,尤其是调性的固定,在其民族群体审美心理上体现出比较明显的统一性思维。譬如,在笔者的一些采风过程中,问及某些民歌演唱时是否可以转向另外一种调性(即升高或降低调高)时,被问及的歌手往往都持否定的态度,问其缘由,则是因为“传统没有这样唱过”,或者“其他人没法与你唱和”。而某些带有调式的转变民歌,大多是由于其调式本身较为简单,且没有突破五声调式的框架。
这首五言三句结构的民歌,第一句典型的强调D商音,由一个re、mi、sol、dol的四音列组成;第二句则是由sol、la、dol、re的四音列组成,强调G徵音;第三句则是将前两句的音列组合在一起,形成dol、re、mi、sol、la的五声调式音列,最后落在C宫音上结束。这样的调式变化在广西壮族很多民歌中是属于常见状态。这种通过三音列或四音列的非完整五声调式,进行着在五声调式框架内的“同宫系统转调”,使人在听觉上造成一种调式的模糊感,而这正反映出壮族人民一种“天人合一”的循环论证思维特征。
二、对简单旋法的框架式重复所反映出的重视感性思维的心理特点
广西壮族传统民歌有着重要的社会属性与功能,其最重要的是作为自身民族语言的一种延伸,即通过歌唱来进行思想与情感的沟通、交流与表达。例如传统情歌中壮族男女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观点与想法时,主要就是通过即兴的歌词内容告之对方。这样一来,歌曲本身旋律的发展则并不重要,最终成为便于双方进行交流的一种载体。因此,壮族传统民歌大多旋律较为单一、结构简洁,意在内容变化。
这首歌看似七言六句的结构,但实质就是两个对应句的反复,即一、二小节与三、四小节的对应反复。
这种框架式的重复实质就是一种语言化的情感宣泄。因为对歌词语言的即兴组织,歌曲的重心是在如何组织更合适的语言——歌词,而不是曲调的如何变化发展。这种歌唱中所表达的情绪必然是直接、简单和随兴的。这也正反映出壮族人民对事物感性认知的倾向。“正因为随性的宣泄,感性表述的情绪情感内容往往较为单一,通常是一事一表,即便是有多个意象,也只是连缀式的联曲,或者构成各种循环变化。”反过来,简单的意象往往也造成旋律与结构的简单,而音乐在线性的延绵中则进一步强化了感性思维的映像。
三、壮族民歌中的即兴与装饰是一种对事物认知的肯定性心理反映,同时,也是个人与集体的矛盾表现
前面谈到壮族民歌的语言功能,因为语言是思想与情绪的表达,而思想和情绪是灵动与变化的。这就直接造成演唱者在歌唱过程中的变化与即兴。其中,装饰性表现手段尤为频繁与突出。例如邕宁壮族民歌《大路不走起青苔》。②
事实上,在该乐谱中几乎所有的装饰音都是灵活的,这是壮族传统民歌的一大特点。“即每次演唱同一基本曲调时,歌手们主要根据歌词的内容及形式的不同而即兴地改变曲调。”这些即兴与装饰一方面是其民族思维语言的延伸,另一方面则深刻的体现出壮族族群中审美心理的肯定性原则。
壮族的传统审美也是以生命为基点,强调与宣扬“美”,抑制与排斥“丑”的事物。如“童罔葬母”③的传说故事,“赎谷魂”④、“接花魂”⑤的传统习俗等,都明确表现出对生命肯定的积极与不利于生命主题的避讳。这种“美”与“丑”的标准与传统的伦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传统审美是群体意识的历史积累,这与个性审美必然会产生矛盾。但是,壮族群体意识的强势,使得个体在这种矛盾中往往采取一种“中庸”的妥协方式,即装饰性的变奏。其变化的依据往往来自于语言(歌词),但其内在还是表现出对原有模式进行变化与突破的欲望。
这首作品从曲调结构来看就是一个乐句的变化重复,即通过引子(前六小节)确定了旋律的基调,其骨干音为dol、re、mi三音,la则是主要以装饰性出现。但是,当乐句第二次重复(15-23小节)时,旋律中前面的装饰音la则转换成骨干音。尽管最终还是结束在宫音上,可第二次反复时前半句则无疑强调了la的重要,这种从装饰性的地位转换成骨干支撑性地位,正表现出对之前旋律模式的突破。
尽管装饰性的表现能够产生一定的突破,但这种突破却从另外一面表现出壮族人民对事物认知的一种肯定性心理,即不愿采取否定传统的做法,而是从整体肯定的态度中寻求变化、对比与不同。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其实也反映出一种缺少批判精神的力量,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一种“求同存异”的心理模式。
四、多声音乐的产生——感性向知性的过渡
多声音乐的产生意味着线性化音乐运动有了空间扩展的需要。事实上,这有可能就是即兴装饰发展的结果。当一群人在一起歌唱时,个别人的即兴不尽相同,这对单一性旋律所产生的张力是巨大而明显的。从欧洲奥尔加农(organum)的发展来看,从最初的严格“平行”(paralle organum)到“平行的变体”(modified paralle organum),再到华丽奥尔加农,“基础旋律”(tenor)⑥正是通过“即兴”一步步解放出来。
但是,壮族的多声与欧洲早期的多声音乐还是有着不同,其根本还是其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的差别所导致。欧洲早期多声部音乐是逐步强调声部的独立与内在联系,譬如主题在不同声部的出现以及节奏的交合。而壮族多声民歌中的多声部其主旋律基本上就保持在一个声部(一般是在高声部),其他声部或者做支声体现,或者是作为主旋律的附合与衬托。譬如广西壮族马山的传统三声部代表“三顿欢”,低声部就是采用长音反复衬托主旋律,中声部则附合着高声部主旋律的节奏与音高走向形成其附属。而且,在最后结束时,则往往三个声部都落在主音上形成同音终止。
因此,虽然壮族多声民歌具有了多声现象,但是,这种多声部现象多还是感性思维发展的延伸。“集体性是壮族多声部山歌产生的社会基础。……他们不但集体娱乐和歌唱,而且还集体进行创作,相互选定某一自然现象或某一件事物作为题材,你一句我一句的编奏……在多次的演唱过程中日臻完善,成为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作品。” 相对“奥尔加农”发展过程中的理性思维的成熟与规则的建立,壮族民歌则多是感性的描述,没有归纳性的形成既定的规则。譬如广西马山壮族传统三声部民歌“三顿欢”,每个村都各有不同的旋律(有些基本旋法还有较大差别),声部之间的关系更是差异极大,很难在歌曲中寻找到明确的规律性结构。
但是,在实际音响与演唱方面,壮族的传统多声部民歌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即演唱者必须严格按照其声部的旋律来进行。笔者从马山壮族多声部民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采风时了解到,传统马山三声部民歌的每个声部都有严格的旋律,演唱者必须按照自己声部旋律进行演唱,而不能穿插到其他声部,否则会被当地的歌者所耻笑。因此,广西壮族多声部民歌尽管还没有理性的表述方式,但是其实际表现过程中却有着相对明确的表达规则,它并不是可以随意即兴发挥的。它对各声部的旋律有着明确的规定,譬如某乐句高声部上行时中声部就只能下行,而低声部则需保持稳定,或也下行等等。但是,这种规定还没有发展到理性概念的普遍陈述阶段,而这正是我们现代民歌传承者所应关注与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广西壮族传统民歌的曲调结构深刻地反映出壮族人民在事物认识、理解甚至表达方面的心理模式。从这些民歌曲调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壮族人民重感性、重整体、求变化的心理特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民歌曲调反过来对壮族族群的心理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正是由于壮族人民世世代代都唱着这样的歌曲,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在潜移默化中也必然受其影响,从而形成独特的心理思维模式。总之,民歌来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就必然深刻地蕴含了人民的文化心理构造,只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挖掘与研究罢了。
注释:
①曹昆:《论广西传统多声部民歌声部间调式运用的特点》,《艺术探索》,2009年第12期。
②范西姆:《我的音乐人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③广西壮族流传的故事,即童罔以杀牛代替传统的“解尸吃肉”的习俗。
④由布麽主持法事,意在求得稻谷丰收的习俗。
⑤一种由布麽主持的,专门为新婚夫妇特别是怀孕后的新娘上天领取胎儿灵魂,以保全正常生产而举行的摩教法事仪式。
⑥与圣咏对应的声部旋律,具有相对严谨的规则变化。
参考文献:
[1]廖明君.壮族自然崇拜文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2]于润洋主编.音乐美学文选[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3]林华.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4]樊祖荫.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论稿[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
[5]Pierik,Marie. The Spirit of Gregorian Chant[M].McLaughlin ﹠Reilly, 1939.
[6]范西姆.我的音乐人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