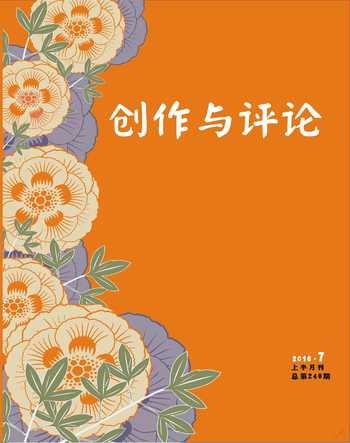疾病的隐喻
郑润良
一
杨少衡的中篇小说《古时候那头驴》(《中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5期选载)塑造了一个悲剧性的基层官员形象:因身有隐疾只好在即将提任之际绝然辞世的某县代县长丁海洋。丁海洋到县里任职前在市委办工作,通晓机关事务,到县里任常务副县长后固然也想有所作为,但在作风强硬的王涛书记面前一直策略性地保持低调。王涛提任本市副市长之后,丁海洋成为县长的热门人选。不料,王涛出事,把本不相干的丁海洋也卷入了一场不虞之祸。仔细考究丁海洋的悲剧,我们会发觉其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内容。
在“官本位”心理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权力通吃”成为许多负面社会现象的内在驱动力的时代,许多官场小说热衷于描述官场的种种“艳情”或“黑幕”,但杨少衡始终把视线聚焦于试图有所作为的基层官员在官场生态环境中所遭遇的两难选择以及由此导致的诸种发展与精神困境。他此前的作品《强降雨》(《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2期选载)中的唐市长向以干练有为著称,但在面对背景深厚的“林公子”承包的市防洪工程中出现的种种质量问题时,既不敢得罪林公子,又担心豆腐渣工程出问题,只好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暂缓另一险要处防洪堤七姑堤的修建工程,导致七姑堤在暴风雨中溃堤,唐市长也因之命丧黄泉。《谁被推倒于地》(《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增刊第1期)中的副县长游胜国在尾矿坝垮塌事件中冲锋在前,为领导分忧,在县里一、二把手因推卸事故责任失和时为他们极力周旋,最终自己却成了替罪羊。《古时候那头驴》中的丁海洋面临的也是一种两难选择。他面对的是要不要被动受贿的问题。王涛是沿山高铁广场工程的总指挥,丁海洋是名义上的副总指挥。丁海洋随同王涛到工地视察,开发商范秋贵往两人的轿车后备箱各放了一个资料袋,说是公司的宣传画册。丁海洋一听感觉有异,但是王涛没有表态,丁海洋只能“按一号意见办”,跟着装聋作哑。待回家后取出来一翻,才发现资料袋里装着钱。这笔钱,对于丁海洋来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把钱上交组织,等于间接告发自己的顶头上司,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放在家里,等于受贿。最后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秘书以“爱心人士”为名,把这笔钱汇给市妇联。王涛出事,丁海洋虽然能够说明自己并未受贿,但也因为隐瞒组织受到牵连,县长一职因此另换人选。丁海洋遭遇的“被动受贿”问题是中国式官场尤为令人忧心的弊病之一。当一个不想受贿的人不能不受贿时,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可见一斑。这也是近年来反腐风暴越刮越烈的现实根由。作为一名直面现实的作家,对社会弊病的深入剖解无疑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杨少衡的官场叙述,正是其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问题意识的直接体现。
二
新时期以来,经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等创作潮流,当代作家在对八十年代以前的二十世纪历史的书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事实上也已经得到了世界文坛的某种认可,比如莫言的获奖。但在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的正面强攻方面,我们的作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包括曾经创作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杰出作品的先锋派主力余华,当他将视线转向当代后创作的作品《兄弟》《第七天》等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声音。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现实及其所包含的中国问题无疑非常复杂,这是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所公认的。作家们面对现实发言的欲望空前高涨,都力图为急剧变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五四以来“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脉流的凸显,无疑是好事。但同时,作家们也面临着新的课题,正如评论家霍俊明所言,“吊诡的是我们看似对离我们更切近的‘现实要更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化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因为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要求的甚至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在政治泛化和权力泛化的时代,“重新发现现实”的当代中国作家们要面对的最严峻课题无疑是当下的官场生态。官场生态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官场叙述因此成为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内在难度的叙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回归、社会转型过程中反腐力度的持续强化等诸多因素促发了官场小说的繁荣。王跃文、张平、阎真、陆天明等作家的名字因为与官场小说的关联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当下的官场叙述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主旋律派”,以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为代表;二是“官场写实派”,以王跃文、阎真、王晓方等为代表。从现状来看,官场小说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热潮后正在陷入日渐同质化、模式化的疲软状态。主旋律派习惯诉诸清官来解决矛盾,显得过于理想化过于简单。官场写实派也出现了批判意向过于显露,故事黑幕化、关系香艳化等不良倾向。这些问题的诞生归根结底是因为作品脱离现实,作家跟风创作。从总体的创作倾向而言,杨少衡也当归入“官场写实派”。但他基于自身丰富的行政任职经验、对官场问题持续多年的关注与深入思考,使其作品在日益同质化、模式化的官场小说中独树一帜。评论家张陵认为对杨少衡来说,不幸的是,他的作品被淹没在现在流行的“官场小说”的汪洋大海之中。更不幸的是,我们的许多评论家,把他的小说归入“官场小说”之中。但如果客观地看待“官场小说”这个概念,反过来也可以说,强烈的问题意识、犀利的批判性思考使他的官场题材小说尤其是中篇官场小说达到了同类题材前所未有的深度,使“官场小说”获得其应有的份量与尊严。
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杨少衡的中篇官场小说独具特色的是“疾病的发现”和“疾病的隐喻”。2010年,杨少衡在《收获》第3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无可逃遁》。小说生动刻画了一个深陷家庭、工作的诸种困境而罹患抑郁症几度试图自杀的官员叶家福的形象,以官员的身心之病隐喻官场生态环境之病,令人耳目一新。有评论者敏感地指出,“《无可逃遁》释放新可能,在‘抑郁症的隐喻下,超越个人经验返观官员生活,批判官场生态,呈现最生动、真实、鲜活的中国式官员经验,贡献新的开掘疆域与审美向度,是对官场文学的发展与丰富。”(廖斌《论杨少衡“党校”小说系列:兼及近期官场小说的限度与可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在我看来,这一论断是极为切当的。《古时候那头驴》中的丁海洋同样病得不轻,他脑颅里长了东西,已被医生判为不治之症。丁海洋所遭遇的被动受贿和因此带来的升职困境无疑令他非常焦虑、纠结。他感觉到命运的不公,却找不到抱怨的对象,只能郁积于心,就像他发病时“头痛欲裂,摔在办公室地上人事不省”,却不能公之于众,因为身体不健康将使他在组织面前失去最后的机会。从叶家福到丁海洋,身体的疾患与他们在官场遭遇的种种本不应有的工作以外的压力直接相关。包括唐市长的牺牲、游胜国的受伤,官员个体在身心上的受创因此成为官场生态问题的隐喻。他的另外一些作品比如《亚健康》《喀纳斯水怪》等都指向了同样的题旨倾向。
三
在我看来,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发生在杨少衡新近的作品《海湾三千亩》(《中篇小说选刊》2014年第5期)中。某市副市长季东升出身寒门,当他发现自己负责接待的女商人欧阳琳身世显赫,可能为自己今后的“东升”带来便利时,他打算牺牲本市人民的部分利益,难得糊涂送出海湾三千亩成就她的“钛合金项目”。但在项目谈判时,欧阳琳的合作者蔡政贪得无厌,连赔青款也不付,完全暴露出“空手套白狼”者的无耻面目。恰在此时,季东升的老父亲为省几块钱自己上老屋“抓漏”,摔成重伤。老父亲的举动让季东升猛然警醒,意识到自己做人做事应该有个底线。最终,凭借季东升几次在欧阳琳发病时出手相救建立的私人情感,“钛合金项目”顺利流产。 这篇小说让我感觉意味深长的是欧阳琳这个形象的塑造。欧阳琳出身显赫,外表光艳照人,却是一个患癫痫、抑郁诸症的病人。她前夫生活腐化终因腐败被抓恐怕也是她病情加重的主要原因。她的“绝症”令我联想到《红楼梦》中诸多贵胄子女的身体上的“先天不足”与外在显赫家世之间的鲜明对比。在这些大家族中,不管是男性的放荡腐化抑或女性的身有“暗疾”,其实都是家族病的某种象征。这部作品中隐疾在身的不是官员,而是背景深厚的“官二代”欧阳琳。欧阳琳并非官员,但其一言一行对于季东升这样的基层官员而言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季东升这样期望有所荫庇又纠结于内心准则的草根官员到身有隐疾、门第深严的欧阳琳,再到戴一顶国际商人帽子、狐假虎威到处招摇撞骗的蔡政,小说展示了更为复杂深广的社会图景。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杨少衡官场小说未来可以继续大力发掘的空间所在。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