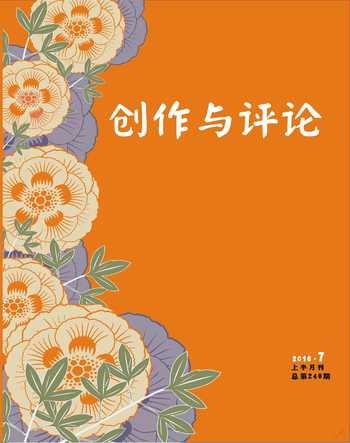微服私访(短篇小说)
杨少衡
直到黄昏将临,下班时间已过,分局办公大楼人去楼空,陆地却未现真容,连咳嗽一声都没有。
我静悄悄坚守于办公室。此刻只能这样,别无选择。起初我曾想给陆地挂个电话,询问领导是不是贵人多忘事?转眼一想不妥,或许人家自有安排,如此胡乱催促,不算以下犯上,至少显得本人耐心不足,涵养不够。
陆地的官不小,常务副市长,本市电视新闻重要演员。我作为本市辖下郊区公安分局的小领导,跟他相距遥远,得翻过若干座顶头大山才可以够着他。但是当年我们之间曾经距离为零,那是小时候,我们为街坊,他家在我家斜对面。我跟陆地同龄,上的不是同一所学校,放学后却常在一起玩,还曾互相打得鼻青脸肿,以此可称发小。长大后彼此各奔前程,距离渐渐拉开,到眼下除了春节发发拜年短信,几乎没有来往。今天下午上班时,我非常意外地接到他一个电话,询问我下午有没有空?拨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吧?我非常确定电话里的声音是他本人,即表示自己没有问题,可以马上动身去市政府晋见领导,听从吩咐。
“备好你的车,在那儿等着。”他交代,“我这里还有点事,完了就过去。”
“到我这里?”
他把电话放了。虽没有正式确认,答案勿庸置疑。
陆地这个罕见电话让我感觉诧异,我断定肯定有些特殊事项。相距如此遥远,让我很难推测该事项有多大特殊性,以多年从警的职业敏感,我觉得其间或许有些棘手,否则领导不会突然想起我来。对我而言,无论该事项暗藏多少麻烦,哪怕如涉枪要案般带有重大险情,我似乎别无选择,只能认账。这就好比有罪犯杀人碎尸,尸块丢在我的地界上,这就是我的事了,不想接这死人也不成。把领导的光临与杀人碎尸扯上,说来似有不敬,其实并无他意,只是职业性毛病。
当天下午我寸步不离办公室。我是区分局副局长,分管刑事,所幸本时段本辖区平静祥和,未发生任何恶性案件,亦无可疑尸块异常丢弃,可容我坐在办公桌后边耐心等待。陆地也显得很有耐心,直到下班时间己过,他人没有到,声音也没有到,像是打完电话之后转眼又把事情忘在脑后。
晚六点半,分局办公楼一片寂静。这时电话终于到了。是他。
“陈水利,”他叫我名字,“在哪里呢?”
“我在办公室。”
“出来吧。”
原来他已经到了,在外边。从他驻守的市政府大楼到本区我这里,正常情况下开车得走二十分钟,考虑到下班高峰期堵车因素,他一定是办完下午的事情之后,下班关了门便直奔我这里而来。
我即离开办公室,出门下楼。楼下门厅除了值班室人员,未见他人。我走到楼后停车处,上车,把车开出车位,缓缓驶出大门。我开的是一部白色警车,为本人的工作配车。我把车开到门外,停在马路边,下车看看,这里人来车往,却也未见领导。
我听到一个关车门的声响:“砰!”转头一看,左侧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后座出来一个人。头一眼我没认出那是个谁,只觉得动作似乎眼熟,待细看一眼,可不就是他吗?陆地,本市重要领导,手里还抓着他的重要公文包。
我得说自己有点愧为刑警,作为一位发小、属下兼办案老手,本应一眼认出该同志,可我还是多用了一眼。说来这也不能全怪本人,主要是黄昏光线显弱,加之陆地的装束有些出位。他穿一件灰色夹克,该夹克我在电视新闻里见过,中规中矩不显异常,但是他的脸部包装与寻常有别:他在鼻子上架了一副墨镜,鼻子下配以一副口罩,二者皆为黑色,刺眼却有效遮挡住其脸部特征,让我这个警察也一眼发懵。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干扰了我的判断:他是从一辆来历不明的轿车上下来的,从车牌看,当是一辆私家车。作为一位够级别的领导,他有自己的公务配车,该车的车型、颜色和车号都是我所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坐那辆总是行驶于众目睽睽中的重要车辆光临本分局。
显然他此番前来需要避人耳目,有如预备作奸犯科。他唯一不回避的似乎只是本警官陈水利的耳目。以此而言,他对本发小信任有加,足以让我受宠若惊。
他走到我的车边,伸出右手跟我握了一下,这当是习惯性动作。握手时我感觉有点意外,他的手掌显凉,很软,似乎气力不支。他没有摘下鼻子上下的遮挡物,看不出他是不是表达出若干笑意。以他出人意料,有如准备去抢银行的装束论,其形象颇具幽默感,如此相见足供彼此一笑。握完手后他看着我,忽然问:“害怕了?”
我连说:“没有没有。”
这是实话,我只是感觉惊奇而已。当警察有时不免要与歹徒狭路相逢,别说戴个墨镜加块口罩,他就是拿条丝袜从头顶套到脖子化装成蒙面大盗,也未必吓得着我。
他没再吭声,自己动手,拉开警车后车门坐进车里。我转身刚想绕过车头去驾驶座,就听“哎呀!”一声,回头一看,领导已经从后车门跳了出来。
“陈水利!那是啥!”他叫。
我一时发懵,立刻冲上前把他推开,打开车门去看。黄昏暗光下,只见一个长条状白色物体弯弯绕绕丢在车后座上。
“不好意思!打惊领导了。”我即道歉。
“打惊”为本地土话,意即害人受惊吓了。丢在车后座上的其实不是什么危险物品,我弯下身子把它从座位上拾起来,拿给陆地过目。
“哈达。就是一条哈达。”我解释。
“怎么有这个?”他追问。
我告诉他,今年本市派出的援藏干部中,本分局也安排了一位,该同志几天前从西藏回来,今天上午到分局联系援藏事务,给在家领导各献了一条哈达。见完面后我即外出办案,哈达暂放在车后座上。
“妈的,”陆地脱口骂了句,“让你陈水利恐惧了一下。”
我知道那是调侃,让他“恐惧”了一下就是吓了他一跳。哈达这种吉祥物件在本地很稀罕,大家通常只在相关电视节目里见过,实际接触不多。我车上这条哈达质地很好,绸类,摸上去细软凉滑,刚才领导一屁股坐进车里,不经意间摸到它,猛一触碰感觉异样,一时好比让什么东西“电”着了,“哎呀”一声就从车门跳了出来。其反应相当敏锐,当然也有些过度。不就是一点异常触觉吗?别说是条哈达,哪怕摸到的是条蛇,似乎也无须“惊”成这样。我记得该领导小时候胆子大得很,爬墙上树没有他不敢的,搞到今天官当大了怎么反倒神经脆弱,连条哈达都能把他“恐惧”一下?
我把哈达抓起来,准备拿开放到后备箱,领导当即制止。
“放着吧。”他说。
现在他不恐惧了,哈达又回到车后排,放在他的座位旁。
我上车,在驾驶位上扣好安全带,发动车子。他在后边忽然开腔发问。
“你的帽子呢?”
他问我的警帽,我管它叫“大头”。我身上穿着警服,这是上班需要。刚才下楼开车时,随手摘下警帽搁在副驾驶位上,因此此刻着装不完整,尚缺“大头”。没想到他注意得如此细致入微。
我说:“在呢。”
他看着我把大头帽戴上。又问:“你的枪呢?带着吗?”
“有的。”
“手铐?”
“车上有。”
“嗯。”
我暗暗吃惊。眼下警察用枪管理很严格,我是因为分管刑事,常需组织并亲自办理涉黑涉毒涉枪要案,因此比较经常带着我那支配枪,我管它叫“火鸡”。我不知道此刻领导要我跟他去干什么?除了一身完整“虎皮”,还要“火鸡”手铐全副抓捕行头。难道是去抓个什么人?弄不好还得使枪弄棒?如果那样可就有问题了。即便该重要领导有令,警察也不可以随便掏枪指住个谁,不可以动不动把人铐起来,使枪弄棒无不有其明确规定,违规滥用肯定吃不了兜着走。领导遮头盖脸前来,似乎并非公务,为此调用警车警力己嫌不妥,如果还要让我为之使枪弄棒,那就不是一般的不合适了。作为一个不小的领导,他自己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一声不吭。此刻情况不明,还需沉住气。或许我只是多虑,人家并不要我掏枪指谁,只是需要一点威慑,有如运钞车武装护卫?今天该领导状况似显脆弱,他要真被什么“恐惧”了一下,身边有人有枪,或能提高安全感。
我把车驶上大路,询问:“领导去哪里?”
“往前,一直走。”他吩咐。
陆地曾在本区任过区长,本区的方位交通于他不是问题,他知道哪个东西在哪个位子,需要时该怎么去,无须如流窜人员行窃般预先踩点。此刻他不明确说出去向,我就不便多嘴,只能听凭指挥。
我们顺着大道往西走,快到路头时,陆地忽然指着右侧一个岔路口说:“右拐。”
我忽有所感,脱口问:“是去那个……”
我并没有说出哪个崎角旮旯,他却知道,一口肯定:“是。”
我觉得还应确认:“青竹岩?”
他没回答,但是答案不言而喻。我驾车右转,不再发问。领导坚持不吭声,彼此心照不宣。
到青竹岩的路长近十公里,都在山间盘旋,路面只有村道标准。我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完,一路上我身后的重要乘客什么动静都没有,一言不发。我从后视镜中可以看到他脸形的轮廓,我总觉得有一团模糊不清的气息罩在其上,难以捉摸,似显不安。
到达目的地时,天己经全暗下来了。我把车停在山坡一个开阔地上,这里没有其他车,四周空无一人。我回头看看陆地。他明白我的意思,即发令:“一起吧。”
我们下了车。我帮他关上后车门时,他突然说:“等等。”
他从后车座抓出那条哈达,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我感觉意外。
从这里到山顶没有车行道路,只有一条陡峭弯曲的石阶路。当晚无月,山间更无路灯,黑暗中那条石阶路显得险峻莫测。我在前头领路,靠手机的手电筒照明。陆地紧随我走,乡野黑暗冷清,他坚持遮头盖脸,防护到底。加之脖上那条哈达,手里那个公文包,领导形象显得格外怪异。还好偏僻山野晚间寂静四下无人,想要引发注意都难。下车时我曾伸出手去,准备帮他拎那个包。据我所见领导干到一定份上,公开露面时通常都空着手,自有人替他拎包。陆地也不例外,电视新闻里总见他走来走去四处比划,没见他拎过包,那东西肯定是在秘书或称“身边工作人员”手里。此刻领导身边没有其他人员,只有警官陈水利,所谓“碰上了躲不过”,看来拎包重任只能落在本人身上。因此我主动伸出手去。不料他摆摆手拒绝,坚持自己担当,于是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一前一后沿石阶向山头攀登,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屋檐的边影在夜空中若隐若现。
这就是青竹岩。青竹岩不是一片竹林,不是一块石头,它是一座寺庙。本地方言多把山间寺庙称为“岩”,这种寺庙通常规模较小,青竹岩亦不例外。以我观察,这座寺庙差不多仅相当于一个乡间中等人家的宅子,只建一座大殿,供着一尊观音,庙侧几间厢房,住着一个和尚。青竹岩香火一般,初一十五有若干香客到此烧香,其他日子比较冷清,出了本区地界,几乎没人知道它,更没有谁知道居然有一位重要人物对它情有独钟,就是此刻趁夜前来的副市长陆地同志。
除了陆地本人,我应当是本内情的极少知情者之一。半个小时前,警车在大路路头右拐时,我之所以忽然脱口说出陆地此行目的,彼此心照不宣,就因为若干年前我们曾经同行,一起到过这里。
我得交代一下我跟这位领导的私人交往。除了发小时一起捉迷藏,时而小拳相向互相打得鼻青眼肿,我俩当年没有更多交情,成人后更是几乎没有来往。几年前情况忽然发生变化:他从市里一个重要部门下来,到我们区担任区长,那以后就开始在本区新闻里崭露头角,让我得以不断亲切回想起小时候追逐打斗的情景。有一天我不惴冒昧,往区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听到他久违而亲切的声音。
“是谁?”他问。
“陆区长,我是陈水利。”
电话里的声音停了会儿:“我在开会。回头联系吧。”
“不好意思。”
我把电话挂了,也决定从此再不联系。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说不定早把当年那小子忘得一干二净。话说回来,少年时那些故事除了提供一点趣味回味外,实没有更多意义,不足以让人想入非非。我不再跟他打电话,也没跟家人之外的任何人提起。
当时我在下边一个派出所任职,当副所长。有一天分局长带着陆地忽然来到本所检查工作,我恰在外头办案,不在所里。领导莅临后即打听:“你们这里有一个陈水利?”于是分局长下令立刻把我召回来,让我们得以重逢。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当着众人的面,也没说些什么,我留下的印象只是一个细节:见面时我向他敬了个礼,他笑,脱口骂一句:“你小子。”而后半开玩笑地抬起手给我还了个礼。毕竟非专业人员,其敬礼姿式非标准,纯属调侃。
几个月后,我给调到另一派出所,提任为所长。作为一个资深副所长,按本人感觉,这个职务早该是我的,但是以往总是与我失之交臂。忽然之间那顶帽子从天上掉了下来,我本人未费吹灰之力。局领导找我谈话时讲了许多场面上合适的话,也十分含蓄地提到一句:“陆区长对你的事非常关心。”
我感觉自己欠了陆地一个大大的人情。我得承认,陆地光临我那派出所之后,我确实曾动过心,想抓住机会,去跟领导反映一下个人职务问题,但是最终打消了该念头。我清楚我与领导间说不上什么交情,好不容易领导一时高兴跑来举手给我行个礼,我要是拿个事找上门,没准又是“我在开会”,自讨没趣,从此不好见面了。我清楚时下求人求事并非只要一张嘴,按照端不上台面却畅行无阻的流俗风气,如果我打算拿当年的鼻青脸肿作为拉关系的敲门砖,通常我需要在敲开门之后立马抛砖引玉,奉上若干干货,例如一份厚礼,或者干脆就是足够的现金,这才有可能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这种事恰好是我干不来的,如果我想干,那无须等到陆地出现。出于这些考虑,我犹豫再三,裹足不前。没想到人家大人有大量,不计较我如此小气一毛不拔,主动给予“非常关心”,让我在吃惊之余十分感激,也自觉很不好意思。
我决定去拜访一下该领导以表感谢。去之前却又很纠结,拿不准要不要带点什么见面礼去上门。时下礼轻未必情义重,送一份厚礼不说成本巨大,万一人家不收,坚决退回,脸就丢大了。纠结半天,结果我什么都没带,两手空空去敲了人家的门。
他见了我就笑:“这也敢来?”
我给他行礼:“给领导敬个礼!”
他大笑:“你小子从小就是铁公鸡。”
那一回相谈甚欢。他告诉我,我给他打电话那回,他确实有事,没法跟我聊。后来我没再打电话,他倒奇怪了,决定侧面了解一下我的情况,结果发现我有点特别,能力与工作业绩都属上乘,缺点就是不会做人,该甜嘴时不张嘴,该出手时不出手,还有些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时下我这样的人难免要吃亏,需要给点帮助,所以他找个机会到我那里检查工作,而后再跟几个关键人物点一点,这就把我的事解决了。
“这些情况你知道就好,外边不说。”
“明白。”
“我知道你可以放心。”他表扬。
原来他已经暗中考察过了。他注意到他来本区后,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我跟他的旧关系。因此他觉得我这个人包括我这张嘴足可信任。
作为一个警察我挺敏感,我感觉他似乎弦外有音。或许他是在暗示什么?或许他不只是认为我这样的人需要给点帮助,同时也认为我这样的人亦有其用处?他不会有些不仅是儿童不宜的事情需要我办,并且要我守口如瓶吧?
后来我很惭愧,因为自己似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其后数年,陆地当他的区长,我当我的警察,工作上时有接触,彼此间一如既往,没有更多的私人交往。数年时间里,陆地曾悄悄交办过几件与警察业务相关的事情,还曾临时抓差让我为他开过几次车。有一次是送他一位朋友去机场,该人物似乎是个大款,面目比较模糊,隐秘客一般,陆地送他不用区政府的车,动到我这里。另有一次他跟人喝酒,完事了让我送他回家。诸如此类,都不算太困难。
有一个星期天上午,他忽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问我知道青竹岩怎么走吗?我告诉他青竹岩在我以前任职的派出所辖区,几年前那一带发生过一起命案,我曾带队去处理过,因此路还熟。
“是个什么案子?”他了解。
那个案子后来查实是一起殉情自杀案。死者一男一女,因感情上的纠缠与失意,在寺庙后边的林子里上吊自杀。
“庙里那个和尚怎么样?”他问。
该和尚我办案时接触过,大约五十来岁,话不多,表面看挺木讷,却又似有城府。听口音是外乡人,像是有点来历。
“是不是会看点病?”
“这个我不清楚。要不要我去了解一下?”
“不需要。”他非常明确。
他要我开车送他到青竹岩去一趟。我遵命立即出动,到区政府大楼接他,直接送到青竹岩山头下。那一次是白天行动,他装束比较寻常,未曾遮头盖脸,但是手中也拎了一个公文包。当时我只跟随他到达山坡上的停车处,下车后他吩咐我呆在车里等他,他要自己进庙去一下。离开时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放在车里,只穿里边一件T衅上山。或许他发现我眼中的疑惑,为此略作解释,自称是“微服私访”。我不知道他是在调侃,或者掩饰。不就是那么一座小庙吗?“微服私访”个啥呀。我当然不好把该想法公然说出,只能一声不响,坐在驾驶室里一动不动,看着领导拎着公文包从那条陡峭的石阶路爬上去,直到消失在那个庙门里。记得那一回他在里边“私访”了很长时间,长得令我压力巨大,产生了若干恐惧。该小庙近侧曾发生过命案,该庙和尚似乎有些来历,万一其中有些隐情,忽然酿出一起意外,把一位在任区长搞出事,我可就说不清了。既然是我开车送他上山,我就在责难逃。出于这一担心,我曾几次打开车门,想爬上台阶进庙看看,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人家领导交代得很明确,只让我呆在一旁等候,没让我去探头探脑。或许人家与本庙和尚有旧,有如与我,他的“微服私访”实为深入基层小庙叙旧,有如当初他光临我那个基层派出所。或许该庙和尚确会看病,专攻某疑难杂症,而他恰苦于该症,需仰仗和尚施以援手。这种事属难言之隐,不容他人窥探。即便不是这样,即便他有一笔欠债要与庙里和尚清算,无论是他把和尚的头按在地板上痛扁,或者相反,他都不愿让别人知晓,我不应当自做多情,没事找事。
还好我终于沉住气了,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终于再次出现在那条石阶路上,手里拎着他的公文包。他回到车上,脸上没有特殊表情,亦未见鼻青脸肿。
上车时他问我:“有水吗?”
我给了他一瓶矿泉水。他咕噜咕噜一口气喝掉了半瓶。
我把他送回区政府大楼。他没做深入解释,下车时只发出一点重要指示:“这件事外边不说。”
我说:“明白。”
我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知道该领导有很多渠道了解信息,有如他曾经打听过我是否暴露与之“发小”关系。但是我也不是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哑巴,我不露行迹地悄悄了解了一点背景情况。我发现青竹岩的历史相当长,始建于明代,曾经香火旺盛,后来于兵荒马乱中衰弱。青竹岩现任和尚的来历挺复杂,似属半路出家,在青竹岩己经呆了十几年,没听说他会治病。按民间说法,青竹岩供的是送子观音,去那里烧香的多为求子,据说还灵。民间亦流传一个偏方,称该小庙的香炉灰能治小儿受惊。这些情况均属皮毛,为了不露形迹我很难深度探访。我断定这座小庙肯定另有内涵,一定有哪个懂行的高人知道,并且点拨给陆地,所以领导才会大驾光临,到此私访。可惜我能耐有限,未得其详。
那次青竹岩之行数月之后,陆地调离本区,提拔到本市另一个区当书记,三年后当了副市长,而后又成为常务副市长。我本人也在渐渐变成资深所长之后,于去年因破获一起要案立功,终于给重用到分局任职。这一重用未曾叨扰领导。这么些年里,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与陆地有关的任何故事,包括那次青竹岩之行。显然陆地知道我像条鱼似的始终一声不吭,所以今天他忽然给我挂来电话,而后遮头盖脸披挂上场,由我护送再次光临小庙。
本次前来情况与上回大有不同,夜间山野,荒僻小庙,林子里没藏着歹徒,也会有野兽,说不定还有若干灵异品种,例如吊死鬼飘摇出没。因此领导难免心有不安,或称恐惧,他需要护卫,全副武装。据说警察制服和手枪阴阳通吃,鬼都退避三舍,其效力与旧时寻常人家贴在门板上的钟馗画像可有一比。
此刻我终于有所放心。我不知道自己的“虎皮”“火鸡”是否真能驱鬼,看起来至少不需要为违规滥用担心。我身后的领导却未能如我一样放松,我感觉他的脚步很轻,似有抖索,不知道是因为上坡累人气力不支,或是让周边暗夜动静不时“恐惧”一下?总之我们走得很慢,黑暗中的台阶路显得格外漫长。
终于走到了庙前。此刻庙门紧闭,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边的灯光。我上前用力打门,里边有人发问:“谁呀?”
“警察。”我说,“请开门,有事情。”
“这,这,怎么会呢?”
“别慌,先开门。”
和尚把门打开。他居然还记得并认出我,张嘴称呼:“是陈所长啊。”他看着我身后的陆地,却未显出认识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陆地的装扮。
“两位领导什么事情?”他问。
陆地即发出指令:“陈水利,你陪师傅说说话。”不待我回应,他就抬脚走向大殿。
我说:“师傅,咱们喝茶。”
小庙大门一侧有一张茶桌,四边各有一条长凳。此刻茶桌上摆着茶具,几只茶杯里都倒了茶水。以此可知在我们两个不速之客到来之前,这位和尚恰关起庙门独自饮茶。陆地把我丢给和尚,独自前去大殿,让我暗暗吃惊,原来他到青竹岩与和尚无关,却与那尊送子观音有涉。我不知道他怎么还会有此类事务需要料理,能够断定的只是护卫进门即可,接下来他要自己行动,不需要我跟到殿前大睁双眼碍手碍脚。
我与和尚在茶桌边坐下。和尚一言不发,烧水沏茶。我也不吭声,一边等茶,一边留意大殿那头的动静,既出于好奇,也存担心。小庙四处有电灯,由附近的山区小水电站供电,电压不稳,灯光较暗。小庙顺山势修建,大殿与我们间隔着几层台阶,中间有一只大香炉遮挡视线,难以把殿上动静一一看准,但是大体也能掌握。
我注意到领导把脖子上的哈达取下来,双手高高捧着,敬献于观音菩萨雕像前的供桌上。哈达献在这种地方当然合适得体,问题是该哈达并不属于他,如果他要用,似应先跟我说一声。或许领导当大了,早已习惯了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已有?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东西了,那包里装的应该都属于他自己,一路紧随始终在他手上。他从里边拿出的却是一支香,不是通常进香用的那种细细香条,是粗大一把有如木棍的特制棒香,属进香奢侈品。估计青竹岩小庙没有此物,领导特地预先做好功课,打点备妥,亲自带上山来。点燃这支棒香似乎比较费劲,感觉他忙活了半天才完成任务,而后他忽然整个儿在供桌前边消失不见,那当是他虔心跪伏下去。
原来他的“微服私访”是来干这个的。考虑到其领导身份,此类私下行动确不宜明目张胆,所以须“微服”,遮头盖脸漏夜潜行以防被人认出造成不利影响。但是问题不仅在他来干什么,还在其为什么,此刻后者才是要害。据我观察,驱动相关人物异常造访寺庙的因素通常是强烈的欲求,或者却是恐惧。我感觉今晚似属后者。
我与本庙和尚喝茶,彼此一声不吭,保持安静,十分默契。殿上了无声息,我感觉那段时间非常之长,长得令人生疑,让我几乎忍不住要起身过去看看,幸而身边和尚见多不怪,始终出神入化,我也就随遇而安。
大殿那边终于有了动静,表明领导并未意外牺牲,只是做一罕见长跪。估计他把膝盖都跪麻了,起身后只能手扶供桌,踉跄移步。我注意他再次打开公文包,从中掏出一迭物品,塞进了供桌侧边的功德箱里。
这当是现钞。看上去数量巨大。
而后他再次消失于供桌前,继续行其功课。
我向和尚低声发问:“你这里送子观音很灵?”
他停了很久才低声回答:“信则灵。”
“除了管生儿子,这尊观音是不是也管一点其他业务?”
他又想了好久,还是那句话:“信则灵。”
“你这里的香炉灰能治小儿惊吓?”
估计万变不离其宗,他还会回答“信则灵。”只是没待他开口,大殿那头即发生异常动静:一阵猛烈咳嗽骤然响起,其声急促而强劲,有如机枪扫射般惊心动魄,剧烈冲击空荡荡静悄悄的小庙。那时顾不得许多,我从茶桌旁站起,大步跨上台阶,冲到殿前。我看见陆地跪伏在地上,手掌扼在喉咙口,浑身抽搐,止不住一阵阵猛咳。
“领导!怎么啦!”
他巨咳,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回答。
我把他从地上扶起,就着殿前灯光看他的脸,只见满脸青紫,表情痛苦万分。我用力拍他的背,帮助他缓过气,而后也不多问,即扶着他离开大殿,走下台阶。和尚己经守候在大门边,他推开大门,向我们合十以示告别。我向他点点头,扶着陆地迈出庙门。陆地听凭摆布,似乎己无力反对。
本次“微服私访”因巨咳和我的介入草草结束。下山那段路走得很艰难。陆地一路咳嗽,说来就来,时紧时松。他浑身无力,腿脚发颤,始终需要我相扶。走到后来他竟无法抬步,我把他背起来,借着初起的一点月光,一步一晃慢慢走完最后一段路。
终于上了警车,我立刻从后备箱翻出一瓶矿泉水,他接过去,咕噜咕噜一口气喝掉半瓶。这时我已发动马达,开车离去。
得益于凉水的作用,领导在车行途中止住咳嗽。我一路快车,一直把他送到我们分局门口。那辆来历不明的私家车还停在老地方,经过漫长得令人生疑的长时间等待,终于等到了把他接走的时候。
陆地一路无话,未曾对本次“微服私访”多加一句注解,最后告别时才有了一点重要指示,还是老话:“今天的事外边不说。”
我说:“明白。”
他已经恢复正常,又回到电视新闻里常见的那种状态。但是临别一握,我感觉那手掌还像上山之前一样无力,甚至微抖。
看来恐惧未解,香炉灰似未显效。
我怀疑陆地在小庙爆发的巨咳与香炉灰有关,尽管我在殿前察看他的脸时,因光线太暗未曾发现那些粉末。虽无直接证据,仅从相关迹象判断,我感觉他是因气管以至肺部呛入香炉灰粉末而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甚至怀疑他不是不慎吸入那些粉末,很可能是抓了一把香炉灰塞进嘴里,不小心让那东西钻进气管,因之巨咳难止。这一推测是否失之荒唐,堂堂领导怎么可能吃那东西?我感觉不能排除。所谓“病急乱投医”,其时哪有什么陆副市长,他就是一个求菩萨相助的香客。如本庙和尚所言,信则灵,或许该领导深信该香炉灰可治小儿惊吓,于成人同样有效。或许上一次他已经试过了,感觉确实有用。
我记得上一次送陆地上青竹岩时,外界正有许多关于他的传闻。陆地当区长时很强势,任内搞大开发,土地和大项目审批权限牢牢掌握在他手中。到了面临提拔之际,市里忽有一个案子发案,牵涉省城一位大开发商,该开发商在本区也开发了几个大项目,有传闻称他与陆地关系非同一般。我怀疑该开发商就是陆地曾命我送过的那个隐秘客。我记得那一阵子传闻汹汹,说得像真的一样,似乎陆地眼看着就要进去了。结果他什么事都没有,终于还给重用,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陆副市长。之所以逢凶化吉,或许人家本来就没事,或许其实有点事,但是最终化解了。谁为他化解呢?难道是青竹岩这尊菩萨,以及本庙的特效香炉灰?或许因为上一次烧香送钱吃灰见效,因此才有了这一次。
无论因为什么,总之他再次光临。较之当年,这一回他显得更其“微服”且更深“私访”。我更清晰地感觉到他心中的恐惧,只是其中缘故更为不详。
那会是什么呢?
两天后,我在本地电视新闻里再次见到陆地,他出席一个会议,正襟危坐于领导人队列里,面无表情,神色专注。我注意到画面下方的新闻标题,神情为之一震:热烈欢迎中央巡视组莅临我市。
领导或许恐惧于此!看来他有点事,可能不小!
恍然大悟之际,我很担忧。假设我的推断成立,陆地可能过不了眼前这一坎。时下腐败官员倒于巡视已经成为一景,如果领导果真不幸中枪,本次“虎皮”“火鸡”护卫下的“微服私访”或将成为问题,到时候我可能会给叫去说清楚。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青竹岩之拜果然有效,领导又是有惊无险,有幸过关,那是祸是福?他可能越发胆大妄为,把更为巨大的国家资财与民脂民膏据为己有,让自己更深地滑入万劫不复。那么我和那尊送子观音都在责难逃,相当于协同犯罪。
我感觉恐惧。
——灵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