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死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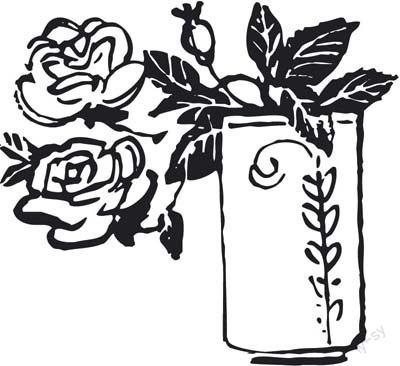
慈禧太后吃鸡蛋
我们一般知道的慈禧太后,是威风八面的老佛爷,坐在金銮殿上,垂帘听政,只字片语就可以决定大清帝国的命运,乃至人民的身家性命。可是,这个拥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徽号的大人物,也曾因为刚愎自用,以至邦国濒临倾圮,本人则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饿了两天的饭,为之痛哭流涕。
慈禧贵为太后之尊,居然饿饭,还痛哭流涕,不是怪事吗?没错,的确是怪事。不过,不能怪别人,要怪只能怪老佛爷鬼迷了心窍,耍弄着义和团打洋人,却被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仓皇“西狩”(其实就是西逃)。当时任怀来知县的吴永,出城迎接圣驾,见到的慈禧是“布衣椎髻”,化装成民妇了。慈禧问他,县城还有多远?答说二十五里;问有没有预备供应?答有。慈禧这才宽了心,说好,有预备就好,随即就放声大哭。
慈禧大哭,有两个原因,都是由于委屈,一是逃亡了两天,才有人来接驾,才有人理她。听听她是怎么对吴永哭诉的:“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 (你)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二是她实在又饿又渴,饥寒交迫,与乞丐也差不多了。吴永是这么记的:“太后哭罢,复自述沿途苦况。谓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慈禧自己述说饥寒交迫,甚至连面子也不顾,直截了当要东西吃:“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且。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
她当然是饿坏了,才会在荒郊野外,向前来迎驾的小知县讨口饭吃。这吴永居然还真准备了一锅小米绿豆粥,不愧是“忠臣”。
慈禧太后平时吃的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极有排场的,吃个鸡蛋算什么?可是在一百年前,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进京,慈禧仓皇西逃时,饿了两天的饭,能得个鸡蛋吃吃,真是胜过“玉食珍馐值万钱”了。
吴永的 《庚子西狩丛谈》 说他在怀来接到公文,言两宫圣驾前来,要准备一桌满汉全席,还要给王公大臣各准备一品锅。怀来小地方,哪能提供如此奢华的宴席?有人建议置之不理,免得供应不如意,自取其祸。吴永想来想去,觉得守土有责,勉强置备了些食物,到城外迎驾,却遭到败兵抢掠。在榆林堡煮了三锅小米绿豆粥,预备给随从作点心,也被抢走了两锅。剩下的一锅粥,本来以为是粗食,不敢献上。慈禧此时已快成了饿殍,反应是:“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复较量美恶?”
于是,慈禧饱餐了一顿小米粥。不过,好像并不满足,得陇又望蜀,因为李莲英出来对吴永说:“尔 (你) 甚好,老佛爷甚欢喜,尔用心伺候,必有好处。”随即就转入正题:“老佛爷甚想食鸡卵,能否取办?”老佛爷喝完小米粥,想吃鸡蛋了。好在她天纵圣明,体谅民情,知道满汉全席是不可能的,退而又退,求其次而又次,提出了吃鸡蛋的要求。
这吴永也的确是个大忠臣,担负起兵荒马乱中找鸡蛋的重任。他在榆林堡中七找八找,居然在一家空肆的厨屉中找到了五个鸡蛋。然后又生火烧水,费了不少劲,煮熟了五只蛋。最后觅得一粗碗,配上一撮食盐,亲手捧交给太监进呈。这一番努力,果然让老佛爷满意。李莲英出来对吴永说:“老佛爷狠 (很) 受用,适所进五卵,竟食其三;余二枚,赏与万岁爷 (光绪),诸人皆不得沾及。此好消息也。”
什么好消息?慈禧一口气吃了三个鸡蛋,吴永勤王护驾有功,可以指日高升了。
情书与公函
章太炎在民国二年结婚,娶汤国黎女士,住在上海。此时民国虽已成立,袁世凯却逐渐暴露其称帝的野心,加以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国是日非,使得章太炎忧心不已。他听信北京共和党人的号召,以为联合各党的力量,仍然可以拯救共和体制,因此结婚才一个多月,便毅然离开新婚妻子,北上救国。然而,这一去便投入虎口,被袁世凯软禁了三年。
刚到北京时,章太炎写家书报平安,情意绵绵,却用极为传统的保守收敛文字,读来十分有趣。全文如下:
汤夫人左右。不佞初十抵津,已有电报,十一早入京,驻化石桥共和党本部。都下戒严,人情汹扰。闻南京又倡独立,翻云覆雨。可谓出人意表。吴淞恐有大战,家居务宜戒慎,一切可询问严先生,庶无惶遽不安之事。夏秋代嬗,天气新凉,宜自珍重。勿多啖瓜果凉水,开窗当风而卧。临纸神驰,思子无极。章炳麟鞠躬。十一日夜。
现代人读起来,是不是会感到别扭?怎么称新婚的妻子“汤夫人”,称自己为“不佞”呢?怎么落款是“章炳麟鞠躬”呢?岂不是冬烘先生写八股家书,以高头讲章代替亲昵的感情吗?林觉民与妻诀别,都写的是“卿卿如晤”,亲爱的感情流露笔端。章太炎怎么板着脸写家书呢?这怎么算情书?何来的情意绵绵?
像国学大师党国元老章炳麟的话吗?
然而,章炳麟的家书虽然没有爱啊爱的字样,却实在是情意绵绵的。你看,他刚到天津,就打电报回家,一到北京就写信。北京戒严,他就怕上海打仗,担心汤国黎的安全。想到季节变凉,就怕她吃生冷闹肚子,又怕她开窗睡会受凉。“临纸神驰,思子无极”,不是刻骨铭心的相思吗?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长达三年之久。一九一五年九月,在北京陪伴他五个月的长女,抑郁自杀,使太炎十分激愤,在九月十日的家书中写道:“仆则生趣久绝,加以悲悼,益不自支持矣。”又说:“两日中连接浙中友人电报问安,盖伪传吾已死也。此虽虚语,然事实亦不相远。吾人生死问题,正如鸡在庖厨,坐待鼎镬,惟静听之而已,必不委曲迁就,自丧名检也。”
负责监视章太炎的京师警察厅大概感到太炎情绪不稳,怕出事,便在十月八日发了一封公函给太炎的夫人汤国黎,劝她以后写信给太炎,“似应格外留意,多用慰藉宽解之词,以开导其郁结”。京师警察厅致函汤夫人,是怕太炎再受刺激,用心可能是好的,但行文措辞粗暴无礼,更语带威胁,完全鹰犬嘴脸。即使最初动机有一丝善意,公函的语气则一扫其伪善的假笑,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信是这样开头的:“径启者。前因章太炎君患神经病症,举动乖张。政府眷念前劳,恐其罹于非祸,交由本厅特别看护,实出于保全太炎之意也。”是说章太炎有神经病,所以软禁起来是为他好,是给予特别优待的保护。
“不意太炎先后径寄女士二电,阅其词意,异常荒谬,自非神经,别有感触,安得有此种电文?”警察厅发现太炎有激愤之语,再次强调他神经病发作了。因此,要汤夫人多用宽解之词来开导太炎,“使彼无所怅触,庶几悖谬言词,不至形于笔墨”。否则,就开始威胁了:“否则扰乱治安,国有常刑。与其维持于后,曷若防范于先?”也就是说,最好劝章太炎少讲话,不要乱讲话,否则就严正典刑。等到出了事再来打点安排就晚了,何若现在就先防范着,别让他胡说八道,“扰乱治安”?
我们很难想象太炎丧女之后的激愤之词,如何会“扰乱治安”,但在京师警察厅眼里,这种感触就有越轨的危险,以至发出公函,威胁汤夫人以后言词要小心,否则……
蔡元培整顿北大
蔡元培新任北大校长时到处延揽人才,请了陈独秀、胡适等人,并大力整顿北大的“腐败”学风。据他本人在一九三四年写的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一文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们平日对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 (兴趣),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蔡元培对这种腐败积习深恶痛绝,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说,就明确指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不但开革中国教员,也开革有后台的外国教员。当时不但有法国教员控告他,还有英国教员动员了英国驻华公使来谈判,并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坚守学术至上原则,对各种社会势力与舆论的明枪暗箭,一概置之不理。
我们赞扬蔡元培。至少要知道,他办大学是有理想的。他捍卫学术的纯洁,独立与自由,义无反顾。
老舍在昆明
抗战期间老舍到云南去游历,大部分时间在昆明,其间也去了大理一趟。在他的笔下,昆明是很有情趣的。他跟音韵学家罗常培一道,住靛花巷,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邻居有历史学家郑天挺、哲学史家汤用彤、爱唱昆曲的统计学家许宝骙,研究英国文学的袁家骅等等,又见到了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好像这条靛花巷是学术文艺中心似的。
老舍说:“靛花巷是条只有两三人家的小巷,又狭又脏。可是巷名的雅美,令人欲忘其陋。”我看原因不是巷名的雅美,是这两三人家,住的全是一时俊彦。就像刘禹锡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不过,老舍说昆明的街名雅美,也有道理。靛花巷附近有玉龙堆、先生坡,都有趣。
老舍随着罗常培下乡,到了北大文科研究所住的龙泉村。这里又聚集了一批俊彦,冯友兰、徐旭生、罗膺中、钱端升、王力、陈梦家、吴晓铃,等等。快到中秋了,徐旭生建议,中秋夜到滇池去泛月,包条小船,带着乐器与酒果,像苏东坡游赤壁那样,畅怀竟夜。商议了半天,毫无结果,因为:“一,船价太贵。二,走到海边,已须步行二十里,天亮归来,又须走二十里,未免太苦。三,找不到会玩乐器的朋友。”充满情趣的计划,没能力实现。滇池月成了镜花水月,不过,情趣还在。
最后,是吴晓铃掌灶,大家帮忙,居然做了一桌可口的菜。在院中赏月,还有人唱昆曲,也是颇有情趣的中秋。
(选自《迷死人的故事》/郑培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