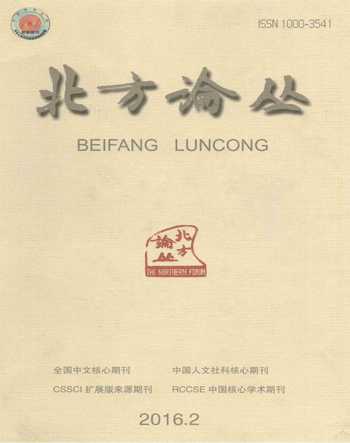祠学璧合:两宋书院祠祀活动及其价值期许
赵国权 周洪宇
[摘要]受政统、道统、学统及庙统等诸因素的影响,具有特殊教化功能的祠宇与两宋时期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融为一体,祠祀便构成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期许书院生徒能够养成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感、树立对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确立“传道济民”的求学目标、达成“希圣希贤“的理想人格以及增进忧国忧民的担当意识,从而与官学中的“庙学合一”相得益彰。
[关键词]两宋书院;文庙;先贤祠;祠学;祠祀活动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100-07
古之庙与祠寓意无别,均是供祀先祖之地,只因所奉祀对象的影响度有别,使得庙的级别往往高于祠。然单就“祠”而言,按创建主体有国祠、宗祠、家祠之分,按所奉祀人物又有先贤祠、乡贤祠、乡宦祠、忠烈祠,以及节孝祠之别。宋之前的祠祀活动在民间已比较普遍,日益成为基层教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开始渗透并影响着民众的心理结构和日常生活。至两宋时期,随着书院这一特殊教育组织形式的兴盛,祠祀活动开始与书院融合,而能与书院珠联璧合的多是先贤祠或乡贤祠,因而书院也往往被称之为“祠学”。元朝宋禧最早提出“祠学”一说,他在《庸庵集》卷十四中称:“国朝于天下祠学,所谓书院者,例设官置师弟子员,与州学等。”此处没有借用“庙学合一”之说,而称“祠学璧合”,如果说庙与官学之合有官方政策性因素的话,那么祠与书院之合则多为书院自主所为,与书院自身传统及教学活动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院本课程”的再生性创造,因此,祠与书院之合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用“璧合”一说更能体现其组合的特质与实效。
一、书院祠祀活动的多元因素助推
祠祀活动非因书院而生,却因书院而彰显,二者之合亦非孤立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兴其盛,无不有其复杂的社会及文化背景。概而言之,两宋书院的祠祀活动至少缘于如下四个方面因素的推动。
(一)维系政统所需
所谓政统,简而言之,即政治传统。自西汉确立以儒治国后,魏晋及隋唐皆秉承儒治传统,且建周、孔之庙供世人奉祀。其间,儒学确实遭受过来自玄学、佛教及道教的冲击,但因儒学自身的包容与吸纳性,不但没有动摇其根基,反在博弈中始终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中心位置。不过,相对于玄学及佛道而言,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显得更为可怕,动荡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业已形成的道德秩序的破坏,无论是魏晋之秋,抑或是五代之乱,无不如此。因而就教化层面而言,带给有宋一代的负面影响颇为触目惊心,在一般民众中“不孝不悌之事,濒见词诉”[1](《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即便是求学士子,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所言,多为“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等。在這种情况下,宋初统治者承袭汉唐崇儒政统,推出“重文”政策,强调尊儒重教,如宋真宗亲撰《玄圣文宣王赞》,称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又撰《崇儒术论》,称儒术为“帝道之纲”等。尤其是入主文庙接受奉祀的,除孔子及孔门弟子外,还有诸多颇具“宣德化”意义的历代乡贤和乡宦。而书院作为一种新兴及新型的教育组织形式,不可能置身度外,只有将自己融入到儒化的背景中去,与时俱进地祠祀先圣先贤,以“指鉴贤愚,发明治乱”,维系政统,如此才能放大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尽管书院的祠祀活动没有纳入国家祀典,但祠祀活动不违背国家祀典:“书院设官,春秋命祀,并遵旧典”[3](《庐峰山长黄禹臣序送别》)。南宋时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明道书院等诸多书院,都置有庙宇专门奉祀孔子,或将孔子与弟子及先贤、先儒、乡贤等一起奉祀。
(二)彰显道统
“道统”一词虽然由朱熹提出,但是,系统阐释道统的却是韩愈,只是韩愈未能完成续传之重任,其使命自然就落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宋朝理学家身上。于是,以二程及朱熹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为证明自己的学说为接续儒学之正宗,纷纷以书院为阵地,积极改造并构建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使儒学道统得以传承和弘扬,同时又要像佛教设寺庙尊崇始祖释迦牟尼、道教设宫观尊崇始祖老子一样,来尊崇自己的道统领袖孔子,最好的一种尊崇方式,就是在自己所办的书院里设庙或祠加以奉祀。朱熹认为,这样做旨在“以明夫道之有统,使天下之学者皆知有所向往而及之,非徒修其墙屋、设其貌像、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为观美而已也”[3](《信州州学大成殿记》)。
尤其是佛、道自东汉末年开始崛起,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具有广泛的政治及社会基础,唐宋之际更是盛行有加,寺庙林立,宫观星布,更以其“法统”对儒家道统发起猛烈的冲击和挑战。相比之下,崇儒之风则有所弱化。对此,两宋的理学家们忧心忡忡,如朱熹在《白鹿书院奏》中称:“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义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阔。”[4](《艺文·白鹿书院奏》)又说:“念庐山一带,老佛之居以百十计,其废坏不无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惧。”[5](《白鹿洞牒》)另据柳诒徵的《江苏书院志初稿》引清乾隆时所修《江南通志》,称茅山书院为“宋天圣中,侯仲遗创建……后为崇禧观所并……咸淳七年更建于顾龙山,今改为圆通庵”。由茅山书院的兴衰,可以看到两宋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博弈,无论是精神层面,抑或是物质层面还是比较激烈的,虽然不可能相互取代另一方,但总要极力抢夺和固守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为捍卫儒家道统,必须树立起自己的精神旗帜,既表明与佛、道有别,又能与佛、道之“法统”或“教统”保持鼎立抗衡之势。也只有这样,既可以接续儒家道统,又能解决“王道之政明,圣人之教行,虽有佛老无自而入”[6](《鹭洲书院记跋》)的现实问题。
(三)标榜学统
如果说道统为源,那么学统为流,有其源则必有其流。自孟子之后儒学便开始分野,两汉时本于经学的师法、家法纷沓而至,且借私学这块阵地通过授徒讲学来延续学统。有此传统,两宋时理学流派亦精彩纷呈,每一流派总有一位开山式人物,如濂学之周敦颐、关学之张载、洛学之二程、湖湘学之张栻、闽学之朱熹、象山学之陆九渊等,而最为门生所尊崇的方式则是在书院设祠奉祀,旨在标榜自己的学术渊源和追求,此所谓“正道脉而定所宗也”。诚如邓洪波所言:“祠堂之上排列的开山祖师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象征书院的精神血脉,表明书院的学术渊源、风尚与特色,是学术传统的具体化。”[7]
(四)延续庙统
中国建庙的历史非常久远,且如同祠宇一样有国庙、宗庙及家庙之别,然此处的庙统专指孔庙与官学的“庙学合一”的传统而言。其实,学校内部祭祀先圣先师的做法,《礼记·文王世子》及《学记》均有论及,无论是学校初成,抑或是开学之际,地方官员及学校师生都要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以示“敬道”。不过,早期文献所载的祭祀活动多与官学的入学教育相结合,祭祀也只是一种仪式,没有用作专门祭祀的场所。而作为专门祭祀之地的孔庙与学校教育的结合,其雏形当自《史记》所载孔子死后第二年就其故居因庙设学开始。如果说这仍属于私学范畴及个案的话,那么就地方上庙学的实质性结合,要追溯到汉初文翁兴学之时,所谓蜀郡“亦学亦庙,有堂有殿……自文翁石室始”[8]。对此,两宋学者均有认同。如吕陶在《府学经史阁落成记》中,谈及蜀学盛事时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9](《府学经史阁落成记》)但作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导向,则实自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诏令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始[10](p.3108)。从此天下学校开始祀周、孔,至唐朝不仅开专祀孔子之先例,而且“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11](《学校考四·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尤其是业已形成的“庙学合一”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及“庙学”这一特殊的文化符号,不仅在中国文化及教育史上掀开了蔚为壮观的一页,还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各级学校的办理。有宋一代更是如此,如当时的四川境内就设有庙学95处,其中成都府路42处,渔川府路34处,利州路11处,夔州府路8处[12]。
既然自私学到官学,再从学校到社会普遍立庙奉祀先圣先师,所谓“宋兴,崇尚文治,吾夫子之祀遍天下”,那么作为书院来说秉承这一教化传统亦在情理之中。因此,有学者称宋代“书院内必崇祀孔子,故每个书院必塑有孔子及十哲的肖像,甚至图画七十二贤一同配飨”[13](pp.233-234)。
二、书院祠祀活动的定制及实施
在多元因素助推下兴起的书院祠祀活动,从宋初的仿效,到南宋时的基本定制,尤其是多有乡贤、乡宦等入主其内接受祠祀,既与地方孔庙及官学大体上保持一致,但又凸显其祠祀的地域性和学派特色。
(一)书院祠祀活动之肇端及演变
书院的祠祀活动到底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定论。可以查阅到的最早的书院祠祀文献记载,当是王禹偁于咸平三年(1000年)所作《潭州岳麓书院记》。文中谈及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时就开始祠祀活动。然而,因继任者不作为,导致“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歌绝音,俎豆无睹”。至咸平二年(999年),新任潭州太守李允则重修书院,“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奠”[14](《潭州岳麓书院记》)。可见,至赵宋开国39年之际,岳麓书院的祠祀活动初具规模,不仅祠祀先师、贤哲,还辟水田为祠祀活动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无独有偶,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诏令重修白鹿洞书院时,亦塑孔子及十大弟子像。应天府民曹诚捐资,就名儒戚同文讲学旧址重建南都学舍后,“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15](《曹诚捐建应天府书院》),并得到宋真宗所赐“应天府书院”额。可以说,在宋初颇有知名度的书院中,均有祠祀活动的存在。虽与官学祠祀有所差别,但在宋初官学沉寂之时书院有此举止,也是对地方官学教化职能的一个重要补充,更使得书院兴办之初,便与官学一样拥有祠祀的话语权。
虽然宋初书院的祠祀活动初具规模,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對传统的“庙学合一”制度多有依赖,且所建书院为数不多,祠祀制度也不尽完善。至南宋时,书院进入快速发展期,书院的祠祀活动也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定制,甚至是“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6](p.158)。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祭祀活动有所扩大,大多要祭祀本学派的先辈或书院的创办者;二是普遍奉祀除先圣先师以外的周敦颐、二程、张载及邵雍等理学大师,旨在推崇学统,提高本学派的地位。元明清时期书院的祠祀活动基本上承袭了两宋时期形成的祠祀传统,且因书院设置普遍而使得受众面更广。
(二)书院与祠宇的时空布局
祠与书院的“璧合”布局是在充分借鉴庙学及地方先贤祠之制基础上而精心设计的,只是因书院财力、各地建筑传统及风格有异,祠之方位与大小也略有不同。
就祠的规模与名称而言,规模较大的书院尤其是得到过皇帝赐额的书院,都有专门奉祀孔子及其弟子的建筑物,称之为文庙或孔庙、礼殿、燕居堂、文宣王庙、先师殿等,这与官学做法相一致。而真正具有书院特色的祠祀先贤、乡贤及乡宦的祠宇则是另置的,名称不一,或直接称之为先贤祠或乡贤祠,或以所祀人物字号命名,或以其学术地位命名,或以所祀人物多寡命名等。如江苏的明道书院设有“程纯公之祠”专祀程颢;江苏的茅山书院设有“先贤祠”,所祀周敦颐等先贤;广东韩山书院设置“泰山北斗祠”,祠祀韩愈;广东的丰湖书院设有“十二先生祠”,祠祀陈尧佐、陈偁、苏轼等。而规模小一点的书院,一般是将孔子及孔门弟子、先贤和乡贤等供奉一处的。如浙江的永嘉书院,中奉孔子,东室祀伊洛诸子,西室祀乡贤等等。
就祠与书院的办理先后顺序而言,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创建书院的同时设祠奉祀,可谓一步到位。如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时,置有先贤祠;淳祐元年(1241年),知州江万里创办白鹭洲书院时,设置文宣王庙祀孔子,又设置“六君子祠”等;二是先有书院,后为追祀某位先贤而添建,如福建的考亭书院,本为朱熹所建,宋理宗宝庆年间,知县刘克庄为祠祀朱熹而在院中创建“集成殿”,以其弟子及门人蔡元定、黄榦、刘爚、真德秀配享;三是先有祠,后为“宣德化”欲发挥其育人的功能,于是设学授徒。如据明洪武抄本《苏州府志》所载,苏州境内的和靖书院,起初为学者尹焞辞去礼部侍郎后,于绍兴年间徙居虎丘西菴读书,嘉定七年(1214年),士人黄士毅请于知府陈芾建祠奉祀尹焞。端平二年(1235年),提举仓司曹幽即其地建为和靖书院。
就祠与书院的空间方位而言,凡与书院相关的祠宇,无论是祭祀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文庙,抑或是祠祀先贤、乡贤及乡宦的建筑,基本上都共处一个院落,只因文庙特有的政治地位及教化价值,在书院中始终处于中心或最佳的位置,其他祠宇在各地书院的布局上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最合乎礼制的布局是左庙祠右书院,或者是前庙祠后书院,如此则存在祠祀区和教学区两个比较明确的活动区域。但因书院地理环境及规模大小不一,具体分布也呈现多元化趋势:
第一,前后为祠祀区,中间为教学区。例如,江苏的明道书院,位于书院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先是“河南伯程纯公之祠”,祠后为会讲之地的春风堂(堂之上为御书阁),堂之后为平日授课修习之处的主敬堂,主敬堂再往后为燕居堂,供奉先圣及十四先贤,呈现“前祠→教学区→后庙”的布局。而江西的象山书院,中为圣殿,后为彝训堂(两边分为居仁、由义、志道、明德四斋),堂后有仰止亭,亭右为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三先生祠,呈现出“前庙→教学区→后祠”的布局。
第二,前为祠祀区后为教学区,如湖北的竹林书院,“有燕居以行舍菜,有公堂以正讲席……前列四祠以彰有德,后峙八斋以肄生员”[17](《公安竹林书院记》);江西的安湖书院,“前为燕居,直以杏坛。旁为堂,左先贤祠。祠后为直舍,缭斋以庑,不侈不隘。”[18](《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
第三,前为教学区后为祠祀区,如:浙江的札溪书院,书院中为讲堂曰“达善”,堂之两翼为东西斋,堂之后为阁,左为“明经阁”,用以藏书,右为“见贤阁”,以祠祀先哲[19](《札溪书院记》);广东的京山书舍,初建时前为书舍斋房,“最后耸以三祠,安定左而昌黎右,瞻仪肃肃,侑我圣师,其规模甚广也,其位置甚严也”[20](《潮州海阳县京山书舍记》)。
第四,庙祠与书院分开设置,各自拥有独立的活动区域,例如,福建的延平书院,先是朱熹的弟子陈宓来守是邦,创书院于南山之下,“以为奉祀、讲学之地”。最初的建筑格局是“祠堂于礼殿之侧”,为“前祠后学”格局,但后来因山洪致使礼殿祠堂被毁,于是,将礼殿重建于百步之外,便有了“礼殿建于右,书院设于左”[21](《艺文志·延平先生书院纪原》)的格局。
(三)书院祠祀人物的考量标准
按《礼记·祭法》所言,凡“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祸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乃虽“圣王之制”,系国家或政治层面的受祀标准,却对学校祠祀活动影响甚大,例如,所立官学必祀孔子及其弟子等。宋朝书院绝大部分属于民办,在选择祠祀对象时,有较大的自由度,除了主祀孔子及其弟子,其他所祀多是与书院、学派及地方治理与教化等相关的人物。至于选择的标准,朱熹弟子黄幹有言,书院立祠设祭,遵行“必本其学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的原则,因而“非其师弗学,非其学弗祭也”[22](《送东川书院陈山长序》)。按各个书院实际祠祀的对象来说,黄幹所言只是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书院的学统标准。元朝学者唐肃在总结以往书院确定祠祀对象时,认为主要依据四个方面的标准:或乡于斯而“有德”,或仕于斯而“有功”,或隐学于斯而“道成于己”,或阐教于斯而“化及于人”[23](《皇冈书院无垢先生祠堂记》)。显然,唐肃的说法更符合当时书院选祀人物的实际情况。近人朱鸿林提出从祀儒者的最高准则是“崇德报功”说,即推崇德行及报答功劳,关键是“报功”,他认为:“从祀儒者之功,就是实践孔子之道之功,发明孔子之道之功”[24](p.2)。
概而言之,两宋书院祠祀人物的考量标准,主要基于个人生前的业绩和名望。依此原则,就具体受祀者来说,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祠祀与书院直接相关的人物,包括书院的创办者、主要修复者、曾经讲学的知名者等,诸如岳麓书院祠祀张栻、朱熹,白鹿洞书院祠祀朱熹,象山书院祠祀陆九渊等,这在两宋书院中最为普遍;二是祠祀与书院学统及学派相关的人物,多是祭祀同一学派的大师,无论是否在此讲学或游学,诸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为大多数书院所祠祀,以此来表明本书院的学术传统;三是本地出生的德高望重的乡贤及乡宦,真德秀就“乡先生何功而祭于此”有过恰如其分的阐释,认为“乡先生之重于乡,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于善也”,其“言行风迹廩廪且存,乡人子弟犹有所观法则,虽历千百祀不可忘也”。因此,南宋多数书院的先贤祠内,均有土生土长的先贤及乡宦受祀,包括汉唐以来的知名学者及致仕官员等;四是在本地为官,政绩突出,为民所拥戴的,虽然没有专设名宦祠(明朝开始有先贤祠与名宦祠之分),却与先贤一起被奉祀在书院祠宇内。例如,江西的白鹭洲书院祠祀江万里,是因江万里仕于本郡,“声名德业,高迈前闻”,“士论胜民俗厚,亦先生之流风系人心,能使其没世不忘如此也”,且足以使后学者“立身、名节一以先生台谏为风采”[25](《白鹭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五是曾在本地隐居读书、治学、授徒的,诸如江西白鹿洞书院祭祀河南的李渤、苏州的和靖书院祠祀河南的尹焞等。另外,能为学子带来学业或仕途好运的也被少数书院纳入祭祀之列,就所查阅到的材料来看,唯有魁星、文昌帝君受祀而已。
(四)书院祠祀活动的场景表达
1祠堂内受祀对象的呈现方式。虽然“古之祭祀,有立尸,有设主,有遗物,有塑像,有绘画”[9]。但对书院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画像,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如岳麓书院“画七十二贤”;广平书院“肖像祠于塾”等;二是塑像,如同其他孔庙一样,在书院多是专为孔子及“十哲”塑像,但也有为先贤塑像的,如据《三阳志》载,淳祐五年(1245年)陈圭重修韩山书院时,“增塑周濂溪、廖槎溪二先生像,并祠其中”等。无论是画像,抑或是塑像,都是书院祠祀活动所必备的,像在圣贤就在,如此才有神圣和庄严之感。
2祠祀礼仪及日期。两宋书院基本上有三项祠祀活动仪式:一是释典礼,依据《礼记》中关于“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古训及当时官学的一些做法,多数书院都要在春秋两季举办祭祀先圣孔子活动,春季为二月初三日,秋季则为八月初九日,所用祭品为猪羊全牲;二是释菜礼或称之为舍菜礼,较释奠礼为轻,所用祭品为“菜”,主祭者头戴皮弁,用芹、藻、菹等一类的蔬菜上祭,表示尊师重道之意。此祭礼一般是在书院开学或开讲时进行的。如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十八日,白鹿洞书院修复后,朱熹便于“鼓箧之始,敢率宾佐合师生恭修释菜之礼,以见于先圣”,朱熹还亲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及《白鹿洞成告先师文》在祠祀仪式上宣读。据明洪武抄本《苏州府志》载,咸淳六年(1270年)三月,学道书院落成后,创办者黄镛“行释菜礼,山长陈宗亮升堂敷绎学道爱人之义,堂讲颜尧焕、胡应青分讲论孟,衣冠森列,听者充然”。一旦书院教学活动进入常态化后,基本上都是在春秋时节进行释菜的;三是谒祠礼,每月朔望(即农历初一和十五)两日,书院师生一起谒祠拜祭先圣先师及先贤等,这也是书院有祠祀活动记载的一贯做法。如南京的明道书院“朔望谒祠,礼仪皆仿白鹿书院”,要求院生必须参加,规定“凡谒祠……若无故而不至者,书于簿。及三,罢职住供”[26](《明道书院》)等。也有的书院每月只祭拜一次,如浙江的永嘉书院,只朔日行祀。
3选任祠祀活动的主持者。一般由地方官、书院山长或监院主持,但规模较大的书院,则专门设置有掌管祠祀活动的“掌祠”一职,且聘请具有一定特殊身份的人担当。如明道书院聘请的是程氏后裔程偃孙、程子材等,濂溪书院由“族之长主祠”,永嘉书院则由“乡先生主祠”等。但无论是地方官员、院方管理者,抑或有特殊身份的人士主持祠祀,都体现出书院对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
(五)书院祠祀活动的费用支持
两宋书院祠宇的建筑,一般是在书院初建或重修、或重建时与院内其他建筑一起建造的,很难将二者的建筑成本区分开来,但在书院文献中,也有部分书院比较明确地规定祠祀活动所需的经费支持,包括修造祠宇,以及常年活动费用等,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官方拨充,或钱或田,以维持正常开支。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迁浙东提举,遣钱三十万,让军守钱闻诗在白鹿洞书院内建殿庑并塑像以祀[27](《白鹿洞书院》);浙江的慈湖书院,据清咸丰刊本《延祐四明志》卷十四载,咸淳八年(1272年),郡守刘黻“拨余姚、定海没入官田以为奠飨之需”等;二是个人捐赠,或钱或粮,多为乡绅或守邦官员所为。例如,南京的明道书院,嘉定年间,真德秀重建程子祠时,自捐金三十万、粟二千斛以助之成[26](《明道书院》);广东的韩山书院,咸淳时郡守林式之“率诸生谒祠下,讲毕,周旋四顾,曰:潮之士知学自文公始,亦犹文公之于蜀,常相之于闽也。邦人奉公香火于今数百年,不忘公之教也……家有弦诵之声,里列衣冠之族,皆公赐也”。于是,捐金40两重修韩愈祠,包括外边的九贤堂等[20](《潮州重修韓山书院记》)。
三、书院祠祀活动的价值期许
书院祠祀同经学讲授一样,都是一种重要的主流文化传播活动,可谓双重路径齐发,相为表里,不可或缺。宋代学者郭若虚所谓画先圣先贤像以祀“与六籍同功”便是此理,而非“文未尽经纬,而书不能形容,然后继之于画也”[28](《叙自古规鉴》)。因此,为“风励士子”,两宋时期的书院人都非常执着地建构祠祀规制,希望通过平日谒祠及定期的祠祀活动,使得在院生徒“于墙于美,如见先哲,昏定晨省,入孝出恭,无非教;受业讲贯,习复计过,无非学”[29](《广平书院记》)。这也使得书院的祠祀活动有着明显的价值期许,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养成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感
对求学士子来说,只有敬畏师道和学业,才能产生自觉和自律,也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而养成君子敬畏感的最佳路径就是在学校内设祠奉祀,以“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景,使人们对先圣先师先贤等供祀对象的崇敬之情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体验”[30]。对此,两宋书院人乐此不疲,所谓“书院设官,春秋命祀,并遵旧典,非徒尊其人,尊其道也”[2](《庐峰山长黄禹臣序送别》)。在祠祀与习经交加的氛围中,使院生的灵魂得以洗礼,并在陶冶中对圣贤、师道及学业产生敬畏之情。如曹彦约《白鹿书院重建书阁记》称,置身书院“莫不求之以诚,守之以敬,揣揣栗栗,如薄冰深渊之在前,而唯恐失步。皇皇汲汲,如驹隙桑荫之易徙,而唯恐失时”[31]。只有对圣贤之道心存敬畏,才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另据袁甫《象山书院记》载,面对当时“世降佑敝,学失师传,梏章句者自谓质实,溺空虚者自诡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的不良态势,设书院及祠祀先圣先贤皆“为明道也”。尤其是“退谒三先生祠,竦然若亲见象山先生燕坐,而与二先生相周旋也……顾瞻之间,已足以生恭敬,消鄙俗,知入德之门。”[32]
(二)树立对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这里所说的文化,包含政治文化、地域文化和书院文化三个层面,三者之间有着以儒学为根基、为主导的渊源关系。但无论哪一层面的文化,要想使学子能产生对文化的认同和自信,除了课堂授受,祠祀活动也有着更为直接、生动且立竿见影的效果。
事实上,书院祠祀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符号,所谓“祭祀的对象,自从被推上受人顶礼膜拜的圣坛之后,无论是圣人还是贤者,都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血肉之躯,而是道德的载体,道统的象征和文化的符号”[33]。它所承载的,一是政治文化,其核心是儒家文化。自两汉开尊儒之先,动荡的魏晋南北朝也始终崇儒,隋唐及两宋无不如此,从官学到私学无不授受儒经,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民间,无不祭拜先圣先师或先贤,即便是所祀为忠烈之士,也是儒家忠孝仁勇及家国同构意志的体现。而书院祠祀作为举国祠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担当者儒学传递及传播的历史使命。那么要使学子对这一政治文化有一种高度的认同和自信,就有必要充分发挥祠祀活动这一文化载体的教化作用。故有学者称:“信仰的产生,往往需要一定的场合、氛围、情景,而书院祭祀活动正是通过种种方式,制造一定的情境、氛围,引发士人对儒学的信仰。”[30]
二是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中国古代的地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除了物质层面文化以外,还有学术及名人文化。继春秋战国之后,最为后人津津乐道,或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两宋时期地域性学派和学派领袖,诸如濂学之周敦颐、洛学之二程、关学之张载、闽学之朱熹、象山学之陆九渊、婺学之吕祖谦等,并且无不在本地书院得以祠祀。诚如袁甫在象山书院建成之际,祠祀陆九渊时所言:“先生之精神,其在何所耶?在金溪之故庐……是可以宅先生之精神,振先生之木铎。”[32](《初建书院告陆象山先生文》)可见,陆九渊生于斯,长于斯,其学术思想诞生于斯,只有在此地设书院祠祀,对其学术思想的光大才更有价值。当然,书院祠祀所彰显的不只是这些学派及学派领袖,还祠祀本地的乡贤及忠烈之士。
涉及书院文化的认同与自信,各地书院文化既是地域文化的一种呈现方式,又具有自身特色,不完全是地域性文化的载体,而是属于书院群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所祠祀的对象不全是本地出生的先儒先贤和名宦,所推崇的学术文化亦有程朱创立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之别,基本上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而以各自书院的学术传统或所属的学术流派加以祠祀,诚如黄榦所言:“必本其学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师弗学,非其学弗祭也”[22](《送东川书院陈山长序》)。例如,江西乐平的慈湖书院,为祠祀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而建,王应麟《慈湖书院记》称,书院“礼殿崇崇,祠宇奕奕……居先生之居,学先生之学,则何以哉?由事亲从兄,而尽性至命;由洒扫应对,而精义入神;由内省不疚,而极无声无臭之妙,下学上达,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庶几识其大者……得心学之传,必将有人焉”[29](《慈湖书院记》)。杨简秉承陆九渊的学术衣钵,自然得心学之传,而要将心学继续接续下去,祠祀杨简无疑是明智之举,皆在强化对学派的认同。尤其是书院通过祭祀活动,更让生徒明白本门学派的学术源流和精神血脉,“自觉地把自己和其他门派区别开来,从内心深处产生对本门派的归附”[33]。
(三)达成“传道济民”的求学目标
在科举的冲击波日益弥散于校园之际,有相当一部分学子会因功名利禄而迷失方向,求学之的多在“为决科利禄计”,这种现象为朱熹、吴澄诸多学者所诟病。如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指责太学“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徳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冐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3]等。官学如此,书院也深受影响。为引导生徒树立正确的求学目标,两宋书院人一方面是理论说教,指示人生或求学之方向,如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明确指出:“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34]包恢《盱山书院记》称:“夫以书院名是,所主在读书也……况读书非为应举也,若其所读者徒以为取科第之媒,钓利禄之饵,则岂为贞志者哉。”[35]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所祠祀人物的事迹加以引领,朱熹在谈及祭祀的作用时就说道,“惟国家稽古命祀,而祀先圣先师于学宫,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使天下之学者皆知有所向往而及之”[3]等。
(四)追逐“希圣希贤“的道德理想
书院祠祀活动同样是对生徒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旨在教会生徒学会做像圣贤那样的“全德”之人,所谓“学也者,因圣賢之书,求圣贤之心,而为圣贤归者也……读圣贤之书,求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也”[36](《青峰书院记》)。其实,做圣贤亦非遥不可及,鉴于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因而要求也不一样,但总之要做到“在家庭则孝友,处乡党则信睦,莅官则坚公廉之操,立朝则崇正直之风”[32](《番江书堂记》)。
为使生徒能够立志学为圣贤,为他们树立一个圣贤的“标杆”显得尤为必要,这是因为“推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34](《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逝去且被社会认可的历史人物自然就被具象化。于是,在书院所祠祀的人物中,既有至高无上的先圣孔子,有先哲孔门弟子,有先贤周、程、张、朱等硕儒,有德高望重、教化一方的乡贤,有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名宦,又有保家卫国的忠烈之士等。可知,“标杆”是具有层次性和针对性的,书院依据学生的志趣,各加劝诫规勉,令其见贤思齐,使其在圣贤事迹的感召下成就不同层次的事业,并最终使自己也成为被文庙或书院供奉祠祀的圣贤。诸如位于广东的韩山书院主祀韩愈,又进祀乡贤赵德(曾协助韩愈推广教化)。后来,文天祥曾以赵德为例,召集兴国县安湖书院学生劝导说:“昔有文公,设教于潮。潮人赵德,以士见招。维文与行,倡于齐民。其则不远,德哉若人。”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惟师帅不鄙夷之,俾获有闻,虽不敏,敢不受教!”[18](《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可见,只有在如此神圣且诗意般的环境中受教,才能成就“抱坚白如玉雪,抗青紫于浮云”之美德。
(五)增进忧国忧民的担当意识
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与礼制一体的祠庙建筑自然成为国家营构的主要建筑,其间各层次的祠祀活动都具有凝聚人心、增强国家认同及培育民族精神的强大作用。尤其是在两宋之际,内忧外患交加,深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强调求学必在“益于人之家国”,如“道不通行于万世,不足为道。学者无益于人之家国,不足以为学”[32](《重修白鹿书院记》)。马祖光《辑〈程子〉序》则称:“登程子之堂,则必读程子之书,读其书然后能明其道而存于心、履于身,推之国家天下,则天地万物皆于我乎赖。”[26]为激励生徒建功立业,有的书院还祠祀诸葛亮等先贤忠烈。如福建的卧龙书院,“刻诸葛忠武侯遗像于其间,图八阵奇正之势,书‘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语于左右壁,而朝夕瞻敬,以寓愿学思齐之意,盖不徒存后迹侈观也”。之所以祠祀诸葛亮,是因为他“躬耕草野,无意闻达,身都将相,所欲不存,视天下无一足以动其心者,其操持甚固也……忠武侯之风烈炳然与日月争光,固其志略所就……抗志明义,不挠不折”[37](《汀州卧龙书院记》)。
当然,正因为受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书院祠祀活动在释放诸多正能量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诸如为强化学派认同而“非其学弗祭”,不仅与儒家的包容性不相称,且与书院教育活动的开放性亦不相称,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书院之间的交流与资源共享。书院祠祀魁星、文昌帝君等无可厚非,也可以说是学子的一种心理需求。但为功利性所驱使,使得本为生徒祈福的活动充满神秘甚至是迷信色彩等。
总之,祠祀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两宋书院的祠祀活动又是祠祀文化中的一朵奇芭,突破了自古“祭不越望”的限制,通过跨地域、跨学派、跨阶层的祠祀活动,彰显书院的学术宗旨和追求,同时也成为当时守望一方历史文脉的重要象征,更对求学士子及周围民众价值观的形成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祠宇的建造及祠祀活动中,地方士绅或乡绅积极建言献策、捐钱赠田,其助推作用不可小觑。且业已形成的祭祀活动传统无论是对后世书院抑或是对韩、日等周边国家的书院,都产生较大影响。而对于当下,如何将弘扬两宋书院的祠祀活动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对接,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有些书院已将开笔礼、成人礼与祠祀活动连为一体,不失为一种再生性创造。
[参 考 文 献]
[1]徐元杰.梅野集:卷十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蒋易.鹤田蒋先生文集:卷上[M].元至正刻本.
[3]朱熹.晦庵集:卷八十、卷六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尹继善,等.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五[M].清乾隆元年刻本.
[5]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二[M].顺德堂藏版.
[6]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邓洪波.祭祀:书院产生的最重要原因[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4-19(B1).
[8]舒大刚,任利荣.“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9]吕陶.净德集:卷十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马端临.文献统考:卷四十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周原孙.宋代四川孔庙的设置及兴盛原因[J].四川文物,1990(5).
[13]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4]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七[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徐度.却扫篇:卷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17]李曾伯.可斋续稿前: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三[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9]程珌.洺水集:卷七[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林希逸.竹溪鬳斋十稿续集:卷十、卷十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李天同.南平县志:卷十七[M].清嘉庆十五年刻本.
[22]黄幹.黄文献公文集:卷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唐肃.丹崖集: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朱鸿林.孔庙从祀与乡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5]刘铎.白鹭洲书院志:卷五[M].清同治十年刊本.
[26]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赵之谦,等.江西通志:卷八十二[M].清光绪七年刊本.
[28]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王应麟.深宁先生文钞:卷一、卷十四[M]四明丛书约园刊本.
[30]肖永明,等.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1]曹彦约.昌谷集:卷十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袁甫.蒙斋集:卷十三、卷十七、卷十四[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徐梓.书院祭祀的意义[J].寻根,2006(2).
[34]张栻.南轩集:卷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包恢.敝帚稿略:卷三[M].文渊閣四库全书本.
[36]欧阳守道.巽斋集:卷十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陈元晋.渔墅类稿: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赵国权:河南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八街文庙棂星门
——巍山文庙
——楚雄文庙
——宾川州城文庙大成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