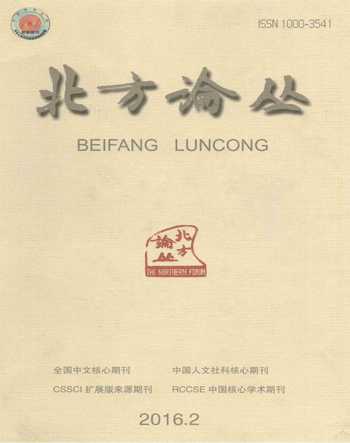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王书艳
[摘要]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唐代;文人园林;政治;仕隐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89-05
Abstract: The literati garden of the Tang Dynasty,which had the independence of private spac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pace.The ruling class relies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intervention on the literati gardens by the political rights in the form of reward and confiscation,meanwhile,the scholar plays political function of literati garden in the Jin Shi and seclusion.Literati garden contains political culture implication in the political control of rule layer and identity politics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ideal that scholars express.This kind of political interpretati reveals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literati garden that has long been obscured,which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the research of garde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ang Dynasty.
Key words:Tang Dynasty;literati garden;Politics;Shi Yin
學界关于文人园林的研究多关注园林的文人性格与隐逸情志,认为园林是文人坚守自我人格独立的堡垒。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文人园林既有“私”的独立性,又在公众世界中受到政治社会的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而非“绝对独立”的空间领域,与政治密切相关。唐代的私家园林亦脱离不了传统政治的统摄,就当权者而言,园林可以作为表现政治权利的有效手段,服务于政治;就官僚士人而言,他们一方面将园林作为进仕之阶、身份地位的象征,以直接的积极方式对政治权威进行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园林作为政治退隐之地,以间接委婉的方式进行政治理想表达。本文拟从政治层面探讨唐代文人园林与公众世界的种种政治关联,以此展现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一、赏赐与没收:政治权利的体现
唐代文人园林从所有权上说属于私人,然而,当政者凭借其政治权利亦可对其进行支配,具有最终裁决权,主要表现在赏赐与没收两个方面。
将园宅赏赐给隐士或功臣,在唐代社会中并不少见。“湘浦怀沙已不疑,京城赐第岂前期。”[1](p.8579)“家贫仍受赐,身老未酬恩。”[1](p.2998)这可谓当政者对私家宅园的权利介入,这种介入使文人园林与社会政治发生了联系,表面看,这些只是简单的赏赐行为,然而,其背后却隐含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当政者为了点缀太平,不辞“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2](p.5116),并亲赐居第别业以示嘉奖。《新唐书·隐逸传》记载了两则赏赐隐士宅园的故事:
“卢鸿,字颜然,其先幽州范阳人,徒洛阳。博学,善书籀。庐嵩山……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制,许还山,岁给米百斛、绢五十,府县为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状闻。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恩礼殊涯。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赐万钱。鸿所居室,自号宁极云。”[3](pp.5603-5604)
“贺知章……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瘩,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刘川一曲。”[3](pp.5606-5607)
赐予宅园嘉奖隐士,可以说是对隐逸之行的官方认定,如同颁发一张盖有公章的许可证,保证了隐逸的可行,对当政者而言既是其举贤重能、苦心治国的明君表现,也是盛世太平的有力妆点,这样的政治目的完美地包孕在普通的赏赐行为中,宅第别业作为赏赐之物也便成为政治权利的直接表征。
如果说赏赐园宅给隐士是举贤任能、妆点太平的话,那么,赏赐宅园给功臣则是“劝忠臣” “导直臣”的政治表现。唐太宗感于魏征之功为其营殿堂,到魏征十五代孙时宅第已几经分割,当宪宗准备造访魏家宅邸时,却发现早已数易其主,这时李师道表示愿意出钱赎回并归还魏家,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朝臣间带有政治性的争论,白居易认为:“事关激劝,合出朝廷。师道何人,辄掠此美?”建议由朝廷亲自买回宅第并赐还魏氏后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劝忠臣”、“事出皇恩,美归圣德”[4](p.3343),于是宪宗采纳了白的提议。诗人陈彦博和裴大章作《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对此予以赞誉:“阿衡随逝水,池馆主他人。天意能酬德,云孙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殁后振芳尘。雨露新恩日,芝兰旧里春。 勋庸留十代,光彩映诸邻。共贺升平日,从兹得谏臣。”[1](p.5542)“邢茅虽旧锡,邸第是初荣。迹往伤遗事,恩深感直声。云孙方庆袭,池馆忽春生。古甃开泉井,新禽绕画楹。自然垂带砺,况复激忠贞。必使千年后,长书竹帛名。”[1](p.8831)皇帝的赏赐行为犹如一则政治宣传,既显示隆恩,又勇激忠贞,成就了千秋美名。
当政者对宅园有赏赐的权利,更有没收的权利,正所谓“今岁官收别赐人”[4](p.243)。马遂在唐代因镇压公元781—785年的叛乱功勋卓著,留名后世,然而,在他死后,儿子马畅则畏于权势将宅邸进献朝廷,史书记载说:“中官往往逼取,畅畏不敢吝,以至困穷……诸子无室庐自讬,奉诚园亭观,即其安邑里旧第云。”[3](p.4890)后世常常将“奉诚园”看作是奢侈蓄厚付出的惨重代价,例如,白居易的《杏为梁》将魏氏宅的“诏赎赐还”与马家宅的“犹存敬奉”进行对比,得出“俭存奢失今在目”的警戒之语。今昔对比亦引起了诗人盛衰之变的感叹,薛逢在《君不见》中说道:“马侍中,韦太尉,盛去衰来片时事。人生倏忽一梦中,何必深深固权位!”[1](p.6320)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俭奢之戒、盛衰之变背后,还有一层政治威势的存在,马畅畏于权势而献园,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没收,决定没收行为发生的原动力则是朝廷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利。
与“官收”相应的是皇亲国戚凭借政治权利对私家宅园的“强占”,大量的史料说明了这一点。《朝野佥载》称安乐公主“夺百姓庄园,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5](p.41)贾岛的《题兴化园亭》中“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1](p.6692),则是对裴度为建构园林强占土地的讽咏。皇亲国戚、权贵官僚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利通过强占别人的宅园扩充自家别业,“强占”行为的发生亦是受政治权势的支配。
“强占”“官收”“别赐人”等行为都受制于政治权势的介入与干涉,是政治权利的直接体现。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些行为导致的后果是园林别业产权的频繁更迭,正如白居易的感叹:“谁知始疏凿,几主相传授。”[4](p.461)剔除诗中的感伤情绪,呈现出来的是居第别业的产权更迭,王维之辋川别业曾是宋之问的故居,驸马都尉杨慎交山池本是徐王元礼之池,等等,园林产权迭替的背后实是政治权势的消与长。
私家园林产权的更迭从小的方面说是家族之势变迁的体现,从大的方面说则又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征候。《舊唐书·文宗纪》记载:“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2](p.561)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唐前期与后期在社会面貌上有着显著不同,这从曲江周围的行宫台殿见出;二是文宗重新建构楼台以图恢复社会升平景象,园林的兴废成为国家兴衰成败的表征。大型的公共园林如此,众多的私家园林更是如此,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说:“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由此“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6](p.54)李格非将洛阳园林的兴废看成是唐宋两代的政权交替,由园林知天下,以园林警当世,可谓《名园记》的写作初衷。
二、进仕之阶:政治权威的正面认同
唐朝统治者出于政治考虑通过赏赐宅园对隐逸之行进行嘉许,这是其政治权利的直接表现,与之相应,唐代士人纷纷建构园林,或以隐求仕,或获取方外之名,又或表征身份地位,对当政者的政治策略深表认同。可以说,唐代士人的政治诉求与当政者的政治需求取得了一致,变六朝时期的“对抗”为“双赢”。
当政者为了彰表贤能、妆点太平,对隐士赐服赐地,而士人对此也表现了极大热情,纷纷“结庐泉石,目注市朝”,隐逸动机由“藏声”变为“扬名”。《旧唐书·田游岩传》记载,田游岩与妻母同有方外之志,后入箕山在许由庙东筑室而居,后来高宗幸嵩山造访,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盲,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异汉获四皓乎?”然后将田游岩封官进爵,使其“并家口给传乘赴都”[2](p.5117)了。其中不免有沽名钓誉之嫌,然而,唐代士人对此不但毫不介意,而且趋之若鹜,纷纷隐逸名山,疏泉弄石,以求仕进。李白曾隐于岷山之南,岑参曾隐于嵩阳,窦常于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进士及第后,隐居扬州柳杨,疏泉种竹,10年后出仕。
隐逸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不为全身避祸,不为消极避世,而是为了扬名增誉。王昌龄在《上李侍郎书》中即说:“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7](p.3353)以隐求仕是唐代士人的普遍行为,说明士人对当政者鼓励隐逸的政治策略普遍积极认同,并付诸构园实践。也正是这种心理认同,唐代士人对朝廷开设的“销声幽薮科”“安心畎亩科”“养志邱园科”“藏器晦迹科”等颇具讽刺面目的应举科目奋力奔走,在今天看来似乎可笑之极,而在当时士人看来却是寻常之事。因此,唐人的隐逸行为推动了园林的建构,而建构园林的目的也多在于以隐求仕,这种从政态度说明了士人对朝廷的政策措施具有普遍认同。
对于未入仕者而言,建构园林的目的在于以隐求仕,而对于那些已经入仕为官者而言,园林则成为他们获取方外清誉的有效手段。《旧唐书·韦嗣立传》记载:“(韦嗣立)尝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两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2](p.2873)皇帝亲自参与到园林别业的欢庆活动中,制诗序、赐美名,从官权贵也积极配合,赋诗称赞,沈佺期《陪幸韦嗣立山庄》:“台阶好赤松,别业对青峰。茆室承三顾,花源接九重。虹旗萦秀木,凤辇拂疏筇。径直千官拥,溪长万骑容。水堂开禹膳,山阁献尧钟。皇鉴清居远,天文睿奖浓。岩泉他夕梦,渔钓往年逢。共荣丞相府,偏降逸人封。”[1](p.1044)别业的环境是“花源”与“九重”相接,花源代表远离政治中心的场所,而九重则指代政治中心,别业的人物是千官万骑与弄泉渔钓的统一,别业的特性也是丞相府与逸人封的统一,两个具有对极性质的事物在此有机融合。韦嗣立对此深感荣幸,其他士夫官人也多生倾慕。结合王维的半吏半隐的生平经历可知他从心里认同这种生存方式,这种认同其实也是对朝政鼓励隐逸的权威认同,致使越来越多的文人志士纷纷投入构建园林别业的浪潮中,以此作为争取方外清誉的手段和方式。
中唐时期的李德裕即是如此。李德裕在洛阳构置平泉庄,虽然30年未归,但还是为其赢得了令人倾羡的方外之名,正如他寄给刘禹锡的诗作《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见呼愧获方外之名……奉寄刘宾客》所言,以平泉庄的建构获得方外之名。为此,刘禹锡也奉和一首《和李相公以平泉新墅获方外之名因为诗以报洛中士君子兼见寄之作》:“业继韦平后,家依昆阆间。恩华辞北第,潇洒爱东山。满室图书在,入门松菊闲。垂天虽暂息,一举出人寰。”[8](p.1420)由此可见,唐代的精英阶层纷纷建构园林以此标举自己的隐逸情性,无形中与朝廷统治者鼓励隐逸的政治策略保持了一致,这不得不说是对当政者喜好的一种有意迎合,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认同。
建构园林在唐代士人中还是政治地位、社会身份的表征。《旧唐书·李义琰传》记载,李义琰居官清廉,不事产业,其弟义琎说:“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2](p.2757)可以看出,唐代士人为官后营第建园的社会风气,为的是彰显自己高高在上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在此心理驱动下,构园的数量也与日大增,元载“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2](p.3411)许多士夫文人拥有的园林别业往往不止一处,白居易有长安新昌坊宅园、洛阳履道坊宅园、庐山遗爱草堂、渭村闲居,裴度除了在洛阳集贤里有宅园外,又于午桥创别墅,牛僧孺在洛阳东城和南郭都有别墅,宅园别墅在唐人眼中既是修养身心的场所,又是社会身份的象征。
同样,在构园细节中也可以看出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性。李德裕与牛僧孺都是收集美石的藏家,《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七载:“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9](p.212)两人在政治上竞相争锋,在构园藏石上也有争高竞比之势,有政治流波所致之嫌。此外,两人所收美石有许多乃别人敬献赠送,李德裕在其诗歌中记录了一些所赠者,叠石为韩给事所遗,泰山石为兖州从事所寄,罗浮山石为番禺连帅所遗,漏潭石为鲁客见遗,赤城石为临海太守所赠,对此《唐诗纪事》中亦有明确记载:“德裕营平泉庄,远方以异物奉之,或题曰:‘陇右诸侯供语鸟,日南太守送名花。”[10](p.727)在这种交相往来中,除了友情的维系,剩下的便是政治地位的效用。
无论是以隐求仕,还是标举方外清誉,又或是表征身份地位,唐代士人充分发挥了园林在仕进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建构园林与朝廷的政治策略保持一致,赢得仕途畅顺,在这种君臣关系中隐含了士人对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
三、退隐之地:政治理想的反向表达
唐代士人在政治权威的心理认同下发挥园林在仕进中的积极作用,而当“正统”与“道统”的平衡被打破时,唐代士人又将园林作为退隐的精神据点,在退隐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朝廷复杂的政治形势左右着士人的人生选择,当朝政形势不符合士人心中之道的标准时,便可以主动退隐,但这种退隐只是暂时的。《旧唐书·裴度传》记载:“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庄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馆,名曰绿野堂……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2](p.4432)裴度因朝政之变而退隐宅园,但此隐并非避世,也非忘世,而是“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暂时闲”,骨子里呈现出来的还是忧患意识。韩愈曾经作诗《和仆射相公朝回见寄》:“尽瘁年将久,公今始暂闲。事随忧共减,诗与酒俱还。放意机衡外,收身矢石间。秋台风日迥,正好看前山。”[11](p.1255)劝慰之意力透纸背,并且此诗题下注曰:“时牛李党炽,裴度介其间。累遭谤讟,故愈诗有高蹈之语。”[1](p.3865)可见裴度因时政乖舛而暂取消闲,以期用高歌放言的外在休闲行为,掩饰邦国无道的焦虑与无奈。盛唐诗人王维的归隐也是如此,张九龄被奸相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刺史,王维带着对李林甫的厌恶,以及对杨国忠把持朝政的无奈而归隐,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半吏半隐的生活,但在他努力争取空寂清淡的平静中,依然掩饰不住跃动的心灵。可以说,这是唐代士人归隐的普遍心态,表面上看是追求闲逸,然而,内心却有着太多的无奈与不平,只得以另一种方式取得心理平衡,正如司马光以独乐园作为他最坚实的政治退隐地一样,退居幕后,远离政治,但政治理想并未泯灭。
面对“正统”与“道统”的失衡,裴度、王维等士人选择的道路是适度退隐,以此保持与政治中心的距离,而柳宗元作为贬谪诗人则在强制性命令的驱使下远离了政治中心。永贞革新惨遭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10年后又被迁往更为僻远的柳州,这是一种迫于朝政命令的远离,然而,这样的贬谪也未能彻底湮灭他的政治理想。柳宗元在此期间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园记,而且亲自买地开荒筑园,正如《愚溪诗序》所记:“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12](p.642)柳氏似乎要将自己心中的苦闷与郁结全都灌注在园林的游赏与建构中,然而,正如苏轼评柳诗所言“忧中有乐,乐中有忧”“忧之深”一样,执着型的个性气质使其始终未能超越贬谪、未能忘却深藏心底的政治理想。柳宗元将他所构亭、池、泉等八处景观一律以“愚”命名,并这样解释:“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12](p.643)在此,作者没有怨恨邦国无道,而是说自己“违于理,悖于事”,是为大愚,其实,作者在這里以退隐的反向方式进行表达,真正要表现的还是诗人矢志不渝的志向与自负。
与柳宗元一样,以构园写志的诗人还有司空图,不同的是司空图所处晚唐社会,政治形势更为严峻。《唐诗纪事》记载:“(司空图)见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乱,即弃官归中条山。”[10](p.946)司空图之隐虽为主动请示,但最终原因还是迫于政治多僻,因此,在退隐的生活中也并非可以真正回归心灵的宁静,政治、尽忠也始终未能彻底消失。《旧唐书·司空图传》记载:“图有先人别墅在中条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颇称幽栖之趣。自考槃高卧,日与名僧高士游咏其中。”[2](p.5083)我们看到的是啸歌赋诗的闲逸生活,然而,诗人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与不平,对豪门权贵把持朝政的不满最终在一篇《题休休亭》中发泄得淋漓尽致:“咄,诺,休休休,莫莫莫,伎两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著。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莫。”[1](p.7282)《唐音癸签》卷二三阐释了司空图由进取到退隐的心理变化过程:“咄,拒物之声。诺,敬言也。图隐身不出,其本怀。姑为拟议之辞,先叱之,随诺之,因以休休莫莫自决耳。”[13](p.246)面对现实不得不放弃,放弃的选择又是万般无奈,既然无可奈何,便只能不断地压抑自我,并以“休休”命亭,时时警诫自己。不仅如此,还仿白居易《醉吟先生传》而作《休休亭记》,名为亭作记,实为自己作传:“休,休也,美也,既休而且美在焉。司空氏王官谷休休亭,本濯缨也……休休乎,且又殁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负于国家矣。复何求哉?”[7](p.8490)同柳宗元一样,司空图以反语劝慰自己,试图压抑时刻升腾起来的不平与怨愤,虽远离政治中心,却又关注朝政形势,虽闲逸地诗酒吟乐,却又纠结在痛苦与无奈中。从其压抑式的表白中可以发现作者的政治态度,这其实是政治理想的一种反向表达。
唐代文人园林从性质上看属于私人所有,从精神上看是文人追求个性自由的空间,这构成了“私”的独立性,然而,文人园林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权利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借此可以窥视唐代文人的社会生活、仕隐心态及统治阶层与士人阶层之间的微妙联系,这是当前学界唐代园林文学研究、园林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参 考 文 献]
[1]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陈植,张公弛.历代名园记选注[M].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7]董浩.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責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