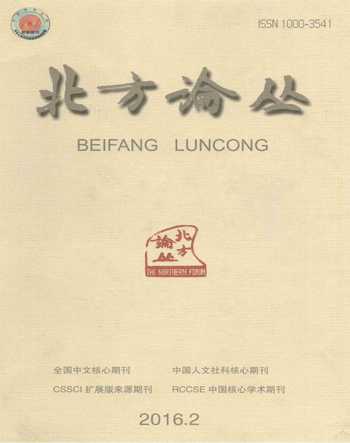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杜拉斯情人系列小说研究
肖凌
[摘要]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杜拉斯“情人”系列小说自传三部曲《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的深度解读,对主人公法国小姑娘与其情人们在对待父权制社会、受虐的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时不同情态的书写,以及20世纪初期封建父权家长制社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跨越种族的爱情及备受考验的亲情与友情的摧残的关注与思考,迸射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光芒。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67-04
一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所受压迫与自然遭受的迫害有着直接的联系,解放女性和解放自然的过程应具有同一性;尝试着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发展的宗旨是解放妇女与自然,批判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父权制的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价值等级思维、价值二元论和统治的逻辑。针对此谬误理论,生态女性主义者强烈呼吁要推翻这种父权制世界观,把解放妇女和解放生态危机、反对压迫作为奋斗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既关注自然与女性之间必然的联系,揭示并批判父权制社会对自然与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又追求男女在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两性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充满了憧憬。
法国当代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是位怀有高度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作品立足女性、书写女性,深度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这种以女性身份书写女性的立场的创作方式让她更能畅所欲言、挥洒自如。杜拉斯以其特立独行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她的情人系列小说惟妙惟肖地在男与女、性与爱、欢愉与痛苦、自我与社会等关系上,彰显了男权社会中失声许久的女性话语。杜拉斯本人虽然在谈话中否认自己是女权运动的领袖,但她确实参加过争取女性权利的各种活动。她的作品中渗透着强烈的女性意识,也是吸引大量女性批评目光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以下简称《堤坝》)、《情人》和《中国北方的情人》(以下简称《北方》)等三部经典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笔者发现,杜拉斯的情人自传三部曲不时地迸射出耀眼的生态女性主义火花:她笔下15岁的白人女孩与中国情人的相识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恋情的终结因女孩踏上了茫茫大海上那艘驶往法国的邮轮;故事的背景都发生在“没有四季之分、狭长的炎热地带”——越南西贡,“等不到春天”的气候预示着爱情的悲剧结局;丧偶却要强的母亲永远在为了那片不能耕种的盐碱地而绞尽脑汁,最终患病;大哥和小哥哥没能给予女孩家庭的温暖,却平添了恐惧与忧虑;中国情人的三次出场已将与小姑娘的情感由金钱交易上升到和谐真爱的高度;但这场爱情的结局却被父权家长制的社会现实判了死刑。
女性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两性的和谐理应包含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中。如果忽略了这一准则,那结局势必走向悲剧的深渊。杜拉斯在《堤坝》里证明了此点。随着20世纪7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法国的诞生与蓬勃发展,《情人》与《北方》在大环境不变的写作背景下,着力描绘了跨越种族的爱情与和谐的性爱体验,但男女主人公面对封建父权家长制的压迫一再选择逃避与妥协,最终真爱被迫停留在女孩返法的那个港口。
二
杜拉斯情感经历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少女时期的杜拉斯,曾与家人拮据地生活在远离家乡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地西贡。其中一个曾经走入杜拉斯生活的富有、懦弱的中国“情人”,留给杜拉斯无限的留恋与遐想。从《堤坝》中的“若先生”,到《情人》中的“他”,再到最后一部《北方》中的“中国情人”,情人的内涵发生质的蜕变,已由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渐变为真实存在的爱情,但世俗的眼光、种族的差异、门第的高低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一路走来仍以分手告终。除了中国情人的形象,杜拉斯还大胆地描写了白人姑娘与自家小哥哥近乎乱伦的感情,以及西贡寄宿学校里与密友海伦·拉戈奈尔之间的同性恋情。这均是在那个时代的禁忌,杜拉斯犀利的笔锋刻画出15岁的白人小姑娘誓与封建父权制不懈抗争的强大内心。
(一)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与自然的迫害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不仅能从内心深处了解自然、保护自然,还能与自然融为一体。比起女人,男人不懂女人和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也无法真正理解“自然母亲”或“地球母亲”的真正含义。父权制,顾名思义,在社会体系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女性应在结婚前服从父亲,结婚后听从丈夫,守寡时顺从儿子。父权制时期,男性居于这个社会的绝对领导层。这恰恰是杜拉斯一家当时的真正生活状态,也是小说《堤坝》的真实创作背景。时年36岁的杜拉斯为了还原18年前的西贡记忆,选择养家糊口的母亲为描述对象,记载了其为保护在印度支那购买的耕地,而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期间发生的事情:丧偶的母亲,领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入不敷出,最后用10年钢琴师攒下的钱,购买太平洋沿岸的一块租借地。然而,年年7月太平洋涨潮,海水都会无情地浸没全部农作物,于是绝望的母亲“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她的租借地是不能耕种的”[1](p16)。而这样的不幸居然“源自她那难以置信的天真”[1](p21):她“纯洁、孤独,与邪恶势力毫无关联,对一直在她周围的殖民地官员的贪婪毫无所知。可耕作的租借地通常要以两倍的价钱才能买到。其中一半的钱则偷偷进了地籍管理局那些负责给申请者分配土地的官员的口袋”[1](p312)。母亲申诉了两年未果,决定与其他毗邻的贫农们一起构筑抵挡大海的堤坝。母亲用尚未完工的吊脚楼作抵押,买了支撑堤坝的红树原木,结果也导致“吊脚楼则永远也没有建完。”[1](p328)而这一切换来的却是“这些堤坝,在太平洋的海涛猛烈而根本性的冲击下,一夜之间竟然如纸牌搭的房子那样坍塌”[1](p333)。穷困潦倒又满身疾病的母亲彻底绝望了,她将最后的希望放在尚未成年的親生女儿苏珊的社交上,情人“若先生”就此出场。这样的决定是荒谬的,但又是无奈的,是一位母亲在男权社会中屡屡碰壁之后认输的表现。
34年后,杜拉斯提笔重温这段往事,在《情人》的开篇便点明了更真实的自我:“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现在,写作似乎已经成为无所谓的事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2](p7)由此可见,《情人》中的叙述应更贴近真实的杜拉斯。
在《情人》中,苏珊的延续体小姑娘“我”成为真正的主角,故事也是直接从15岁半的“我”登上回西贡寄宿学校的湄公河轮渡写起。对于湄公河,给予母亲的印象是好的,她曾说过:“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3](p10)而对于我,却满是恐惧:“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在河水之下,正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2](p13)母女俩对待河水迥然不同的态度也暗示了两人隔阂的存在。那个时代现实中的湄公河的确不是那么美好:“河水从洞里萨、柬埔寨森林顺流而下,水流所至,不论遇到什么都被卷去……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死鸟,死狗,淹在水里的虎、水牛,溺水的人,捕鱼的饵料,长满水风信子的泥丘,都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但一切仍浮在河流冲力的表面。”[2](pp24-26)很显然,环境污染与生态保护问题已然在当时进入普通人的视角。对于越南西贡这片土地,“我”的记忆是“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2](p39)这样的语言映射出毫无留恋的情感,“单调”概括了15岁半的“我”当下生活的常态。接下来,代表着父权威严的大哥出场,他替代了那片盐碱地,继续折磨着母亲、小姑娘及可怜的小哥哥。杜拉斯在中国情人出场前这样写到:“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他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非把这遮住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非把那个由他、由一个人代表、规定的法权搞掉不可,这是一条禽兽的律令。”[2](p41)由大哥代表的父权已经让年仅15岁的女孩有了杀人的冲动,而一贯纵容大儿子的所作所为、被封建社会磨平了棱角的母亲却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最终,“哥哥始终是一个杀人凶手,小哥哥就死在这个哥哥手下。反正我是走了,我脱身走了”[2](p51)。女孩的家庭是不和谐的,她整日生活在绝望与恐惧之中,如同她周遭的环境一般炎热、单调,所有的一切都可能瞬间被卷走,荡然无存。在这样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氛围中,中国情人优雅登场,成为女孩临时的避难所。爱情自然降临。
《北方》中,女孩压抑的情感多方面爆发。在与母亲流泪争吵时,女孩哭诉:“你不明白。我爱保罗(小哥哥)胜过世界上的一切。胜过你,胜过一切……保罗像是我的未婚夫,我的孩子,对于我,他是世上最宝贵的。”[3](p25)这样乱伦的话语一出,母女二人都感到羞耻。但女孩依然我行我素,当找到教室外熟睡的小哥哥保罗时,她情不自禁地“吻他的头发、脸、搁在胸口上的双手”[3](p29)。睡意正浓的保罗俨然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月亮,它把鸟儿吵醒了。”[3](p149)兄妹二人的情感严格上说不是爱恋,而是一种依恋,是迫于大哥的淫威下达成的一种临时结盟。但这种联盟总会有瓦解的时候,中国情人的出现,使这段不伦之恋逐渐变淡;而与中国情人分手之时,小哥哥又重新成为女孩活下去的勇气。
曾经有两个月的时间,法国白人女孩和富有的中国情人在单身套间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情爱生活,并非为了钱,而是为了真正的爱情。但在中国情人的父亲知晓此事之后,万能的父亲改变了一切,包括这场爱情的性质与结局:“我不能同意你对我,你的父亲,提的要求。你要求我给你一年时间,可是过了这一年,你更不可能离开她了。那时候你就会失去你的未婚妻和她的嫁妆。这以后她也不可能爱你。所以我不改变双方家庭约定的婚期。”[3](p151)中国父亲的两封信中丝毫未提儿子今后的幸福與否,任何的决定均建立在“约定的婚期”与“嫁妆”上面。20世纪初的中国家庭还处于典型的封建礼教束缚之下,因此,中国情人与父亲之间是没有对话权利的,他们之间的常态是“父亲的儿子,他几乎总是跪着听他说话”[3](p156)。接下来的一切,都在父亲的计划之中:“我了解这个姑娘的母亲的处境。你必须打听清楚,她需要多少钱才能偿还她为修筑堤坝而欠下的债务。”[3](p181)软弱的儿子听从了父亲的一切安排,包括与白人女孩母亲的第一次会面:“我父亲不同意他儿子与您女儿结婚,夫人,不过他愿意给您足够的钱,帮您还清债务,离开印度支那。”[3](p267)就这样,在中国情人父亲的掌控下,母亲、大哥、中国情人、堤坝、债务等一切不和谐因素一起葬送了白人女孩的纯真初恋。
(二)女性、男性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诉求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男性彼此是相互关联的。人类应该抛弃男人和女人关系中二元对立的统治与被统治逻辑,充分认识两性的差异,尊重两性的价值,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为此,倡导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两性和谐、男女平等、种族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且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社会。这样的和谐主题也体现在杜拉斯的情人三部曲中。
在《堤坝》中,若先生所占篇幅不足1/3,他的出现似乎不过是起到调剂和反衬的作用,而且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人格,杜拉斯都不惜笔墨地对其加以鄙夷。自然而然,苏珊和若先生之间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爱情。或许,这是事实的一面,但从后两部情人小说中可知,它并非事实的全部。青年时期的杜拉斯还不能对种族及性爱等道德问题轻易释怀,因此,在第一次提及这段跨越国界、种族的恋情时,她选择了轻描淡写的口吻一带而过。相反,在小说的最后,母亲病重,兄长约瑟夫选择离开、弃母妹于不顾,苏珊彻底绝望了,她认为,自己的出路只有“等待猎人们的汽车”,随便跟谁离开此地:“我会跟他走的,甚至,即使她(指母亲)正在生病,我也会立刻就走。”[4](p540)平原上从事鸦片和酒走私的阿哥斯迪成为那个准备带她走的人,但代价是苏珊的身体。他们的第一次结合选择在阿哥斯迪家菠萝园附近的森林空地上。“相比之下,森林里空气凉爽极了,让人以为浸润在凉水中……当然,在那儿,她感觉比在其他任何空旷的室内更加安全”[4](p540)。就这样,苏珊献出了自己的童贞,但她同时也领悟到一点:“在爱情中,种种差异竟能够这样一笔勾销,苏珊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点。”[5](pp79-80)最终,母亲过世后,成长了的苏珊没有选择与阿哥斯迪一起留在平原,而是踏上约瑟夫和其情人的汽车,远离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在《情人》中,杜拉斯续写了自己和中国人那段跨越种族的爱情。法国小姑娘“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贞操献给了若先生的发展体——中国情人“他”。这里面既有爱情的推动,也有生活的胁迫。由于贫困,两个儿子一事无成,盐碱地更是无法耕种,日渐长大的女儿成为一家人的筹码。“正是这个原因,母亲才允许她的孩子出门打扮得像个小娼妇似的,尽管这一点她并不自知”[6]。女孩梦想着逃离母亲、大哥及贫穷带给自己的束缚,决心反抗,情人似乎在正确的时机、正确的地点成为正确的人。两人的第一次性行为也是女孩子占据了主动权:“他在颤抖着……好像在等她说话,但是她没有说话……他没有去脱她的衣服,只顾说爱她,疯了似的爱她……她一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他了,他讨她欢喜,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6]接下来,在女孩的鼓励下,“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6]。在此和谐愉快的性体验之后,二人继续交往了前后一年半的时间,感情越发真实,爱情真的降临了。但“我们是从来不谈自己的,自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未可预料,当时我们根本不谈将来。”[6]对待真爱面前的重重困难,男女主人公同时选择了逃避不提,这势必为今后的分离埋下伏笔。
在《北方》中,随着情人形象的进一步升华,小姑娘与中国情人之间真正的爱情被全面激发出来。虽然“无名无姓”,但“中国人”和“法国女孩”这样第三人称的陈述更能从客观的角度表达一切情感的真实性。似乎所有的环境、人物、背景、铺垫都只为了“爱情”两字而存在。在这部小说中,金钱不再成为二人相识、相爱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一见钟情:当中国情人问她接近自己目的是不是为了钱时,女孩坚决地回答说:“在渡轮上,没想到钱。完全没有。”[7](p11)她耐心地倾诉着对中国情人的真爱,甚至可以暂时抛开白人的身份优越感;为了争取中国情人父亲的同意,女孩考虑过各种可能,包括希望怀上中国情人的孩子。再有,杜拉斯在本部小说中花了较大笔墨描写中国情人父亲最终安排儿子和所谓门当户对的中国女人订婚后,两个相恋的人儿所面临的痛苦。为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情人不再软弱,他一再地去乞求自己的父亲,希望能与自己真心相爱的白人女孩结婚。再未获准许的情况下,中国情人为了挽留爱情,又让步到求父亲允许他们再交往一年,但结果毫无改观。万念俱灰的中国情人选择了自暴自弃,狂抽鸦片来麻醉自己:“我不干别的。我没有欲望了。我没有爱情了。”[7](p78)小说的结局,数年后他打了电话来,说他还爱她,这辈子都无法停止爱她,一直到死。最后,二人都听到对方在电话的另一头哭泣着。
三
纵观三部情人自传体小说,杜拉斯围绕“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一主线,刻画了三个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生态女性主义主题。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同样的恶劣:天气炎热,洪水泛滥,地籍员不公,分配到无法耕种的盐碱地,导致寡居母亲一家穷困潦倒。面对这一状况,《堤坝》里母亲和大哥选择向贫困低头,让尚未成年的女儿靠美貌勾引富有的若先生;并在成功骗下一枚钻戒后断绝了与其来往。最终母亲病逝,女儿失身于当地的鸦片走私犯后成功觉醒,离开平原。在《情人》中,家里的困苦之外,多了法国回来吸食鸦片、暴戾的大哥对家人的压迫。女孩因为钱一眼恋上了湄公河轮渡上高贵的中国情人。几经交往,感情升级,二人满足于眼下的爱情。但面对来自父亲的阻挠,中国情人没有勇气放弃对家庭的依靠,停止了抗争;法国女孩除了留恋亦无能为力。二人的爱情停留在客轮驶出印度支那的一刹那。《北方》中的女孩抗争意识更强,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迫,她先是恋上从小相依为命的小哥哥,以此支撑自己走下去;后又在寄宿学校结交了美丽女孩海伦·拉戈奈尔,二人以同性的身份热烈地相恋着;最后在轮渡上遇到了英俊帅气的中国北方情人而一见钟情。面对中国情人父亲的阻挠,二人用尽一切力量抗争,争取那一丝丝在一起的机会。但残酷的中国父亲将女孩全家赶离了印度支那,逼迫儿子迎娶了门当户对的中国新娘。由此更能印证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坚决反对父权制社会与人类中心论的压迫,寻求社会底层的妇女与受虐自然之间的姻亲关系,最终力争达到女人、男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位不朽的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出的这三部情人小说带给世界读者心灵的震撼。杜拉斯以法国人独有的浪漫情怀,加之在印度支那生活时养成的东方思维,刻画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情人世界”。情人三部曲的创作早已超出其原有的文学意义,无论用哪种文学批评手法来解读,都会收获颇丰。情人小说的价值在于在世界层面上描绘中越之间的族源关系、法越之间的殖民关系和法中之间的文学关系的交融。这看似复杂的三重关系以“情人、堤坝”为主线、在微妙的情境中交织与延展,碰撞出生态女性主义的火花,成就了文学巨匠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另一种伟大。
[参 考 文 献]
[1][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M]. 谭立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中英法三语版[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3][法]瑪格丽特·杜拉斯. 中国北方的情人[M]. 施康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Margerite Duras,Hiroshima mon amour,in Duras,romans cinéma,theater,un parcours 1943-1993[M]Gallimard,1997
[5]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tome 1:La Volonté de savoir[M]Paris,Gallimard,1976
[6]Interview de Marguerite Duras réalisée par Yann Andréa,Marguerite Duras:cest fou cque jpeux taimer[M]Libération, mardi 4 janvier 1983
[7]Bernard Alzet et 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dirigé par), Duras, éd.de lHerne,2005Marguerite Duras,La Vie matérielle, Paris,POL.1987,coll“Folio”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