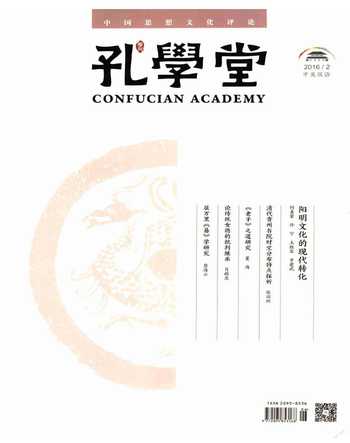论《拔本塞源论》的三个维度
许宁 秦蓁
摘要:《拔本塞源论》是阳明心学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本文以《拔本塞源论》为文献依据,力求揭示其内在的三个维度:一是追本溯源,阳明肯定“万物一体之仁”,改造朱子“十六字心传”为“十二字心传”,在追寻和重构“三代”以来的儒家道统谱系中发掘其历史维度;二是拔本塞源,阳明从圣人之心、圣人之学、圣人之治层面就人心私欲、异端异学、霸道功利提出了系统的破斥,从而凸显了批判维度;三是正本清源,阳明在“立道统”和“辟异端”基础上,提出“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强调了心学的为学宗旨,与其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相互呼应,展开了他晚年哲学建构的基本理论维度。
关键词:王阳明 《拔本塞源论》 道统 致良知
作者许宁,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蓁,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 710119)。
《拔本塞源论》是王阳明晚期著述中一篇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文献。该篇见诸《传习录中》,系《答顾东桥书》的最后一部分。阳明后学认为这篇文字思想深刻、意蕴丰赡,特别独立命名为《拔本塞源论》。陈来指出阳明的“拔本塞源是就‘私己之欲‘功利之毒而发的,而正确的拔本塞源的方法在他看来就是真正的、没有受到曲解的圣人之学”。“拔本塞源”语出《左传·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大意是拔掉树根、塞住水源,指断绝恶之根源,要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该篇不仅详细阐述了这种需要“拔本塞源”的私欲之恶和功利之习,而且阐述了唐、虞、三代时期“天地万物一体”的圣学本源,最后提出“良知之明,万古一日”以说明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才是复兴圣学的宗途。阳明正面追溯道统,从反面批判异端,由此建立起“良知”学理形态。
笔者立足《拔本塞源论》文本,力求揭示其内在的三个维度:一是追本溯源,在追寻和重构“三代”以来的儒家道统谱系中发掘其历史维度;二是拔本塞源,从圣人之心、圣人之学、圣人之治的层面就人心私欲、异端异学、霸道功利展开了系统的破斥,从而凸显了批判维度;三是正本清源,阳明在“立道统”和“辟异端”的基础上,提出“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强调了心学的基本宗旨,与其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相互呼应,形成他晚年哲学建构的基本理论维度。
一、立道统:《拔本塞源论》的历史维度 [见英文版第17页,下同]
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体现了对“三代之治”的向往和追求,亦是阳明对道统的追溯与探源。从道的层面看,圣人之心、圣人之教和圣人之治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阳明将天地万物一体作为心学本源,提出了对朱子“十六字心传”的看法,进而推展至社会和国家治理之道,由此构成一个整全的道统论。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
阳明的“万物一体”观念既是儒学精神旨趣的传承,也是对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以及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识仁篇》)等宋儒思想成果的总结。
“万物一体”既包含了“气”的事理层面,又包含了“仁”的道德层面。“气”是“万物同体”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本源。人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由于“气”流贯通达,故无人己、物我之分。“万物一体”之“物”首先指人,即万人同体,因此才有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皆待之以兄弟同胞;其次指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即天地之间、宇宙之内的任何物种都与人同体,如鸟兽、草木、瓦石。
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万物一體之“仁”彰显了人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关联。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之所以如此,缘于仁心的灵明和感应,通过天地之间的感应才能达到血气相通、精神流贯、志气通达。仁的大端被视为“恻隐之心”,此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阳明喻之为树木抽芽发干、生枝生叶,由此仁爱之心生发推广扩充至仁民、爱物,达到与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阳明以三代“十二字心传”为圣人之教的本源,提出了心学道统论的总纲。之所以称为“十二字心传”,是因为朱熹将“十六字心传”作为其道统论,而阳明与朱熹的本质差异恰在于此。阳明从心学立场出发,吸收程朱道统,并给予批评改造。笔者认为阳明的道统论入于程朱而又出于程朱,建构了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心学道统论,是宋明时期道统论的深化和突破。
阳明立足心体,主张心的一元论,强调道心,提出“心即道”。首先,重新论述了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梁涛评价道:“道心是符合仁义之理之心,人心指生于形气之私之心,而‘允执厥中就是要省察‘危而不安的人心,持守‘微而不显的道心,时时以仁义之心即道心为标准,‘执中,无过不及。所以在以仁义为道的本质内容上……朱熹将仁义与道心、人心的区分联系在一起,将仁义形上化,哲学化。”可见,在朱熹的道统论中,人心与道心是两回事,道心就本体的形上层面而言,只有道心才符合天理,人心应以道心为标准才能“执中”。同时以道心为主,人心要听命于道心。虽然朱熹也认为道心、人心实为一心,但朱熹的道心、人心实是在其天理宇宙论的整体架构下来讲的。尅实言之,朱熹的道统论实是一种二元论。阳明因此批评朱熹将心分作了两截,是向外假求于道。在阳明看来心只有一个,此心纯明即为道心,道心又等同于仁心。阳明基于心的一元论立场批驳朱熹,认为道心、人心只是一心,“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重新论述了道心与人心的关系。冈田武彦在辨析朱、王之不同时指出,朱熹侧重人心,阳明侧重道心,阳明批判朱熹为“二心”说,其道是富于生命力的,不同于朱熹之道的崇高严正。所以阳明在引用“十六字心传”时并不引用“人心惟危”,而将其改造为“十二字心传”。
其次,重新论述了心与道的关系。阳明提出“心即道”是源于他“十二字心传”的心学一元论。所谓“心即道”,并非心与道的合一,若是合一则是两个以上才能论合,在阳明看来心、道无二,是一回事,求心也是求道,圣人传心实际就是圣人传道。阳明批评朱熹过分言道,从知识求学上来寻道,是假道于外,使道更加晦涩。为道需要从心上体认,非知识技能可以达到。阳明的“心”有着丰富的层次和意义。秦家懿总结为三层:一是原始的、纯洁的“本心”;二是受私欲所蔽的“人心”;三是成圣者重新光复而得的“真心”。谈论道就离不开人心,道寓存于人心之中,是人心本来就有的,而真正的道实际就是“本心”的复然和“真心”的再现。所以阳明说:“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虽阴晴晦明千态万状,而白日之光未尝增减变动。”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暭暭,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
阳明以三代天下一家的盛况作为圣人之治的本源。他提倡王道,主张实施仁政,以成德为务行,以道德教化百姓,如此才能“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一方面,于官,应举德而任之。只有立足于仁的道德,才可终身居其职而不易,如同夔、稷、契三者,并不嫉妒羡慕有才能的贤臣,而是各尽其能忠于职守,各安其位;另一方面,于民,也应各安其职、各勤其业,相生相养。如同社会中农、工、商、贾各种职业的划分一般,人人都能按照各自的才能定位和效能而各职其业,并不以辛苦和卑贱来区分。如此,不但官员能同心同德,以百姓安宁为目标、为己任;人民也能同心同德,以天下为一家之亲;官员和百姓之间才能各安其职、各尽其能、各勤其业,天下和睦,社会安定,圣人之治才可显现。这说明阳明的道统论更注重庶人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之道的作用,无论官员还是百姓,抑或士人,“四民异业而同道”,都是这个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安天下之民,成天下之治”。沟口雄三认为官吏、农民、商人分别在各自的日常行为的环境中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阳明将社会关系纳入道德秩序中,是道德实践的平民化和主体的扩大化。阳明不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也重视庶民阶层的平民性;不但指出了心学成圣的重要性,也重视日常生活的实践,将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二、辟异端:《拔本塞源论》的批判维度 [21]
异端是相对于儒家仁义道德之正统而言的。道统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狭义上是指宋儒所辟之佛老异端;广义上则不仅限于佛老,同时还包含了对儒学内部之异学的批判。而阳明“辟异端”的特点在于:不仅从外部批判佛老异端,而且还从内部批判儒家异学;不仅从道的义理上批判佛老,还从心学角度批判当时的思想流弊。以下分三个层面讨论《拔本塞源论》批判维度。
(一)从圣人之心层面批判人心私欲。[21]
虽然阳明同朱子都注重道心,但朱子将道心和人心分为心的两个层面,而阳明只讲一心,此心即道,也是理。朱子的心以知觉为功能,觉于天理便是道心,觉于人欲便是人心。而阳明的心只有一个,道心即本心,人心就是夹杂了私欲的、不能明现的道心。因此阳明批朱子过分注重人心而将心分作两截。阳明说:“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一于道心,则存之无不中,而发之无不和。”在阳明看来,道心微弱,人心危伪,人心只是夹杂了人伪私欲并未得其正的道心而已。
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圣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圣人与凡人都有着相同的本心,即道心。凡人因私欲和物欲之蒙蔽,因而大我之心变成了小我之心,能够同心同德而相通的心也被堵塞了,故而出现了所谓的人心。阳明以道德上的“仁者”为圣人,圣人存有道心,与万物浑然一体。虽然凡人也有道心,但被私欲蒙蔽,此道心的仁便有所减损。可见圣人之心与凡人之心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去私欲以明道心。阳明用“明镜”比心:“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这是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凡人之心如昏镜,圣人和凡人本来都有道心,二者的本质相同。只是凡人被私欲所蒙蔽,道心变得昏蚀了,需要做一番去除的功夫才可使得道心明现。换言之,“在天赋上,圣愚虽各有别;在功夫上,愚夫愚妇也可入圣。枢纽在于发明本心”。另外,阳明说的“私欲”与朱子的“人欲”也是有区别的。朱子的“人欲”作为“人心”所发若违背天理,便是恶的,则成为“私欲”。所以其“人欲”与天理相对立:“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阳明的“私欲”只是因为道的本心被遮蔽,其实是一心。所以阳明说“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命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二)从圣人之学层面批判异端异学。[22]
阳明批判的异端不仅是佛老,还有儒家的俗儒与杂儒。
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惟以成其德行为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 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
佛老向来是儒家主要的批判对象。《拔本塞源论》中,阳明对佛老虽没有明白揭示,但以鲜明的儒家立场回应了佛老的观点。这在文中主要表现有三点:一是注重“五伦”节目之教;二是有着儒家“修齐治平”的现实关怀,期望“共安天下之民”,此点完全不同于佛老的出世追求;三是注重“同心一德”的道德实践,这也区别于佛老的宗教性和神秘性。此三点明确体现了阳明对佛老的批判。秦家懿也肯定:“阳明的论辩结构,得自禅宗,又有禅宗的辩证色彩。他用的譬喻与字句,也多得自禅。但是他的基本上的‘意向,却与禅不同。阳明的根本精神,是入世精神;他要‘拔本塞源,使人除去功利之心,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与之相比,阳明对儒家内部异学的批判更加激烈。
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 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 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世之学者,……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
他所针对的是指孔孟儒学之后,汉唐以来出现的各种儒家学派,有经学、训诂学、辞章学和其时正处于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阳明将这些全部都视为异学,斥之为“无用之虚文”。阳明指出正因为这些异学使得圣人之道晦暗不明,日繁日难,且越行越远。将圣人之学昭明天下正是“拔本塞源”论的目的所在。
(三)从圣人之治层面批判霸道功利。[23]
三代以前,世人同心同德,百姓安勤乐业;东周以来,王道没落,霸道盛行,富强功利跻身治国之道,官吏以满足一己之欲为能事;孔孟之后,霸道亦不能行,圣人之道芜塞,人人都追求功名利禄,以致治世之道最终沦为禽兽夷狄的邪道,亦即法术等功利之道。阳明批判霸权法术,主张王道,实际源自于孟子“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以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阳明不论正面追溯三代圣人之道,抑或反面批判后世之霸权法术,其实质都旨在溯源唐虞三代与孔孟的圣人之道。
三、致良知:《拔本塞源论》的理论维度 [23]
阳明在文章总结中提出“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揭示出《拔本塞源论》的主旨。王阳明立足“万物一体”的心学立场,改造“十六字心传”为“十二字心传”,将心传作为理论基点,将“致良知”作为理论形态,这是《拔本塞源论》的价值所在。秦家懿认为阳明心学以一心观万物,以一心成万物,道破了多数人只会说而不明白的“人心道心”之微意,又发扬了新的“道统”的序列;以良知为新道统的传心决。王阳明将“良知”作为心学的核心范畴,以“良知”为圣人之道;将“致良知”作为修身功夫和治理之道,以“致良知”为圣人传道,这是阳明整体的思想体系。阳明强调“致良知之外无学矣”,以“致良知”取代程朱的学理形态,在圣人与道方面具有瓦解传统成圣观念的理论意义。
阳明良知说与程朱理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程朱理学将理作为最高范畴和终极原则,并在理学架构内区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所以程朱的理、道、性、心都有层次划分。而在阳明看来,良知即心、即道、即理、即性,同时也是道心。第一,良知即心体。阳明心学将“心”作为起点,以复归于本心为终点。良知与心的关系体现为:良知即心之本体。“良知者,心之本体。”“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阳明从孟子的“四端”出发,说良知是个是非之心,有着人人都先天具备的、内在的特点。并且良知是人心中固有的、自然的、不分圣贤的、不分时空的道德知觉和道德准则。第二,良知与道、天、道心、理、性之间的关系。“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阳明通过以上的定义,以心为中介,将良知与道、天、道心、理、性贯通起来。至此,阳明力图用“良知”本体范畴消解程朱理学中对所谓理、道、性、心之间的层次划分。秦家懿指出阳明“良知”说是对程朱“性理学”的“取而代之”,阳明发挥程朱说“心”和谈“传心”的含义并反对他们的理论,将“性理学”完全带上“心学”的路,脱出了程朱学的范圍,而自成一说,这不是“改造”,而是“创新”。
“良知”是阳明的心学本体和成圣理念,“致良知”是“良知”的修身方法和成圣途径,二者一起构成了其思想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形态。首先,从阳明“心传”来看“良知”与“致良知”之间的关系。道心就是在“良知”范畴之内讲心学,是静态的,并非是动态的。所以“心”是以照顾本然的状态,不能自传。也就是说“‘心学之传实是指每一代的‘自得。为师者,可以启发或感悟求学者……‘心心相印之学,令各自在本心内,日新月异的发先生任之‘道”。“良知”要昭明的功夫和途径就是“致知”,因而有了“致良知”,也就是阳明所谓的成圣方法。“致良知”是动态的,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这也是阳明对自宋代理学以来对如何成圣的解答。所以,“良知”与“致良知”,一个是本体,一个是功夫;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说心,一个说传心;二者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道统体系,从而“解决了‘道统说内在的矛盾”。其次,从“致良知”来看“心传”的方法论。良知本来能够自明,“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此处要从“过”和“不及”中谈良知,即是自“心传”的“允执厥中”上讲良知;而“允执厥中”的功夫,全在格物致知上,是从诚意上讲正心、修身功夫。“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如果“良知”是阳明成圣的道德本体,那么“致良知”便是阳明成圣的道德实践,阳明心学是将道德本体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体系。所以钱穆以为,要论阳明的《拔本塞源论》,就必须从“事上磨炼”讲,此论是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举凡政治、教育、才能,莫不一以贯之。
《拔本塞源论》成书于阳明晚年思想成熟的关键期(1524年),不仅在阳明整体思想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在古代中国同样有着非凡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其学术思想的内容与意义,在冈田武彦看来是将王阳明学术思想“几乎毫无遗漏地记录在其中”,“不应将其仅看作一篇论文,而应看作书信中的名篇”。而日本研究阳明学的著名学者三轮执斋和佐藤一斋分别评其为“至论中之至论,明文中之明文。秦汉以来,数千年间,唯此一文”,誉之为“古今独步”。《拔本塞源论》中体现出阳明挽救时弊,复兴圣学的责任和担当,字字句句都映现了他的忧世情怀,这也正是古代中国儒家精神与境界的体现。所以刘宗周在读此《论》时感慨“快读一过,迫见先生一腔真血脉,洞彻万古。愚尝谓孟子好辩而后,仅见此篇”。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