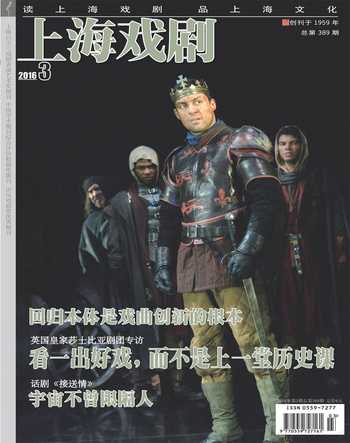昆曲音乐创作应回归传统曲牌体的技术层面
我认为昆曲音乐的创作发展,应该遵循“传承——要探本寻源,创新——要适时有度”的基本理念。
当下的昆曲作曲中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比较集中的是:
第一,剧目创作中,唱腔的
设置不够精细
我觉得昆曲的作曲出发点是昆曲本体,不能因为昆曲格律难就另辟蹊径。昆曲是怎样就是怎样,必须要搞清楚,要探本寻源。一个合格的昆曲曲牌体音乐设计,应该有成套唱腔的总体铺排。还要有几支能充分发挥人物情感的经典曲牌及套数,在剧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家都谈到,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昆曲是“音乐结构主宰了剧本结构”。对于昆曲来说,就是用曲牌来传达故事的起承转合。所以,必须强调曲牌体唱腔音乐的设置在昆曲一度创作中的重要性。选择曲牌还要看角色,更进一步地说要看演员。所以选牌不够精心,唱腔布局比较马虎,是当前创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第二,昆曲唱腔音乐创作中
如何写腔
有些做法是:昆曲主要的腔是十二句半,只要按照这十二句半来写就八九不离十,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虽然这样做听起来还有些昆曲的味道,但这不是曲牌体的昆曲,这种“牌是曲非”的自由体写法,只是在误导一些对昆曲完全没有认识的观众。而这种不抓曲牌的主腔(表征意义的主要腔调),只求腔格(字腔)昆曲化的做法在音乐创作中还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做法容易乱,不能形成昆曲唱腔的应有格局和韵味,让我很忧心。其根本的错误在于没有“依牌谱曲”,没有表达不同曲牌、不同情感类别的特性腔调。比如【太师引】第一个字就是去声字,是一个高耸入云的高腔。《金雀记·乔醋》里的“顿心惊”的“顿”字,就是一个顿生惊讶的高腔。在新创剧目《班昭》中,班固忽闻朝廷解禁汉书时,我们安排了这段【太师引】,也利用此曲牌的特性腔,彰显【太师引】曲牌的特定功能。
关于曲牌“主腔说”,我认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昆曲的这些经典曲牌之中。当然,昆曲那么多的曲牌,有不少是流水型的粗曲,不是说每个曲牌都有那么明显的主腔。袁玉冰同学的文章中谈到,《范例集》存在夸大“主腔说”,拔高“主腔说”的问题。对此我持保留看法,我觉得从整体上看,《范例集》并没有拔高“主腔说”,而是从词乐对应的原则,揭示了昆曲大量经典曲牌的主腔及其应用规律。我的老师王守泰先生(《范例集》主编)出身昆曲世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撰写出版《昆曲格律》。又是东南大学理工科教授,他用科学的分析方法,领导编写组成员,对浩如烟海的众多昆曲曲牌,抓住“主腔”这个“分析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归纳,总结出曲牌的“乐式”。有些地方,特别是一些粗曲,确实如袁玉冰所说,有所谓“拔高”的情况。但“主腔说”还是实实在在存在于大部分的曲牌之中。所以昆曲音乐创作上要抓好这一点,在经典曲牌中把这个主腔写出来。比如这次的《夫的人》,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的曲子写得好。前半部分南曲中存在问题,正是曲牌选择不精细,曲牌主腔呈现不够,听起来就有点像“十二句半”了。创作是个细活,我们一定要注意多学、多思和多问。
第三,冷僻曲牌和经典曲牌
在运用上的分寸
冷僻的曲牌,我在创作中不是不用,但是用得少,经典的曲牌我则是多用和常用,这也是俞振飞老师当面嘱咐我的。一出新创昆剧中,不能是生僻的曲牌太多,这样它在乐理和唱腔上会显得没有表现力。我有一个理念是:“多唱多宣传经典常用曲牌,来奠定昆曲唱腔传统格局和韵味”。比如《范例集》中例举了50个孤牌,我主要分析和使用的是其中26个经典的。成套的话,北曲8套,南曲22套(实际南曲经典套数少于22,没有那么多套),经典的曲牌一定要常用。其实,关于经典常用,俞振飞言慧珠两位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排《墙头马上》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当时言慧珠和俞先生经常商量,要选用一些好听的曲子,安排在重要场子中。经过反复研究和调整,曲牌及套数最终由俞先生和编剧苏雪安定稿,为常用曲牌奠定昆曲唱腔格局和韵味,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以上三个问题,我认为是现在昆曲作曲上要克服的乱象。所以我赞成新编剧目新创剧目在唱腔设计上,重要的是要回归传统曲牌体的技术层面。具体实施上,第一步要设置曲牌套数,这是曲式的问题。第二步要“依声填词”,这是曲和乐对应的关系,也是《范例集》这套书做出的一大贡献。第三步是“依牌谱曲”,要抓主腔。同时,“创新要适时有度”——努力把握昆剧唱腔的古典韵味,创新不可少,但要与传统找到平衡点。
我为昆曲努力了一辈子,搞昆曲音乐,从台前转到幕后,我不感到后悔。如今是要把这一切交到年轻人手里了,昆曲的事业应该是青年们的事业。戏曲,戏是大千世界,曲乃半壁江山。戏曲音乐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戏曲各部分工作者的共识,当下昆曲唱腔音乐创作也越来越受重视。年轻人:戏曲之祖,戏剧之核——昆剧,值得你为之奋斗终身! (本文据作者在“顾兆琳《昆剧曲学探究》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