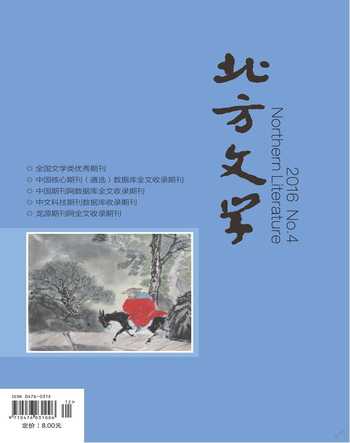丰富的烦恼
段蕴恒
摘 要:在“人生三部曲”中,池莉以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冷峻的叙述角度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仿真描摹。她展现了世俗生活的窘迫困顿与庸常人生的烦恼焦灼,重新发现了生活价值,强化平民意识,真实再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平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池莉;“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平民意识;审美向度
池莉钟情于日常生活的书写,并执着地探索生活,冷静地表达日常。她以《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记述了武汉市民阶层一幕幕无奈与无事的悲剧,书写了普通百姓生存窘境的烦恼,刻画了凡俗社会中的灰色人生与阴暗灵魂。池莉注重展现“汉味”情调,关注和表现世俗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消解精英文化与虚幻爱情,以直面现实人生的姿态、冷峻客观的叙述和质朴世俗的语言对平民阶层忙碌嘈杂的现实生活进行了仿真描摹。这一创作阶段的池莉坚守着新写实的创作立场,以强烈的平民意识承担着她的文学道德使命。
一、世俗生活的窘迫困顿与庸常人生的烦恼焦灼
新写实小说主张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侧重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描写和对生存过程的展示,在关注现实的方式上也由反映生活转向对生活的感性体验。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作家在直面人生,打破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同时,也并非完全采取零度写作的姿态和生活流式的客观记录。他们将自己的主观思考和情感体验灌注于小说对世俗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之中,将处于窘迫困顿中的人们对平淡生活的感触,对庸常人生的体验和对喧闹社会的醒悟都融汇到小说人物的生命进程中。
《不谈爱情》从一对新婚夫妇庄建非、吉玲从恋爱到婚姻的波折坎坷,再到婚后的矛盾纠葛,展现出现实人生的烦恼,具有强烈的感受性。池莉以“不谈爱情”来命名这则爱情故事,实则用现实解构浪漫的爱情,撕裂爱情婚姻的神话,婚姻成为现实的隐喻和代名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庄建非不顾家庭的反对,克服重重阻力与出身花楼街小市民家庭的吉玲相恋并结婚,但他们在婚后却因琐事而几乎离婚。妻子离家,庄建非的生活变得杂乱无序,并陷入烦恼和焦灼;他去花楼街找妻子,却被岳母怒斥;他找同事诉说心事,却被人背叛导致家庭不和的流言遍起,并影响出国深造。吉玲密友张大姐劝其离婚,庄建非旧情妇梅莹劝其合好。庄建非父母为了儿子出国深造而出面道歉,最终平息了这场波澜。庄建非也在这场家庭危机中理解了婚姻的意义,个人的家庭、社会责任,并向现实妥协,从而“长大成人”。小说的创作视角集中于小家庭外的大社会,作家的关注点不在于爱情本身,而意在展现普通人在窘迫生活中的烦恼——夫妻失和引发的社会压力与精神负担,着眼于繁琐纠葛的现实——夫妻间争吵所引起的各自家庭,乃至双方各自代表的市民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混战。贫困粗俗的花楼街与富裕高雅的大学校园,泼辣世俗深谙世事的邋遢女人与满腹经纶随机应变的大学教授,揭示人人不可超脱的生存状态的缺陷。
《太阳出世》则集中关注大社会里的平凡人生和小家庭,更多的着眼于窘迫生活与烦恼人生对普通人的改变。小说记述了赵胜天、李小兰夫妇从结婚到孕育、抚养孩子的过程,展现了夫妻的人生烦恼和各自家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情感纠葛,更呈现了他们从青年向成年转化的生命过程。赵胜天夫妇的烦恼主要在于经济拮据和繁琐家务引起的烦闷。但生活的束缚却唤起了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动力,赵胜天以婚礼为序幕脱离了对父母的依赖,在女儿诞生的精神震撼与拮据窘迫中经历了觉醒与升华,在对自己工作的再思考中确立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也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存在的同一性的认同。在这一系列的情感历程中,赵胜天走向了真正意义的成年。李小兰意识到自己不会当家过日子,不懂得世事艰辛,不知道许多常识性的生活道理,在图书馆工作几年没有读完一本书,十分后悔。母性意识的觉醒和生育的痛苦促成了她心里的成熟。“太阳出世”是一个暗喻在象征新生命诞生的同时,也象征了婴儿的父母在新生命孕育、诞生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人生体验和蜕变。
池莉在《烦恼人生》中聚焦于世俗社会中的烦恼个体,截取了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断面,凸显了普通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物质匮乏。半夜儿子跌伤,早上排队洗漱,妻子的抱怨与恼怒,带儿子跑月票拥挤争吵,只得到三等奖金的恼怒,对雅丽一往情深的恍惚,对肖晓芬刹那间的情愫,为父亲准备礼物的尴尬,住房拥挤经济拮据等,诸多杂乱繁琐而又不得不应付的事都在纠缠着印家厚,使这一天显得如此漫长难耐。这种漫长难耐感不仅仅来自于生活本身,也来自于由生活引起的主人公心理上一连串的烦恼。池莉把人物外在生活的窘迫困顿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其中包含了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对现实的无奈等复杂的体验。池莉在小说中通过对世俗生活中平凡人物的仿真式书写,撕裂了盛行的理想主义话语,改变了传统文学序列中对经典英雄的呼喊与虚构。
池莉新写实小说的内容是从人们生活自身撕裂出的原始景观,读者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不禁思考烦恼与窘迫的来源。作家之所以执着于对生活质感实感的真切还原,不是为了追求某种人生理想,更无意于批判或者讽刺现实的黑暗。作家是为了对窘迫生活与烦恼人生进行简单描写,在呈现生命与生活本质面貌的同时,进一步把筆触伸向人类生存困境这一命题,探索烦恼产生的原因:物质的匮乏,社会秩序的混乱,精神的苦闷荒芜,道德、伦理、世俗观念的矛盾。新写实小说的思想内蕴已经超出了对现实的表象还原和仿真叙写,将外在生活的窘迫困顿转化为内在的情感体验——烦恼焦灼,并逐步触及人类自身生存困扰的深度。
二、生活价值的再发现与平民意识的强化
池莉通过文本搭建民间俗人俗世的想象空间,在还原普通人在匮乏的物质条件和逼仄的精神空间挣扎奔突的同时,关注凡庸卑琐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对普通人投向了关怀。池莉审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及生存策略,将视角转向人类永恒的生存矛盾,探索平民精神和民间生存哲学的存在。作家在文本中创造了一系列非脸谱化、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打破了传统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对人物行动中交织着深切的生活感受和复杂的情感体验的描写,使人物具有丰富内涵,浮躁与坚韧、谦卑与自强、谦和与焦灼、宽容与不满,构成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写出了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庸常社会中凡俗、“反英雄”式的小人物。他们放逐理想,消解崇高,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以特定的方式顽强而坚韧地生存,充满生存智慧和生活能力,“不屈不挠地活”的生存理想卑微但也朴实。
印家厚曾是一个做过“带着浓厚理想色彩”的少年梦的青年,也曾是一个从里到外血气方刚,衣着整齐,自我感觉良好的小伙子,但现实中房子小、收入少、负荷重、乐趣少、前途无的状况,使他自卑地感到“他几乎从来没有想是否该为少年的梦感叹。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入非非呢?”[1]使他将这一切化为一声叹息:“生活”,“梦”。他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全部的生存方式。印家厚理解妻子借儿子掉下床而爆发的积怨,用车到山前必有路的道理安慰因房子拆迁而心酸无助的妻子。面对生存的重压他选择隐忍,努力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寻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他的生活烦恼但不沮丧,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渴望,积极对待工作,工作加班加点,努力报考电大,看到不如意老友的来信会庆幸自己的安稳幸福,面对儿子会陡然觉得生活充满了信心。[2]
出身花楼街的吉玲的生存策略体现了鲜明的反抗意味。她为摆脱声名狼藉的出生地和粗俗卑陋的家庭环境,实现自己“弄一份比较合意的工作”“找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丈夫”的“人生设计”,进行“坚定不移地努力奋斗”。在解决工作问题后,她开始谨慎务实地经营自己的婚姻,以自己的“单纯质朴”赢得庄建非的好感,如愿嫁入高知家庭。但夫家的冷漠无视与丈夫的轻慢让她感到不满,吉玲为捍卫自己的婚姻幸福不惜采用怀孕、离婚的方法,迫使夫家改变观念终于“把她当回事”。庄建非相较印家厚的隐忍,则更具有知识分子特有的智慧,对生活的反思和体悟更加深入。他面临的危机是精神的困窘,夫妻失和引发的家庭危机、社会矛盾让他懂得生活的意义和婚姻的本质:“自己的婚姻并非与众不同”,也“逃不过今天的时代”,“婚姻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你不可能独立自主,不可以粗心大意……过日子你就要负起丈夫的职责,注意妻子的喜怒哀乐……”[3]。赵胜天和李小兰也都在窘困的经济和繁重的家务压力下实现改变。产后第一个月的艰难几乎压垮赵胜天,但他仍能感受到凌驾于困苦之上的幸福。生活的充实愉快正是来源于挣扎与磨难。他们克服了诸多矛盾不合,脚踏实地地履行父母的職责,在工作岗位上实现自我价值。
三部曲的主人公都以坚韧执着素朴的态度面对烦恼人生,他们不是富有时代意义的英雄人物,而只是世俗社会中的平凡人。他们或是隐忍坚持,或是挣扎反抗,或是反思体悟,共同以不屈不挠、坚韧厚重的市民精神为旨归。池莉从他们身上开掘出了“不屈不挠地活”的平民精神,以下沉的创作视点和摒弃虚构的细节提升了生活本身的价值。
三、“人生三部曲”的审美向度与价值开掘
从总体来看,池莉在题材选取、人物塑造、叙述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格,具有鲜明的新写实特征,并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创作亮点。
第一,创作方式上的新写实特征。池莉站在平民立场,以世俗的眼光平实地叙写庸常人生,努力摹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了世俗生活的窘迫困顿与庸常人生的烦恼焦灼,将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融入写作,透露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思考。小说多采用生活流式的叙述,用近乎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按照生活时间的先后流程结构作品,不去刻意虚构和编造故事情节,淡化了传统小说中因果承接关系的逻辑结构,重视还原现实的原生美和丰富生动的细节,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都融汇到人物生命的进程之中。小说的语言是通俗化平白易懂的,能更好地反映都市世俗人物的人生境遇。
四、结语
“《烦恼人生》的写作之于池莉,不仅在于对女性写作界定的撕裂,更重要的是对八十年代主流文化中的伟大叙事的撕裂,但在池莉的表述中,它却更象是另一种民族语言与伟大的许是营造。”[4]池莉将创作视点下移,真切袒露了生活的本质面貌。她一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的“宏大叙事”和“伪宏大叙事”,弥补了新时期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断裂,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拉近了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提升了生活的价值,高扬了平民意识。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家们吸纳了现代派的艺术特点对传统文学创作进行了革新,其突出贡献在于动摇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给了作家自由表现生活现实广阔空间,将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池莉.烦恼人生[J].上海文学,1987(8).
[2]池莉.我写<烦恼人生>[J].小说选刊,1998(2).
[3] 池莉.不谈爱情[J].上海文学,1989(1).
[4] 戴锦华,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J].文学评论,1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