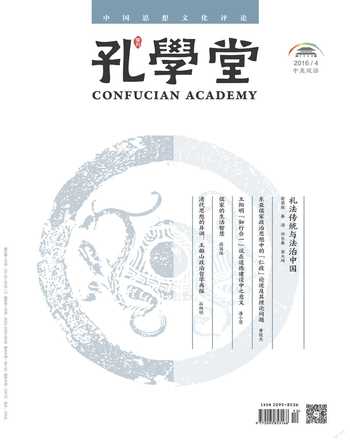律令体系还是礼法体系?
摘要:“律令说”由日本学者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认可。“律令说”虽然以中国古代法律语词为外衣,但其背后体现的仍然是日本人效仿大陆法系的历史过程所产生的“法典情结”;“律令说”的有效时段是魏晋到唐宋,这种对中国法律史掐头去尾,难以囊括中华法系的法历史;“律令说”只能用于表述中国古代刑事、行政方面的成文法,不能表述大经大法、祖宗之法、天下之法,难以涵盖中华法系的法体系;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从体系上看,包括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从历史上看,包括原型期、重组期、成熟期、衰落期四个阶段。
关键词:律令说 律令体系 礼法体系 中华法系
作者秦涛,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重庆 401120)。
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律令说”,并以之来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整体。20世纪90年代,“律令说”引介到中国,并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文考察“律令说”从产生于日本到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探讨了“律令说”的本质,并对之提出商榷,认为中华法系不是律令体系,而是礼法体系。
一、“律令说”的由来和盛行 [见英文版第30页,下同]
最早用“律令说”来研究中国古代法的整体,乃至整个中华法系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学者。
要想了解日本学者为什么会使用“律令说”来研究中国,我们先要知道“律令制”在日本的情况。日本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叫“大化改新”。隋唐时代,中国国力强盛,声威远播海外,日本人慕名而来,派出了大量的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他们发现唐朝有一部《唐律》,律之下还有令、格、式等法律形式。整个官僚系统就在律、令的框架之内有效运作,行政效率很高,他们就把这套“律令”制度引进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的孝德天皇效仿中国使用年号纪年法,定年号为“大化”,第二年就颁布诏书开始改革,这就是历史上的“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就从以前大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一跃成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律令制度是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制度建设,所以日本人对律令制是很有感情的。他们将大化改新以后的以律令制度作为基础制度的国家形态,叫“律令国家”。20世纪日本历史学家竹内理三主编了一本《日本史小辞典》,专门设有“律令国家”的条目,说:“大化革新时建立,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的日本古代国家,以律令为基本法典,故称律令国家。”日本比较早期的历史学家,比如桑原骘藏,也把日本的律令和唐朝的律令作一些对比研究。但是他们只是说中国古代有“律”和“令”两种法律形式,还没有提出具有理论内涵的“律令制”概念。
但是,明治维新以来,这一现象发生了改变。19世纪,西洋人仗着坚船利炮,打破了很多东方国家原本封闭的格局。日本发现,原先“大化革新”时学习的那套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此时已经落后了。日本以巨大的魄力和行动力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文化,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型。
在法律制度方面,西方有两个大的法系:一个是英美法系,一个是大陆法系。日本学习的是大陆法系。大陆法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看重“法典”的编纂,所以又叫“法典法系”。法典是把整个法律体系分成若干法律部门,比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然后把每个法律部门的所有法律文件都整理、审定一遍,去掉其中矛盾、重复的部分,系统编纂成一部基于共同原则、内容协调一致、有机联系的统一法律。日本人认为,法典是一种先进的法律编纂形式,是法律进化的产物,所以当时很多日本法学学者推崇法典。
但是,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不免于伤到自尊心。他们认为,西方有先进的法典,日本历史上有没有类似法典的东西呢?他们找到了律、令,想要构建一个概念,在古代的律令制和近代的法典之间,建起一座桥梁。这个概念就是“律令说”。
1904年,日本学者浅井虎夫完成了一部名作——《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这是早期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名作。这本书把中国古代的法律统统分装在“律”和“令”两个箩筐里面,说:“中国法典体裁上之特色,在其略有一定。养(原文如此,疑误——引者按)中国法典,得大别之为刑法典及行政法典二者。刑法典,则律是也。行政法典,则令及会典(包含《六典》在内)是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浅井虎夫虽然还没有提出“律令说”之名,但是已经有“律令说”之实了。
最早明确提出“律令说”的,应该是日本著名的法律史学家中田薰。1933年,中田薰在为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作序时,写道:“大概依据可否属于刑罚法规,而把国家根本法分成律和令两部分,这是中国法特有的体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田薰陆续发表了三篇有关中国律令体系沿革的文章,系统阐发了“律令说”。他认为:“所谓律令法系,是指由律和令两种法典形式组成之国家统治的基本法的支那独特的法律体系。”那么,中田薰的这些“律令说”,是基于中国什么时段的法律制度提出来的呢?他的后继者大庭脩说,“律令法”的概念是“中田博士在其晚年著作《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发展》一文中,根据唐代法律提出来的”。池田温则进一步探索这个概念的起源,认为中田薰“早在比较日本国固有法时,就将此作为概念使用”,而在战后又将之移作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由日本法制史学之父中田薰氏创造出了‘律令法这一名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作为法制史术语广为普及”。
中田薰提出“律令说”的概念,是开辟工作,来不及对一些问题进行仔细的论证和推敲。比如:用一个日本法制史的术语,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用一个隋唐断代法制史的术语,来描绘“上起汉代,下迄清王朝”的法制通史,是否有效呢?是否准确呢?有没有局限性呢?这些问题,中田薰都没有进行细致的论证。不过,这并不影响“律令法”的概念对此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者们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滋贺秀三很快接过了中田薰的接力棒。他的《关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1955)结尾部分根据唐代律令的情况明确提出,人们去判断一个法系是不是“律令法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律令法体系”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关键要看两个标准:第一,法律要分成刑法和非刑法,刑法就是律,非刑法就是令;第二,律只有一部,那就是律典,令也只有一部,那就是令典。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不是说有了律和令,就算是律令制度。比如秦朝、汉朝,虽然既有律又有令,但是不符合两个标准,不算律令制度,只算律令制度的前身。在中國古代,律令制度是在曹魏、西晋的时候成立的。在中田薰提出“律令法”概念短短几年后,滋贺氏就进行了这样精致的考证,并且对中田薰的概念进行了修正和响应,这就让学界来不及对“律令法”概念本身进行反思,就直接开始了更加具体的细部考证。
随后的60年代,西嶋定生提出了“东亚世界”的概念。他认为:在古代,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圈,叫“东亚世界”。哪些国家或地区是这个文化圈的成员呢?那要看它是否符合四个条件:第一,使用汉字,有汉字文化;第二,遵奉儒教;第三,国家实行律令制;第四,有比较昌盛的佛教文化。其中,“律令制,是以皇帝为至高无上的支配体制,通过完备的法制加以实施,是在中国出现的政治体制。此一体制,亦被朝鲜、日本、越南等采用”。西嶋定生的论说,使得草创未久、尚应争议的“律令制”概念跨出了法制史的研究圈子,超越了国界,具有了更广泛的文化与文明意义。
在此之后,堀敏一、大庭脩、富谷至等学者也对中国的“律令制”进一步精耕细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今,“律令制”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研究中国法制史乃至中国史的基础性概念与前提,研究者要是研究中国法制史而不知道、不认可律令制,那就是不入流的表现。2014年,大陆翻译出版了一套日本学者编写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其中《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分册就说:“所谓‘律,是指刑罚法规,‘令则是指有关行政、官僚组织、税制等与刑罚无关的法令”,“以律、令作为两个基轴来宣示权力的普遍性及统治的正统性,这样的时代就被称为律令制时代”。
虽然“律令说”在日本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但也有一小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保留意见,展开了冷静反思。最早进行反思的是京都史学派的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他在1977年写的一本普及读物《中国史》里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就是要研究事实。如果对事实加以提炼、归纳,抽象出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理论,那就要格外警惕。因为概念和理论一旦离开事实,可能就会“独立行走”。比如说,日本模仿中国制定律令,有了“律令国家”“律令制度”这些词语,但是我们不能以日本的情况来推测中国。就算都有“律令”这个名称,在自发产生的地方(中国)和将之引进的地方(日本),律令的存在基础和存在形态都是不一样的。宫崎市定的这段论述非常深刻,发人深省。
再比如,1985年日本出版了一部《大百科事典》,也就是“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里收录了“律令格式”“律令制”“律令法”三个词条。其中,“律令格式”词条说了中国、日本、朝鲜的情况,但是“律令制”和“律令法”两个词条,却只说了日本,没有写到中国和朝鲜。由此可以看出,《大百科事典》的编写者认为中国、日本、朝鲜都有“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这是事实;但是“律令制”“律令法”这样富含特定理论内涵的概念,可能只是日本的特产,未必适用于中国。
1992年,池田温先生主编出版了一部论文集,题目是《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以“中国礼法”与“日本律令制”相提并论,透露出对中、日两国古代法加以区别的认知。
不过,以上这些反思和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法制史学界是非主流。而主流的“律令说”很快就流传到中国来了。
中国的法律史学起步于清末。沈家本写《历代刑法考》,其中有“律令”九卷,分别考证律、令、科、法等法律形式的名称及自上古至明代的法律。民国时期,程树德继承了沈家本的法律史研究传统,写了《九朝律考》(1925),对已经亡佚的汉律至隋律进行辑佚考证。这两种著作,代表了擅长于辑佚考证的“汉学”传统和古代律学的传统方法研究趋向。它们对“律”或“律令”之名的选择,都不过是列举式的,并不带有建构理论的企图。
清末民初法制史研究的新潮流,是以现代法理学概念“整理国故”。其中开创之作,当属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4);而后续踵武的代表作,则有梁启超的弟子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以及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等。在这些著作里,律、令都只是作为一种法律形式的名称出现,不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和日本学者的“律令说”是有区别的。
日本学界兴盛“律令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逢共和国鼎革之初,中国大陆的法律史学研究也烙上了“革命法学”与阶级分析法的深深印记。由于显而易见的历史和政治原因,日本的“律令说”不可能流传到中国大陆,更不可能对中国大陆的法制史研究产生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法史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律令说”也随之映入了研究者的眼簾,引起了学界的青睐。1998年,张建国先生发表《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正式将“律令法体系”的概念引入中国学界。张建国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过多介绍日本学者对“律令说”的论述,而是对其进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修正。文中写道:“律令法体系是指以律令为主体、包括众多的法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体系”,“以律令法体系作为自战国(部分诸侯国)至唐代的中国法律体系的一种代称,还是比较确当的,同时也是有较高学术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在对自己论文修订后收入其《帝制时代的中国法》一书时,增加了一段“夫子自道”,坦陈引入这一概念的两大意义:第一,引入“律令说”可以避免“翻来覆去总是以某某为纲,靠某些定性语句构成的简单生硬的研究套路”;第二,引入“律令说”“有利于展开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和具有认真、严谨、扎实的学风的日本学者之间的交流”。
“律令说”一经引入,便迅速在国内学界占领了巨大的市场。具有较高学术权威性的《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的“法律史卷”也收录了“律令制”的词条:“律令制,以律、令为法的基本渊源的制度。以这种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国家体制为律令制国家。律令制起源于中国汉晋,并为周边国家所模仿。”有趣的是,该词条除上引寥寥两句涉及中国外,剩下的主要篇幅都在讲日本的律令制。
其他以“律令说”为基本概念的论著也层出不穷。从战国秦汉,到隋唐宋,再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的“律令制”都有学者在研究。粗略看来,这些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将“律令说”的适用范围自秦汉延至明清,贯穿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第二,对“律令说”中诸如“律令制”“律令法制”“律令法系”等等概念多属拿来就用,顶多略加介绍,很少对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诠释或研讨。
再进一步而言,还有很多研究以“律令说”为前提,提出了更多的推论:既然中国古代只有刑法典(律)和行政法典(令),可见中国古代没有“民法”,重刑轻民、民刑不分;既然中国古代的律令都约束不到皇帝,可见中国古代是一种独裁、专制、黑暗的人治;既然律令是中国古代的成文法,而中国古代还经常引用一些律令之外的法源作为判案、行政的依据,可见中国古代是罪刑非法定主义,是任情破法……正如宫崎市定所担心的那样,“律令说”的概念脱离历史事实以后,开始“独立行走”“结婚生子”了。
那么,“律令说”到底符不符合中国古代法的全貌呢?以“律令说”为前提的这些推论,到底能不能站住脚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律令说”进行一番正本清源的辨析。
二、中华法系不是律令体系 [34]
我认为,“律令说”不能涵盖中华法系的全貌,中华法系不是律令体系。要证明这个观点,就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律令说”不能囊括中华法系的法历史。[34]
中国古代法萌芽于上古三代,解体于清末,有长达四千年的法历史。“律令说”能不能用来认识中国古代法如此漫长的法历史呢?恐怕是不行的。我们先来看日本学者使用“律令说”这个概念的时候,通常是指哪一段历史时段。
先看“律令说”的鼻祖中田薰的说法。中田薰说:“上述律令法系,如果从时间上说,上起汉代,下讫清王朝,存续了约二千余年。”在持“律令说”的日本学者里面,中田薰所断的时限是最长的,但也只不过是把时间的上限定在汉代。其实呢,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汉代的律和令都还分不太清楚,从内容上来讲,律和令也不是刑法典和行政法典的关系,而是含混不清的。所以,滋贺秀三在考证曹魏律的篇目后,认为:“在魏《新律》编纂以后,历史上其实并不存在单行律。”所以他明确提出:魏晋律令“创造律令体系的最初形态”。滋贺秀三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从此以后,日本学者基本认同“律令体系”的时间上限是魏晋。
“律令说”引进中国以后,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者们普遍忽视日本学界对时间上限的讨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时间下限。作为“律令说”的引入者,张建国先生利用出土文献把“律令说”的时间上限上推到战国(部分諸侯国),而把下限限缩至唐代。他发现,“此后(指隋唐以后——引者按)律令法系嬗变的结果,与早期中国律的地位已有所不同,而令更是逐渐消失了。”所以在结论部分,他写道:“至少可以说,以律令法体系作为自战国(部分诸侯国)至唐代的中国法律体系的一种代称,还是比较确当的。”另外,高明士先生赞同日本学者的时间上限,而将比较严格的下限定至唐代:“拙稿所谓律令法,指令典成为完整性的法典而与律典成为相对关系的法典体系,……就律令法的实施而言,较具体可谈,辄为西晋及隋唐而已。”
为什么他们都说“律令说”的下限是在隋唐,而不是宋朝和宋朝以后呢?
因为自从宋代开始,“律”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令”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大明令》以后,就被废除了,朱元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令”这么一种法律形式了。所以,名副其实的“律令说”时间下限只能到唐代,而形式上的“律令说”也止于明初。
“律令说”是指的中国历史上哪一段历史时期呢?有长、短两种说法。短的说法认为,“律令说”的有效时段是魏晋到隋唐,只有600多年的时间;长的说法认为,“律令说”的有效时段是战国到明初,约1800年的时间。不管是持短之说还是持长之说,都有掐头去尾之嫌。
从“掐头”来看: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早在三代就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之经,礼与刑”的“礼刑体系”。就出土文物而言,“礼刑体系”至少在殷商已经初具规模,到周公制礼作乐、吕侯制刑,典章文物灿然大备,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礼法制度的早期典型。显然,“律令说”难以容纳这一段历史。
从“去尾”来看:宋代诏敕凌驾律令,律令的地位明显下降。元代没有律典。明初《大明令》之后就没有令典。所以,无论从实质来看,还是就形式而言,“律令说”都难以容纳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法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元以降的法制就没有特色与进步。日本学者就提倡“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中国学者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个阶段恰恰是“律令说”难以囊括的。
用“律令说”这个概念来认识中国古代法的历史,不仅有“掐头去尾”之弊,而且存在曲解之嫌。“律令说”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思维方式:唐朝的律令是“东方法制史枢轴”(仁井田陞语),而唐代律令制的模式形成于魏晋时期,所以魏晋以前的法制史只不过是律令制的形成史,隋唐以后的法制史只不过是律令制的衰亡史。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容易在“律令说”光辉的掩盖下,忽视不同时段法制的自身特色,而且带有历史目的论的嫌疑,从而恰如一叶障目,遮蔽了古代中国博杂而自洽的法体制整体。所以我们说:“律令说”不能囊括中华法系的法历史。
其次,“律令说”难以涵盖中华法系的法体系。[36]
古代中国的法体系博大庞杂,以前学界往往用部门法体系来表述,比如中国古代的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等;也有的用法律形式体系来表述,比如律、令、格、式、科、比等等。但是却很少有从中国古代法自身规律出发来归纳的。“律令说”虽然用的是传统法制的用语来命名,但是却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很难涵盖中国古代法体系的全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律令说”所谓的法体系,从产生渠道来讲,是国家制定法;从表现形式来看,是成文法;从内容来看,是刑事法(律)和行政法(令)。这不仅是“律令说”的视野,近代中国法制史学科刚刚成立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历史上的“法制”,也是这样看待的。
梁启超在中国法制史的开山之作《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4)中说:“成文法之定义,谓国家主权者所制定而公布之法律也。”所以在梁启超看来,“惯习法”“君主之诏敕”“法庭之判决例”都不属于成文法,不在论述范围之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如果查阅梁启超这篇文章的参考书目,就可以知道:他的参考书目里,除了中国的古籍以外,全是日本学者的著作,比如穗积陈重的《法典论》等等。而且梁启超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本人也正在日本避难。所以,梁启超的视角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是很深的。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者就产生了一个深深的“法典”情结,这个“法典”情结直接来自于“法典法系”,也就是欧陆的大陆法系。所以,从这一层渊源来讲,“律令说”只不过是为“成文法”或者“法典”这种视角,加上了中国式语词的外衣而已。为什么日本学者把“律令说”移治中国法制史的时候,会格外关注其时间的上限而忽视其下限呢?因为一直到魏晋时期,“法典”的编纂形式才告成立,而明清时“法典”的存在已经毋庸置疑,也就不必再管“律令”的有无了。
在这样一种“法典”的视野下,“律令说”难以看到古代中国法丰富多彩的法律样态。
首先,“律令说”难以容纳中国古代的乡规民约、家法族规——底层的“活法”。[36]
持“律令说”“法典论”者,常常说中国古代缺少私法。其实中国古代不是没有私法。中国古代的私法并不以律令、法典的形态呈现,而是大量存在于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以及习俗之中,是一种民间的、底层的“活法”。在古老久远的礼法社会中,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还无人不晓,是真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无法之法”。
以家法族规为例,费成康在撰写《中国的家法族规》的时候,仅仅过目的家法族规就有“上万种”之多,该书附录里收了55种家法族规,各具特色,可以窥其一豹。再以契约为例,据学者“保守的估计”,截至20世纪80年代为止,仅“中外学术机关搜集入藏的明清契约文书的总和”,“也当在1000万件以上”。如此庞大数量的契约文书,如果说其背后没有一种“私法”在起作用,是不可想象的。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习惯法还有宗族、村落、行会、行业、宗教寺院、秘密社会、民族习惯法等。清末至民国时期,为了制定民商法典,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进行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先后编纂成《民事习惯大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里面收录的那些“习惯”,全都是活在社会中的规则体系。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撰写《中国家族法原理》的时候,也对已往的方法论进行反思。他说:“旧中国的私法那样的研究对象本身,我认为带有不能接受法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的那样的特性。”而这种“法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正是“律令说”与“法典论”的基本立场。所以,处在中国古代法体系底层的丰富多彩的“活法”,难以进入“律令说”的法眼。
其次,“律令说”难以容纳中国古代的大经大法、祖宗之法、天下之法。[37]
日本史学家西嶋定生的说法:“律令制,是以皇帝为至高无上的支配体制。”其实在中国传统法理中,皇帝并不是最高,律令更不是。比皇帝和律令更高的“高级法”“法上法”“理想法”还有天道天理、“先王之法”和“天下之法”、“经义”和礼制、祖制和祖训,等等。
天道天理是帝制统治和立宪定制的根本法源,所以有“奉天承运”“口含天宪”之说。
“先王之法”和“天下之法”是上古的圣王,比如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作为评价当时政治法制的标准。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用先王之法、天下之法来批判秦汉以后帝制中国的法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经义、礼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创法立制的成果,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一般被尊为“大经大法”。祖制和祖训统称“祖宗之法”,是本朝列祖列宗创法立制的成果,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又可以表述为“先祖法度”“祖宗故事”“祖宗家法”“祖宗典制”等。在律令之外,大经大法、祖宗之法也都是司法、行政的重要依据,甚至会成为终极依据。
以经义为例。经义是议政议法的重要依据,也是司法、行政中高于律令的直接依据,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又称为“经义决狱”,是西汉董仲舒首先倡导的。史书记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两汉时代,从事“经义决狱”的代表人物除了董仲舒以外,还有公孙弘、兒宽、应劭等。
到了晋朝,当时人提出来一种制度设计:基层“法官”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文,不允许搞例外;但是对于少数“事无正据,名例不及”的疑案,允许朝廷大臣来“论当”,也就是通过讨论的方式,来寻找一个恰当的判决。大臣依据什么来“论当”呢?东晋主簿熊远在奏议中说:“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大臣们要么引用律令这些成文法,要不然就必须符合经传、以前的判例。到了北魏,“经义决狱”进一步制度化:“诏诸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由此可见,在“律令体制”成形以后,“经义决狱”的遗风尚存。法史学界有一种比较通行的看法,“春秋决狱”到唐朝以后就式微了。作为一种定谳依据,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议刑议法的理论依据上看,经义仍然发挥着权威依据的作用。以唐代翻来覆去争议的是否允许复仇为例,韩愈的《复仇状》、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无不征引经义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比如康买得复仇案,最后宣判“减死一等”,而依据就是“《春秋》之义,原心论罪”。
礼制在中华法系的法体系中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宪法学者张千帆先生对“礼”进行考察后认为:“总的来说,宪法是对‘礼的最合适定性。”来自部门法学者的眼光,对我们反思中华法系不无启迪。
再看“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主要是开国君主制定,用来约束包括后代君主在内的最高统治者的“家法”。比如说,汉高祖刘邦曾经杀白马为盟:“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不是姓刘的,就不能称王;没有立功,就不能封侯。如果有谁不遵守此约定,天下人一起讨伐他!“白马之盟”曾经被大臣们引来反对吕氏封王,反对封王氏外戚侯,反对封匈奴降者侯等,在两汉历史上起到了强有力的规范作用。再比如,宋代有一个“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宋太祖有一个约定,刻在碑上,藏在太庙里面,说:我朝绝不杀大臣,绝不任用宦官,违反者不祥。又比如,清朝的顺治皇帝曾经“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也就是让工部在宦官办公的衙门口树了一块铁牌,上面写着:严禁宦官干政,否则凌迟处死、决不宽贷。类似于这样的祖训、祖宗之法,史不绝书。这些祖宗之法的效力位阶要比一般律令来得高,后世的君主非但不能违背,而且轻易不得修改,否则会遭到巨大的舆论压力。
另外,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一套规则体系,不是“律令说”所能够容纳的,有学者称之为“天下法”。从宋《册府元龟·外臣部》体例来看,其内容包括封册、朝贡、助国讨伐、和亲、盟誓、纳质、责让、入觐,等等。“天下法”以政、刑、礼、德为基本要素,由此而展开结合、统治、亲疏、德化诸原理的运作,从而建立天下体系。违反“天下法”的制裁手段,就是“大刑用甲兵”的刑。
综上所述,来自日本、流行于中国的“律令说”,难以囊括中国古代法的法历史,难以涵盖中国古代法的法体系,以“律令说”认识中国古代法,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我们指出这些,并不是要弃“律令说”而不用,而是试图对其适用范围加以限制,从而更好发挥其功用;同时探索出一套更加符合中国法律史实际的概念体系,为中华法系正名。
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系 [39]
中国古代法不仅仅有“律令法”“律令体制”,还有“大经大法”“祖宗之法”“天下之法”,以及规范普罗百姓民事生活时空的大量民间“活法”。中国古代法不能归结为“律令法”“律令体制”“律令体系”“律令法系”,而是“礼法”。“律令”生于“礼法”,合于“礼法”,“礼法”统摄“律令”,包含“律令”。借用“律令说”的话语方式,它是一种“礼法”法,是“礼法体制”“礼法体系”。
“礼法”不是“礼”和“法”,或“礼”加“法”,也不是指“纳礼入法”,或“礼法融合”。“礼法”是一个双音节词汇,一个名词,一个法律学上的法概念,一个法哲学上的范畴,也是古代“礼乐政刑”治国方式的统称。质言之,“礼法”即法。确切地说:“礼法”是古代中国的法。
前面我们说过,“律令说”难以囊括中华法系的法历史,难以涵盖中华法系的法体系。那么,礼法能不能做到这两点呢?
首先,礼法能够涵盖中华法系的法体系。[39]
成熟状态的礼法体系包括三个子系统,分别是礼典子系统、律典子系统、习惯法子系统。
礼典子系统,包括国家颁行的成文礼典,还包括各种典章制度、仪文节注,以及在长期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惯例和礼仪惯例。礼典子系统,不是某个皇帝心血来潮编撰的结果,恰恰相反,皇帝要受到礼仪的制约。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截取明代的一个普通年份,来展现整个帝制中国时代的运作常态。书里说,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一生中要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参与、主持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从每天的早朝、经筵,到每年的籍田礼、祭礼,到自己的冠礼、婚礼,不一而足。对礼仪稍有违反,就会遭到大臣的进谏和纠正,比如明代的“大礼议”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那么,这些礼如果不是皇帝制定的,是哪里来的呢?礼的来源,一般有两大部分:一是历代相传的礼制。这些制度,可能来自古老的夏、商、西周,也可能经过历朝历代乃至本朝的损益增删。二是圣贤的经典。三代的礼仪、礼制、礼义,在先秦“轴心时代”经过圣贤的整理和提升,制定成了经典。这些经典,是考正本朝礼制的理论标准。每当遇到现实的制度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大臣们总是习惯于回到经典中去,汲取圣贤的智慧,再活用到现实中去。每一代的士大夫,都阅读着同样的经典成长起来,形成了具有类似价值观的共同体,他们结合本朝的现实问题,以经义为理论标准,改造历代相传的礼制,就制定出了本朝的礼制。经过皇帝的认可和颁布,就是本朝的礼典。礼典本身只是正面的规范,不带有负面的罚则。罚则主要通过律典子系统和习惯法子系统来规定。
律典子系统,包括国家颁行的成文律典,还包括令、格、式等成文法律,以及狱讼判例。中国古代的礼和律,并不是并用的两种手段,而是有先后之分、本末之别,礼先律后,禮本律末。先用礼来预防、引导、规范,可以使得绝大多数的行为都纳入常轨。还有极少数难以为礼所化的行为,再动用律的强制力加以制裁。如果单独动用律,那就是儒家所反对的“不教而诛”,是陷害老百姓的表现。而最好的治理状态,就是礼能够预防几乎全部的犯罪行为,使得律典、刑罚不起作用,这叫“刑措”。措,就是放在一边的意思,刑罚放在一边不用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清平盛世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
武王灭商以后,殷商遗老箕子曾经传授给武王一篇统治心法,叫《洪范》。《洪范》把一个国家的制度分为八类,叫“八政”,排列顺序是: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其中,内政是前六项,也就是先要让老百姓有饭吃(食),有钱花(货),有精神生活(祀),有房子住(司空),受教育(司徒),如果还有人铤而走险犯罪的,再加以刑事制裁(司寇);外交方面,也是先礼(宾)后兵(师)。唐朝有一部政书叫《通典》,一共包括九个分典,分别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排列顺序也是:先让百姓有吃有用(食货),再通过推举考试的方式(选举),组成政府(职官),以礼、乐进行教化,用军队保障安全(兵),如果还有人铤而走险,那么用“刑”来制裁。这是律典子系统在礼法体系中的位置。脱离了礼法体系的律典系统,就会变成专任刑法的暴政;礼法系统统摄下的律典系统,才是天鹅绒手套中的铁拳,“以生道杀人”,使老百姓“虽死不恨”。
习惯法子系统,包括礼法社会底层的各种形式的“活法”。这些“活法”主要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俗”,经过士大夫的改造和上层文化的熏陶,“约之以礼”,逐渐形成的合于礼法的“活法”。中国自古以来,中央政府就是一个有限政府,讲究“皇权不下县”。政治权力不能一竿子捅到底,不能用行政手段、政治权力去干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底层形成了一种“自治”的秩序。一家有家法,一族有族规,一乡有乡约。这些“活法”,有很强的地域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些“活法”,又有很强的共同性,都不能违反国法,都要合于礼义。这些“活法”,未必形成书面的白纸黑字,但即便是文盲也能够轻易了解,自觉遵守,日用而不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其次,礼法能够囊括中华法系的法历史。[41]
从原始习俗到礼仪、礼制的初成,再到“礼法”的提出和“礼法体系”的成熟,又最终走向衰微,曲折跌宕,贯穿整部中国法律史,从大体上来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型期(夏、商、西周)
夏、商、西周,史称“三代”,这一阶段的礼法体系表现为“礼-刑”结构,“礼”就是夏礼、殷礼、周礼;“刑”就是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周朝的九刑。“礼-刑”结构的运作模式是“违礼即违法,出礼则入刑”——你违反了礼,就等于违反了法,那就要受到刑的制裁。这是礼法的原型期。特点是:礼刑一体、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出礼入刑。当时还没有发展出后世精密的礼典、律典系统,礼法的法体系还处于萌生阶段。
第二阶段:重组期(春秋—秦汉)
通常的说法是,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这是以儒家为视角、从负面进行的评价。如果从整个礼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来看,这一阶段是旧的“礼-刑”结构的礼法形式的崩坏,而律典系统则开始生长壮大,从而催生着新的礼法结构和帝制时代的“礼法体制”。
汉代开始尊崇儒术,陆续重拾礼仪。由于春秋战国到秦代的律典系统规模初现,一时成为法律思维定式,以至于弄得其复兴之礼典却无处安放,只好统统称之为“律”。比如叔孙通制定的“礼仪”称为《傍章律》,赵禹制定的“礼仪”叫作《朝律》。正如章太炎所说:“汉律之所包络,国典官令无所不具,非独刑法而已也。……汉世乃一切著之于律。”与礼、律在形式上相混同的同时,是礼、律在精神上的分离。“引礼入法”只能通过司法领域的“春秋决狱”、律家的律章句等方式从侧面切入,个案地进行,而无力制定一部真正的礼典和渗透礼义精神的律典。所以两汉时代虽然已经独尊儒术,但是仍然只能称之为礼法的重组期。
第三阶段:成熟期(魏晋—明清)
“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曹魏《新律》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编纂的律典,也是第一部儒家化的律典。曹魏后期司马氏执政,开始制定《新礼》,到西晋第二任皇帝晋惠帝的时候颁行天下。西晋《新礼》是“中国第一部依据儒家学说体系编撰,而且是由国家所正式颁行之礼典”。从西晋的《新礼》和《泰始律》开始,此后的王朝在开国之初,大多都要同时并举礼典与律典两项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而有雄心壮志的帝王也大多都要重修前代的礼典、律典,比如南梁《普通礼》与《天监律》,隋朝《开皇礼》与《开皇律》、《仁寿礼》与《大业律》,唐朝《贞观礼》与《贞观律》、《显庆礼》与《永徽律》、《开元礼》与《开元律》,宋朝《开宝通礼》与《宋刑统》,明朝《大明集礼》与《大明律》,清代《大清通礼》与《大清律》等。总之,这些王朝无不以“制礼作律”为功成治定的标志。这就是帝制中国“礼-律”结构的礼法体系。所以,从魏晋到明清,是礼法法系的成熟期。
第四阶段:衰落期(清末以来)
穷变通久,久则不免于僵化。自明清以来,专制集权加强,君主自毁礼法之精神,墨守礼法之形式,致使“制礼作乐”沦为粉饰太平的道具。西方法系强势入侵,保守派却不知变通而固守成规,错失了变法良机。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下,中华法系走向解体,礼法也就此湮没不彰。
近现代中国,列强欺凌,战乱频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其所遭受的“礼崩乐坏”远甚于孔子时代。中华文化数千年之道统毁损,法统断裂。为护持华夏国权国域祖产和民族血统文脉,从“师夷长技”到洋务运动,从君主立宪到共和立宪,从开明专制到军政、訓政、宪政的建国方略,从实业救国到主义救国,从维新改良到共和革命,从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师法欧美到“以俄为师”……志士仁人不避血雨腥风,不懈探索,从未停滞推进民主、科学、宪政、法治的步伐。
剥极必复,贞下起元。我们终于等来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宣告。它意味着法制和法学领域迎来了根本性的转型:从过去崇尚以维护阶级专政为目标的革命工具型法制,转向构建“良法善治”的治理型法制;从过去着重于移植欧美或苏俄的移植型法制,转向与人类民主法治文明相向而行又富有中国范儿的特色型法制。实现这两个方面转型需要上上下下的齐心协力。道统绍续,法统维新,政统重建,时不我待。就其学术层面而言,认识中国法律史的自我,破解中国古代法的遗传密码。非此,无从有效吸纳传统法文化“良法善治”之智慧,而特色型法制如果不能得到中华五千年传统法文化的支撑,也无疑会成为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