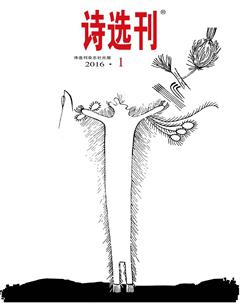重温田间的《抗战诗抄》
刘向东
1949年9月,诗人田间编就《抗战诗抄》,次年出版,窃以为,这部诗集与早已声名远播的《给战斗者》相比毫不逊色,最能体现田间先生诗的风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再次看见有那么多报刊重印了田间的“诗传单”《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成为一个特别文化现象。同样特别的是,除了特别的纪念,多年来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诗人圈子里,一提到田间和他的诗,就有人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是过时了。真的过时了吗?我看未必!不断重温,越看越觉得先生的诗有诗性和血性,形象,让我一眼就看到了握着枪的诗人,拿着笔的士兵,看见他们在马兰纸上,在墙头上,依旧排着出击的队形,从血管里喷出鲜血,从枪管里喷出怒火,那是对现实的确立,对历史的命名,是血写的诗经。
像《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那样的诗,多么有力、自然,多么简明、深刻、令人振奋,只需看一眼或听一遍,就牢记终生,刻在骨头上。1994年11月,河北省召开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时任文化部长王蒙和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接见十位代表,谈到田间先生的影响力,王蒙问,谁能背诵?大家便异口同声声情并茂地朗诵起来: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对于田间个人来说,这是一首“小诗”,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无疑是催人奋进的鼓点,也可以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
田间写在民族危难时期的街头诗、诗传单,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了都会感到惊心动魄,铿锵的声音,四两拨千斤,对整个中华民族说:你永远也不要对侵略者奴颜媚骨,不然,你就是让人家活活捅死,也会被指着骨头斥为贱骨头、奴隶!这样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激发无数人保家卫国。这些诗,从先生的心中产生,从他的骨肉中产生,而不是从他对某个事物的观念产生。他首先是一个战斗者,然后才是诗人,他是在取得了一个合格的战斗者的资格之后才取得了诗人资格的,这本身极为重要。
在我们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田间没有半点犹豫和徘徊,他坚定、勇敢、迅速地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正如他在《义勇军》-诗中所描述和在《保卫战》中所号召的,他的横枪跨马是身心一体的,他面对纸和笔也是身心一体的,他为之奋斗的,远远高于个人生活的范围,他所关心的也远远不是作为诗人的事业,因而,在国难当头,在共同的仇恨比爱情、友谊之类的文字更能号召、鼓舞、团结人民的时刻,他的诗是武器,是民族精神和心灵的代言。几十年之后,当我们重新读他的这些诗,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的一瞬感受到永恒,我们会感到他的诗所代表的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趣味,而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拥有并需要长期拥有的血脉和魂魄。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能够拿来与田间先生这些诗媲美的类似题材的诗作不多,记忆深刻的有两题,一是前苏联P.鲍罗杜林的《刽子手……》,可谓异曲同工:
刽子手……
充满了绝望神情的眼睛。
孩子在坑里恳求怜悯:
“叔叔啊,
别埋得太深,
要不妈妈会找不到我们。”
一一选自《苏联抒情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守仁译
另一题是《哪怕我们必死》:
哪怕我们必死,也别死得像猪,
被兜捕到肮脏地方关入栏圈,
疯狂的狗围着我们乱吠狂呼,
把我们悲剧的命运当作笑谈。
哪怕我们必死,也要死得高贵,
这样我们宝贵的血就不至于
白白流失;甚至我们抵抗的恶鬼
也得被迫对我们的死表示敬意。
哦同胞们!我们必须共同抗敌!
尽管众寡悬殊,也要现出勇气,
挨打千次,也要回敬致命的一击!
即使面前是坟墓又有何关系!
面对残暴又胆怯的匪徒,像男子汉
退到墙根,即将死去,也继续作战!
——选自外国文学出版社《美国现代诗选》,赵毅衡译
这是美国诗人克劳德·麦开最为人传诵的一首诗,曾被丘吉尔在向英国议会报告战况时引用,成为反法西斯的战斗口号。但麦开写作此诗的原意,却是为纪念1919年黑人暴动,说来别有一番滋味。
离开历史的思想和诗篇是不存在的。尽管时过境迁,我们仍然有必要研究田间的诗、田间的行为,这才是对历史负责。有学者道:“有一个奇怪的文学现象:抗战初期前线战况持续恶化,而后方诗歌界却普遍乐观和欢欣,这鲜明比照的形成是,在全民抗战的呼吁中寄寓着民族新生的历史要求,抗战怒潮造成了近百年民族积郁的总爆发。所以,诗人们要求成为战士,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说法固然不错,作为特例,田间却另当别论。有别于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的是,他是真的投入到枪林弹雨中去了。在河北文学馆征集史料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田间,当时真正和士兵一起拿起真刀真枪投入战斗的诗人寥寥无几。我想这才是为什么田间在诗中从不表现趴下的中国人,而是有力地表现站着的中国人、视死如归的中国人的原因吧。“只要我们一个村庄,/受到/突然的包围,/老婆子呀,/小伙子呀,/统统扑过去,/(横竖是死)/就是死吧,/尸首还在家乡,/像活着一样地歌唱!”(《保卫战》),悉心比较,这和他的同辈诗人的同期创作形成差异,即便与同样被称作战士的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相比,也有着根本的不同。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回过头去看,并不是那个时代一过去,那个时代的诗人也就可以放下了。尽管我们反映抗战题材的作品众多,但至今表现我们民族英雄气概及直接打击侵略者的作品不多,尤以诗画为甚,倒是常常表现我们失败了,兄弟被打死了,姐妹被蹂躏了,有的美术作品表现的是中国人被日寇杀死后的成堆尸体,竟然得了奖。表现中国人的失败和耻辱,而不努力去反映中国人打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不表现中国人战胜侵略者的场面,不歌颂中国的勇士们顶天立地、气震山河的形象,并形成一股风气,这问题说来非常严重了。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总是缺少明确的核心价值、精神结构和心灵深度,又无天骨开张的胸襟、气度、信仰,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但凡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赤诚的诗人或读者,投入地去读一下田间先生的诗,心灵就会被震颤,同时也会感到,作为中国新诗的前辈诗人,田间自有他独特的魅力。他是唯一的,自成一体的,无可替代的,更是我辈望尘莫及的。
当然,从根本的性质上来说,诗歌无疑是想象和虚构世界的艺术,有一定鉴赏力的人,大体不难区分侧重于存在的具象的诗歌与侧重于虚构的想象的诗歌。田间的这些诗,是“呱唧就是”的诗。或许不是他不会运用比喻性语言的迂曲和暗示的表述方式,大敌当前,让一首诗变成一个喻体是不可思议的,他让他的诗直接指向真实,是需要,其实也是能力。他的诗中那极致的部分不是靠修辞和技巧推动的,而是靠生命固有的气息,命运中深刻而独特的遭际,即那惟一的、无人可取代的“命定性”来推动的。
这再次使我想到,我们的文学观里多年以来一直滋生着这样的一个念头,说是不能与现实靠得太近,太近了,其作品的文学性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受到质疑,因为我们很多文坛的老前辈是有教训的。我觉得根本问题不是离现实近不近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方法问题,说到底是襟怀和气度问题。田间先生的抗战诗抄,抓住的是民族大义最本质的东西,你有权质疑它,但是谁又奈何得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