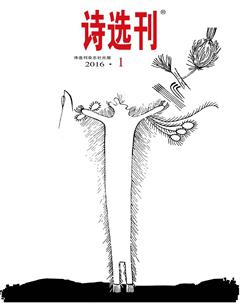江南民居:朱厅弄12号
王学芯
我走向一个陌生而又并不陌生的地方,作为一个或者许许多多人的曾经存在,江南民居已经消失,我三十年栖息的光阴也已枯竭。记忆的弦,在纤细的安静中,我感到过去的门正在为我又一次地打开。
——题记
1
从寻找到寻找 一道墙的界线
砖的背脊 积成致命的血压
血地被水泥密封
楼群突兀起伏 刺眼的玻璃
像锋利的刀 割完过去
挂在天际线半空 闪着冷冷的光
只有湿气和运河 没有
名字的呼唤 沉浸在江南风里
民居就是血脉 颤动的草
构成形体和眼皮 回忆中的沮丧
两手空空 雪白的衣领
在绿荫大道翩翩飞出
没有一只蟋蟀在高楼的墙角发声
砖已不见迁移的静止
蟋蟀是民居的缩影
血地过去落下的一点红
失去了隐现在墨水中的灯
此刻 内心的体腔变小
我带着几十年风雨中的头发
在疯长的楼房边停下
每一棵不知身在何处的树
显示慵散的脸庞 上升一种
虚无的睡眠 在渐变的星光中
一滴江南民居的光阴
熄灭在江南储藏的天空
石头的钟点
在石头内部沉淀
一个祖传的家族之后
手握不紧一块墙砖
房子倒毁之后椅子倒下
废墟泡在水里漂走
随同江南小巷的光线扭动
闭上江南民居的嘴唇
江南一粒血地的种子
在靠着运河的水边吹走
2
地名像日历撕走之后
不可修复的触觉开始了疼痛
唤起的意识被
混乱的小巷团团围住
那寸土之地
天井吸着天空的雨水
屋檐下的广阔 穿进针眼
天井大的事情 转动
四间房子的轮子 自我的转化
我像一只飞翔的鸟
拖着翅膀 触到墙头
在砖地上扑腾
岁月是没有失眠时光的长长影孑
而屋子里的腑脏
血脉忽强忽弱地搏跳
红布里的地契在樑椽上融化
一缕鲜红的光 变成发亮的钥匙
夜以继日 对着世家的锁眼
咀嚼五光十色的日子
伸进煎熬的黑夜
墙!每一层砖的暗缝
把光的喉咙涂得发黑
围合的深处 我每天跟一只
没有纸罩的灯泡说话
说得太多时 我的心脏肿胀
故意恍动光影
改变投射的沉寂
让手边的钟
跟任何影子缠结一起
变成可爱的事物
时光就这么流逝
一滴凝滞的金黄色水源清冷
我停顿过一次脉搏
3
门的缝隙 在时光里开裂
弯折的光线 做成
耳朵和眼睛的词语
由里往外 我听见天空的叫喊
从门缝里的世界
看见一缕芬芳的烟
长着牙齿的眼睛 由外往里
从门缝的一声光里
目光像很薄的指甲
那种用眼睑摧毁世界的
窥视我看到了
一只捕鸟器
那种营巢于过去
或者现在的荆棘
在隐秘中我们拔不出来
我们每天血肉里的门缝
光有任何感觉
我无任何感觉
4
没有一张老照片 镜框空白
夜在流转 祖辈是
迷蒙的月色。珍藏的一只杯子
祖辈在杯里隐藏
水是永恒的空气
生命中的水 等候一切的视觉和听觉
补上时空的面对
现在我用手指轻点着水
水波开始流动
波纹向着一些迹象
瘦瘦的身躯整体显示出来
我凝视长久
喝下一幅影像
手指再次触动着水
出现的眼睛有神 对着世界微笑
像鱼在运河的水里游泳
穿越了无所不在的波浪
颤动的杯子 泛起细小水泡
水泡居中 环视杯中的元气
像在民居的天庭
吸着脉搏里的气息 看一看
现在家况如何
一杯水的力量重新成为一切
杯沿上的嘴唇
全部是没有年龄的花朵
包括我 居住在这个杯里
在自己的入口 祖先
清晰的人影一个一个涌来
在月下散步只是他们
一个转身 手摸不到墙
目光飞快地分割
杯子装满了眼睛的碎石
最后一只杯子从高空脱落
追赶上了江南民居的终结
5
遗产凝视落日的遗嘱
落日后的遗嘱
没有在我耳边升起
遗产是四个平行空间的天地
遗嘱是灵魂的灯光里
没蘸墨水的毛笔
遗产是真实的存在 遗嘱
是视觉离开光亮
藏在胸口的内部幽深
遗产安静地躺下
遗嘱像天上的流云
被关紧的窗隔开
遗产是无字的白纸
留在一片寂静之上
遗嘱让发热的空气冷却下来
遗产说:白色的墙闪光
遗嘱的松动
墙会在瞬间支离破碎
终于在一个节日
我离开我的遗嘱日子
走上没有遗产的大街
6
雪来了。那是这个月
父亲寄来的信笺吗?
我需要信封里五块钱的生活费。
信是晚上送到的。
我拆开每封等待的信 黑色的纸上
是白茫茫的字
每个字棱角分明 都是书房里的自语
飘着羽翅的影子
我把一封封信放下 一封封信
像吹来的叮嘱
在围墙上堆积
那个夜晚 我呼吸凛冽
用哈气温暖着手
墙一次闪动 发出一声怪叫
看不见的墙在窗边倒塌 踉跄的时光
原本很轻的雪
变得特别沉重
我的双手插在裤袋里
人变成霜冻的冰棱
而巷子幽暗
雪片谜一样凌乱
那年我十五岁了
7
视线开始模糊 眯起眼睛
想看清一个字 我寻找自己的眼镜
祖辈的眼镜遗忘在抽屉里
他们找不到眼镜
就闭上了眼睛
我看不清一个字
愈加想看懂
一个字的制成
这现实的一个字
虽然是巨大的谜语
但它靠得我很近
一只手揉动眼睛
另一只手翻遍傍晚的空无
我在来回一步之内发呆
迷漾濛的天光
在头顶像雪一样落下
祖辈的眼皮在我脸上重现
一个字隐在雾里
像在答复我寻找的眼镜
我从这个字开始
忘记自己的明析
用镜框去遮掩目光
8
猫翻动瓦片 雨水滴在
床上 铁的颜色溅进搪瓷脸盆
响起巨大回响
我以后的漫长雨天
雨都会飞出那种破碎的闪光
让黑夜抹不掉阴影
天长日久我在瓦片上行走
脚有树叶的轻 捕捉
猫用力发春撼动瓦片的残迹
那时候 收拾好瓦片
完成雨和床的分离
如此而又重复地飞
一只潮湿的猫躲在远处看我
像我面对生活
但它不明白我的手为什么乌黑
这样我耗尽当年的雨水
一次再次 听不到屋内的雨声
达到致远 我又看见那只猫
它找不到瓦片
藏在楼群间的灌木深处
独自如一朵
很卑微的光
9
在江南的民居小巷 一个男孩
用扁担拖起两只水桶 肩胛上的血
听见路面被水湿透
男孩屏住呼吸
在重量中长高
缸又见底 雨水被风吹得很远
压迫的叹息 男孩在墙角挖井
泥土围绕光阴上的手指
水看见了天空
暑天歇下来的静止
在初春的水里熄灭了火
夕阳变成水泥杆上的路灯
蛾虫围成了棋局
一个男孩的双脚浸入两只水桶
抓住光中的夜在墨汁的笔画中
让长硬的骨骼
穿上诗人的鞋子行走
10
祖父一个西式药柜 几只
精致的玻璃小瓶像父亲书架上
《审美学》的精髓
从肉体和精神
阻拦生命的枯萎
从我这第三代开始的桌上
阅读和诗的姿势显示我在延续
西药一丸救命
美学像进入隧道 眼前的光线
是暗还是明亮
张开还是睡眠
而那一致的抚慰 从我的诗里
正在来临
这个傍晚 我跟祖父和父亲
说了些话 开始同许多诗人
闲聊诗歌在一些
非常不同的水平上 我说
诗是冰冷的铁上锈出花朵
在花茎里注入血液
以心尖上的痛缝合衬衫和苍穹
或者把自己竖直起来
割出自己的血
让旗杆变成一面旗帜
此刻 在黑暗的夜晚
我的额头调亮黎明的光
一只清晨的鸟
从窗帘缝里看到坟墓和山谷
树枝 在潮湿后燃烧
除这一切 幽远的风吹过田野
它不会带我们坐上山丘
11
揣摩已久 终于暴露欲望
切割一块完整的平行空间
像咬一只苹果缺口就成了磨刀石
近邻实现牙齿的霸权
我捏紧心跳沉默
齿印的羞辱让我记住九平方米的邪恶
直到近邻年轻的儿子背脊佝偻
一个女儿嚷着提前出嫁
直到一天整个空间告别江南民居
近邻三兄弟为一间新房电闪和雷鸣
我突然懂得原始中的无情
可以无罪
12
姐姐从这里出嫁
我一个人透过老式的小方格木窗
看到手掌大的花坛
被几株摇曳的花融化
我居然没有言语
推开窗子 用窗钩把两扇敞开的窗
钩住 花坛上的绣球花正在发生变化
花瓣裹成小球
靠在月季一边没有疏远
那种紧挨的尺度
就像拇指和食指
在一只手套里弯动
走近了花坛 月季的红
显得那样幸福 一声嘟哝的开门
我触摸到月季的枝杆
手指开始疼痛
过后的瞬间 变得
月季的红一模一样
后来我一个人创造了诗歌
把月季和绣球花插进汽水瓶子
放在孤独的窗边
13
祖母的手。偌大的房子。无数角落,
藏好隐秘的零食,坐在那里
两手空空。
现在看起来
我是奇才。角落没有幽暗
一只眼睛里的嗅觉
经过另一只眼睛的光芒
世上最美好的事
就给了我最愉快的一天
一切的无痕
重复地演绎
存在和不存在的荒诞
祖母哑然。我或是一只
轻轻经过饥饿墙角的猫
14
我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
睁开眼睛 看到北京第一只灯泡
也是这个日子 我成为江南民居储存的血脉
祖母的气息做了我的皮肤
目光成为依赖的空气
这个日子我会吃到面条和鸡蛋
面条拉长万事万物
蛋清的月色浸透每颗升起的太阳
而酱油色的汁液
一年比一年黝深
这个日子 巧合我许多巧遇
小学毕业。意外的打架鼻梁偏向左边
巧合祖母去世 我的脸
陷入一只黄蜂的翅膀里
巧合一只脚走出师范 另一脚
跨进大学。巧合居住的房子倒坍。
巧合梅雨季节 被人误解
巧合一次醉酒 拆散
三本笔记本 那一切驯化
和遗忘的事情……
这是流水中的节点
这个日子我明白自己做了什么
我不会忘记自己的方式。
不管怎样这个日子站立不动
但每年的间距 正在
飞快靠拢 或者接近重叠
七月三日:我的生日。
15
江南民居:朱厅弄12号
一个掉着头发的客厅,两个天井
经常流泪,三个书香的房间,
侧房稻草潮湿
灶间等待柴烟
那刻着143平方米的契印
是清末明初的玉石
门牌泻下我脸额上的光
墙如石子沉入井中
光阴没有一丝皱纹
现在记忆中的绒毛吹来
抽出来的光泛白的虚影
是强光里的黑色
一只三岁的皮球皮球
碰撞了门反射 白色的瓷器破碎
拖拽出震响的叹息
祖母越走越慢 如同枯叶
飘在老屋的床上一丝目光
比被子上的棉线更细
而红色的天气低垂
房屋变得愈加没有深度
从幽黑抽屉里抽出的金条
悄然跳进夜深的运河
金条坠入水中 祖母的神色飞扬起来
坐回客厅的椅子
脸 慈祥动人
门再次吱吱地响
祖母穿戴好衣服和帽子消逝
天上的雨水 顺着地上的缝隙
流淌到我的床边
闪现的光中 墙开始倾斜
钙化的墙面从每块砖的缝里
长出白色的蝙蝠
翅膀一只只凋落……
一个没有了过去的现在
遗忘是最好的平静
那三十年的光阴 各种颜色
像铁皮火车 在加速演变
划出灰黑的时光 而再加速
进入隧道 那背去的影子
已在钱币一样大的孔中
最后消失
仅存的一点虚影
仅在偶尔幸存
没有注解的江南民居
像本书已被好多人读完
而我再次翻阅 肯定不是
我一个人的眼睛
或者我一个人的开始
我的江南民居:朱厅弄12号。
风再次吹来
我在大街上来回走着脸
感到湿润
被楼截断的风 弄反方向
回旋成一只陀螺
过去在现在的时间
永远是过去光阴在幸福中枯竭
世上一切都已明明白白
双手拨开那些诉求 剩下的
就是好好生活
就像我的眼睛
退出偌大的空间
眼泪是被风刮出来的水珠
门环忘记为风开门
雨中的瓦片已没有
喝水的嘴唇
我的那道门离开
是干净的大街
脱掉的一只旧鞋
现在周围新鲜的景象
芳香的风温润
多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