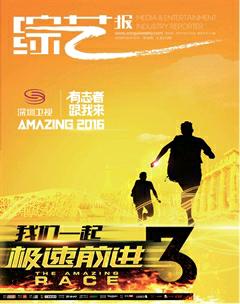“网红经济”:从夜总会到德云社
包冉
网红自古有,今年特别热。
大出风头的papi酱、各类直播平台上20万余男女主播,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在分众、垂直、细分领域,众多粉丝体量不大、黏性和盈利能力一流的“专业网红”,呈现出更持久的生命活力。更别提在资本和资本市场追捧下,正前赴后继踊跃投身于网红事业的无数老中青。
与以往一样,出于投资者和被投资者的强烈名利动机,关于“网红经济学”的炒作又开始了。典型打法老一套,无非有三:
其一,整出一些新名词,鼓吹一场新颠覆,不惜把小姑娘比喻成“当代鲁迅”,也不顾“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放眼全球互联网发展,只有“长尾理论”“免费的经济学”和“共享经济”可以视为互联网对经典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原发创新。其他,影响力大如“社交网络”者,其理论基础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便由人类和社会学家提出并验证,互联网对社交网络当然很重要,但解决的是应用层面的问题,即为其提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运营试验场。一个客观现实是,迄今为止的三大原发性网络经济理论创新,其商业实践和理论提出均源自美国。以中国互联网大而不强的发展现状,动辄标榜理论颠覆创新,不是勇敢者的自信,而是无知者的无畏。
其二,轰轰烈烈搞运动,新瓶里面装旧酒。网红是什么?“网”,说的是媒介,其核心是互联网带来的自媒介形态;“红”,说的是目标,是大众关注度和舆情话语权。
传统意义上的“造星”,有一套成熟的自上而下的拔擢、培养和推广机制;严格意义上的“网红”,则是自下而上、不依赖组织、网民自发追捧的成名路径——二者殊途同归,但法则截然不同。所以,当文娱类上市公司捧出大手笔的“网红计划”,其实质还是工业流水线上的造星机制,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网红生态。
其三,网红的商业模式很传统,要么是夜总会,要么是德云社。“粉丝打赏”“虚拟礼物”“广告竞标”“社群激励”“电商变现”……看上去很“互联网思维”的立体商业模式,究其实质,要么是消费服务,要么是消费产品。
消费服务的典型模式是夜总会,其标准动作叫“捧”,消费动机是欲望宣泄,最大乐趣在撒钱速度、力度和广度的比拼。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成功者如YY、9158和六间房,其主力业务的实质就是“在线夜总会”——“名伶献艺、公子撒钱、屌丝喝彩”,也顺便捧出了一批“网红”。
消费产品的典型模式是剧场和影院,其标准动作叫“购票”,消费动机是短暂的梦境和对现实的遗忘,最大乐趣在角色代入的快乐或悲伤、人以类聚的共鸣或共诉;老话儿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进者,如逻辑思维,其实质和德云社无二——你负责掏钱买票“爱的供养”,我负责让你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做“快快乐乐的衣食父母”。
夜总会和德云社,走到一定规模,必然会带来品牌溢价。前者的老板可以凭此溢价大开分店,消费价格一定会高出市场均价;后者的老板可以做平台,想捧谁就捧谁,想让谁红就让谁红,就像郭德纲之于小岳岳,罗振宇之于Papi酱。二者的老板都可以做自有品牌附加值的衍生产品,就像夜总会的酒、德云社的班、逻辑思维的书。
商业本质的雷同,并不否定后来者的天资、勤奋和成功。但非要包装成“伟大的创新”,那可就有点矫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