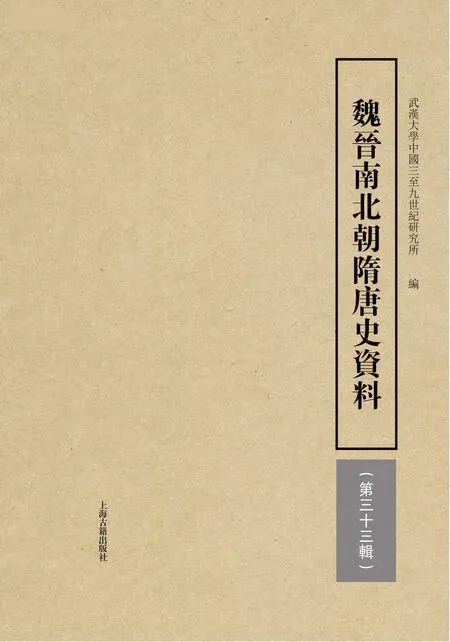温庭筠《百韻》詩考注
牟懷川
温庭筠《百韻》詩考注
牟懷川
開成五年(1)秋,以抱疾郊野(2),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3)。將議遐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4)、察院陳李二侍御(5),回中蘇端公、鄠縣韋少府(6),兼呈袁郊苗绅李逸(7)三友人一百韻(8)
(1) 開成(836—840),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甘露之變後,于次年正月一日所改年號。其間與本詩相關的大事是唐文宗太子李永之死及文宗本人之死。《舊唐書》卷一七五《文宗二子傳》載,“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游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御史中丞狄兼謩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太子歸少陽院。……其年薨,勅兵部尚書王起撰哀册文。……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開成三年十月)暴薨。……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資治通鑑》卷二四六記載,開成年間,文宗形同囚拘,自嘆“受制於家奴”,不如赧、獻。開成五年正月戊寅,文宗不豫;己卯(次日),“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開成四年十月立)復爲陳王,立潁王爲皇太弟”。辛巳(又二日),文宗薨於太和殿,年三十三;皇太弟即皇帝位於柩前,是爲武宗。武宗即位,宦官專權形勢下的牛李黨爭形勢再次翻盤。辛卯(十日後),武宗殺陳王成美及安王溶、賢妃楊氏。文宗遭宦官軟禁,雖不知究系毒死或逼死,然非良死也。

(3) 與鄉計偕: 指舉人隨考吏赴長安參加禮部試。鄉,指貢士的地方州、府(包括京兆府);計: 指計吏,即上計,本漢代主財政、考試之吏員,在唐專指考吏。《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序》:“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爲弟子。”司馬貞《索隱》:“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唐代生徒、鄉貢,皆偕計吏“升於有司而進退之”(《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王府: 指朝廷有關官署或府庫機構。《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且绝民用以實王府,由塞川原爲潢洿也”。此指唐代皇家負責遴選進士的有司,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即指禮部。
(4) 殿院徐侍御,應指徐商。兩《唐書》有傳。《全唐文》卷七二四李騭《徐襄州碑》曰:“文宗五年春,考登上第,升朝爲御史。會昌二年,以文學選入禁署。”(即以殿中侍御史補禮部員外郎)又《全集》卷八《河中陪帥遊亭》爲大中八至十年間爲徐商作,卷一一《投憲丞啓》爲咸通五六年間投徐商作。
(5) 察院陳、李二侍御: 陳,無考。李,或謂指李遠,待確證。據《全唐文》卷七六五李遠《靈棋經序》“開成末,予將適閩中。……後予福州從事,居多暇日。……然離閩數日,忽宸書降,召爲御史”云云,則李之爲御史是在開成末遠適福州、離閩歸來後,比開成五年冬晚至少兩年。
(6) 回中蘇端公: 指時在涇州的侍御史蘇某,不詳其人;回中,古道名,此指唐涇原節度使治所涇州;端公,即侍御史。唐趙璘《因話録》:“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为端公。”鄠縣韋少府,不詳;少府,縣尉别稱。
(7) 袁郊: 咸通時祠部郎中(《唐詩紀事》卷六五)、虢州刺史(《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四》)、昭宗朝翰林學士(《舊唐書(卷一八五)袁滋傳》)。有《甘澤謡》一卷(《直齋書録解題》)。苗紳: 會昌初進士(鄭畋《唐故朝散大夫京兆少尹苗府君墓誌銘並序》),咸通八年任江州刺史(陳舜禹《廬山記》卷五)。温《詩集》卷四有《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苗紳先輩》詩。李逸: 未詳。
(8) 詩題: 《全唐詩》卷五八一簡作“病中書懷呈友人”,而將本詩題當做詩序,似非正。詩題寫出詩人開成五年冬雖得“等第”,卻因形格勢迫,乃放棄參加禮部試的機會,“罷舉”而將遠適吴地;故痛定思痛,向諸位好友披瀝情懷。題目中所涉諸人,多深知其事者。尤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回中蘇端公,觀其在詩中角色,當與“比侍御史”的司直有關而與温共有從遊莊恪太子之經歷的人。
(一) 逸足皆先路,窮郊獨向隅。
逸足: 飛蹄,代指駿馬,喻良才。漢傅毅《舞賦》(《文選》卷一七賦壬):“良駿逸足。”先路,本謂爲王先驅,此兼有捷足先登意;《離騷》:“來吾道夫先路。”窮郊,荒僻遠郊;但相對“逸足”之謂馬,此句“郊”或當作“蛟”,對愈工而義更勝,而不與“向隅”意義犯重。《唐詩紀事》卷六五:“(袁)郊,與温庭筠酬唱,庭筠有《開成五年抱疾不得預偕》詩寄郊云‘逸足皆先路,窮蛟獨向隅’是也。”《紀事》比於《全唐詩》,雖非正本,然其作“蛟”字,其實可參。首聯以“逸足”(題中諸公在其位者)與“窮蛟”雙起(以下主要單承後者,是所謂雙起單承);意謂朋輩皆捷足先登,爲王先驅,自己卻蹭蹬失意。
(二) 頑童逃廣柳,羸馬卧平蕪。

此處“朋友”指裴夷直。温《上裴舍人啓》有“孫嵩百口,繫以存亡”句,用《後漢書·趙歧傳》典故,也説明温依靠裴舍人者如孫嵩幫助趙岐一樣捨命救助自己,才免於被宦官捉獲。其事與“頑童逃廣柳”當同指,都是寫温開成二三年間從遊莊恪太子後,在極其危險的境地中一度不得不靠朋友相助,通過非常手段脱身。開成年間裴姓中書舍人唯有裴夷直。《新唐書》卷一四八《張孝忠傳》附:“字禮卿,亦悻亮。(文宗末)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册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户參軍。”近年新出土李景讓《唐故朝散大夫左散騎常侍贈工部尚書裴公(夷直)墓志》(《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更可確證裴“詔遷諫議大夫,旋兼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在開成三年至開成五年之間。文宗升遐,李黨執政,乃於“開成五年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見《温庭筠上裴舍人考》,待刊稿。
(三) 黄卷嗟誰問,朱弦偶自娱。
黄卷: 古代書籍用黄紙繕寫,故代指經書或學問。《晉書》卷九二《褚陶傳》: 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黄卷中,舍此何求!”朱弦: 語本《禮記·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案“朱弦”既用於清廟,而據《詩經·清廟》鄭玄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故所謂“朱弦”者,本指廟堂之樂,而代指嚴肅文學,此處即指本詩。或引《舊唐書》本傳“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謂詩人偶借音樂自娱,非。《詩集》卷一《織錦詞》“玫瑰作柱朱弦琴”之“朱弦”用法,與此異曲同工。本聯浩歎滿腹經濟學問無人過問,只好借寫此詩自遣。
(四) 鹿鳴皆綴士,雌伏竟非夫。
鹿鳴: 《詩·鹿鳴·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又《新唐書》卷四五《選舉志下》:“每歲仲冬……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敍長少焉。”《五十韻》中,詩人原注“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試有司”之前也有“空愧鹿鳴篇”的句子。故“鹿鳴”者,代指詩人得“京兆薦名”後而參加的“長吏”主持的“歌《鹿鳴》之詩”的“鄉飲酒禮”。綴士: 謂及第而入朝士之列;《文選》卷一六晉潘岳《閑居賦》“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雌伏: 自謂委屈不得意;《後漢書》卷二七趙温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非夫: 不是大丈夫;《左傳·宣公十二年》:“聞敵强而退,非夫也。”此聯説,與他同得“等第”而參加京兆府“鄉飲酒禮”者,多名登上第,只有自己屈身辱志。
(五) 采地荒遺野,爰田失故都。
原注: 余先祖國朝公相,晉陽佐命,食采於并、汾也。
采地: 亦作“菜地”,卿大夫的封地、食邑;《漢書》卷二三《刑法志》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爰田: 或作“轅田”;《左傳·僖公十五年》“晉於是乎作爰田。”杜預注:“分公田之税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故“爰田”也就是將公田賞給貴族。故都: 指唐代北都晉陽,李唐王朝發祥之地;隋開皇十六年析晉陽地置清源縣。據《全集》卷一一《上蔣侍郎啓》二首之一“遂揚南紀之清源”句,知温離開南國的“清源”第二故鄉,則北方的“清源”爲其祖籍所在也。原注所云,可證以兩《唐書·温大雅傳》,而温本傳云温爲“彦博裔孫”;温大雅,封黎國公;温彦博,封虞國公;温大有,封清河郡公。高祖嘗謂温大雅曰:“我起兵晉陽,为卿一門耳。”温氏封於并州、汾州,就近食采;温《上裴相公啓》也提到“爰田錫寵,鏤鼎傳芳”的家族榮耀。二句説先祖采地荒棄并、汾舊野,皇賜爰田也不復見於晉陽故都。
(六) 亡羊猶博塞,放馬倦呼盧。
“亡羊”句: 本《莊子》外篇卷三《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今案,温變用穀因博塞而亡羊之典,其義承第五韻之“失”謂即使亡羊(即使“爰田失故都”),猶博塞不止;實以“亡羊”喻失去禄位,而“博塞”則喻其失禄位之因,當指温氏傳家忠直之道也。放馬: 原作“牧馬”,雖引申爲用兵意,亦不合上下文;疑由“放馬”(意同“歸馬”)訛誤而致,用法出《尚書·武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本言偃武息兵,此喻放棄競爭,故接“倦呼盧”,謂倦於“博塞”(“樗蒲”之賭勝),即厭倦於求仕之奔競也。呼盧: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六《樗蒲經略》:“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此爲最高之采。按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亦名呼盧也。”二句承上由祖業説到自己,謂雖祖上(以忠直)失官,自己猶不改其道;只好退出科舉求仕的競爭。
(七) 奕世參周禄,承家學魯儒。
奕世: 累世。周禄: 因“魯儒”之時而稱,指唐禄。孔子魯人,故以魯謂儒也。温《全集》卷一一《上裴相公啓》亦云“思欲紐儒門之絶帷,恢常典之休烈”。二句言世食朝禄,儒業傳家。
(八) 功庸留劍舄,銘戒在盤盂。
功庸: 泛指文治武功。《國語·晉語》(卷一三):“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韋昭注:“國功曰功,民功曰庸。”劍舄: 同“劍履”;“劍履上殿”是舊時皇家給重臣的殊榮。《初學記》(卷二二)引周遷《輿服雜事》:“舊制,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銘戒: 在金石器物上銘刻的警戒文字。盤盂: 圓盤方盂,所以刻《盤盂書》者。劉歆《七略》(《全漢文》四一)謂:“《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黄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二句言傳家的劍舄和傳國的盤盂猶顯示先祖劍履上殿、輔佐帝業的殊榮。
(九) 經濟懷良畫,行藏識遠圖。
經濟: 謂規劃國計而有益黎民,所謂經世濟民也。良畫: 猶言妙策、嘉猷。行藏: 指政治上的進退。《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遠圖: 忠謀遠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二句自謂有報國的智術、出處的深謀。
(十) 未能鳴楚玉,空欲握隋珠。
鳴玉: 《禮記·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行則鳴佩玉。”《晉書》卷八九《嵇紹傳》:“鳴玉殿省。”故“鳴玉”比喻君子出仕在朝。楚玉: 指和氏璧;參第67韻解。隋珠: 即《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引隋侯救傷蛇,蛇所銜以報之者;《文選》卷四二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二句自謂空負美才,未能出仕而展其用。
第1—10韻,經過一場政治風波,庭筠的朋友們皆以英才爲王先驅,只有自己落荒而逃;所以詩人浩歎滿腹才學無人過問,只好寫詩自遣,抒發自己“等第”而“罷舉”的不平。温氏雖以忠直中衰,自己決不以世路枉曲而易其直,而只能引退。先祖儒業傳家,功業煊赫,自己則懷才抱忠,英雄無用武之地。
(一一) 定爲魚缘木,曾因兔守株。
二句用“緣木求魚”(《孟子·梁惠王上》)及“守株待兔”(《韓非子·五蠹》)典,隱約説及自己準備應舉前毫無結果的一段努力,即從遊莊恪太子的經歷。温詩文中屢暗示這種經歷;如《温集》卷三《古意》:“不慮見春遲,空傷致身錯”、《五十韻》“投足乖蹊徑”皆是。其事始自開成二年夏秋間,終於開成三年十月太子死;其後,乃轉向由科舉求進身。見拙作《温庭筠從遊莊恪太子考論》,《唐代文學》第一期,1984。
(一二) 五車堆縹帙,三徑闔繩樞。
五車: 謂所學淹博,語出《莊子·天下》“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縹帙: 淡青色帛做的書衣,代指書卷;徐陵《玉台新咏序》“方當開兹縹帙”。三徑: 自指幽居處;見《文選》卷四五陶淵明《歸去來辭》“三徑就荒”後李善注引趙岐《三輔決録》。繩樞: 用繩子做軸的門,此以誇言貧窮。漢賈誼《新書》卷一《過秦論》“甕牖繩樞之子”。二句謂自己在貧寒中閉門專心博覽群書。
(一三) 適與群英集,將期善價沽。
群英: 指參加京兆府試的衆文人。“將期”句: 即“待價而沽”意;《論語·子罕》,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二句説自己接着與衆文士一起參加科試,期求以自己所學博取名位。
(一四) 葉龍圖夭矯,燕鼠笑胡盧。
葉龍: 用劉向《新序·雜事五》“葉公好龍”典。夭矯: 屈伸飛騰。燕鼠: 其實是合用“燕石”與“鼠璞”二典。燕石,《太平御覽》卷五一録《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 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鼠璞,《戰國策》卷五三(又見《後漢書》卷四八注引《尹文子·大道》)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賈曰: 欲買璞乎?鄭賈曰: 欲之。出其璞,視,乃鼠也。因謝不取。”胡盧,見上,亦作盧胡,發於喉間笑聲。或謂“燕鼠”當做“燕石”,而認飛卿誤記典故;其實“葉龍”與“燕鼠”對仗,應是作者預設。蓋周客以鼠璞惑鄭賈買玉璞,笑宋人以燕石(玉璞)爲寶玉;合觀之,有寶玉被誤作燕石,又被説成鼠璞的多層訛傳,雖牽强,畢竟可通。前句以葉公好龍比喻考官“求似賢而非賢者”而不能真接受自己;後句説自己這塊璞玉被誤成“燕石”乃至鼠璞,匪夷所思地被人誤會嘲笑。
(一五) 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
賦分: 指天賦才能和資質。前定: 前生早定的,有以家學淵源自豪意味。寒心: 畏懼擔憂。厚誣: 嚴重誣蔑、大肆誣蔑。二句自信有才堪試,只是未試之前已憂懼會遭受無情的誹謗誣蔑。
(一六) 躡塵追慶忌,操劍學班輸。
躡塵: 謂踢踏塵土、奔跑神速。慶忌: 吴王僚之子。《吴越春秋·閶闔列傳》: 吴王曰:“慶忌……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数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操劍: 指“班輸”的技藝;班輸,即公輸班(般)、魯班,春秋末魯國名匠。接上韻,二聯四句錯綜相承: 能“操劍學班輸”者,因“賦分知前定”也;而不得不“躡塵追慶忌”者,“寒心畏厚誣”之故。二句自言奔跑神速,可比慶忌,而技藝高超,勝過魯班;實喻應試前的準備。“躡塵”句自謂爲避開“厚誣”,乃如慶忌奔逸絶塵,實喻爲暫避開宦官勢力的“厚誣”而改名應試的行爲;“操劍”句乃以公輸般之運斧操劍的絶技,自喻謀篇爲文之意匠經營。
兩《唐書》本傳謂温“本名岐”,大誤。所以致誤之因,當是根據《唐摭言》卷二“等第罷舉”條開成四年條載“温岐”名的事實,及開成四年後温常以庭筠爲名的證據,而認爲“庭筠”乃由本名“岐”而改之名也。然温既有弟曰庭皓,豈改後方與其弟同取“庭”字?更無兄弟二人同時改名之理。故“岐”非本名,而爲應京兆府試所改之名,後世史傳作者不察而誤記也。詳見拙作《温庭筠改名案補考》。
(一七) 文囿陪多士,神州試大巫。
文囿: 文章苑囿,此處即指考場。多士: 語本《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謂同時應京兆試者。“文囿陪多士”换言之即“適與群英集”。神州: 指京兆府;京兆府解送,較之地方州縣貢士,乃中晚唐時一種特殊的鄉貢。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條“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等同及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知貢舉)倚而選之,或至渾化(全部録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神州即京兆府,亦可證之於《文選》卷二一左思《詠史詩》“靈景曜神州”吕向注“神州,京都也”。試大巫: 《太平御覽》卷七三五《方術部》一六《巫》下引《莊子》“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三國志》卷五三《吴志·張紘傳》“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裴松之注引《吴書》:“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此字面上用“大巫”語,借指通過科試定文才高下。
(一八) 對雖希鼓瑟,名亦濫吹竽。
原注: 余去秋試京兆,薦名,居其副。
“對雖”句: 典出《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孔子使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華回答後,孔子問及曾晳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乘涼風舞於求雨壇下),咏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希鼓瑟”即上引文中“鼓瑟希”之倒文,意謂像曾晳一樣應對别具一格而出衆。“名亦”句: 用《韓非子·内儲説上》“濫竽充數”事,自謙徼幸得名。
原注所謂“去秋”(即開成四年秋)云云,與《唐摭言》卷二“等第罷舉”條“開成四年”載“温岐”名完全相合:“試京兆,薦名”,就是參加京兆府試,被京兆府録取,就是“等第”。見第17韻注。“居其副”並非如有的論者所言,是得了“第二名”,而是名在正榜之外另外附加名單上,即在解送名單的副榜上。仍據《唐摭言》卷二“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敍”:“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爲名,等列以十人爲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即六月沖宵之漸也。”看來“在上十人”屬於“等第”正榜;正榜之外,是年或有副榜。
(一九) 正使猜奔兢,何嘗計有無。
二句語序倒裝,自言(改名應舉得“等第”)本來何嘗是志在必得,(改名事洩後)更徒使人猜忌自己是趨名逐利之徒。從第17韻注知,當時得“等第”者前十名,“或至渾化”;遭到“罷舉”,頗爲例外,故温之“罷舉”必有特殊原因。而若非“罷舉”,“等第”後安能有以下苦境。這個“特殊原因”即自江淮受辱以來温被宦官捏造謡言,横加誹謗,本想通過改名應試避開宦官,卻因改名事洩而更無法自辯。


(二一) 市義虚焚券,關譏漫棄繻。
“市義”: 收買“義”的名聲。據《史記》卷七五《孟嘗君傳》,馮諼爲孟嘗君收債,乃焚其債券而賜諸民,且歸報曰:“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上句在此解作“虚焚券以市義”,似指京兆府選士者徒然“焚券”——允許自己改名、掩蓋身份應考——而“市義”的行爲。“關譏”句: 典出《漢書》卷六四下《終軍傳》: 軍步入關,關吏予軍繻,……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繻: 古代帛製通行證,上書字,分兩半,過關則驗合以爲憑。此句變用典故,其義爲“漫棄繻而關譏”,言自己猶如終軍棄繻而在關前受到譏笑,參加考試時實空有取功名如探囊取物的豪氣。
(二二) 至言今信矣,微尚亦悲夫。
至言: 本最中肯精當的話;《漢書》卷五一《賈山傳》載其《至言》,此處或用其意,尤指忠言不用則身危之類的勸誡。微尚: 謙語,自指微不足道的志向。
第11—22韻,先暗示自己是在從遊莊恪太子李永之後,閉門讀書而準備應京兆府試。但在考試之前,已見京兆府有司官员徒有好才之虚名而不辨賢愚。自己則雖有才堪試卻害怕宦官勢力的誣蔑中傷,乃詭譎道出: 以奔逸絶塵的方式——改名的方式——參加京兆府試,當然還要發揮自己意匠經營的文才。然後開成四年秋應試京兆府,文章出衆,故榜上有名,得“等第”。其後爭名者之猜忌,援引者之無奈,當然還有加害於己者之强横,使詩人努力成空,壯志成灰,不得不悲嘆失敗而自認晦氣——當然皆因改名事洩。
(二三) 白雪調歌響,清風樂舞雩。
“白雪”: 《文選》卷四五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清風”句,見第18韻注“風乎舞雩”。二句自嘆曲高和寡,只好聊效曾晳以賦閑林下自樂。
(二四) 脅肩難黽俛,搔首易嗟吁。
脅肩: 聳雙肩以示敬懼,諂媚貌;見《孟子·滕文公下》“脅肩諂笑”。黽俛: 勉力,勉强。《詩·小雅·十月之交》:“黾勉从事,不敢告勞。”搔首: 焦慮無奈貌;《詩·邶風·静女》:“爱而不見,搔首踟蹰。”嗟吁: 嘆息。二句説不能勉强自己阿諛奉承權貴,面對其結果只有徒歎奈何了。
(二五) 角勝非能者,推賢見射乎?
角勝: 較量勝負,此即喻名場角逐。曹植《與司馬仲達書》(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三):“無有争雄於宇内,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推賢: 推舉賢人,此謂科舉選士。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伍。”射乎: 《論語·八佾》,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二句言自己在文場爭勝並非能人,因當時科舉選士並非君子之爭(要靠奧援、通關節,忌宦官),並不靠“射”的本領(即文章高下)而定棄取。
(二六) 兕觥增恐竦,杯水失錙銖。
兕觥: 據《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鄭玄箋孔穎達疏,即角爵,“禮圖云: 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一説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其作用應似後代之酒樽或者酒壺,所以注酒入杯供衆人飲者。“兕觥”而能“增恐竦”,必以“兕觥”喻人;與“杯水”相對,當喻給予名第的考官。而“杯水”則喻接受名第的應舉者,此即指温本人。故“杯水失錙銖”者,個人失去微不足道的“錙銖”(皆古之小重量單位,喻細微)名位也;失之之因,即“兕觥增恐竦”,即考官多恐懼(畏懼宦官)也。是爲温庭筠被“罷舉”的直接原因。
(二七) 粉垛收丹采,金髇隱僕姑。
粉垛: 塗成白色的箭靶;丹采,紅色靶心。髇: 響箭箭頭,即鳴鏑。《漢書》卷九四《匈奴列傳上》“冒頓乃作鳴鏑”句下引“應劭曰: 髐(“髇”之異體字),箭也。”僕姑: 亦箭名,春秋魯國之勁矢也,《左傳·莊公十二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二句字面謂“收粉垛之丹采,隱僕姑之金髇”,即箭靶已收,良箭只好藏了;此以武喻文,謂考場對己不開,而不得不放棄求進士之努力。
(二八) 垂櫜羞盡爵,揚觶辱彎弧。
本聯“羞”“辱”二動詞明顯指人的行爲,故其前其後的四個動賓詞組分别代表施行或接受這種動作的人,而解作: 垂櫜之士子(自己)羞見盡爵之友;揚觶之宦豎侮辱彎弧之臣(自己)。又,垂櫜、彎弧皆有關射事乃至“鄉射禮”(喻應禮部試);盡爵、揚觶皆有關飲事乃至“鄉射禮”前的“鄉飲酒禮”,這也正合温參加“鄉飲酒禮”(長吏會屬僚)而不能應禮部試的窘境。
垂櫜: 《左傳·昭元年》:“伍舉請垂櫜而入。”杜預注:“示無弓也。”無弓,則無以射,自喻“等第”之後不能應禮部試。因而“羞盡爵”,即羞愧面對“鄉飲酒禮”之儀式中“盡爵”的“綴士”者。揚觶: 據《禮記·鄉飲酒義》“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禮記·檀弓》記晉平公在寢宫與師曠、李調鼓鐘飲酒。膳宰(宰夫)杜蕢入寢,罰師曠、李調飲酒。又自罰而出。……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于是“杜蕢洗而揚觶”;下文且言“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所以,揚觶,本謂洗淨之後高舉酒杯,而此處指“揚觶”之人,即杜蕢,代指宦官。彎弧: 《文選》卷十四班固《幽通賦》有“管彎弧欲斃仇兮,仇作后而成己”句,用管仲事公子糾而射中小白,及小白立爲齊桓公,用之爲相而成其霸業的故事(見《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温竟自喻“彎弧”之人管仲。因爲,第一,宦官壟斷皇位更替而選擇的皇位繼承人武宗對前朝與皇位有關者如陳王、安王、楊賢妃皆殺之,對擁戴莊恪太子者(如温)有敵意;第二,温忠事文宗及其太子,此前反宦官言行可能被親宦官者歪曲爲反對新君,而加罪焉,温用此也表示對新君效忠。
《全唐文》卷六三二温庭筠業師李程《鼓鐘於宫賦》“《禮》失所譏,想杜蕢之揚觶”云云卻對這段讚揚杜蕢的記載有異議;他實際上把大言無忌的膳宰杜蕢比之於當時專權的宦官。温受其師影響,在其《上學士舍人啓二首之一》中,有“摧殘膳宰之前”句,説自己在“膳宰”面前受盡欺凌垂頭喪氣;此所謂“膳宰”,正是借膳宰杜蕢事指宦官。
(二九) 虎拙休言畫,龍希莫學屠。
“虎拙”句: 出《後漢書》卷二四《馬援傳》“效杜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龍希”句: 出《莊子·列御寇》:“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二句可讀作: (計)拙休言畫虎,(術)希莫學屠龍。所謂“畫虎不成”,疑是效劉蕡抨擊宦官,而遭致迫害;“莫屠龍”云云,是因而反省滅除宦官之難行。
第23—29韻,詩人只好孤芳自賞,澹泊養志;自己不愿諂事權貴(尤指宦官)的代價是在困境面前徒嘆奈何。考官“畏宦官,不敢取”,所以罷舉。因爲宦官排除異己,對自己横加羞辱中傷,乃至新君有忌,自己才“畫虎”不成。

轉蓬: 隨風轉的蓬草,自喻生涯無依。曹植《雜詩》:“轉蓬離本根。”款段: 本馬行遲缓貌,此借指自己閒散不羈的生活。《後漢書·馬援傳》:“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斯可矣。”墳壚: 原作“墁壚”。“墁”字在此處平仄不协而且講不通,當作“墳壚”,高地的黑硬土。《書·禹貢》:“下土墳壚。”孔穎達疏:“壚,音盧,《説文》‘黑剛土也’。”墳: 《禮·檀弓》:“古者墓而不墳”。鄭玄注:“土之高者曰墳。”二句寫自己當年羈旅飄泊中鋤草開荒的清貧生活,語帶誇飾。

(三一) 受業鄉名鄭,藏機谷號愚。
“鄭鄉”: 典出《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受業於“鄭公鄉”推論,温所從受業之師爲當時之名儒也。《五十韻》亦有“鄭鄉空健羨,陳榻未招延”句,自言空爲名儒弟子而爲人羨慕,只是未得仕進機會。“愚谷”: 典出《説苑》卷八《政理》,齊桓公出獵入山谷,問老公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二句説到自己受業名師、隱遁僻谷的經歷。所謂鄭公鄉、愚公谷當從比喻義解之。
(三二) 質文精等貫,琴筑韻相須。
質、文: 此處指文章之樸質或藻飾。《文心雕龍·通變》:“斯斟酌乎質文之間。”温《全集》卷一一《上蔣侍郎啓二首》之一:“質文異變之方,驪翰殊風之旨。粗承師法,敢墜緹緗。”筑: 古代打擊樂器,形似箏,其音激越。相須: 謂音色相得益彰。《全唐文》卷六三二有許堯佐《塤篪相須賦》。二句自謂對文質兩種風格,都得其精華而融會貫通;有如琴筑和鳴,各有韻味而相得益彰。
(三三) 築室連中野,誅茅接上腴。
二句互文見義;築室、誅茅(芟除茅草而結廬)也是同義詞,皆謂造房;在靠近“上腴”之地的田野中建房爲家。《楚辭·九歌·湘夫人》“築室兮水中”;又《楚辭·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上腴,本指最肥沃的土地,但此處似專指其隱居之地,今試求之。班固《西都賦》:“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漢書·地理志八》:“故秦地……爲九州膏腴”;《新唐書·太平公主傳》:“田園徧近甸,皆上腴”;《舊唐書·李林甫傳》:“林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白居易《策林》第二九:“都畿者,……田有上腴之利”;《新唐書·宦者傳上》:“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杜佑《通典·州郡典》:“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又,“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四塞为固,秦氏資之”。則唐人尤以“上腴”指關中甚至天子腳下的京畿,參前“郊野”、鄠縣注,或即指鄠縣。
(三四) 葦花綸虎落,松瘿鬭欒櫨。
綸: 《全唐詩》一作編,似以“綸”爲勝;即縱横穿插意。虎落: 即竹籬;《漢書》卷四九《晁錯傳》“爲中周虎落”句師古注:“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癭: 樹瘤。欒櫨: 屋中柱頂承梁之木,曲者爲欒,直者爲櫨。鬭: 謂相接而逞奇。二句説竹籬上葦花,上下錯落有緻;而房梁間樹瘤,姿態各異。
(三五) 靜語鶯相對,閑眠鶴浪俱。
(三六) 蕊多勞蝶翅,香酷墜蜂鬚。
(三七) 芳草迷三島,澄波似五湖。
三島: 即《史記》卷二八《封禪書》所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五湖,據《國語·越語下》“戰于五湖”韋昭注,即太湖;與《詩集》卷四《利州南渡》“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之“五湖”同。二句言所隱之地芳草馥鬱、澄波蕩漾,使人如迷三山,如臨太湖。知非太湖也。參第三三韻“上腴”解。
(三八) 躍魚翻藻荇,愁鷺睡葭蘆。
葭蘆: 即蘆葦。《詩·豳風·七月》“八月萑葦”孔疏:“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
(三九) 暝渚藏鸂鶒,幽屏卧鷓鴣。
暝渚:“暝”,諸校本作“冥”、“瞑”,字皆通;昏冥之江渚也;唯作“溟”(滄海)者,非鸂鶒所能藏。幽屏: 謂僻靜隱蔽,如在屏後。《藝文類聚》卷九張衡《温泉赋》“處幽屏以閑清”。


(四一) 笑語空懷橘,窮愁亦據梧。
懷橘: 用《三國志》本傳陸績“懷橘遺親”典故。所謂“空懷橘”之“空”,似言空有奉母之心,其母當已辭世。案温會昌二年《五十韻》詩亦有“懷橘更潸然”句,可見温念念在懷而時時彰顯喪母之事。據梧: 意即倚桐而高論或悟道。《莊子·齊物論》:“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二句自謂隱貧居而能達觀快樂、學而忘憂;言下亦特别提及對母親之懷念。
(四二) 尚能甘半菽,非敢薄生芻。
半菽: 謂半菜半糧、粗劣飯食。語出《漢書·項羽傳》:“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顔師古注引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生芻: 鮮草,語出《詩·小雅·白駒》:“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陳奂《詩毛氏傳疏》:“芻所以萎白駒,托言禮所以養賢人。”故爲禮賢之典。而《後漢書》卷五三《徐稚傳》:“(郭)林宗有母憂,稚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故生芻爲弔唁朋友之親的禮物。二句自謂能安於貧窮,並感戴朋友的幫助,似亦暗涉母親之死。温與唐宗室有姻親關係,史料奇缺,只能找到以下有關資料以俟深考。
温《詩集》卷九有《寒食節日寄楚望二首》;其二云“獨有恩澤侯,歸來看楚舞”,乃以“恩澤侯”自指。《漢書》卷一八《恩澤侯年表》所謂“恩澤侯”,指姻親受皇帝私恩而封侯者。由《新唐書》卷九六《諸帝公主傳》(亦見《唐會要》卷六),知(唐高祖李淵女)“安定公主,下嫁温挺(温彦博之子)”。而(睿宗女)“涼國公主,先嫁薛稷之子薛伯陽,後降温曦(温彦博玄孫,官太僕卿)”。又(玄宗女)“宋國公主,始封平昌。下嫁温西華(即涼國公主與温曦之子,官秘書監),又嫁楊徽。薨元和時。”《全唐文》卷八三《涼國長公主神道碑》有“子西華扶杖而立,茹荼以泣”等句;可見涼國公主死後陪葬橋陵時,温西華是其最重要的兒子。温西華本身是駙馬之子,他作駙馬娶過的宋國公主“薨元和時”。我們即使只據以上資料,説温庭筠和李唐皇室有“何所托葭莩”(本詩第94韻)的遠親關係應是成立的,因爲《新唐書》卷九一云“彦博裔孫廷筠”。而彦博子孫中,兒輩的温挺,第五代的温曦和第六代的温西華,共有三代駙馬都尉;其中第六代温西華,和温庭筠時代相接;很似温庭筠父輩。如果確定本詩第41韻、第42韻果然包含温喪母的消息,依照本詩的時間推算,其事應發生在第47韻所説的大約元和十年温入太學之前的早年隱居讀書時期,這又和上面提到的宋國公主“薨元和中”相合。又,温氏與唐皇室通婚的記載,似乎史有遺漏。芮挺章天寶三載編就的《國秀集》中有徐晶《贈温駙馬汝陽王》一篇。從詩題可見,有一個温駙馬,且封汝陽王,而未見任何史傳;雖難考究係温氏何支,觀其文采博雅,也頗疑與庭筠有關。
(四三) 釣石封蒼蘚,芳蹊艷絳跗。
絳跗: 紫红色花萼。
(四四) 樹蘭畦繚繞,穿竹路縈紆。
“樹蘭”句: 《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二句隱然以蘭竹自喻君子之德。
(四五) 機杼非桑女,林園異木奴。
機杼: 本指織機及梭,引申指爲文、行事或謀生的風格、方式。桑女: 比於農夫,可指以農桑爲業者。王充《論衡·自然》:“或説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做農夫、桑女之徒也。”木奴: 本指橘樹,此指祖宗田園遺産。《三國志·吴書·孫休傳》“丹陽太守李衡”裴松之注引《襄陽記》:“(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歲得绢數千匹,家道殷足。”二句自道生涯: 不像農夫桑女參加勞動,但也没有可保豐足的遺産。
(四六) 横竿窺赤鯉,持翳望青鸕。
赤鯉: 乃仙人坐騎,“窺赤鯉”含求仕進之暗喻。據《列仙傳·琴高》,琴高入涿水中取龍子,後乘赤鲤來;又其《子英》篇敍,子英得赤鲤,一年長丈餘,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升天。”“持翳”句: 謂手拿障蔽物窺望青鸕捉魚,亦似有韜晦而羨魚意。翳: 本指行獵時用以蔽體的僞裝,使獵物看不到射者;此處指不使捉魚的“青鸕”看見,似難解。青鸕: 即鸕鶿,體色青,俗稱魚鷹,能爲人捉魚。二句雖寫隱居景事,亦有伺機求名或隱而待仕的意蘊。
(四七) 泮水思芹味,琅琊得稻租。
泮水: 本魯國學宫,此處指洛陽太學(見前“徐商”注)。語出《詩經·泮水》:“思樂泮水,薄採其芹”。“琅琊”句: 據《舊唐書·李百藥傳》(又見宋孔平仲《續世説》),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德林嘗與其友陸乂、馬元熙宴集,讀徐陵文曰“既取成周之禾(《左傳隱三年》“秋又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曰:‘鄅國在琅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皆曰:“此兒神童也。”今案: 檢清吴兆宜《徐孝穆文集箋注》,未見上引之句,恐已失傳。又“鄅國,今琅琊開陽縣”乃《左傳昭十七年》“六月,邾人入鄅”句下杜預之注,非“鄅人藉稻”之注也。“鄅人藉稻”句下注曰“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瓚曰:“藉,蹈藉也。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另一説,見應劭《風俗通》卷八《祀典》:“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瑯琊得稻租”句謂自己如李百藥由原句指出“藉稻”的典實一樣,亦少年歧嶷;其中“租”字,當由以“租借”解“藉田”而用之,見上應劭解;因趁韻而略顯勉强。二句追懷在太學讀書的時光,自己也如李百藥那樣早慧。《上裴相公啓》“占數遼西”之後的“横經稷下”正指這段經歷。
第30—47韻所指這段隱居生涯,與《上裴相公啓》“占數遼西”一語相對應。而隱居之末“泮水”二句,與《上裴啓》緊接的“横經稷下。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題。思欲紐儒門之絶帷,恢常典之休烈”互爲表裏(横經,聽講時横向打開經書,謂受業讀經也;梁任昉《厲吏人講學詩》“旰食願横經”)。所以“横經稷下”後,因而有機會“仰窮師法”,仰慕研索自己的業師李程教授的賦詩爲文之道。鑒於温平生入官學應只有一次,所謂“稷下”與“泮水”應指同一官學;由温《投憲丞啓》“某洛水諸生,……曾遊太學”云云,知此“官學”指洛陽太學。
《新唐書·選舉志》“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元和二年,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則温在東都太學就讀之時的年齡首先要限制在十四歲至十九歲之間(811—816)。可見温庭筠當時尚有父祖輩餘蔭可霑。接上引《上裴啓》,文曰“俄屬羈孤牽軫,藜藿難虞;處默無衾,徒然夜嘆,修齡絶米,安事晨炊。既而羈齒侯門……”意爲入學不久温便由家庭變故而陷入貧困(王胡之貧困不受陶胡奴米、吴處默清廉冬日無被;事見《世説新語》之《德行》與《方正》),不得不輟學而開始了四方遊宦的生涯;而温的太學生活在《百韻》中只用第47韻一句形容,在《上裴啓》中,也是一句話帶過而已。我們估計温在太學的時日不久,而其輟學與家庭變故以及年齡都有關。根據温生年爲798年之説,假定温入太學在元和十年(815)左右,也許接近事實。《舊傳》載李程“元和十年,入爲兵部郎中,尋知制誥。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吏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温在太學期間當有機會師事李程。
(四八) 杖輕藜擁腫,衣破芰披敷。
藜杖: 用藜的拳曲老莖製的手杖,唐人輒以策“藜杖”表隱居遺世姿態。如《全唐詩》卷一二八王维《菩提寺禁口號又示裴迪》“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擁腫: 語出《莊子·逍遥遊》:“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此謂藜杖拐節凸顯,亦有暗比自己大而無當、“才戾於時”的意味。芰衣: 語出《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與“藜杖”同爲隱者特徵用語。披敷: 花葉開散或招展。二句自嘆瓠落守拙、孤芳自赏的隱居生涯難支。
(四九) 芳意憂鶗鴂,愁聲覺蟪蛄。
芳意: 謂惜時報國之心。鶗鴂: 喻讒人。《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五臣云:“鷤鴃,秋分前鳴,則草木雕落。……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又《後漢書·張衡傳》中《思玄賦》“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句李賢注“鶗鴂,鳥名,喻讒人也。”蟪蛄: 即寒蟬,其爲物夏生秋死;《莊子·逍遥遊》“蟪蛄不知春秋”;《楚辭·招隱士》“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二句謂聞鵜鴂鳴、蟪蛄聲,未仕進之先,已有憂讒悲秋之意。

“短檐”句: 明寫短短的屋檐上燕雀的聒噪,可比擁擠的官場上士人們爭名爭利的喧囂。參見温《偶題》詩“櫻桃拂短簷”句。“高木”句: 以飢鼯從高樹上墜下自喻從相對優裕的環境跌落,將爲稻粱之謀。鼯: 鼯鼠;《爾雅·釋鳥》“鼯鼠,夷由”注:“狀如小狐,似蝙蝠。”二句寫景兼設喻,隱然自道由地位的下降而不得不面臨的仕途謀生形勢。
(五一) 事迫離幽墅,貧牽犯畏途。
二句謂爲事所迫、爲貧所累,離開所隱幽居,走上兇險仕途。
第48韻以下至此聯,多飢貧之音愁蹙之情。由“事迫”推斷是發生家庭變故,經濟拮据,讀書難以爲繼,故被迫踏上仕途。這又恰對應於前引《上裴相公啓》“横經稷下”所接言“俄屬羈孤牽軫”等困境。羈孤, 羈旅孤兒也。《禮記·深衣》“如孤子”注“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牽軫,執紼而牽引柩車,謂父亡也。宋聶崇義所纂輯漢鄭玄、晉阮諶等人所傳之《三禮圖集註》卷一九:“柳車名有四:……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輤則曰軫車。”
(五二) 爱憎防杜摯,悲嘆似楊朱。
杜摯: 是温《上裴相公啓》在緊接上文“安事晨炊”之後,敍述“既而羈齒侯門,旅遊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而提到的迫害自己的人物。《上裴啓》本身表明,“杜摯相傾,臧倉見嫉”之事明顯發生在“羈齒侯門”之後的“旅遊淮上”之時。而此處所言“愛憎防杜摯”則是在家庭變故後、被迫踏上兇險仕途之初。“杜摯相傾,臧倉見嫉”爲互文,故杜、臧屬同類的傾陷加害温庭筠的人物。據《孟子·梁惠王》載:“嬖人有臧倉者沮。”所謂“嬖人”者,據《左傳·隱三年》“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之釋文:“嬖,親幸也。賤而得幸曰嬖。”考慮晚唐形勢,當曲指宫中嬖幸,即得皇帝寵信而專權的宦官。由此推理,所謂“杜摯”者,應亦是宦官。參前第28韻“揚觶”之解,“杜摯”當作“杜蕢”。“楊朱”句,典出《淮南子·説林訓》:“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二句謂踏上仕途之始,自己就受到宦官的迫害,而仿徨岐路,不知所之(可見温與宦官的仇恨起自上一代,而温的出仕甚晚而長期隱居,有避地避仇之意)。
顧嗣立《詩集》援引《三國志·魏志·劉劭傳》附“郎中令河東杜摯”事而謂之曰“事未詳”。其人不相干,固不得其詳也。劉學鍇《全集》則引《史記·秦本紀》(亦見《商君本紀》之反對商鞅變法的杜摯,亦與温詩文之上下文無關。爲了識别這個杜摯,我們不得不考慮兩個可能: 一是歷史上尚另有關於“杜摯”的記載,今亦不得見也;二是别有一人,其名在多少世紀的版刻印刷中發生訛誤,被寫成今日的形態,今本“杜摯”或應是稍不同的另一個名字。由本詩第28韻“揚觶辱彎弧”之注可證“杜摯”應作“杜蕢”,“蕢”字因版本朽爛、字迹模糊而被誤認作“摯”,“杜蕢”本是膳宰(亦宦官之一種)之名,而即指宦官。温受宦官迫害的證明,見前第2韻“頑童逃廣柳”句注引《上裴舍人啓》。受迫害而猶努力進取,在江淮受辱、從遊莊恪、改名“岐”以應試,等第而罷舉的系列事件中有豐富生動的表現。所以本詩第52韻“爱憎防杜摯“及《上裴相公啓》“旅遊淮上。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中的“杜摯”均應作“杜蕢”。
(五三) 旅食常過衛,羈遊欲渡瀘。
過衛: 衛地在今河南淇、滑縣,語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過曹”;言奔波道路,而屢經衛地。羈遊: 長期客遊他鄉。渡瀘,語借諸葛亮《前出師表》“五月渡瀘”,瀘即今金沙江;“欲渡瀘”,謂遊蜀深入腹地,幾乎渡瀘而西。
(五四) 塞歌傷督護,邊角思單于。
“督護”: 即《丁督護歌》,晉宋間曲,“其聲哀切”,詳見郭茂倩《樂府詩集·清商曲辭二·吴聲歌曲》宋武帝《丁督護歌五首》解題;多寫戎馬艱辛和戰爭造成的思婦哀怨。單于: 唐角曲;《樂府詩集·横吹曲辭四·梅花落》解題云:“唐大角曲亦有《大單于》、《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聲猶有存者。”角曲,軍中之樂也。杜佑《通典·樂典》載“蚩尤師魑魅與黄帝戰,帝始命吹角,作龍鳴以御之。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爲軍容也。”二句謂出入邊塞,聞塞上督護之歌而傷懷,聽邊庭大角之曲而興感;概括自己的軍營感受。
第48至52韻,既而自傷老大,又由地位的下降而爲生事逼迫,不得不棄隱求仕。但仕途伊始,就要謹防宦官迫害。第53至54韻,寫羈旅四方(包括出塞入蜀)到處依人的經歷。這一段經歷與温《上裴相公啓》所謂“羈齒侯門”漫游四方的敍述相應;只是詳略不同而已。
(五五) 堡戍摽槍槊,關河鎖舳艫。
堡戍: 駐軍營壘。摽: 通標;誇示、高舉。關河: 函谷關與黄河,或泛指一般關口與河道。二句寫戍樓槍槊林立,關河舳艫禁鎖;分明是緊張的非常形勢。
(五六) 威容尊大樹,刑法避秋荼。

第55至56韻,當時(甘露之變)特殊形勢下,温所依“大樹(將軍)”既倒,禍及自身,他只能選擇逃之夭夭。這兩聯實際上隱括了甘露變後他在揚州受宦官侮辱,而回長安的原因。這段經歷與《上裴相公啓》“羈齒侯門”後面緊跟的“旅遊淮上”(即江淮受辱)等語相應。温“旅遊淮上”之事件在唐宋間筆記小説中乃至正史中都有片段或者歪曲的反映,温本人詩文中也有隱晦的點睛式的透露。把這兩方面的文字表述剪輯整合在一起,方可得其全貌。
“旅遊淮上”以下,《上裴啓》原文是:“投書自達,懷刺求知。豈期杜摯相傾,臧倉見嫉。守土者以忘情積惡,當權者以承意中傷。直視孤危,横相陵阻。絶飛馳之路,塞飲啄之塗。射(應作涉,讀若喋)血有冤,叫天無路。此乃通人見愍,多士具聞。徒共興嗟,靡能昭雪。”尤其“通人見愍”數句,正説明迫害温庭筠者舍宦官無他人。
如上,本詩與《上裴相公啓》的敍事梗概完全一致。“自頃爰田錫寵,鏤鼎傳芳”對應第5至8韻;“占數遼西”對應第30至46韻;“横經稷下;因得仰窮師法,竊弄篇題。思欲紐儒門之絶帷,恢常典之休烈。俄屬羈孤牽軫,藜藿難虞。處默無衾,徒然夜歎。修齡絶米,安事晨炊”對應第47至52韻;“既而羈齒侯門”對應第53至54韻;“旅遊淮上”云云對應第55、56韻。其自敍生平甚爲清楚: 都是説自從祖宗建功立業,後因“直道”而衰微,自己則不得不避地隱居,曾讀書太學;但因家庭變故,難以維持生計;乃“羈齒侯門”、其後則“旅遊淮上”。雖詳略互異,甚至有互補之處,寫的都是温到江淮受辱爲止的全部經歷。那麽,温在江淮受辱之後,有什麽遭際呢?下文57至74韻可以看出温回到長安經過很多周折乃有從遊莊恪太子的特别际遇。
(五七) 遠目窮千里,歸心寄九衢。
九衢: 義同九逵、九陌,指長安。二句可解作“窮千里之遠目,寄九衢之歸心”,有戀闕思君之意。
此時回京師,其事即《舊傳》所謂“受辱”之後“庭筠自至長安”;其時不是《舊傳》所云咸通中,而是在大和開成之際。温在揚州有《上吏部韓郎中啓》,求“分鐵官之瑣吏,厠鹽醬之常僚”以解決買妓爲妻費用,結果受到宦官勢力毫不留情的人身攻擊和造謡誣蔑,是之謂“江淮受辱”。我們本來粗定江淮事件發生時間,也就是上本啓的時間在大和開成之交。啓中語“弦弧未審,可異前朝”,自謂連“弦弧”(指弓箭)都不能審視一下,比喻連參加科舉考試的機會都没有;這和“前朝”之“劉蕡下第”事件難道不同嗎?今得此一言而確定該啓上於開成元年;經歷受辱最後赴長安,當在開成元年下半年或更晚。
(五八) 寢甘誠繫滯,漿饋貴睢盱。
寢甘: 睡眠酣足也。《莊子·徐無鬼》“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繫滯: 牽繫而滯留,謂宦途久不通達。漿饋: 語出《莊子·列御寇》“列御寇……遇伯昏瞀人。曰: 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謂曾要就食的十家賣漿店中,五家把漿先送來,喻被各家款待。睢盱: 張目仰視貌。二句可解作: 若圖“寢甘”誠當“繫滯”,欲得“漿饋”,貴在“睢盱”;謂圖舒適而不勉力,當然仕途久無所就,要想在京城有所得,貴在會瞪大眼睛,窺伺求索。
(五九) 懷刺名先遠,干時道自孤。


齒牙: 猶言口舌;《南史》卷一九《謝朓傳》“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激發: 激而發之;謂有人貶抑而更有人推舉自己。簦笈: 簦爲有長柄的笠而笈即書箱,簦笈謂未仕文人全副裝備,而代指其人或其宦途。二句謂經有關人物多次或貶或褒,或抑或揚,自己仕途仍然不順。意思與《上裴舍人啓》所謂“王尊一身,困于賢佞”(“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見《漢書·王尊傳》,即“三期賢佞”)相似。
(六一) 蓮府侯門貴,霜臺帝命俞。
蓮府: 亦作蓮池、蓮幕,美稱幕府,此謂宰相府。《南史》卷二二《王儉傳》“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所謂“蓮府侯門貴”,指李程、裴度等看重并推薦自己。霜臺: 本御史臺之别稱;此處實指“比御史臺”的太子左春坊司經局。第60韻説自己被人貶褒抑揚,尚無進身之階,已經伏下了受推薦而飛升的可能。故本聯之得貴人重視皇帝俞可自然承上説自己。二句謂蓮府侯門貴我,因而帝命俞我效命所謂“霜臺”,即經宰相李程等的推薦,皇帝俞可,而任職於“比御史臺”的太子左春坊司經局(見下),成爲太子李永的侍從文人。詳見《温庭筠從遊莊恪太子重考》(待刊),今僅列其主要論證如下:
劉學鍇《全集》謂本句以下説的是題中諸位御史的活動,完全脱離了詩本身的連續性。事實上,本詩一百韻,無一句不關温自己者,無一句非親受親歷親見親聞者。即使僅從局部看,第57至第60韻也是每一句都説自己,豈能毫無過接就一下子轉到别人身上?如果全是説别人,以下至第74韻以侍御史爲主的朝見儀式更不是未列朝班的温庭筠所能想象的;若自己未經其事,卻又以想象之筆寫給經歷其事的諸位侍御史看,也完全不合理。那樣讀下去,詩人的詩思、敍事的邏輯,也完全失去着落,不知所云了。
温《詩集》卷六《洞户二十二韻》專寫温從遊莊恪太子事。其事始自開成二年夏秋間而終於開成三年十月莊恪死之前,前後僅一年略多時間。該詩第4韻就交代了自己初見莊恪太子的特定時間和地點:“粉白仙郎署,霜清玉女砧”——當初秋霜清玉女搗砧之時,在宫省粉署諸曹仙郎之地。經過以比爲賦的諸多描述而又值蕭瑟摇落之時,至第20韻“綠囊逢趙后,青瑣見王沈”,謂狠毒的寵妃和猖獗宫掖的宦官合謀害死了年幼的太子,實指楊賢妃與宦官仇士良等合謀害死了莊恪太子李永之事。《新唐書·文宗二子傳》王起《莊恪太子哀册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於少陽院”。所以説,飛卿開始從遊莊恪太子的時間(應比初見太子早)應略早於開成二年秋。
我們從這個判斷繼續推理(並且也考慮温在開成元年“江淮受辱”的經歷),所謂“襄州李尚書”應符合開成元年二年間任職尚書、又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的條件。符合這個條件者非李程莫屬。由《新傳》知李程“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爲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可見,李是從右僕射兼判吏部尚書之職務,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的,稱之爲襄州李尚書,固有由。蓋爲尚書時,當已經推薦温,以待委命,而鎮襄之後,温乃至長安赴任,然後謝官也。其時間當在李程開成二年三月在長安受命赴襄州,並且到任安頓之後。考慮李程調動官職準備旅行而由長安遷至襄陽所需時間,以及温庭筠就任新官所需手續過程,估計此啓大致寫於開成二年五六月間。
《謝紇干相啓》(簡稱《謝紇》)與《謝襄州李尚書啓》(簡稱《謝李》)皆載列於《文苑英華》卷六五三《謝官》條目下。温終生仕途偃蹇,我們本就懷疑他究竟有幾次機會,能使他像《謝李》那樣“托羊角之高風”,或像《謝紇》這樣“冥升而欲近烟霄”説得如此隆重,都是直接擢升至高位;以温之措辭的準確,即使語帶誇張,若不是真接近了天家,斷不至用此等文字。而温平生得以接近帝王的際遇,只有一次而已,就是從遊莊恪太子。故二啓所謝之官都應指從遊莊恪太子時所任太子左春坊司經局屬官。只是在《謝李》中,用“豈知畫舸方遊,俄升於桂苑;蘭扃未染,已捧於芝泥”之語婉言,而在《謝紇》中,用“楚國命官”與“棲於宥密”曲指而已。更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是,無論是《謝紇》所言“揚芳甄藻,發迹門牆”,還是《謝李》所言“寵自升堂,榮因著録”皆清楚表明,温是經由其業師的推舉薦引,才得此寵榮而有此“發迹”,才“顧循虚淺,實過津涯”而“榮非始圖,事過初願”的。不能設想,經一個業師,温有兩次如此扶摇直上的際遇;同樣很難設想,温有兩位業師都曾薦引他平步青云。一言以蔽之,《謝紇》、《謝李》二啓,實爲同一事件而寫,所“謝”是同一個官職。
趙璘《因話録》曰:“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敕頭孫河南瑴,先於雁門公爲丞。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封雁門公。”由此知所謂“紇干公”乃紇干臮;而他就是《謝紇》的啓主。紇干臮未曾任宰相,不可稱爲“相公”;但觀趙璘稱之爲“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我們受到啓發,温也可同樣稱之,也許本啓原來的題目是《謝紇干公啓》,至《文苑英華》成書,被妄加了“相”字而已。紇干臮開成三年,以刑部員外郎任考官,且是“書判考官”(王讜《唐語林》卷四引《因話録》);這個職務,應該看作他開成二年“揚芳甄藻”(選拔文官)的繼續。换言之,他應是在開成二年已經任職吏部,負責銓選官員的。
李程乃當時名儒名師、又是宗室丞相,以頂頭上司吏部尚書兼師輩身份指使他的下屬紇干臮這個書判考官選取温庭筠,應是名正言順的。這也可從温文中看出: 《謝李》乃謝其大力推薦,謝紇則謝其順水推舟也。不管怎麽説,温庭筠在此説的清楚,是老師器重自己的文才而向紇干推薦自己,才獲此高就的:“此皆揚芳甄藻,發迹門牆”是也。其中負責“揚芳甄藻”者是紇干臮,而温所從發迹之“門牆”,指李程宅第。再補充説一句,紇干臮乃元和十年(815)進士,李程則爲貞元十二年(796)狀元及第,資望才德不可同日而語,温絶不會拜李爲師,又拜紇干爲師的。所以温的謝啓中也就是對紇干説幾句如“末由陳謝,伏用兢惶”的客套話而已。
紇干是“揚芳甄藻”或“秉甄藻之權”的官,是選拔文官的官,也就是在吏部銓選中負責“書”和“判”的考官。據《新唐書·選舉志》:“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擇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温庭筠當時並無功名,並無職務,他如何能有資格參加吏部這樣的銓選呢?愚以爲,除了李程的舉薦(所以有文宗認可,即“帝命俞”也),紇干的推轂,温恐怕只能是通過“用蔭”的途徑入仕的。根據《新唐書選舉志》“凡用廕,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國公子,从八品下。”從這個表看來,温庭筠的父輩至少爲正五品。
(六二) 驥蹄初躡景,鵬翅欲摶扶。
驥蹄、鵬翅: 指代駿馬、大鵬,自喻良才。躡景: (讀如影)追趕光影,即飛騰意;《文選》卷三四曹植《七啓》“忽躡景而輕騖。”李善注:“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摶扶: 盤旋而上,喻被迅速擢拔而高升;《莊子·逍遥遊》“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二句説自己因此扶摇而上,幾可一展鹏程;即《謝李》“托羊角之高風”與《謝紇》“冥升而欲近烟霄”也。
第57—62韻,敍述回到長安後,孤道干時,多費周折,終經宰相推薦,皇帝認可而開始從游莊恪太子,飛騰有望。自此以下,全是在左春坊司經局從遊太子時所見所歷,其中關于侍御史的描寫,是對“比侍御史”的司直的描寫而已。
(六三) 寓直回驄馬,分曹對暝烏。
寓直: 謂郎官以下官員寄宿直廬值夜。驄馬: 青白雜色的馬,本指侍御史坐騎,此指太子司直。《後漢書》卷三七《桓典傳》: 是時宦官秉權,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分曹: 分别部曹,或分司意。暝烏,即朝夕烏,亦御史之典。《漢書》卷八三《朱博傳》:“是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此聯自敍在所謂“霜臺”任職,與其同僚(應包括題中侍御史諸公),值夜、輪班,目睹而且身歷司經局屬下諸曹日常活動。必須强調指出,温絶不會把一些他自己没有見過的想象的描寫,寫給經歷其事的題中諸公看。
(六四) 百神歆髣髴,孤竹韻含胡。
“百神”句: 用王延壽《鲁靈光殿賦》(《文選》卷一一)“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髣髴”句意(“魯”字暗射莊恪太子李永初封“魯”王)。歆: 嗅聞也,髣髴,隱約、依稀之意。句謂百神隱隱約約聞到殿中的馨香(歆享而保佑太子)。孤竹: 以孤竹所製之笛。《周禮·春官·大司樂》“孤竹之管”鄭玄注:“孤竹,竹特生者。”賈公彦疏:“謂若嶧陽孤桐。”按“嶧陽孤桐”,語出《書·禹貢》孔傳:“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韻含胡,謂其聲不清晰而若有若無,亦有暗示太子前程黯淡的作用。二句描寫“皇太子朝宫臣”時殿陛間飄渺的馨香和肅穆的音樂;同時也暗示雖望太子有神明護持,畢竟前景可憂。
(六五) 鳳闕分班立,鴛行竦劍趨。
鳳闕: 漢宫殿名,後世常用以代指皇宫或朝廷。分班立: 本指百官按品級和官署朝謁皇帝時依序分組而立,此指皇太子小朝廷内之班序,同時照應諸位侍御友人,言與之同侍東宫也。《新唐書·百官志四下》:“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宫寮及率府之兵。皇太子朝,則分知東西班。”《唐會要》卷二四亦云:“太子司直二人,……凡皇太子朝宫臣,則分知東西班。”故温與諸侍御史友人中當有二位爲“分知東西班”的司直或扮演司直角色的人(當包含温本人)。鴛行: 鴛一作鵷,字通,猶言鷺序,因鴛鴦、鷺鷥或飛或行,皆井然有序,舊習之以喻百官上朝的行列。竦劍趨: 劍身直挺而趨身進殿;參見第8韻注引周遷《輿服雜事》。
此聯“鳳闕”、“鴛行”説得隆重,其實是寫“皇太子朝宫臣”的氣象,温自然也在所謂“宫臣”之列。考皇太子所朝之宫臣中,能持劍上朝者可謂特别。頗疑此人即開成三年拜太子太師的宰相鄭覃。《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開成三年)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舊唐書》卷一七二《馮定傳》“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新唐書》卷九五《文宗二子傳》“開成三年,詔宫臣詣崇明門謁朔望”。《唐會要》卷二六《皇太子見三師禮》,“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 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少陽院東有南北街,街北出崇明門”),内外門所司陳設。依奏。開成三年四月敕: 宣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門下,與前件官詣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並權停。其年八月,敕太子太師鄭覃: 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宣令每月更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一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其輟朝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敕處分。九月敕: 太子太師及東宫,每月二十六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温本人在開成二年夏秋閒得以臨危受命,從遊而輔佐莊恪太子。太子開成三年十月被害後,温避難於故人之家,於開成四年得以改名温岐應京兆府試而得等第,其後經痛苦的努力和觀望,開成五年終不得不“罷舉”而“行役議秦吴”,也就是從此開始了“濫竄於白衣”(《唐摭言》卷二)的過程。直到大中十二年才如《唐摭言》卷二所言“爲等第久方及第”,而勉强以一個特殊的案例得第,如《温集》卷一一《投憲丞啓》所言“遂竊科名,才沾禄賜”。
(六六) 觸邪承密勿,持法奉訏謨。
觸邪: 本古代傳説的一種神羊。王充《論衡》(卷一七)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識有罪。皋繇洽獄,有罪者令羊觸之。”後因以其辨觸姦邪之能而指御史之職,此處亦以形容“比侍御史”的司直抵制奸邪(尤指宦官)的實際行爲。密勿: 意爲機密;《三國志》卷一六(《魏書》卷一六)《杜恕傳》:“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訏謨: 大計,宏謀;《詩·大雅·抑》“訏謨定命。”毛傳:“訏,大;謨,謀。”鄭玄箋:“大謀定命。”此聯謂“比侍御史”的司直,承皇帝的密旨抵觸奸邪,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支撑皇朝的大業。
按以上63、64、65、66四韻的順序似應依次爲63、66、65、64。這樣第63韻“寓直”、“分曹”寫“侍御史”的日常活動便和第66韻寫御史的職能使命密切連貫了。而第65韻“鳳闕”“鴛行”寫“皇太子朝宫臣”的氣象,接以64韻“百神”、“孤竹”宫中焚香的肅穆和奏樂的莊嚴也密切連貫。而照目前的順序,第63韻“寓直”之後接言64韻“百神”、65韻“鳳闕”兩聯而描寫宫中氣象,然後再回到描寫御史功能的第66韻,順序似嫌混亂。這種錯誤應是排版時“串行”(是“串列”)造成;舊式豎排版,每列兩韻,把前一列的上半,接上後一列的下半;而把後一列的上半,補上前一韻的下半;是《百韻》這樣的長律排版時容易發生的失誤。
(六七) 鳴玉鏘登降,衡牙響曳婁。
鳴玉,參第10韻解。又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章表》:“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登降,猶進退,指登階下階進退揖讓之禮。衡牙,《禮記·玉藻》:“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孔穎達《正義》:“凡佩玉必上繫衡,下垂三道,穿以賓珠,下端前後以懸于璜,中央下端懸于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触璜而爲聲。”曳婁: 此謂餘音摇曳不絶。語本《詩·唐風·山有樞》:“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毛傳:“婁亦曳也。”二句寫東宫群臣進退有節、正大堂皇,謹事儲君。
第63—67韻,寫左(右)春坊“司直”的日常活動及衆宫臣“詣崇明門謁見”太子的氣象,尤其此中關於“司直”的描寫,自有温庭筠身影。
(六八) 祀親和氏璧,香近博山爐。

(六九) 瑞景森瓊樹,輕冰瑩玉壺。
瓊樹: 喻擁護太子的賢人。《世説新語·賞譽》:“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輕冰”句: 鮑照《代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王昌齡詩:“一片冰心在玉壺”。此聯承上,寫宫中景、物而兼含喻: 先言東宫之臣: 以瑶林瓊樹喻太子周圍賢人衆多;再説東宫之主: 以玉壺冰喻指太子方年幼而天真無邪。

豸冠: 見第66韻解,關於獬豸的類似説法很多,如《後漢書志·輿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後,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獸,能别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爲冠,秦滅楚,以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螭首: 指殿上陛下之頂端呈龍頭形的短柱。《新唐書》卷四七《百官志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後因以“螭頭載筆”表示史官侍值。按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屬於門下省,對應的東宫官應該是左春坊司議郎。《新唐書》卷四九《百官志四上》“司議郎二人,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謁、從祀、釋奠、講學、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册者,録爲記注;……歲終則録送史館。掌侍從規諫。”二句表明詩人職責所在似兼與司直、司議郎有關。
(七一) 内史書千卷,將軍畫一厨。

今按: 在晚唐時,王羲之書帖和顧愷之畫很可能藏於左春坊司經局所領崇文館,温《洞户二十二韻》中“書帖得來禽”句可爲旁證。此聯透露温從遊太子期間在崇文館看到皇家珍藏。當時温似爲太子司直兼文學侍從,或只如“監察侍御里行”一樣,只是見習而已。但毫無疑問的是,温確在“皇太子”所“朝”的“宫臣”之列。
(七二) 眼明驚氣象,心死伏規模。
眼明: 猶言大開眼界。心死: 此謂心中極爲傾服。氣象: 即規模,當謂書畫珍寶的精美絶倫以及皇家制度儀仗的豪華尊嚴。
(七三) 豈意觀文物,何勞琢碔砆。
文物: 指皇家獨有的典藏記録和文化精品;《左傳·桓公二年》:“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碔砆: 一種似玉之石頭,此謙而自比。《文選·子虚賦》卷七“礝石碔砆”句張揖注曰:“碔砆,赤地白彩,蔥蘢白黑不分。”二句謂本未料有此近接天家、開闊眼界的機會,今退身也不必勞官家雕琢這塊不成玉的材料了。下句帶反諷語氣。
(七四) 草肥牧騕褭,苔澀淬昆吾。

第69—74韻,用隱晦華麗的語言,盛飾自己從游莊恪太子所歷所見;寄託自己銘心刻骨的政治感觸。尤其其中關於“司直”的第二次描寫,令人不得不强烈懷疑是詩人自道。
(七五) 鄉思巢枝鳥,年華過隙駒。
巢枝鳥: 思江南故鄉之自喻;《古詩·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過隙駒: 時間過得很快的比喻;《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七六) 銜恩空抱影,酬德未捐軀。
抱影: 謂孤獨自處、形影相弔;《楚辭·哀時命》:“廓抱景而獨倚兮。”捐軀: 效忠獻身之謂;曹植《白馬篇》:“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二句自謂感念皇恩,而當道無知音者;欲思報答,卻無效命機會。
(七七) 時輩推良友,家聲繼令圖。
此二句自言當時人士視己爲良師益友,自己也無愧温氏美譽,應是真實寫照,非飛卿自飾也。可與李商隱、段成式、紀唐夫、皮日休等多人評論及有關史料相證。唐宋間筆記雜説於庭筠之誣蔑不實之詞及其後代的翻版,亟須澄清。
(七八) 致身傷短翮,驤首顧疲駑。
致身: 盡忠事君報國之謂;《論語·學而第一》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短翮: 短的鳥翎,比喻個人能力和奧援皆不足飛騰。驤首: (蛟龍或駿馬)抬頭,常狀人意氣軒昂,指題中諸公。疲駑: 即第二韻所謂“羸馬”,自喻疲憊無能,憤懣語。二句自傷無緣報國,愧對諸友人。
(七九) 班馬方齊騖,陈雷亦并驅。
班、馬: 班固、司馬遷;《隋書·經籍志》:“遠覽馬《史》、班《書》。”陳、雷: 陳重,雷義。《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列傳》:“太守張雲舉(陳)重孝廉,重以讓義,……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舉茂才,讓於陳重……鄉里爲之語曰:‘胶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二句謂諸位友人文名、宦途皆進。

言爾志: 孔子使弟子“盍各言爾志”,見第18韻注。吾徒: 本孔子指其門徒,此借用;《論語·先進》:“非吾徒也。”又《論語·子罕》: 子曰“後生可畏”。二句謂昔日與諸公有同門之誼,今後生可畏,升沉異路也。
(八一) 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轆轤。
氣干牛斗: 用《晉書·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後得豐城寶劍故事。轆轤劍: 古代一種寶劍名,其劍柄爲玉制·由兩塊玉相套合而成,“環口中間似轆轤旋轉”(陶宗儀《輟耕録·玉轆轤》),故名。二句以寶劍劍氣沖天而無人識自喻懷才不遇。
(八二) 客來斟綠蟻,妻試踏青蚨。

温《五十韻》於其事亦言“宦無毛義檄,婚乏阮修錢”,説自己遊宦則没有毛義那樣的傳檄任命,辦婚事則没有阮修那樣“衆人爲之斂錢”的機遇——其實也是向李僕射訴説自己不得不謀職揚子院的苦衷;正因他在宦官勢力麇集的揚子院謀職,並且得到錢財資助而買妓爲妻,才碰上仇家的残酷迫害。此聯是從詩人角度寫出了下聯積毁銷骨的原因。詳見拙作《温庭筠江淮受辱本末考》。
(八三) 積毁方銷骨,微瑕懼掩瑜。

其一,《玉泉子》曰:“初將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揚子子留後姚勖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多爲狹邪所費”與“妻試踏青蚨”,只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而已,前者含嘲諷而失真,後者嫌刻琢而近晦耳。正因第82韻所言買妓爲妻;才有本韻説的受盡誣謗,“微瑕掩瑜”的結果。
其二,温《上鹽鐵侍郎啓》“强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謡諑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折之路斷”,所言雖然含蓄委婉,其事就是第82、83韻這段爲妓女贖身、買妓爲妻,而横遭誣蔑的情事: 自己硬把那眠花宿柳的麋鹿狹邪之情,來效法雙飛雙宿的夫妻之愛,這不是以所遇青樓女子爲妻又是什麽呢?麋鹿之情,一般解爲狂放不羈,特殊解爲淫放多情。《禮記月令》:“麋角解”句下孔穎達疏“麋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而麋鹿亦是一夫多妻制的象徵。鴛鴦之性: 指追求夫妻恩愛、男女佳配的情性。至於“幽蘭”句,語本《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及“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謡諑謂余以善淫”,自謂像屈原好修那樣遭到群小的攻擊,被誣爲“善淫”。丹桂句,自言竟然因此不能中第而落魄窮途。
其三,温《上吏部韓郎中啓》“諸葛之娶妻怕早”句,也説到自己老大娶妻,不得不求韓助己在揚州鹽鐵院謀職,這和《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婚乏阮修錢”之描述自己結婚没有阮修那樣有名流爲之斂錢爲婚的排場又不謀而合。
其四,温《偶遊》詩“與君便是鴛鴦侣,休向人間覓往還”及《懊惱曲》“玉白蘭芳不相顧,青樓一笑值千金”,也説明温確實對此妓女有“鴛鴦之性”,並且爲了這位青樓女子的“一笑”,不惜千金即爲之贖身,傾其所有“盡爲狹邪所費”。這些證據能若合符契地證明温破費錢財買妓爲妻事,應該不是偶然的。
其五,劉學鍇《全集》卷一一《上鹽鐵侍郎啓》之校注認爲《全唐文》卷七八六“强將麋鹿之情,欲學鴛鴦之性”應從《文苑英華》卷六六二作“鴛鸞”,“同鵷鸞,喻朝官。朝官班行整肅有序,備受拘束,與‘麋鹿之情’正相反”。這種解釋與本句後半句直接矛盾。試問: 雖個性狂放不羈,學習和效法鵷行鷺列的班序,怎麽就蒙受“善淫”的“謡諑”而斷了考取進士的路呢?
以上第82、83韻其實是在説完從遊莊恪太子之事後,回顧前塵,説到自己在江淮買妓爲妻、被宦官勢力當做把柄,而受辱、受毁謗事。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和背景,則在前文第55、56韻已有説明。江淮受辱之本末如此簡略地前後出現在本詩中,也是很多論者不能發現此事的原因。
第75—83韻: 如今自傷老大而懷鄉,欲報皇恩而無緣。朋輩青雲,獨我蹭瞪,追究起來,自己在江淮買妓爲妻之“微瑕”乃是受盡毁謗的根本原因。
(八四) 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
蛇矛: 此處喻唐政府的軍隊。《樂府詩集·雜歌謡辭·隴上歌》:“隴上壯士有陳安,……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舊唐書》卷一七八《鄭畋傳》:“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魚服: 《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爲比喻帝王變服而被困之典。又劉向《説苑·正諫》(卷九),伍子胥諫吴王勿從民飲酒曰:“白龍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 魚固人之所射也;今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此處喻“受制於家奴”的皇帝。二句謂國家政局未穩,而皇帝又受制於宦官。
(八五) 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誅。
“欲就”二句,謂想在其中做手腳,欺騙社會輿論(就算是當世人不知道),安能逃得過冥冥中鬼神懲罰。《莊子·庚桑楚》:“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按“就”字當介詞用,其賓語(如帝位繼承)省略;二句的主語(宦官勢力)亦然。
(八六) 是非迷覺夢,行役議秦吴。
是非已夢幻一樣地迷失,詩人乃計劃自長安遠適吴地舊居(而淡出物議)。
(八七) 凛冽風埃慘,蕭條草木枯。
風埃: 猶言風塵、風物。二句想象冬日東歸途中所見。
(八八) 低徊傷志氣,蒙犯變肌膚。
低徊: 流連回顧。蒙犯: 蒙受、面對(風日雨雪寒暑等)。
(八九) 旅雁唯聞叫,飢鷹不待呼。
二句因途次所見爲喻,詠羈旅失意情懷。飢鷹: 杜甫《贈韋左丞丈》:“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

兩句頗見雕繪刻琢。上句謂自己“織夢”之“梭”爲促織所催而頻抛,言夜間輾轉苦思而不能成眠也;下句則謂自己心緒之結效法蜘蛛之繭,紛亂封於心中而難與人言。促織,蟋蟀别名;《詩集》引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鱼疏》云:“蟋蟀,……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九一) 寧復機難料,庸非信未孚。
機難料: 可參《三國志·魏志·高貴鄉公髦傳》“高貴鄉公卒”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提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信未孚: 語出《左傳·莊公十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上句言(宦官)廢立之謀其實世人可知;而下句謂: 難道不是信用尚不足以服衆嗎?好像非常隱晦地暗諷武宗,而明似批評宦官。
(九二) 激揚銜箭虎,疑懼聽冰狐。
二句是温庭筠的自畫像;説自己受盡傷害,激憤難已如中箭之虎,而處境險惡,心懷疑懼如聽冰之狐。《水經注·河水一》引晉郭緣生《述征記》:“狐……善聽,冰下無水乃過。”
(九三) 處己將營窟,論心若合符。
營窟: 謂經營避禍逃生之方;《戰國策·齊策四》“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請爲君復鑿二窟。”合符: 比喻兩件事物完全相同或一致;《孟子·離婁下》:“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符,符節,中國古代朝廷傳令、調兵遣將等事務的憑證,以金屬或竹木等爲之,作鳥獸等形;雙方各執半,合之以驗而信;參見第21韻“繻”之解釋。二句自言將避禍引退,正符合諸位友人之勸告,聽從明哲保身的古訓。
(九四) 浪言輝棣萼,何所托葭莩。
棣萼: 棠棣的花和萼,亦作“棣鄂”,喻兄弟或兄弟友愛。《詩經·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葭莩: 蘆葦中的薄膜,喻疏遠的親戚。《漢書·中山靖王劉勝傳》:“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上句謂休想兄弟會榮耀自己,下句謂沾一點遠親也託不上任何方便。案上句所謂兄弟或指温造之子温璋;下句則指温與唐皇室的遠親關係。
(九五) 喬木能求友,危巢莫嚇雛。
喬木、求友,語出《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危巢: 應喻岌岌可危的名位。嚇雛: 語出《莊子·外篇·秋水》:“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云云。上句自謂能求同道舊友而遷喬出谷;下句自比鵷雛,言己雖以改名事招致種種誹謗,但名位——危巢之於己,不過鵷鶵所視鴟梟之腐鼠而已。按: 或以“嚇雛”爲飛卿此時已經有子之證,即使與温實際得子的時間粗合,亦恐不足爲訓;蓋解“雛”爲其子,則以危巢嚇其雛,離開上下文以“己”爲中心的主線,無意義。
(九六) 風華飄領袖,詩禮拜裙襦。
領袖: 《晉書》卷三五《裴秀傳》:“時人爲之語曰: 後進領袖有裴秀。”“裙襦”之“裙”各本皆作“衾”,誤;蓋“裙”之古字君上衣下,而訛爲“衾”也。裙襦: 出《莊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二句言有些人看似士林領袖,道貌岸然,實不過“以詩禮發塚”的僞君子而已。又,上句或可解爲詩人自詡領袖後進。
(九七) 欹枕情何苦,同舟道豈殊?
“同舟”句: 顧本校,豈一作固;此變用“同舟共濟”意。《孫子·九地》:“夫吴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共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二句自謂所以倚枕不眠者: 本來是同舟共濟之人,“道”怎麽會不同呢?考慮“豈”字的異文“固”,此句似在譴責某人。按温改名舉場參加京兆府試,得“等第”而罷舉,當然因爲改名事泄;雖遲早要洩露,但其過程中畢竟有爭名者出賣。“同舟道豈殊”的反問,或“同舟道固殊”的反話,都似包含詩人對告密者的譴責。
(九八) 放懷親蕙芷,收迹異桑榆。
蕙、芷: 皆香花香草,以喻賢人或代指隱者家園。《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收迹: 謂隱退。桑榆: 日落時餘光所照之處,常用以比晚年;《淮南子·天文訓》:“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二句言自己只好縱情林下生涯,不過隱退尚非老年(日後或猶有可爲)。
(九九) 贈遠聊攀柳,裁書欲截蒲。
攀柳: 即折柳。《三輔黄圖·橋》云:“灞橋在長安東,跨水做橋,漢人送客至此,折柳送别。”《樂府詩集》卷二二梁武帝《折楊柳》解題引《唐書·樂志》曰:“梁樂府有‘胡吹歌’云:‘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此歌辭元出北國,即鼓角横吹曲《折楊柳枝》是也。”截蒲: 據《漢書》本傳,路温舒父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今案: 當時正當嚴冬,不唯“折柳”爲想象之語;“截蒲”亦湊韻之詞耳。

第84—100韻,詩人縱觀所處形勢: 宦官罪惡,總是難逃天譴;自己遐適保身,也是無奈;親戚無所託,摯友尚可依;“以詩禮發塚”的僞君子及“道殊”的“同舟”者不必提;表現了無限遺憾而並不絶望的心情。
綜上注釋及分析: 按其敍事和抒情的總體順序,全詩可分爲七段。第一段爲第1—10韻,感歎自己應試失敗,經歷厄難,報國無門。第二段爲第11—29韻,婉曲道出改名(温岐)應試的苦衷、得“等第”而“罷舉”的原委。第三段爲第30—47韻,因而只好退居林下,故轉而描述當年隱居讀書生涯,其末有“横經稷下”及客中喪父的經歷。第四段爲第48—56韻,言己仕途之初已受宦官迫害,“羈齒侯門”之後,“大樹”無依,乃“避秋荼”而赴京;其事即隱括詩人之“江淮受辱”也。第五段爲第57—74韻,言自至長安,多費周折,得職“霜臺”,且通過描寫“詣崇明門謁見”太子等氣象,盛飾自己從遊莊恪太子所歷所見所感。第六段爲第75—83韻: 如今自傷蹭瞪,亦自知江淮買妓爲妻之“微瑕”,實爲“積毁銷骨”之肇因。第七段爲第84—100韻,詩人鞭撻宦官,反省自身,珍重友誼,批評僞善,終能自勵而不爲人生之災難擊倒也。
其中江淮受辱事,以《玉泉子》所記,與温《上裴相公啓》、《上吏部韓郎中啓》、《上鹽鐵侍郎啓》、兩《唐書》本傳以及《懊惱曲》、《偶遊》等,尤其本詩比勘對照而得。從遊莊恪太子事,則賴温詩文中《莊恪太子輓歌詞二首》、《洞户二十二韻》、《謝李尚書啓》、《謝紇干(相)公啓》、《上封尚書啓》等多項内證繹出。“等第罷舉”及改名詳情則由本詩提供真實細節。温平生祕事,多在此也。尚有大中期間所作《菩薩蠻》評價聚訟紛紜,攪擾場屋而貶尉隨縣一案衆説喧騰,值得深深考究;其實也與以上三事因果相及,可見研究透徹此三事的重要性。謹獻拙見,希望得到學界批評指正。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三十三輯
2016年7月,113— 151頁